弗朗西斯·福山:平衡的政治艺术
2015-12-08阮帆
文/阮帆
弗朗西斯·福山:平衡的政治艺术
文/阮帆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ViVi摄影)
1989年初,对自由民主制充满信心的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在文中,福山断言,民主将“成为全世界最终的政府形式”。随着几个月后冷战结束,柏林墙轰然倒塌,他的断言犹如一个变现的寓言,在西方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1992年,他在原文章的基础上扩充,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其核心论点——“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布尔乔亚是最后之人”穿越世纪,历经了热烈的拥抱和不一而足的批评。
去年9月,福山出版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在接受英国时政周刊《新政治家》采访时,福山承认“使自由民主制度奏效是何其艰难”。在书中,他表达了对美国政治现状的失望,认为即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成熟民主国家,也可能经历政治衰落过程。过去二十多年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使福山意识到了西方民主自由制也是讲条件的,在下结论时也考虑得更加全面而谨慎。不过,他并无意推翻之前的结论,而是在肯定自由民主制的前提下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由民主的前提是国家能力,除此之外,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在法治下运行。
4月中旬,弗朗西斯·福山来到清华大学,与青年学子们交流了他的政治思想。此外,在国家外国专家局,福山与中外专家学者们就如何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和社会治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作为外国专家为中国的政治治理和发展建言献策。对于他的政治思想,我们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希腊危机是官僚主义的衍生品,图为希腊民众示威抗议政府财政紧缩政策
自由民主制仍然是政治的不二归宿
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福山开篇就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历史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而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因此,自由民主的“理念”已经不能再改良了。
这一结论刚刚面世,就受到了批评家的各种质疑:其意图动机是什么?命题是否有点太狂妄了?批评家们纷纷用“民主国家的乱象”,“威权国家的韧性”来批驳福山的核心论点,举出柏林墙的瓦解、伊拉克侵虐科威特来证明历史还在“持续”。
面对这些质疑,福山并没有感到困扰,相反,他认为不管是从经济发展的方面考量,还是从黑格尔对于人们追求“普遍而平等的承认”的论述来看,这种社会形态都将使历史终结成为必然。
然而,在去年9月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里,人们发觉福山的学术思想似乎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曾经那个对于自由民主制度自信满满的拥护者却在这本书里花了很大篇幅论述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的种种弊端,警示“政治衰败”的可能。
“一种制度曾经很成功、稳定不等于它永远会如此”,福山在书里写道。他认为,美国已经出现了“过度民主”的危险,“否决民主制”导致政府被民主和法治逼到“已经无法做出艰难抉择的处境”。
为了说明美国的司法机构如何削弱其行政机构,福山用美国森林局来作比方。成立于1905年的美国森林局曾经是美国高质量官僚机构的典范,但如今它的每一项使命都对应于不同的外部利益集团:木材商、环保主义者、森林居民。到底是要砍伐木材,放任森林野火还是保护树木,森林局却不能自主决定,因为它“受到国会和法院的多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命令”。
一些媒体开始评论,福山的学术思想有了重大转折,他已经开始承认,相较于民主和法治而言,国家能
力对繁荣更加重要。
对此,福山认为这显然是对他观点的误读。在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的采访时,他解释道:“我的论点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让国家能力与民主和法治相平衡。”
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里,福山概括说,政治秩序的三个要素——政府、法治和民主——相互补充。虽然这三个要素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比如民主要求控制政府而政府又要求自主,又比如法律的严格运作限制了行政的酌情决定权。但不管它们之间的摩擦有多大,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承认每个公民的尊严和价值,这是自由民主制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从根本上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创造了一个环境让人们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它是捍卫尊严的自由民主社会的源动力。
在最后一章里,福山总结说,“尽管民主在21世纪初出现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义上仍然保持良好”,“虽然高质量的民主政府时而供不应求,但对它的要求却与日俱增……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因而,“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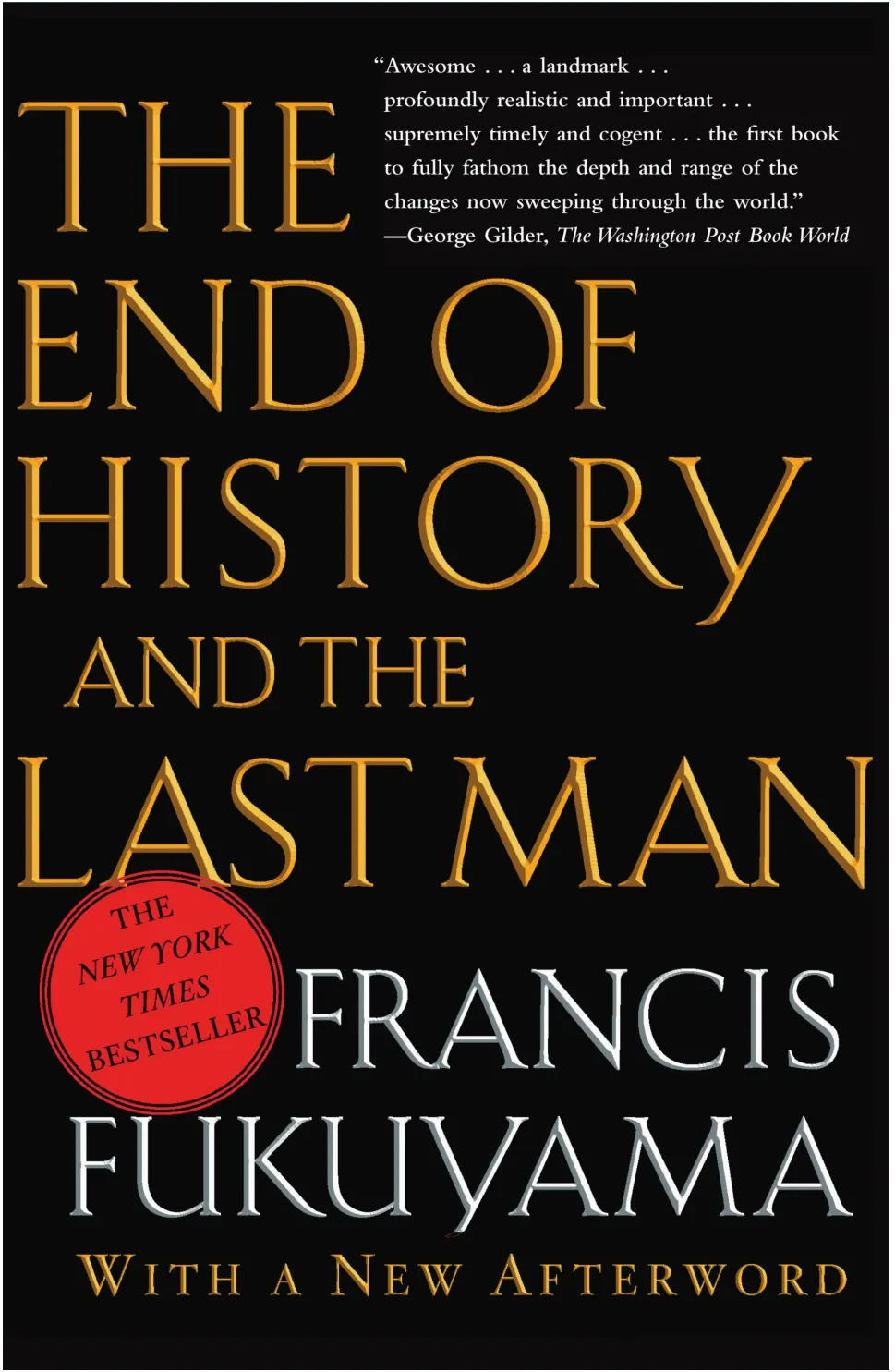
福山最具代表性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此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被先后译为20余种文字
没有国家能力的民主不是好民主
既然自由民主制是社会的终极形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都获得了不同形式的肯定:自由国家和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民主是否真能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以不变应万变?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国家大量出现,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也逐渐高涨。然而,良好政治秩序的建设却并非易事,它取决于许多条件和偶然因素,但关键无非在于强政府、民主和问责制。三者往往不可兼得,彼此之间也常常难以达到平衡,但是缺少任何一方,制度就很难运行好。于是,制度要素的发展顺序至关重要。
在福山看来,理想的顺序是先建立强国家,继而发展法治,最后走向民主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丹麦。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的前言,福山写道:“丹麦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从世袭制转型为现代国家,丹麦依靠的就是顺序铺垫的这三大基石。
举两个反例可以说明这个论点。比如希腊,希腊在没有充分完成国家建设的条件下“过早地”进入了民主化阶段,在19世纪希腊的普选权实践中,政治精英在选举中收买民众,以提供公职就业机会等方式交换选票。结果在19世纪70年代,希腊的人均公务员数量是英国的7倍。政治精英为获得短期政治利益而导致官僚膨胀化的传统在希腊一直残存,1970年之后的40年间,希腊公职人员的数量增长了5倍。
又比如印度。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目前,这个国家却饱受普遍的裙带关系和腐败困扰。在法治、民主问责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中,印度满足了两个,却离大功告成差之千里,问题就出在这个顺序上。也许正是出于此种觉悟,2014年,印度果断地转向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希望他能提供坚决的领导,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取代过去10年来无能腐败的国大党领导的联盟。
希腊和印度二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是精英利用特
权和资源向较为弱势者提供保护和利益、换取支持和服务,即政治学家所称的“庇护主义”。庇护主义常常是弱国民主的常见病,它不仅是腐败的温床,也导致了低效政府,加剧了社会不公。先行于国家与法治建设的民主化进程可能造成脆弱的政治秩序,这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晚近“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转型之中。
“在我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的研究当中,我发现一些地区的国家会愈发贫穷,主要是国家能力不足导致的负面效应。它比政治发展中其他任何成分的缺乏所造成的影响都更严重。”福山在一次采访中说。
他说自己同许多生活在发达国家中的人一样,有时候会把国家能力看作理所当然的事,但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观察当中,他意识到如何发展国家能力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一个政体在限制权力之前,首先必须行使权力。”
现代国家的起源和中国模式
福山认为,如果要追溯历史终结的政治思想从何而来,就不得不从古代中国说起,因为古代中国是整个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是研究世界政治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环。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福山花了很长一章专门写古代中国。他提出,要谈一个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马克思·韦伯式的现代国家,我们应该把眼光聚焦到中国的汉代——它那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早出现了1800年。
汉代的国家是围绕官僚体系和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一方面,福山认为,这是战国时代各国相互竞争共存状态的产物,因为如果要打胜仗,政治上就必须选贤任能,而不能依靠家族传承。另一方面,他认为这表明中国古人怀有一种抱负,认为政府是把公民当公民看的,而不是以家族裙带关系或地方豪族。正是这种对于世袭主义的克服,给中国的政治种下了优良的基因。
他在书中写到,当今的中国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的一种延续。尤其是清王朝后期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这漫长而巨大的苦难让人们产生了一个共识——国家必须强大,才能使人民得到保护和教化。不过,同时让他觉得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比如法治或西方的选举责任制,来制衡国家。
在他归纳的“向上负责制”和“向下负责制”两种政治负责制中,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属于后者。其潜在危险是否决政治,体制可能被分离联盟俘获并固化,走向政治衰败。而前者常见于一些一党专政的国家,这种负责制很可能存在腐败、滥用权力等一系列问题。
“向上负责制的风险在于,你首先得有个好的领导人。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它能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解决信息问题,如果管理得当,权力下放能加快政府的反应速度,更有效地满足公众利益。”福山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为自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好,所以中国体制能够在1978年以后比民主国家更快速地改变经济体制的基础。但他认为,仍然有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确保永远都能遇上好的领导人?
福山在外国专家建言座谈会上介绍说,要将向上负责制的风险降到最低,就必须依赖法治。“中国有以法律为基础的决策体制,但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现有的趋势,最终走向真正的法治。”他说。对于中国的现状,他认为如何将法律应用的范围扩大,将法律的决策制度做得更加透明公正乃是中国的领导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所有的决策和决断都应当是公开的、正式的、开放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就能够限制自由裁量权,在低级别的政治当中尤为重要。”福山说,“因为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不限制行政权力的话,对于自己的政治体系非常危险。”
谈及中国自十八大以来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福山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提道,希望能够比较快地建立一个程序或者规则,不然的话,一开始对于反腐行动的支持,很可能到后来就成为过度个人意志决定的东西了。
抛开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与自由民主到底相差还有多远,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乃是现在唯一看上去可以与自由民主相竞争的体制。“最好的官僚机构能够自主地运用判断力做出决定,去冒险和创新。而最糟糕的官僚机构执行他人制定的详尽规则”。
回首二十多年前做出的历史终结的判断,福山最新的两本力作似乎在试图阐释历史走向这一终点的复杂而崎岖的路径。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也许只要方向是对的,我们就该意识到制度和程序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