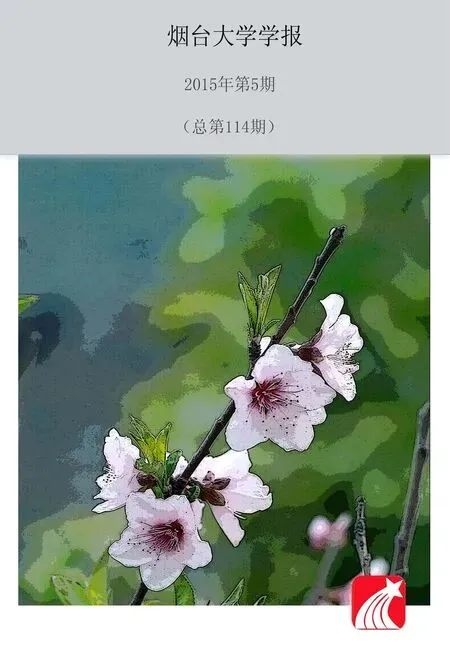论朱湘的“纯诗”世界——基于中西纯诗诗学的观照视野
2015-12-08田源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5)05-0078-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5.05.009
[收稿日期]2015-03-21
[作者简介]田源(1987- ),男,重庆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及中外文学关系。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纯诗’诗学视域下的中国新诗研究”(20151110102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朱湘在1924年《文学旬刊》上以“天用”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桌话Table-Talk》的文章,里面较早提出“纯诗”的理念:
我相信用纯诗——的眼光来看济慈这首诗的人看到此处,不仅是不觉得不满,并且极为愉快的。考古学者虽然在这里发现了一点时代错误anachronism,我们并不得因了这层绝对的真理的原故而减低我们对于诗的真理——即是美——的鉴赏。 ①
朱湘的“纯诗”理念指涉“诗的真理”与“美”。一方面,“诗的真理”指向包涵某种绝对意味的权威属性,彰显出诗之为诗的文体与精神层面的纯然境界。关于诗文分离的诗体实验在穆木天《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The pure poetr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我们要求纯粹的诗的Inspiration。” ②连续四个“我们”发出强烈的呼吁,“纯粹诗歌”的独特品味源自诗人的独特视角,王独清在《再谭诗》中进一步阐释:“常人认为‘静’的,诗人可以看出‘动’来;常人认为‘朦胧’的,诗人可以看出‘明瞭’来。这样以异于常人的趣味制出的诗,才是‘纯粹的诗’。” ①
另一方面,“美”包括了内容与接受两个层面。朱湘认为美的范畴包罗广泛的诗歌题材,既有人工的“雕梁画栋”,也有自然的“奇山异水”,还有“高贵”、“平凡”、“梦幻”、“现实”的人生。由内容的美扩展到接受的美即是审美的层面,梁宗岱在《谈诗》中说:“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的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 ②读者在与诗人的情感共鸣中获得审美快感,并转化为对某种更深境地的反思。
朱湘的“纯诗”观既与西方纯诗诗学的某些观点相通,也开启了以穆木天为代表的中国化纯诗理论的建构之路。若用“诗的真理”和“美”来概括“纯诗”将显得过于笼统与抽象,结合朱湘的诗文可以将其界定在和谐音韵、唯美情景、严整结构三个方面。
一、纯粹的音节与动听的旋律
音节是诗歌格律的重要元素和诗歌本质的潜在能量。关于诗歌格律,与朱湘同为新月派的闻一多认为它可以从“视觉方面”和“听觉方面”去界定,从而引申出诗的“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③音节涉及诗歌的音乐属性,是基于听觉层面的考量,音节在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朱湘在寄给曹葆华的一封信中说道:“音节之于诗,正如完美的腿之于运动家。……想象,情感,思想,三种诗的成份是彼此独立的,惟有音节的表达出来,他们才能融合起来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 ④如果没有“两条好腿”的支撑,“运动家”无法成为优秀的体坛健将,这些机能与理念将彼此剥离。诗歌亦是如此,如果只谈其中的深邃奥义,无法彰显诗的独立地位。新月派的另一位诗人徐志摩也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他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却不能说是诗。” ⑤音节不仅是诗歌形式的外在表现,更重要地是衔接了诗歌内在的思想感情,是串联诗歌生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精华。
中西纯诗诗学都强调音乐性。法国诗人瓦雷里用“绝对的诗”替代“纯诗”,它是“对于由词与词的关系,或者不如说由词的相互共鸣关系而形成的效果,进行某种探索”。 ⑥词汇间的碰撞在语言层面上,实际就是音节的创造,并由此支配人的听觉领域。魏尔伦强调“音乐至高无上”,他“是自由诗的最大底功臣,自由诗不是不重音节,乃是反对定形的音节,而要各人依自家性情、风格、情调与一时的情绪而发与之相应的音节”。 ⑦音节不是某种固定的格调,它随着诗人内心的情绪变化而平行演进,是动态音符的节奏化呈现。中国纯诗诗学也有相似观点,梁宗岱尤其强调音节的重要性:“至于新诗的音节问题,虽然太柔脆,我很想插几句嘴,因为那简直是新诗底一半生命。” ⑧押韵、停顿、平仄、清浊是诗歌组织结构的基本因素,维系着新诗生命的血与肉。
观照朱湘的诗歌创作,他在平仄用韵的音节实验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朱湘以《恳求》一诗为例,谈论自己择取音韵的良苦用心。该诗共三节,在每节的第三行“不料我们聚首”、“你的温柔口吻”、“连月姊都心痒”的尾韵都为上声;每节的倒数第二行“那时候”、“低声问”、“今晚上”的尾韵都为去声;每节的最后一句“你要重逢也无由”、“你偏是摇手频频”、“你竟将归去空房”皆用平声韵收尾。对于平仄韵的转化,朱湘谈到自己的用意:“仄声韵的运用是为了要复杂化诗章的节奏;去声韵的运用,是为了要在上声韵之后,逼紧一步,使得情绪紧张起来。每诗章之末,用平声韵来煞尾,是想着凭了弛缓的音韵来暗示出恳求后得不到答应的那时候心绪的降堕。” ①仄声韵的复杂化是从整个诗篇布局去考量的,因为仄声韵前后均为平声韵,引入仄声韵产生平-仄-平的交错形式,丰富了音韵的抑扬顿挫效应。去声韵和平声韵的使用,基于一种短促急切与舒缓温润的情感需求,彼此间还有起承转合的节奏支点,是诗人心理流程的复现。诗中的持续律动感正如穆木天所言:“一个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 ②
诗歌的音乐性还体现在吟唱过程中给人以愉悦的美感体验,其本质是音节的整体协和的感染力。朱湘在《草莽集》中有一首名为《摇篮歌》的诗,共四节,现引前两节如下: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
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
你瞧日光它移的多慢,
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
睡呀,宝宝,
蜜蜂飞的真轻。
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
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
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
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
睡呀,宝宝,
蚯蚓都停了声。
整齐的音节传递出温馨的音响,每节诗歌六行的尾韵,遵循平平/仄平/平平的对称音律,传递出悠缓宁静的格调。苏雪林在一次文艺会上倾听朱湘吟诵此曲,她对现场众人的反应和感受印象深刻,评价道:“其音节温柔飘忽,有说不出的甜美与和谐,你的灵魂在那弹簧似的音调上轻轻簸着摇着,也恍恍惚惚要飞入梦乡了。等他诵完之后,大家才从催眠状态中遽然醒来,甚有打哈欠者。其音节之魅人力可想而知。” ③听众如痴如醉地享受歌声中的安宁氛围,正如瓦雷里所言:“当我们听到一种纯音,即在某种程度上是稀有的声音时,就立刻会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我们觉得充满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期待心情,这种期待仿佛是渴望产生一种同听到的纯音所引起的感觉在性质上一样纯正的感觉。” ④大家仿佛都进入到“宝宝”的纯真婴儿世界,不自觉地游走在由睡眠引导的虚幻世界,它与现实的喧嚣混乱截然隔绝开来。
二、真实的经历与唯美的想象
诗歌除了和谐音乐营造出的动听旋律之外,还必须在文字上经历一番过滤、筛选与择取,深化诗歌的思想与意义。朱湘认为一首好诗的生成必历经复杂的锤炼,这不仅需要在平仄、押韵、停顿等音节方面的功夫,更需要借助经验与想象的张力来完成对诗歌的创作。
经验是诗歌创作的基础,它包括直接与间接两种体验模式。朱湘以《恳求》一诗为例,将自我的亲身经历纳入诗歌的创作背景中:“我与一个同学在小山上散步并闲谈;我们在一个藤萝之棚下停住脚步,望着杨柳梢头的一钩新月。藤萝的以及棚条的淡影映在身上与脸上,我自视时,起了一种含有奇异的感觉。” ①独特的体悟源自诗人在秋夜目睹杨柳与月亮的光影交织的感兴,“天河明亮在杨柳梢头”、“树影往来亲”两句诗即是诗人起兴的凭证。与亲身体验相比,阅读所获取的经验是一种潜在的储备。该诗第一节第二行与第六行的诗句分别为:“隔断了相思的织女牵牛”和“一旦,我俩间也隔起河流”,诗人在此处援引了牛郎织女的民间神话故事,让我们想到狠心的王母娘娘与可怜的牛郎织女,“恳求”的苦恋因素在诗人过往知识积累的释放中获得崭新意义。另如历史题材的《昭君出塞》一诗也是对阅读体验的运用:“琵琶呀伴我的琵琶: /这儿没有青草发新芽,/也没有花枝低亚; /在敕勒川前,燕支山下,/只有冰树结琼花。”诗人再现了大漠的恶劣气候,带有某种依依不舍的怜惜之感。
英美纯诗理论家们特别重视纯诗中的经验因素。英国学者墨雷明确地表达了经验的影响力:“诗歌乃是一种整个经验的传达。不管我们(因为自己是道学的人们)赞成那传达出来的经验,但是这对于我们,总是一种召唤。” ②也许我们无法在诗人所处的月夜里产生对爱情的渴望,也许我们无法理解在光影交错中的迷离感,但朱湘的个体经验引发了我们对于恋爱的思考。牛郎织女的传奇与昭君出塞的故事也唤起了我们共同经验积淀的因子,发出或哀叹或忧愁的情感共鸣。美国纯诗学者罗伯特·潘·沃伦也大力肯定经验之于诗的重要性:“凡是在人类的经验可获得的东西都不应被排斥在诗歌之外。……一个伟大的诗人就要取决于他能够在写诗上掌握的经验的范围大小。” ③诗人是鲜活的灵肉之躯,经验不仅是传播感受的基石,更是衡量一位诗人素养的重要标准。中国纯诗理论家梁宗岱认为最完美的“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 ④“全人格”依托于实际经验,诗人如果没有对经验的诗化转述,无法形成“最纯粹的结晶”。梁宗岱虽未提及“经验”二字,但他在随后转引里尔克的散文《勃列格的随笔》节选中提到:“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象,徒是感情(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结合中西方纯诗理论家对经验的论述,反观朱湘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他倡导的“复杂之过程”中的经验是一种具体诗歌实践的典范。
经验固然折射出诗歌内在的生命,但如果缺失了想象的血液,诗歌将是苍白乏味的理性堆砌。朱湘在《诗的产生》中将想象的功效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恳求》一诗的倾诉对象是一位女性,但实际陪伴在诗人身边漫步小山的是他的男性同学,如何实现性别上的巨大转变?朱湘回忆道:“我想象着这站在身边的是我所极爱的女子,一个同我一般年纪,一种性格,同我一样羞涩不多说话的女子。……在心头拥抱起了这个甜美的感兴,我便回房去创作我的诗。” ⑤玄妙的想象神奇地改写了实际的经验,将同性的友谊转变为理想的恋情,在这种浪漫的唯美世界中,诗人有意识地将时间季节和地点背景也作了修改,“秋夜”变成了“夏夜”,清华的“一片林地”被置换成北京城“红墙侧的一些马缨花”,这些经过想象过滤后的选择最终都指向了“恋爱”的中心意义。
想象在纯诗理论中具有三重属性。第一,对极致美的憧憬。朱湘在《草莽集》的序诗中遥想“光明”的极致美景:“太阳升上时我已起床,/我跟它落进睡眠的浪: /太阳照在我生动中央。圆月在夜里窥于窗隙,/月映着坟上草迷离: /月光照我一生的休息。”(《光明的一生》)诗人想象自己在光明的极乐世界中自由生长,白昼沐浴着阳光,夜晚又接受月光的洗礼,这种极致的虚幻世界正如梁宗岱所言:“诗人却纵任想象,醉心形相,要将宇宙间的千红万紫,渲染出他那把真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创造来。” ①
第二,想象具有难以言说的神秘特质。朱湘的长诗《猫诰》展现出一个隐秘的猫的世界:“有一只老猫十分的信神,/连梦里他都咕哝着念经。/想必是夜中捉老鼠太累,/如今正午了都还在酣睡。……我姓之起远在五千年上,/那时候三苗对尧舜反抗,/三苗便是我猫家的始祖,/他是大丈夫,不屈于威武。……我猫家个个谙习韬略,/只瞧我刚才的出如兔脱。/须知强权是近代的精神,/谈揖让便不能适者生存。”(《猫诰》)家族式的猫的谱系是基于人类世界的想象,拟人化的猫既传递出某种灵异的气氛,又以猫的独特视角折射出人类的生存处境,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正如英国纯诗学者雷达在《论纯诗》中所言:“诗的一切神秘与幻术,都可以用一个名词表示,即是想象。” ②
第三,想象排除理性的干扰,依照诗人的直觉显现。朱湘《草莽集》的最末一首诗《梦》将想象演绎为幻想:“梦罢,/日光里的梦呀其乐融融……梦罢,/坟墓里的梦呀无尽无终!”(《梦》)与现实彻底对立的虚幻梦境呈现出温暖芬芳的愉悦与冰冷阴暗的凄凉的两极分化,直觉式的想象正如美国纯诗理论家布拉德雷的论述:“诗对于我们的‘诗的’价值,只在它是否满足我的想象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其余的,如我们的知识或良心,只能照only so far as它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变成的形状,(来)评判诗而已。”朱湘对梦境的抒写也将想象与经验融为一体,这也诠释出布拉德雷对诗的定义:“诗是一种惬心的想象的经验”。 ③
三、精密的构思与完整的思想
如果说对音节的强调是对纯粹诗歌形式的审视,对经验与想象的发掘代表着纯粹的诗歌的生成与接受机制,那么关于创作纯粹的诗歌应保持的姿态和视野,朱湘在寄给曹葆华的一封书信中倡导:“现在的新诗,有一部分是感伤作用的,这便不算镇静;还有一部分是囿于自我的,这便不是全盘。” ④“镇静”与“全盘”既是洞察社会人生的法宝,又是指导新诗创作的良方。“镇静”的创作态度能合理引导情感的深发,朱湘显然排斥“感伤”的颓废情绪,并将之归入非理性的精神状态;“全盘”是对全局的整体统摄的视野要求,集聚在自我的园地而不进入广阔的社会人生,朱湘对其持否定的观点。由“镇静”与“全盘”引发的诗歌创作主体的意识,与纯诗理论的相关主张不谋而合。
冷静的思想状态承袭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要求。道家学派崇尚虚静说,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天道》)是提倡人精神的寂静与天地万物的融汇的哲学观,后世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更将之引入文艺创作的范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虚静”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前提条件,它将诗人引向一种深邃的境地,在宁静的环境中思索并刺激灵感的出现,形成无限的创作源泉。
从新诗发展史来看,朱湘的“镇静”说也体现了新月派“理性节制情感”的诗学观。创造社的情感宣泄的诗风受到新月派诗人的批评与摒弃,他们推崇华兹华斯所言的“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朱湘在《草莽集》第一首诗歌《热情》中写道:“我们的热情消溶去冰冻,/苏醒转月宫的白兔,桂花,/我们绑起斫情根的吴刚,/一把扔去填天狼的齿牙。”原本亢奋炽热的情感在冰冷的月宫典故中稀释,朱湘不像郭沫若“天狗”般呼啸展露热情,而是在寂静的状态中观察热情,逐步将其分解揭示。
中西纯诗诗学对于诗人的精神状态有相似描述。瓦雷里认为:“诗人不再是蓬头垢面的狂人,他们总是在昏热的夜晚拈诗一首,而是近乎代数家的冷静的智者,应努力成为精炼的幻想家。” ①冷静中蕴含智慧,“代数家”的形象比喻赋予诗人严谨的才能。穆木天也号召:“我们要求的诗是数学的而又音乐的东西。” ②冷静的态度触发了物我交融且形神皆忘的境界,朱湘在《葬我》一诗中写道:“葬我在荷花池内,/耳边有水蚓拖声,/在绿荷叶的灯上/萤火虫时暗时明——葬我在马缨花下,/永作者芬芳的梦——/葬我在泰山之巅,/风声呜咽过孤松——”自我被埋葬在宁静的大自然中,这种现实与虚幻交错相生的美感正是因为“放弃了动作,放弃了认识,而渐渐沉入一种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在那里我们底心灵是这般宁静,连我们自身底存在也不自觉了” ③。
冷静的思维空间也充盈着思辨的哲理。朱湘很多诗歌涉及的死亡意识正是“镇静”思绪的产物。朱湘幻想着“有一座坟墓,/坟墓前野草丛生,/有一座坟墓,/风过草像蛇爬行。”在这座坟墓周边还“有一点萤火……有一只怪鸟……有一钩黄月”(《有一座坟墓》)奇怪的意象烘托出死亡的诡秘与恐怖,进而“被转换成为一种浪漫想象的驱力和诗的资源” ④。朱湘对于死亡的诗化表达不仅是基于现世经验的奇谲想象,更带有一分庄严肃穆的意味:“死神端坐在檀木的车中; /车前有燐火在燃着灯笼; /白马无声的由路上驰过,/路边是两行柏树影朦胧。”(《死之胜利》)死亡如同神灵般掠夺生命,连“燐火”与“白马”这样清晰的意象也变得模糊,“柏树影”的恍惚更增添了死神不可捉摸的神秘感。诗人在对死亡冷静的观察与想象中,暗示出脆弱的生灵和生存的困境,是对人性本质的拷问。由冷静渗透出向死而生的纯诗情的快感“导源于对美的静观、冥想。在对美的关照中,我们各自发现,有可能去达到予人快乐的升华或灵魂的激动” ⑤。
与冷静相对照的是一种整体把控的全局意识,朱湘的“全盘”说与穆木天在《谭诗》中的“诗的统一性”一脉相承:“一首诗是表一个思想。一首诗的内容,是表现一个思想的内容。”诗歌中的中心思想应该贯穿于每个诗节,朱湘的诗歌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例如:“母亲样/摩抚着儿童;……轻吻着/女郎的笑容;……催出泪/到老人眼中。”(《春风》)比较生动地涵盖了春风对不同人群的影响,透露出春风温馨、柔和与无情的多重特征。又如:“童年之内,是在这盆旁,……到青年时也是这盆旁,……到中年时也是这盆旁,……如今老了,还是这盆旁”(《残灰》),将烤火的情境贯穿人的一生,在纵向的深度上形成统一的整体。
整体的全局意识还体现在朱湘将旧诗词融入新诗创作的艺术特色。譬如:“苍凉呀/大漠的落日: /笔直的烟连着云”(《日色》)读到这里,不禁想起王维的《使至塞上》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又如:“看哪!一轮红日已经东升,/杏黄的旗旆在殿脊飘扬; /在一万里的青天下荡漾,/听哪!景阳楼撞动了洪钟!”(《晓朝曲》)该节第一句来自王维《早朝》的“苍茫连天曙”,第二句来自王维《春日直门下省早朝》的“旌旗映阊阖”,最后两句来自王维《早朝》的“始闻高阁声”。但朱湘并非生搬硬套,他的改写与重组体现了不同用意和风格:“在王维是谀上,在朱湘却是怀古;在王维是写实,在朱湘却是想象”。 ⑥朱湘将古典诗词的内容和格调选择性地纳入新诗中,将二者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沈从文对朱湘的诗歌给予高度评价:“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在保留到中国诗与词值得保留的纯粹,而加以新的排比,使新诗与旧诗在某一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连续,而这形式却不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朱湘的诗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 ①
四、余论:“纯诗”世界的瑕疵
无论是对音节的推敲选择,还是对虚实相生的情景描绘,抑或是严密精细的思想流露,都表现出朱湘在建构“纯诗”世界过程中对“诗的真理”和“美”的不懈追求。然而,要想在现实中实现这种完美的构想却是异乎寻常的困难。朱湘于1932年底投江自杀,宣告了诗人“纯诗”世界的终结,也暴露出“纯诗”理念的局限。
诗歌创作在朱湘心目中是一项长久的伟业:“诗,……是一种终身的事业,并非靠了浅尝可以兴盛得起来的。” ②若要达到诗的纯粹境界,非浅尝辄止能够实现,因此诗人用毕生的心血探索诗歌的终极目标,直至生命的陨落。同时,朱湘的“纯诗”世界排除了功利等外在因素的干扰,是纯然自我的心声,他呼吁道:“我们如想迎合现代人的心理,就不必作诗;想作诗,就不必顾及现代人的嗜好。” ③
朱湘的诗学观固然有积极一面,但真正能响应其号召的人却寥寥无几,更别提朱湘的诗歌能被多少人理解与接受。朱湘是一位性格极其鲜明的诗人,他在《我的童年》结尾总结道:“我真是一个畸零的人,既不曾作成一个书呆子,又不能作为一个懂世故的人。” ④朱湘始终徘徊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默默忍受着孤芳自赏的寂寞与痛苦。对于朱湘的死因,文学界众说纷纭,很多人将朱湘失业的经济因素列在首位,却忽略了诗人内心的挣扎。刘大杰在与朱湘的交往中发现:“在他的生活的根底里,有两件苦痛的事。第一,他认为他的诗是美丽的。但是中国没有人认识他。第二,是结婚的生活,丧失了他的自由和艺术的灵感。” ⑤正是在高度紧张的精神世界中,诗人感到现实的无助与迷惘,连最亲近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于是在深深的绝望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朱湘在《文艺作者联合会》一文中谈道:“文艺作者的性格是最怪癖,执拗的,一句话不投机,或是坚持一种异于流俗的主张,便可以自绝于生路。” ⑥朱湘的生命是极度脆弱的,他的“纯诗”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阻隔,缺乏丝毫沟通的可能性,麻木凄凉的现状令诗人心灰意冷,理想与现实的龃龉将诗人逼向绝境,正如何德明在《悼朱湘》一诗中所写:“世界到处都长满荆棘,/不容许你自由地呼吸; /光明,灿烂,是你的希望,/你所获得的只是昏黄; /忧郁早已涂遍你的心,/但你还写诗一行,二行,……” ⑦朱湘精心设计的音节被现实的嘈杂遮蔽,苦苦追寻的美被现实的丑掩埋,缜密统一的思想却是一种曲高和寡的存在。
朱湘之死与其说是“纯诗”世界的悲哀,不如说是“纯诗”世界的完美谢幕,正如瓦雷里所言:“纯诗的思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典范的思想,是诗人的趋向、努力和希望的绝对境界的思想……” ⑧瑕不掩瑜,朱湘在不断趋于“纯诗”的尝试中呈现出诸多诗美的特质。
朱湘:《桌话Table-Talk》,载《文学旬刊》1924年第142期。
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王独清:《再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页。
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刊》1926年第7期。
罗念生编:《朱湘书信集》,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29页。
徐志摩:《诗刊放假》,《晨报副刊:诗刊》1926年第1期。
瓦雷里:《论诗》,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5-66页。
刘延陵:《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诗》1922年第1卷第5期。
梁宗岱:《论诗》,《诗与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0页。
朱湘:《诗的产生》,《文艺创作讲座》1932年第2期。
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苏雪林:《论朱湘的诗》,《青年界》1934年第5卷第2期。
瓦雷里:《论诗》,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第69页。
朱湘:《诗的产生》,《文艺创作讲座》1932年第2期。
墨雷:《纯诗》,曹葆华编译:《现代诗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9页。
罗伯特·潘·沃伦:《纯诗与非纯诗》,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81页。
梁宗岱:《论诗》,《诗与真》,第30页。
朱湘:《诗的产生》,《文艺创作讲座》1932年第2期。
梁宗岱:《谈诗》,《诗与真二集》,第2页。
雷达:《论纯诗》,曹葆华编译:《现代诗论》,第192页。
A·C·Bradley:《为诗而诗》,李健吾、朱佩弦译,《一般(上海)》1927年第3卷第3期。
罗念生编:《朱湘书信集》,第31页。
瓦雷里:《论诗》,黄晋凯等编:《象征主义·意象派》,第74页。
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梁宗岱:《象征主义》,《诗与真》,第94页。
方长安:《死亡之维与新诗研究的反思》,《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
爱伦·坡:《诗的原理》,载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501页。
赵景深:《朱湘的短诗》,《大江月刊》1928年第1期。
沈从文:《论朱湘的诗》,《文艺月刊》1931年第1卷第2期。
朱湘:《北海纪游》,《中书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第14-15页。
朱湘:《北海纪游》,《中书集》,第16页。
朱湘:《我的童年》,《中书集》,第168页。
刘大杰:《朱湘的死》,《华年》1934年第3卷第5期。
朱湘:《文艺作者联合会》,《中书集》,第199页。
何德明:《悼朱湘》,《青年界》1934年第5卷第2期。
瓦雷里:《论诗》,黄晋凯等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第71页。
On ZHU Xiang’s Pure Poetry World
——Combine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Poetics of Pure Poetry
TIAN Yuan
(Chinese Language&Literature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ZHU Xiang in Chinese early literary circle called for the creation of the“pure poetry”,and devoted all his life and energy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his poetic ideal based on the essence of“poetic truth”and the form of“beauty”.ZHU Xiang’s poems build up a colorful world of“pure poetry”,undergoing the unique experiment in three aspects of syllable’s considerations,imagery’s intake and conceiving perfectly,combining Chinese and western academic poetics of pure poetry,highlighting the collision blend musicality in the exquisite phonological combination,transferring distinctive melody,revealing the charm of imagination in the real experience,and arousing aesthetic pleasure,with ZHU Xiang’s meditating the mysteries of life in the calm thinking and giving overall consideration for the new poetry.The poet’s suicide seemingly gives the“pure poetry”world a dark end,in fact,from the reverse perspective it can be interpreted as an illumination of his pure poetry poetics adhered in the lonely anguish adherence.
Key words: ZHU Xiang; pure poetry;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责任编辑:诚 钧]
Kraft J,Kraft A.“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Journal of Energy Development,no.3(1978),pp.401-403.
Stern D I.“A multivariat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energy in the US macroeconomy”,Energy Economics,no.22 (2000),pp.267-283.
Soytas U,Sari R,“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causality relationship in G 7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s”,Energy Economics,no.25(2003),pp.33-37.
Fatai K,Oxley L,Scrimgeou F G,“Model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in New Zealand,Australia,India,Indonesia,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no.64(2004),pp.431-445.
Lee C.C,“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DP in G-11 countries revisited”,Energy Policy,no.34 (2006),pp.1086-1093.
AlIriani M.A,“Energy-GDP relationship revisited: an example from GCC countries using panel causality”,Energy Policy,no.34(2006),pp.3342-3350.
Yoo S,“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ASEAN countries”,Energy Policy,no.34(2006),pp.3573-3582.
Ferguson R,Wilkinson W,H.R,“Electricity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nergy Policy,no.28(2000),pp.923-934.
Alice Shiu,Pun-Lee Lam,“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Energy Policy,no.32(2004),pp.47-54.
Wolde Rufael,Y.,“Coal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Applied Energy,vol.87,no.1(2010),pp.160-167.
Rashe R,Tatom J,“Energy resources and potential GNP”,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vol.59,no.6(1977),p.68.
赵丽霞,魏巍贤:《能源与经济增长模型研究预测》,《预测》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