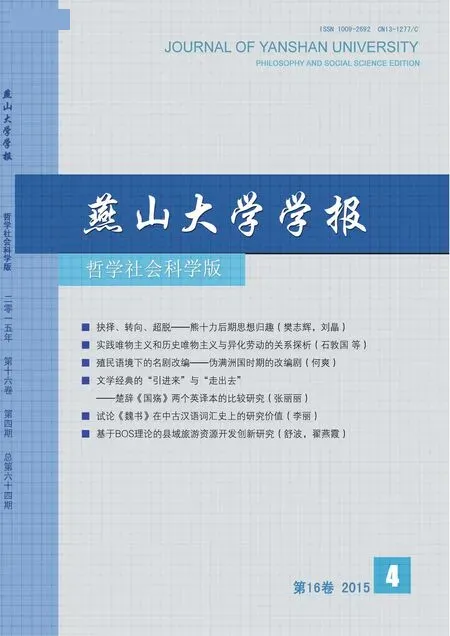文学经典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楚辞《国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2015-12-08张丽丽
张丽丽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文学经典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楚辞《国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张丽丽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通226019)
文学翻译的翻译方向影响了译者“为何译”、“为谁译”和“如何译”。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是中国古典文学译入与译出的先驱人物和杰出代表,论文以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国殇》为例,通过比较译者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翻译方法和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探讨翻译方向对译作的生成以及译文接受产生的影响,为当下中华文化“走出去”大形势下理想的译者模式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翻译方向;《国殇》;阿瑟·韦利;杨宪益;戴乃迭
一、引言
翻译方向是指译者从外语向母语,还是从母语向外语翻译,前者也称直接翻译(或曰译入),后者又叫逆向翻译(或曰译出)。[1]关于翻译方向与典籍英译译者资格问题曾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潘文国[2]驳斥了汉学家Graham认为汉籍英译只能由英语译者“译入”,而不能由汉语译者“译出”的观点,呼吁中国译者在加强中英语言和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胡安江[3]以葛浩文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认为理想的汉学家译者类型应同时具备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四个方面元素。黄友义[4]认为中外合作翻译不失为理想译者模式的一个选择。典籍英译译者资格已经无需辩驳,中外译者都可以独自或者以合作方式从事汉籍英译工作。然而,从译文接受角度观察,译入翻译与译出翻译能否取得同样的接受效果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作为中国文学源头之一的《楚辞》,19世纪初即开始传入欧洲,一百多年来相继出现十多个英译本。与楚学其他分支的研究相比,《楚辞》英译研究相对滞后,在近几年才逐渐受到重视。①《楚辞》英译译者主体也有两股力量: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楚辞》英译研究中最为多见的是经典译本的评述和针对具体诗歌的多译本比较研究:经典译本中又以两位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和阿瑟·韦利的英译本受关注度最高②;多译本比较研究中关注的多是不同译者翻译方法和策略的差异③。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多学者关注中国本土译者的《楚辞》译本。严晓江[5]提出在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形势下,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的主动译介。她认为许渊冲《楚辞》英译版本是对其文学翻译“三美论”的践行。[6]
《国殇》是《九歌》中惟一一篇铿锵高昂之歌,是屈原追悼为国牺牲的阵亡者而作,歌颂了楚国将士为保卫国家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国殇》以其英雄史诗和爱国主题引起中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与其他楚辞诗篇相比,相对浅显晓畅的语言也使其更容易引起中外译者的共同关注: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理雅各(James Legge)、韦利(ArthurWaley)和霍克斯(David Hawks)等相继将其“译入”英语文学。本土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下文简称杨氏夫妇)、许渊冲、卓振英、孙大雨等也先后“译出”该诗以传播我国中华文化精神。阿瑟·韦利和杨氏夫妇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先驱人物,他们的译本堪称中国典籍英译的译入翻译与译出翻译的杰出代表,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翻译方向决定了“为何译”、“为谁译”以及“如何译”。换言之,文学翻译的翻译方向决定了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文化策略。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译者模式才是理想有效的?笔者通过《国殇》的两个译本的比较研究,探讨翻译方向对译作生成和译文接受的影响,并尝试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
二、引进来:《国殇》的译入翻译
1.译作细读
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是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终其一生从事东方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成绩斐然。韦译《国殇》收录在1918年由伦敦康斯特布尔公司出版的《汉诗170首》中。这是第一部在西方世界公开出版的汉诗英译集,让西方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东方文学艺术的内蕴和魅力。
韦利灵活运用直译、意译两种方法,文化策略上以归化为主。在这篇《国殇》的英译文中无论是标题的选择、译文的视角以及选词用字都体现了韦利对读者的用心。韦译以“Hymn to the Fallen”[7]为题,意为“献给为国捐躯者的赞美诗”。“hymn”是基督教的赞美诗,圣歌。译文标题既契合原诗的主题意义,又体现出西方宗教文化,易于引起译文读者共鸣。古典诗歌往往既有叙事又抒发感情,翻译时需要选择人称——让诗人以“客”的身份出现,还是以“主”的身份出现。韦译《国殇》让诗人以“客体”身份出现,以第三人称视角切入,前半部分的战争叙事部分,韦利选择以第一人称直接引语译出,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后半部分的抒情转以第三人称,犹如西方神父为死者亡灵祈祷,充分体现出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为译文读者所作的考虑。诗歌翻译中最难处理的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诗歌形式中的韵律和节奏又是难中之最。韦利认为,韵律对于诗歌固然重要,但由于语言体系不同,在语音和用词上很难对位。全诗采用“跳跃韵”,巧妙灵活地把握并体现原诗的节奏,而不强求押韵。
韦译中也有明显与原作相悖的变形之处,但是译者整体上保留了原诗的文学性。周建忠[8]曾探讨《国殇》的饲主,认为本篇的饲主应为楚国主将,是从大将军屈匄、唐昧、景缺等殉难将领中概括出来的人物形象。屈原感悟于将士们为国献身的高尚精神,为之做诗,祭祀、慰藉英魂而鼓励生者,在写主将的同时,也写到了广大献身的士卒,这是屈原接触下层、同情人民的表现。韦译叙事部分以“we”为主语,统领所有动作,用“they”指代敌军,描绘出惨烈却有些模糊的战争群像。然而,细读原诗的读者会发现原诗中既有群像描写,也有个体特写,从群像逐渐聚焦到个体。前四句“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是群像描写;后四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桴兮击鸣鼓”是对主将个体的描写。在古代战场上,只有主将才能驾战车,“援玉桴”、“击鸣鼓”。韦译中“the fallen horses block ourwheels,our chariot is held fast;we grasp our jade drum-sticks,we beat the rolling drums”似乎战场上每个人都有战车和战马,每个人都能击战鼓。后半部分以第三人称出现,诗人化身为神父,为死者亡灵祈福。结尾部分点睛之笔“Their bodies perished in the fight;but themagic of their souls is strong——Captains among the ghosts,heroes among the Dead!”突出了勇武刚强的楚国将士形象,升华了英雄永垂不朽的主旨精神。Captains与heroes对应出现更彰显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军魂。对于译文读者而言,群像与个体特写并不重要,他们更加不会去考究中国古战场上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驾战车、击战鼓这样的细节,他们能产生共鸣的是战争的惨烈悲壮和英雄的视死如归,这些是超越了时空距离的人类的共通性。
2.译文接受:无意插柳柳成荫
虽然在韦利之前,已经有不少汉学家选译了《楚辞》部分诗篇。翟理斯曾选译《卜居》、《渔夫》、《九歌·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和《国殇》等篇,分别收录于《古文选珍》和《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但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译者缺乏汉语助手,译文多有诟病。理雅各1895年发表《<离骚>及其作者》一文,其中选译了《离骚》、《国殇》和《礼魂》等篇目,此译本曾被西方汉学界视为权威。韦利译本的出现使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真正改观,他的中诗英译为转型时期的英语诗歌注入了东方血液。
韦利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的成功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多种因素。首先,接受环境十分契合。在20世纪头20年的英美文坛,以庞德为核心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正当风头之上,自由体及素体诗也越来越深入人心,韦利的英译汉诗契合了这一时代潮流。其次,韦利的目标读者非常明确。他对于西方读者的文学传统和审美取向了如指掌,自然能够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为了和朋友分享其阅读中国诗歌的快乐。他的这些朋友包括T.S.艾略特、罗杰·弗莱、洛斯·迪金森以及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9]。他在诗集序言中说:“本序是为普通读者而作,因此只简单明晰地陈述我的观点,并未涉及那些少数专家才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④因此,韦利的英译本不光在汉学界而且在文学界乃至普通大众读者中都受到普遍欢迎且影响深远。不少读者将韦利的英译汉诗当作英语诗歌来欣赏,甚至忘了这是英译的汉诗。《国殇》的英译本后来被选入《牛津战争诗选》[10],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第三,韦利的翻译属于个人行为,可以遵从个人的审美趣味。他的文学天赋也在翻译中得到全面的发挥。随着对中国文化文学研究的深入,韦利在自娱自乐和与朋友分享的过程中无意间推广了中国文学,成功地为西方公众打开一扇东方文学之窗。
三、走出去:《国殇》的译出翻译
1.译作细读
1938年杨宪益还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出于好玩儿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格式翻译出来。1953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部分篇目,结集出版了《<离骚>及屈原的其他诗作》,《国殇》亦收录其中。杨译《国 殇》题 为 “For Those Fallen For Their Country”[7],意为“纪念为国捐躯的将士”,也契合原诗主题,但译者未用“hymn”以迎合西方文化。译诗在韵律形式上采用了英雄双行体,双行押尾韵:“aabbccddeeffgghhii”对仗工整,朗朗上口。在译文视角的选择上,杨译让诗人以“主体”身份出现,采用第一人称视角,作为中华传统继承者和参与者见证了古战场的惨烈与英雄的献身精神。开篇群像描写用复数“we”作主语:
的表达水平 PBMCs于37℃水浴复苏后,HBSS洗涤,取(1~2)×106个细胞,加入1 mL Trizol,按照说明书提取总RNA。检测RNA纯度及浓度,取1 μg RNA的液体量,配制反转录反应液,37℃ 15 min、85℃ 5 s,逆转录cDNA。取cDNA 1 μL,配制qRT-PCR反应液,反应体系为20 μL。反应条件:95℃预变性30 s,95℃扩增5s,60℃延伸30 s;共40个循环。以GAPDH作为内参,记录Ct值,计算相对RNA含量。
We grasp long spears,clad in rhinoceros’hide;
Our chariots clash,the daggers gashing wide;
Flags shade the sun,like lowering clouds the foe,
While arrows fall our warriors forward go;
They pierce our line,our ranks are overborne.
随后镜头聚焦到将领身上,译文转以单数“I”作主语:
My left-hand horse is slain,its fellow torn;
My wheels are locked and fast my steeds become,
I raise jade rods and beat the sounding drum.
后半部分,译者如屈原附身,亲临战场,见到惨烈的战后情景,感受到将士们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爱国激情。逝者已矣,他们的爱国热情通过诗篇得以永世传颂。
Warlike indeed,so resolute and proud,
Undaunted still and by no peril cowed,
Our spirits deathless,though our bodies slain,
Proudly as kings among the ghosts shall reign.
相比较于韦译模糊的英雄群像,杨译的人物刻画更为清晰,爱国精神的渲染更为强烈。与韦译相比,更加忠实于原作。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曾评价杨氏夫妇《离骚》译文像蒲伯译荷马史诗那样富有诗感,但不忠实于原文。他说:“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11]杨氏夫妇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时一向以信为本,他们忠实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明的精神。
2.译文接受:有心栽花花不开
杨氏夫妇坚信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而翻译是在不同民族中进行文化传播的手段。杨宪益认为艺术审美的超时空性和文化类同可以消除古典文学作品翻译中的时空距离: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时间相隔久远的问题。拿《诗经》来说,其中有些作品是公元前800年写的,当然不能确切反映今日中国人的感情。然而,我们对这些诗歌还是赞叹不已,原因是它们都是杰出的诗篇。[12]
作为中国汉译外和传播中国文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氏夫妇终其一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有强烈的责任感与献身精神。自19世纪以来,中译外与外译中相比一直显得势单力薄。直到上世纪中,我国都没有专门从事中国经典外译的部门。1951年,杨氏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自此开启了他们“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的伟大工程。他们想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清末再到鲁迅选150种,当代文学从鲁迅起到现在选几十到100种。[13]187-188当然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宏大的翻译计划并未完成。
1966年,戴乃迭在译完《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后,用英文写了一个批语交给了领导,阐述了自己对文化交流基本原则的理解。她认为:“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必须首先把互相尊重放在首位,中国人不仅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同时也要尊重外国文化的传统,在一个对外宣扬自己文化的刊物上肆无忌惮地攻击他者文化乃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14]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的所言所行有些不合时宜,但足见一个在华外国专家的坦诚与敬业。杨苡谈到杨宪益夫妇对于翻译文学名著的工作态度时说:“他的工作并不是那样轻而易举,文学翻译绝不能一挥而就,更不是人云亦云的依样画葫芦。翻译实际上也是创作,而且比创作更苦累人……杨宪益从来不说一句气馁的话,他是主张埋头苦干的。”[15]
杨氏夫妇的文化传播理想以及严谨认真的翻译态度在国际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英国伦敦大学把他们(杨氏夫妇)的译著,如司马迁的《史记》、《唐代传奇小说》、洪昇的《长生殿》、明代《平话小说》以及《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当作中文系必修的教材。荷兰著名的莱顿大学,有半壁书架挤满了他们的译著,其收集之博,比他们自己记忆的还要多。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大学,也收藏了一大书架他们的译著。香港大学更为他们的译著单设了特别的书架。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授予杨老荣誉会员与院士称号。1993年3月,香港大学特地颁发杨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贡献。[13]260-261
他们的译作在国内学术圈中好评如潮,但在国外读者中却遭受冷遇。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接受环境缺乏内驱动力。译文的接受需要与接受环境进行时空对接,对接上了译文成功;对接不上译文必然受到冷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读者的接受需求是相左的。行政干预和编审行为中的意识形态至上使刊物在内容选择和翻译方法上容易带有保守色彩,对读者缺乏吸引力。其次,杨氏夫妇的目标读者比较模糊。在接受澳大利亚杂志访问时,戴乃迭女士曾坦言做翻译时对自己的读者不是很了解:“我们是为看不见的人民作翻译……我们不仅在为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作翻译,也在为亚洲国家中懂英语的读者而工作,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读者究竟是谁。”[16]第三,在古典文学英译的翻译方法上,杨氏夫妇倾向于流畅前提下的直译,文化策略上以异化为主。杨宪益认为:“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该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17]译者在其文化立场指导下让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也影响到译文的可读性,有时甚至会让读者产生自然的抵制情绪和逆反心理。政治第一、国家至上的指导思想使译者无法尽情发挥他们的文学才能。杨宪益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13]219
四、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韦利以西方文化身份自居,他的“译入”翻译以拿来主义为指导思想,变东方古典为西方经典;杨氏夫妇以东方文化身份自居,以强烈的责任心苦心孤诣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却很难达到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无论是韦利的“译入”翻译,还是杨氏夫妇的“译出”翻译,从语言文字上分析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而翻译中的变形或对原文的“不忠”也都有译者自己的考虑和理由。然而,从译文读者接受角度考察《国殇》的两个英译本,可以由点及面管窥“译入”翻译和“译出”翻译的差异,其接受效果正应验了一句中国古诗:“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国殇》英译本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从翻译方向与译文接受角度看,成功的文学翻译往往是译入翻译。国际译联只能接受译入语为母语的翻译,这样的国际惯例已成传统,不是一两个译者或一两代人能够撼动得了的。谢天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丛书》总序中曾说:
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厢情愿地向异族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译入活动只需要交出一份“合格的译作”,基本不用考虑译入语环境中制约或影响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就自然而然能够赢得读者和市场。……(中国本土译家)在对译入语国家读者细微的用语习惯、独特的文字偏好、微妙的审美趣味等方面的把握上仍然无法跟西方汉学家相比。[18]9-10
因此,同等条件下,从事逆向文学翻译的译者至少多了三个方面的困难:语言的阻力、文化的障碍、接受环境的内驱动力。“译入”和“译出”都很重要,但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选择和喜好。中国本土译者要想在海外市场与汉学家的译文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但是他们的努力并非没有价值和意义,他们的译本至少为翻译学习和语言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标准化”的单一译本已经不可能一统天下,应该鼓励多样化的典籍英译本。
其次,在东西文明的交融过程中,双方都会立足于自家文化,对外来文化加以阐释、吸收、利用,误读和歪曲在所难免。文本的传播从来不是简单的平行移动,处于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语境中的翻译主体对于意义有不同的把握。因此,对于汉学家的翻译,国人要有包容心态,不要动辄苛责译者有帝国主义话语或歪曲中国文化的恶意,而无视它在文化传播中的成功。毕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翻译家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
第三,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之前就要有清晰的读者定位,要以目标读者的文化为参照系,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达到译介的目的。评价译文的好坏不能止于文字的转换,语言的等效、文化的交流、意识形态的导向、读者的接受和传播效果都得考虑。
第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文化的“双向”流通。汉学家和掌握外文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模式值得借鉴推广。除了译者的国际合作之外,更要加强出版界的国际合作:可以通过国际书展、版权代理等方式联系海外出版社合作译介和出版发行。
文学译介是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译者是文学交流的推手,“一个好的作家遇上一个好的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19]。本土译者“译出”翻译也好,汉学家“译入”翻译也好,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与互动。我们应该允许多种译本并存,在市场中优胜劣汰,让读者各取所需。当然,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让西方读者走进来,让他们亲历中国历史与文化,有助于读者扫除理解中的障碍。文学翻译是个系统工程,只有赞助人、出版界、译者、研究者和读者共同参与并加强沟通,中国文学才能有效地走出去,中西文化交流才能实现双向沟通与良性互动。
注释:
①据文军、刘瑾(2013)统计,1992—2012年间,与《楚辞》英译相关期刊论文33篇,大多集中于2008-2012年发表。参见文军、刘瑾:《国内<楚辞>英译研究综述(1992—2012)》,《外文研究》,2013年第1期,第84-90页。
②代表性论文如程章灿:《论霍克斯教授的<楚辞>翻译——读<楚辞:南方之歌>》,《中国楚辞学(第18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3月26日。蒋林、余叶盛:《浅析阿瑟·韦利<九歌>译本的三种译法》,《中国翻译》,2011年第1期,第65-71页。
③如张煜(2010)选取杨宪益夫妇、大卫·霍克斯和卓振英的《山鬼》英译本为例,从多方面对译本做了综合分析,管窥三位译者在楚辞英译方面的策略方法和优劣得失。
④见《汉诗170首》1962年版介绍部分。转引自陈惠:《阿瑟·韦利翻译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原文为英文,引文为本文作者的翻译。
[1]史凯,吕竞男.文学出版走向世界:谁来译?[J].中国出版,2013(8):57.
[2]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中国翻译,2004(2):40-43.
[3]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J].中国翻译,2010(6):10-16.
[4]黄友义.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的翻译——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J].中国翻译,2010(6):16-17.
[5]严晓江.《楚辞》英译与中学西传[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4(9):122-130.
[6]严晓江.许渊冲《楚辞》英译的“三美论”[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2-96.
[7]吕叔湘,许渊冲.中诗英译比录[M].香港:三联书店,1988:46-49.
[8]周建忠,贾捷.注评《楚辞》[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8-73.
[9]陈惠.阿瑟·韦利翻译研究[M].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10]程章灿.东方古典与西方经典——魏理英译汉诗在欧美的传播及其经典化[M].中国比较文学,2007(1):31-45.
[11]张煜.《楚辞》的英译比较研究——以《九歌·山鬼》为例[J].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2010:1-15.
[12]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13]杨宪益.杨宪益对话集: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14]邹广胜.谈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的学术成就[J].外国文学,2007(5):119-124.
[15]杨苡.杨宪益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6(5):40-41.
[16]禹一奇.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17]Kenneth Russell Henderson,杨宪益,等.The W rong Side of a Turkish Tapestry[J].中国翻译,1981(1):5-9.
[18]谢天振.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丛书总序[M]//刘小刚.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与跨文化交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19]高方.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家毕飞宇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3):49-53.
In-coming Translation and Out-going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Guo Shang
ZHANG Lil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019,China)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 influences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W ith Arthur Waley and the Yang’s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one of the poems in Chu Ci as a case study,this paper trie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coming translation and the out-going translation in purpose of translation tasks,implied readers,translationmethods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and hopes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an ideal translatormodel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direction of translation;Guo Shang;Arthur Waley;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H315.9
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150406606
[责任编辑 董明伟]
2015-08-09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资助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楚辞》英译的文化翻译观”(2013SJB750014)
张丽丽(1980—),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