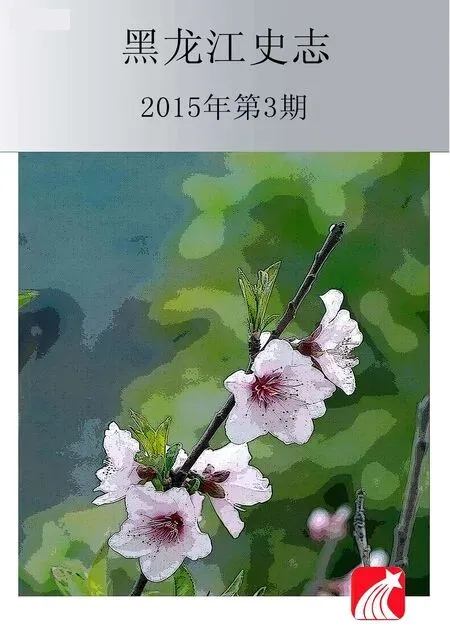揭露“满洲青年联盟”反动组织
2015-12-07安源
安 源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揭露“满洲青年联盟”反动组织
安 源
(哈尔滨师范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由“满洲铁路会社”成员为主体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是一个鼓吹“民族和睦”、“满蒙独立”的民间团体,其政治活动历经“满洲青年议会”、“自治指导部”等过程,最终提出了建立协和会的构想。本文试从满洲青年联盟的政治活动与发展过程等角度分析满洲青年联盟的实质,揭示伪满洲国协和会与满洲青年联盟之间的继承关系。
伪满洲国;满洲青年联盟;协和会
伪满洲国协和会是以吹嘘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等思想,美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侵略为主要政治理想的组织。其机构的确立不仅是在关东军严密控制之下构建的,而且与协和会组织创立前在中国东北进行反动活动的在满日本人团体以及紧接出现的自治指导部都有紧密联系。“所谓协和会,是对于满洲事变前饱受旧张家政权榨取压迫的严厉暴政,满洲三千万民众奋起之事态,以此作为成立之发端的。即是在事变之前有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运动,在事变之后有自治指导部之成立以及建国运动。”[1]可以指出,作为伪满洲国政府精神母体的协和会是在满日本人团体在中国东北的长期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政治需求而建立的。
一、满洲青年联盟初创期的政治思想
协和会的前身即协和党,是在伪满洲国建立后,出于宣扬伪满“建国精神”的需要,原“满洲青年联盟”成员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在得到了石原莞尔的大力支持后策划而成的。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作为协和党构想的提出者与满洲青年联盟重要干部之一,他们提出“协和党”这一概念秉持了满洲青年联盟曾经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的基本思想。
满洲青年联盟是“于1928年11月在大羽时男、山口重次的提案下,由关东州及满铁沿线附属地中居住的日本满铁社员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扩张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2]从其创立的历史背景看,当时日本的近代议会制度在国内已经开始起步,但是日本在东北以满铁工作人员为首的日侨领导人对于在中国东北没有能代表日侨的舆论发言机构,自身仍然要受到本土任命的掌权者的命令而深深不满,同时在日本国内,政友会、民政党两大政党交替执政,满铁的领导也随之更迭,对于东北的殖民经营就出现了缺乏计划性和长远性的缺陷。另外,在中国国内对于日本侵略意图反对浪潮高涨的情况下,日本的左翼及自由主义者中产生了“满蒙放弃论”,这对于右翼殖民势力来说,无异于让他们放弃“在明治大帝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并为之牺牲了十万同胞的圣地”。[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是加重了日本国内的经济和政治负担,把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独占市场的“满蒙生命线”理论被大肆宣扬开来,日本舆论开始偏向于把中国东北作为其摆脱危机的出路。于是,1928年5月,以满铁社员为主体的日本在东北侨民召开了第一次“满洲青年议会”,商议把中国东北如何变成日本殖民地的问题。虽然该议会具有模拟议会的性质,但是已经提出了要把“任凭当权者摆布的满蒙”变为“靠全体国民浴血奋斗换来的满蒙”。[4]在1928年11月11日,满洲青年议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青年联盟成立方案,并作出宣言,宣示青年联盟的任务是从事夺取政权的活动,“从‘旧时代的当政者’手中,夺取‘确立满蒙政策运动’的领导权,通过国民外交,‘夺回满蒙’”。[5]
可以看出,满洲青年联盟是具有浓厚的参政意识和自治意识的。青年联盟的参与者们不满足于他们话语权的薄弱,积极自主地结成政治结社,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满蒙问题已经引发中国方面强烈反日浪潮的情况下,日本国内政府依然态度保守迟缓,不得不引发在中国东北生活的日侨对能否保住其“圣地”的担忧。无论是对掌权进行预演的满洲青年议会还是将其纲领付诸行动的满洲青年联盟,都表露出在满侨民试图由自身掌握在中国东北政治行为的意愿。
而这种自治意识与国内政府对在满侨民的态度也有关。币原喜重郎外相在第五十九届议会上对在满侨民进行了批评,他说,“一面徒然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一面对政府一味依赖”,这是“满蒙形势不佳”的原因。[6]“对政府依赖”显然是对在满日本人团体的误解,而“以优越感对待中国人”也无非是指出了日本侨民和满铁社员们在中国东北显著的民族主义特质。但这种指责明显激怒了已然将中国东北视为家园的青年联盟的不满。青年联盟在随后采取了积极的宣传措施,以图在日本国内掀起舆论上的同情。一方面,满洲青年联盟派出母国游说队,于1931年6月底回到日本会见各政党领袖、政治首脑、新闻机构和社会团体,攻击币原外相的“软弱外交”与左翼势力的“满蒙放弃论”;另一方面,满洲青年联盟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满蒙三题》等宣传册,其主要内容为:鼓吹“满蒙生命线”理论;攻击日本当局对在满侨民的忽视;在中国东北推翻旧军阀建立起“民族和睦”的把日本文化为主要基调的殖民乐园,并分发到国内政府机关、国会议员、新闻和杂志社、各社会团体甚至于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满洲青年联盟于1931年6月在大连的演说大会上也提出所谓“期望在满洲实现各民族协和提案”,鼓吹在中国东北建立起“和平协和”的氛围。满洲青年联盟的宣传策略虽然在日本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没有达成他们最终想要的政治效果。应当指出的是,满洲青年联盟的“民族协和”理论前提是建立在“满蒙自治”基础上的,而他们所提出的“满蒙自治”又是出于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在野青年和满铁青年社员参与到政治中的愿望,这一点从满洲青年联盟的最初形态,也就是所谓“满洲青年议会”的模拟议会诞生的出发点来看,并不难理解。
二、协和会成立前夜的自治指导部
满洲青年联盟成立之后所进行的多次议会中有一项名为“满蒙自治制”的议题,提出该议题的理由是“满蒙特殊区域,深受中国军阀野心之灾祸……故特制定满蒙自治制,以期满蒙获得发展”。[10]在向日本国内进行多次游说依然没有引起预期效果的情况下,与其寄希望于摇摆不定的内阁政府,不如与已经采取了激进措施的关东军合作。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于对东北各地方政权进行控制的需要,利用满洲青年联盟对所谓“新满洲建设”的热情设立了自治指导部,用以监督和控制各县行政,“宣抚”人心并为伪满洲国的建立制造舆论。自治指导部的成员是以满洲青年联盟的理事长金井章次与中西敏宪、山口重次以及大雄峰会的笠木良明、中野虎逸等人的合流为基础构成的。1931年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成立。自治指导部部长是提倡“绝对保境安民主义”,提出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成立独立国家的于冲汉,而掌握实权的顾问中野虎逸和中西敏宪不但具有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背景,同时中野虎逸还是关东军军部政治部主任。作为自治指导部骨干的笠木良明在战后供述说:“板垣征四郎大佐主持这个部,石原莞尔大佐担任策略,土肥原贤二大佐在沈阳主持特务机关。那一个中国人(于冲汉)对我们的计划表示好意的情报,多半由土肥原大佐的机关供给。”[7]
1931年11月10日自治指导部成立当日,以于冲汉名义发表了所谓“自治指导部布告第一号”,该布告称“自治指导部之真精神乃是将天日下过去一切之苛政、误解、迷想、纠纷等扫荡干净,志在建立极乐土……要在此大乘相应之地创建史上未见的理想境地,倾全部努力即成兴亚大涛,纠正人种偏见,着眼于确立中外不悖的世界正义……由本部渐次向各县派遣指导员实行善政,县民安定受其指导,兹布告之。”[8]这份布告从表面上说是把卖国主义强行解释为“扫荡苛政”,从其实质上说是在关东军指导之下进行美化殖民主义的宣传策略。该布告的中心思想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满洲青年联盟一贯的政治要求的体现,他们以往鼓吹的“民族协和”、“建立满蒙独立国”等思想在自治指导部得到了初步实现。自治指导部在各县设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职,指导各县的政策实施,后者则由当地的亲日派担当头目,实际上在县一级的权力已经被由日本人把持的县自治指导委员会控制着。1932年3月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自治指导部解散,“由此……加入满洲国政府参与政务的主要是大雄峰会系,而青年联盟系则被疏远,成为在野的势力。”[9]正是在此阶段由满洲青年联盟系成员山口重次和小泽开策提出建议,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协和会。由此可以看出,协和会概念的提出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民间团体的政治诉求的继承关系。
三、满洲青年联盟与协和会的关联性
1932年7月25日,在新京国务院举行了协和会的成立大会,确定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为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国务总理郑孝胥任会长,中央事务局方面由谢介石任局长,中野虎逸任次长,满洲青年联盟系的小泽开策、山口重次等人担任中央事务局委员。在执政溥仪的训词中,强调“建国精神在以王道谋求民族协和”,又在创立宣言中有“本会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以王道为主义、牢记民族协和,以加强我国之基础,宣化王道政治”,明确了协和会的使命。会上提出了协和会的纲领:“宗旨:以实现王道为目的,铲除军阀专制之余毒;经济政策:努力振兴农政,改革产业,以期保证国民生存;国民思想:重礼教,乐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敦睦。”[10]
结合对协和会的纲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得出协和会和满洲青年联盟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主要联系:
1、“宗旨:以实现王道为目的,铲除军阀专制之余毒。”就是要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一个由以“王道政治”为招牌,实际上处于关东军掌控下,政治上完全脱离中国政府的“满蒙独立国”。在关东军的理论中,“王道政治即哲人政治,并非中国古来所有的王道思想,具有体现天皇御意的含义……当前关东军司令官于满洲国来说是王道政治之中心,其真意在于司令官乃是以天皇御意为己意的公务人员的哲人。”关东军司令官俨然成为了在“满洲国”具有无上地位的最高统治者。协和会纲领中所谓“王道政治”,表面上是在伪满洲国内实行继承自中国古代的以仁政为思想的治国理念,创造“日满亲善”之下虚伪的“王道乐土”。在东北的日本民间团体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在东北进行经济殖民的满铁会社,如何保障其所在会社的利益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自治指导部解散后其成员大部分下野的满洲青年联盟把建立“满蒙独立国”的构想寄托在已然拥有伪满洲国一切政治经济权力的关东军身上,其“建国理想’的映射就是协和会。重要的是,“今日的协和会的精神最多的是从自治指导部的衣钵继承过来的”。
2、“经济政策:努力振兴农政,改革产业,以期保证国民生存。”就是把东北的各项产业置于日本方面的控制下,通过协和会开展所谓“勤劳兴国运动”、“农业增产运动”、“矿工业增产运动”,对东北地区丰富的人力、农业、矿业资源进行殖民性质的掠夺,以支持日本法西斯的扩张。到协和会时期,其所谓农村振兴、增产供出工作,也与改善民生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把满洲青年联盟的主张进行了一定的包装进行资源掠夺而已。满洲青年联盟的大部分成员作为满铁的员工,他们出于对日本陷于经济危机的考虑,控制并保护这一殖民地市场显得尤为重要。1932年1月满洲青年联盟印发的小册子中提到:“吾等之祖国日本于此秋季将满蒙作为重点之主张迅速确定,便应明确此主张之合理性,一路迈进……即将东北四省之‘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有关经济、治安、生活方面一并列举,我等应将其置于与日本帝国共通的圈内。”可以看出,满洲青年联盟对于“满蒙独立”的构想并非为了改善东北民众的生活,而是要把东北纳入到日本的控制中来,变成日本经济圈内的一环。
3、“国民思想:重礼教,乐天命,谋求民族协和与国际敦睦。”就是在“民族协和”的口号之下,掩盖伪满洲国实际始终存在的民族问题。作为政府精神母体的协和会在活动上与满洲青年联盟的思想如出一辙,在统治政策上把日系作为主体,分化其他民族。1943年提出的《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中提出:“以民族协和为基础……促进普及日本语,以使之能理解日本文化”,这就把日本文化设置成为了伪满洲国的文化基调。同时,对各民族分别实施国民训练,对日系的训练目标是“要成为各民族的中心,并且具备被人敬爱的素养”;对鲜系的训练目标是“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和忠良的日本臣民……实施以精神教育和日本语教育,并奖励入籍”;对满系和蒙系则是“昂扬国家意识,理解一心一德的真义,信仰惟神之道”。满洲青年联盟要在东北建立以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国家,这一“理想”可见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是依然被协和会借用着的。
四、结论
满洲青年联盟在“满蒙独立国”构想孕育之初,为鼓动国内舆论支持出兵东北,在宣传手段中把东北军阀政权的独裁统治比喻为“吸血鬼”,急需日本出兵,以期建立“民族和睦的新国家”。而协和会成立宣言中说“绿林之辈盘踞此地擅权争政之二十年……暴政日甚……所幸今日天赐之机会新国家成立矣”,同样将“出于协和精神把东北人民从暴政中解救出来”作为日本出兵的借口。然而在满洲青年联盟的宣传手册中曾列举出从1926年开始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发生的“东三省中国方面损害我方权益之实例”共计52则,其中有关铁路修建、征税、采矿等经济方面的纠纷为41则,与日本方面实际没有针对关系的3则,具有实质性排日情绪的仅为8则。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出兵东北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经济利益而非“解救东北人民”,“建立民族和睦”。综上所述,协和会的“民族协和”,“建国精神”等口号,正是来自于满洲青年联盟一贯秉持的思想,而满洲青年联盟的政治主张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协和会的形式得到了实现,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
[1]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满洲建国五年小史》(日文),康德四年六月。
[2]南龙瑞,《日伪殖民统治与战后东北重建》(日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
[3][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
[4]同上书第112页。
[5]同上书第114页。
[6]同上书第151页。
[7]姜念东伊文成谢学诗吕元明张辅麟,《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8]南满洲铁道总裁室弘报课,《综合情报十一之号外协和会的发展》(日文),昭和12年,第122页。
[9]日满中央协会编,《满洲帝国協和会に関する懇談会記事要録》(日文),昭和12年,第37页。
[10]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吉林省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124、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