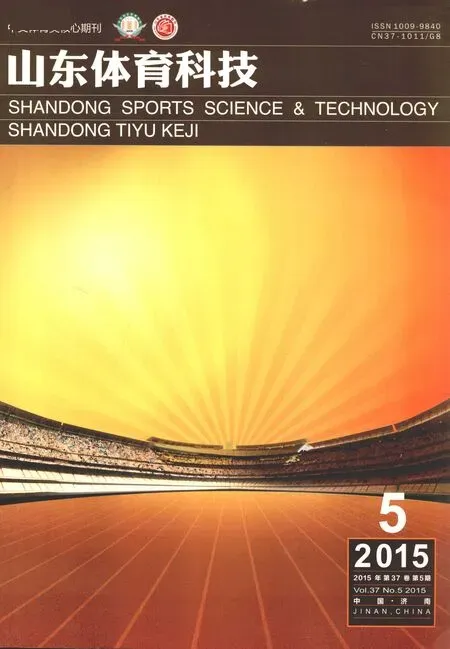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多维思考
2015-12-05仝其宪
仝其宪
(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 034000;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多维思考
仝其宪
(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 034000;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刑法理论中关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存在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正当风险说以及国家允许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等,但这些学说和理论缺乏解释的力度和深度,也缺乏普适性,需要进一步甄选。规范刑法学视角可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予以充实。不仅如此,对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深度回答还需要从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作多维思考。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期待可能性
在竞技体育运动中,由于参赛运动员之间激烈而又频繁的身体碰撞,导致赛场上的伤亡事件司空见惯。究其行为性质,大致有正当行为与违法行为之分野。也即是说,竞技体育伤害不但包括排除犯罪化事由的正当行为,而且也涵盖受法律规制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对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不能因为其披着“正当行为”的面纱而一概而论,需要撩开这层面纱识别其“庐山真面目”,正确区分合法伤害行为和非法伤害行为。但从危害后果来看,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可能发生致人伤亡的严重后果,而从法律后果来说,前者属于对社会有益的“可允许的危险”,而后者却是对社会有害的“禁止的恶”。简言之,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因其具有竞技性而排除犯罪化,国内外刑法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项法定的或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并提出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正当风险说以及国家允许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等。但这些理论学说因为缺乏解释的力度、深度和普适性而无法成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解释范式,这其中的理论根据非规范刑法学一门学科所能够解释完满,需要规范刑法学和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多维思考。
1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刑法学视角拓展
关于竞技体育中的伤害问题,基于比赛目的且未犯规的伤害行为,大多数国家都不将其作为犯罪进行处理。尽管各国刑法理论中对此有不同的称谓,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而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之为合法抗辩事由,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称为排除犯罪化事由或正当化事由。但不论是哪种语境下的正当行为,都是指的是客观上虽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形式上似乎符合某种犯罪的特征,但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排除刑事违法性的一类行为[1]。由于各国法律文化以及刑法理论的差异,对于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理论根据也存在较大不同。
1.1 国外学说简评
纵观各国刑法理论中将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的主流学说,所有这些学说将竞技体育本身风险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作为排除犯罪化事由都试图努力找到自说自话的完满答案。
正当业务说为日本刑法学界所主张。大谷实教授认为,竞技中的伤害行为应当属于日本刑法第35条规定的正当业务行为而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只要是在正当业务范围内实施,尽管符合伤害罪或暴行罪的犯罪构成,也应作为正当业务行为而阻却违法性[2]。应当说正当业务说将竞技体育中的人身伤害行为解释为在业务必要上所为之正当行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该学说对于业余运动员或普通体育运动员参加的竞技比赛解释为业务行为显然过于牵强。况且,在日本学界对于竞技行为分为职业竞技者与非职业竞技者两种情形。对于前者直接根据日本刑法第35条的规定认定为正当业务行为,而对于后者则不认为是业务行为,这就出现正当业务说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不仅如此,正当业务说也没有给出判断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属于正当化的判断标准,所以需要其他理论予以充实。
被害人承诺说为德国刑法学界所推崇,德国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大多将竞技体育中的伤害问题以被害人承诺说予以处理。该学说认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阻却违法性,在于这种伤害行为得到被害人的承诺,因为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侵害行为就相当于权利人的自由处分行为。西方古已有之“得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崇尚自由权利的英美国家对于竞技伤害行为也是以被害人承诺作为合法辩护理由的,英国以“参赛即为同意”原则而美国以“默示同意”原则均作为否认竞技伤害行为并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应当说被害人承诺说在运动员自愿接受竞技体育带来的普通风险上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不意味着运动员对来自竞技体育中的所有风险不加区分地予以接受,对于被害人承诺的权利范围应当仅限于轻伤以下的健康权利,对于那些故意制造或超出可允许的风险,像造成重伤或致人死亡的权利侵害,运动员就没有容忍此类风险的义务。也就是说,被害人承诺对于自己有权处分的法益尚且有效,而对于重伤和死亡这些重大法益是没有正当处分权的。
正当风险说认为,虽然某种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但该行为对整体的社会有益并为社会所期待,那么,就应该将具有危险可能性的行为作为合法化事由予以认可。该学说为俄罗斯刑法界所认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正当风险行为作了详尽规定,为了达到对社会有益的目的而在正当风险的情况下对刑法所保护的利益造成损害的不是犯罪[3]。俄罗斯的正当风险说影响深远,对其他独联体国家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应当说正当风险说风险来源广泛,不仅适用于职业领域,而且也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强调行为人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该学说仍是基于整体的社会利益考虑,而忽视了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
国家允许说认为,竞技体育能够增强人们体魄,弘扬人文精神,展现国家精神面貌,国家许可竞技体育开展,因此对竞技体育中造成的伤害不予刑事归责。简言之,正是对竞技体育的允许,使得竞技体育的伤害行为成为正当行为。国家为达到共同生活的目的基于人们的习惯而允许、默认竞技体育所导致的风险,注重人们的共同生活,从国家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强调对社会法益的维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过于强调国家意志的作用,却一定程度地忽视了公民个人法益的保障,仍然有失偏薄。
法益衡量说认为,当两个以上法益存在不可两全的冲突时,基于优先考虑法益更大者而不得不损害另一较小法益,那么这种法益侵害行为就具有正当性。意大利学者杜里奥·帕多瓦尼就是这一学说的力挺者,他认为,“冲突利益的平衡”为确立正当化原因的原则,当两个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法律优先保护的利益应通过价值比较来确定[4]。反映在竞技体育中,竞技体育带给人们的积极作用这一整体法益显然要大于运动员的个人法益,那么法律应当优先保护竞技体育的整体法益,而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作为排除犯罪化事由对待。可以说法益衡量说注重更大法益的保护,对于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它漠视了较小法益的保护,特别是对运动员个人法益的保护显然不足。法益衡量说也不能提供法益比较可考量的确切数据,在法益不同位阶体系中像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之间法益衡量就无法进行。其实,在现代社会,公民个人的生命健康权利是最基本的、最广泛的法益。因为社会法益是个人法益的集合体,侵害个人法益的行为都必然会侵害到国家和社会这一整体法益。反之,如果重视个人法益保护,也会促进国家和社会法益的发展,保护好个人法益是维护好国家和社会法益的最佳途径。可见法益衡量说仅注重整体法益而忽视个人法益的保护做法并不周延。不仅如此,法益衡量说过于注重结果的无价值而没有适当考虑行为的无价值,容易导致为实现较大法益保护而不择手段地损害较小法益,与法秩序的基本精神相悖[5]。
社会相当性说认为某种行为如果符合历史所形成的社会共同生活,其行为就具有社会相当性。那么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只要没有超出社会伦理秩序的范围就可以作为社会相当性排除犯罪化事由。社会相当性说为德日刑法理论中关于正当化事由的一般原理的通说。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行为最终被国家和社会的伦理规范所允许,乃是统一地把握所有正当化事由的原理[6]。应当说社会相当说基于社会的一般观念和社会整体法益来审视行为的违法性,既注重社会的发展,又不脱逸于社会共同生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社会相当性也有一定的缺憾,一方面社会相当性本身是一个颇具抽象性的概念,其借助的社会观念本身也是一个变化不居、极不清晰的术语。如何判断社会相当性,又不得不借助法益衡量说进行法益权衡。另一方面以社会相当性来解释刑法问题,不免带有主观随意性,容易侵蚀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进而导致刑法的滥用。
1.2 国内学说甄别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在我国刑法中是一种超法规的正当行为。我国刑法学者认识到国外各主流学说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于是他们对上述各学说进行了有机整合。譬如,有学者提出了“一体两翼”理论,即以可容许的危险理论为核心,以正当业务行为和被害人同意理论为两翼构建竞技伤害行为的合法化根据[7]。有学者主张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根据只有社会相当性更具有包容性、解释力和说服力[8]。还有学者主张被害人同意说。反观这些学说只不过对国外各主流学说的组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创新,并且我国学者对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主张又存在位阶混乱、逻辑不清之现象。
我国学者在探讨竞技体育伤害正当化行为时有将不同层次的概念混淆的倾向。多数学者将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正当风险说和国家允许说(目的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说等这些学说放在同一个层次相提并论,这就把违法阻却事由和违法性的实质混淆。其实,违法性阻却事由及其原理分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事由为下位概念,是用以解释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而后者原理为上位概念,是为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作理论根基的。事由表现为具体的行为类型,可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而原理为较抽象的理论描述,不可以直接适用于具体案件。申言之,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和正当风险说分别为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刑法中的违法阻却事由,这三种事由都可以用目的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的原理予以阐释[9]。不难发现,将违法阻却事由及其原理这两类不同位阶的概念置于一起存在逻辑上的自洽性。
1.3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补充
除了上述解释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理论根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引入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理论予以补充。在异常激烈的体育竞技比赛过程中,身在局内的运动员往往比身在局外的人期待可能性有所降低,完全期待运动员在激烈对抗状态中作出合乎比赛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从而应当免除或减轻其责任,这就蕴涵了期待可能性思想。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10]。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就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责难,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试想,法律强制要求运动员在紧张激烈对抗的紧迫状态下,以理性冷静地判断自己的行为并作出完全合乎规则的动作,显然是强人所难。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意蕴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仅是司法人员的裁判规范,而且也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以禁止和命令为内容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要合乎法律的要求,否则将遭致法律的制裁。然而,法律不是随心所欲而设定规范的,必须反映人们的实际情况,也即是说,法律设定的禁止规范和行为规范应以人们在行为当时可以不违反禁止规范和命令规范为前提条件的[11]。从“法律不强人所难”和法律规范的设定规则都要求立法者在设定刑事责任承担时必须充分考虑运动员在体育竞技比赛这一特殊场景极为容易作出违规行为,进而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而触犯法律,这属于事出有因,其可责性相对较低,对其免除处罚或从宽处理具有法理存在的正当性。
鉴于此,笔者认为,基于比赛目的且未犯规的竞技体育任何伤害行为都应当排除犯罪化,其中,造成轻伤以下危害后果可因“被害人承诺”而排除犯罪化;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职业运动员可因“正当业务”而排除犯罪化;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非职业运动员可因“正当风险”而排除犯罪化。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其中造成轻伤以下的可因“被害人承诺”而排除犯罪化。这些排除犯罪化事由均可以目的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等原理予以解释。基于比赛目的且犯规并造成重伤以上危害后果的行为应“入罪”,但可因“期待可能性”理论而减轻责任。只有基于非比赛目的且犯规的恶意伤害行为“入罪”无“宽恕”理由。
2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人类文化学根基
众所周知,竞技体育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紧密发展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现象,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文化表述。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向前推进,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诉求不断提升,竞技体育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现代文明社会又赋予竞技体育新的意蕴,成为一个国家富强、文明、健康、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竞技体育本身就蕴涵着浓郁的竞争与对抗,参赛运动员通过竞争与对抗获得满足和成功,而观众通过欣赏而获得刺激和愉悦。在竞争和对抗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攻击性行为,进而发生伤亡事故,这就使得竞技体育带有“暴力”性质[12]。然而,从古至今,人们对这一“暴力”场景已经司空见惯,不但毫无惧怕,反而心安理得、津津乐道,对竞技体育如此钟爱以致于如痴如狂。那么人们对此何以欣然接受而又心妄想之?要回答这一问题,从人类文化学的深层积淀论起更有说服力。
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竞技体育“暴力”并不是文明的对立物,而是与人类文明史相伴而生。竞技体育之滥觞就是以战争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古代奥运会的雏形初具以及现代奥运会的伟大复兴都与战争息息相关。这要追溯到奥运会的诞生地——素有欧洲文明发源地之称的古希腊,当时以城邦为中心建立的共和国也并非太平祥和,而是城邦之间各自为政,战乱绵延不断,民不聊生。人们在这充满暴力的战争中受尽痛苦与磨难,早已厌倦了“鼓角铮鸣”,而作为上层统治阶级也耗尽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政权岌岌可危、苟延残喘。无论上层统治阶级抑或普通百姓都对战争深恶痛绝,期盼和平的到来尤为强烈。于是在这众望所归的时机下,伊利国王和斯巴达王于公元884年签订了《神圣休战条约》,定期在奥林匹克举行集会,以体育竞赛方式代替了战争。从此出现了体育竞技以一种符合规则的文明“暴力”扬弃了昔日战争的赤裸暴力。然而,好景不长,19世纪未,妄图瓜分世界的德国又掀起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奥运会被迫停止,历史似乎又回到原点。但代表和平、友谊的奥运精神却生生不息,以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世界人民再次遭遇战争的洗礼后推动奥运会得以复兴。从此以竞技体育形式为载体的奥运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将竞技体育推向前所未有的巅峰,同时也推动了世界各国大大小小的竞技体育运动,使得竞技体育越来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透视现象揭示本质,竞技体育同样充斥着“暴力”,但它已经变异为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在这一特殊形式的冲突中已散去了昔日的“硝烟弥漫”,也远去了往日的“鼓角铮鸣”。可以说竞技体育将真正的战争场景演变为战争的游戏规则,尽管暴力依然存在,但已经柔化为一种文明的符合规则的暴力。
直面竞技体育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不尽心生疑问:对于前者人们何以如此欣赏?而对于后者何以为社会法律和道德所排斥?这主要在于体育竞技中的“暴力”这种原真性的历史遗留,经过漫长的人类进化而逐步被铸就成固定化的身体运动类型,人们早已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具有本能攻击性的体育竞技作为宣泄疏导的一种工具,从中获得快感和美感。不仅如此,这种体育竞技中的“暴力”也被人类认识并理解为在一个公平游戏规则之下的身体和情感的充分表达。其中比赛规则为它架设了一条通往社会公认的规范坦途,在这规范之下,日常生活中被禁止或责难的暴力行为,在这里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
竞技体育中的“暴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与人类本性相契合。精神分析学家弗洛里德将人的心理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其中“本我”就是代表人的本能天性,表征出人天生具有好斗或攻击的内驱力,这种攻击性能量与外部环境无关,而是来源于个体内部持续不断地集聚的潜能量,当它适逢外部环境引发刺激时,就有可能爆发并外显为攻击性行为。那么,如何将人的这种内部攻击能量以相对合理而安全的方式宣泄出来,体育竞技承载了这一历史使命,为人类心理能量的释放提供了一个既安全而又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安全阀,在社会冲突中起到很好的减震缓冲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演进,体育竞技暴力越来越融入到人类文化的血液之中,成为被社会伦理所许可而对社会有益的正当化行为。
3 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心理学视角阐释
在竞技体育比赛过程中基于角色的差异,参赛的运动员和普通观众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完成不同。一旦比赛开始,双方参赛的运动员就立即进入各自扮演的角色,处于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或狂奔或跳跃,动作千变万化,目光转换不断,回旋于场内外。一般而言,人在这极度紧张亢奋状态下遭遇外部刺激时都会做出反向回应以求得自我优势,这是在对抗性比赛中参赛运动员的本能反应,并且当外部刺激愈频繁或愈强烈时,人的这种动作反应也就表现得更为迅速或强烈。从心理学角度,可以将人的行为分为反射性行为、下意识行为、冲动行为和意志行为。反射性行为是行为主体遭遇外部刺激而迅速做出的本能反应,下意识行为是行为主体针对外部刺激而自动做出的反应,冲动行为是行为主体基于心情激动而产生的激情爆发行为。这三种行为都属于一种较少受意志控制的反应行为,并且这种刺激和反应之间时间间隔极短或紧密相连,常常混杂在一起而无法区隔。只有意志行为是基于行为人理智考虑行为客体而意欲达到一定目的活动。
又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参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不断遭受外部刺激而激发动作的千变万化,这期间会产生兴奋紧张、心跳急促或情绪激动等诸多身心表征,并且在这些心理状态支配下,运动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力和判断力大大下降,理智分析能力受到抑制,其自我行为的控制力也会大大减弱甚至急剧短暂丧失,导致大脑神经中枢不能运用自如地支配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走样,出现误差或失误。即使是富有百战经验的运动老将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应,而初出茅庐的运动新秀更为尤甚。难怪我们在观看许多大型竞技体育比赛时,经常对一些运动员因动作失误而与奖牌失之交臂的惋惜。这就足以印证了人在激情场景下其大脑所支配的规范的意志行为可能即可会变异为反射性行为、下意识行为或冲动行为的缘故。既如此,我们经常说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运动员的完美动作与其说是对精湛技术的表达,不如说是其良好心理素质的展示。
竞技体育运动总是发生在激情状态这一特定场景之中,尤其在现代社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体育竞技运动通常在大型场地举行,环境开放,人流涌动,欢呼雀跃,运动员不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不良干扰,进而影响其判断力,更加剧了动作失误或误差。如今体育竞技越来越充斥着商业玄机和功利色彩,盛行以成败论英雄,利益机制触动运动员获胜的动机不断强化,使得竞技赛场上各类运动项目的争夺异常紧张与激烈,尤其是一些对抗性强、危险性大的竞技项目,其激烈对抗更加白热化。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迅猛发展,一些更为刺激、危险更大的竞技项目不断推新,其运动技术和战术水平不断挑战人类身体的极限,这无疑增加了竞技伤害的概率。尽管如此,人们却不以为然,仍心旷神怡。种种迹象表明,在竞技体育运动中,参赛运动员身处的这一特殊场景出现人身伤害行为在所难免,其可责性自然要免除或降低。
4 结论
不管是规范刑法学中的正当业务说、被害人承诺说、正当风险说以及国家允许说、法益衡量说和社会相当说,还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引入,抑或从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视角,都不同程度地回答了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的合理内核。唯有从规范刑法学、人类文化学和心理学等视角进行多维思考,才使得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排除犯罪化事由的根基更加坚固,更富有韧性。
[1]康均心,古筝.体育竞技伤害行为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版),2012(1):118.
[2][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法讲义总论[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2.
[3][俄]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6.
[4][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某种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36.
[5][日]大塚仁著.冯军,译.犯罪论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41.
[6][日]大塚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320.
[7]林亚刚,赵慧.竞技体育中伤害行为的刑法评价[J].政治与法律,2005(2):92.
[8]吴情树,陈慰星,王方玉.论体育运动中的正当行为—以大陆法系刑法为文本[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5,(4):28.
[9]潘星丞.体育竞技致损行为“排除犯罪性”事由[J].体育学刊,2010(4):16.
[10]张明楷.外国刑法刚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43.
[11]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27.
[12]曲伶俐,吴玉萍.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刑法解读[J].山东社会科学,2010(3):84.
M ultidimensional consideration of excluding crim inal causes of com petitive sports injury actions
TONG Qi-xian
(1.Dept of Law,Xinzhou Normal College,034000 Xinzhou,Shanxi,China;2.School of Law,Anhui University,Hefei230601,Anhui,China)
There aremany doctrines in the criminal law theories aboutexcluding criminal causes of competitive sports,such as legitimate business doctrine,victim's commitment doctrine,proper risk and countries'allowance doctrine,interest measure and society considerable doctrine,but these theories and doctrines are lack of strength and depth for explanation and also lack of universality and need for further selection.The theory of anticipated possibility can be introduced from criminal law perspective.Also,the answers to competitive sports excluding criminal causes also requiremultidimensional reflections from human culture and psychology.
competitive sports;injury actions;excluding criminal causes;anticipated possibility theory
G80-05
A
1009-9840(2015)04-0029-05
2015-01-12
仝其宪(1974- ),男,河南濮阳人,讲师,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