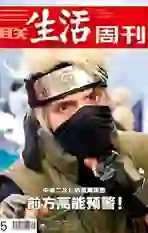爱尔兰:苍凉与温暖之地
2015-12-04吴琪
吴琪
似乎有一种说法,将英国人的拘谨古板归结于阴沉沉的、难以明媚的天气。可是如果你去探访一下英国人西边的邻居,就会对这种说法充满怀疑。爱尔兰的天气古怪多变,爱尔兰人最喜欢拿来开涮的就是他们湿润多雨的天气,海洋吹来的气流带来雨云,使得这儿一年里晴空万里的日子寥寥可数,地上似乎总是没干过。这样的地方总该带着雨伞吧,可是人们会告诉你,带了用处不大,因为大风随时会把雨伞吹翻。于是你见到雨中的街头百态十分动人:人们该打球的打球、该散步的散步,该去小酒馆的就去小酒馆,路上见到了慢慢寒暄。雨水只是最无关紧要的背景,并不妨碍人们乐滋滋的生活。
郁郁葱葱的翡翠岛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与中国的重庆市面积相当,其中7.02万平方公里为爱尔兰共和国,剩下地区为英属北爱尔兰。岛屿面积实在不大,不过离开城市一点点,便能面对成片的绿地以及浩瀚的大西洋边连绵的悬崖,使它的景象显得荒凉辽阔。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城市风味明显,多如牛毛的小酒馆以及活跃其间的爱尔兰音乐,让这里湿冷的天气有了暖哄哄的气氛。爱尔兰人生性浪漫,轻松幽默,可是他们的文学和歌谣里又浸染着沉重的忧伤。一种说法是,爱尔兰的神话传说如此丰厚迷人,是因为爱尔兰人喜欢逃避现实中的问题。如果进一步了解爱尔兰的历史,会发现这里处处可见奇特的矛盾:爱尔兰共和国的人口大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爱尔兰教士们却记录了欧洲最多的异教故事;爱尔兰人自豪于自己的凯尔特血脉,却大都不会说爱尔兰语。整个爱尔兰,挺像一部正在放映着的欧洲老电影:中世纪的古堡、成群牛羊、各有特色的本地佳酿、至今还活跃在人们头脑里的精灵鬼怪……历史和神话传说成为它的汁水,让这里风味浓厚。
神秘的《凯尔经》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爱尔兰岛是欧洲的尽头,四面被海浪隔绝,这儿的标志性景象多与荒凉诡异相连。这里是沼泽、荆棘、废墟、浓雾、峭壁之家,是矮仙和精灵的仙境。深受威尔士文学熏陶的托尔金在创作《指环王》时,其中的精灵族就是根据凯尔特传统中仙族的形象而创作的。爱尔兰岛也成为《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权力的游戏》等影片的取景地。莫赫悬崖、巨人堤有如开天辟地之时留下的原始景象。虽然与欧洲大陆之间被海洋隔绝,但这片岛屿上的人类活动痕迹远达公元前数千年,爱尔兰人将族源追溯到凯尔特人,始终强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
被称为“诞生于天使之手”的《凯尔经》(Book of Kells)成书于八九世纪之交,它是一册以“岛屿大写体”抄就的拉丁文福音书。虽然文字内容并无特别,但是装帧的奢华精美使《凯尔经》成为人类创作的最出色的手稿之一,这部经书标志着凯尔特传统艺术最高成就,是爱尔兰人骄傲的民族象征。今天旅行者们探访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个热门目的地,就是去圣三一学院一睹《凯尔经》真容。
圣三一学院位于都柏林市中心,这所建于1592年的古老大学,有着充满魔幻色彩的著名图书馆,电影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曾在此取景。159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为“教化”爱尔兰而参照牛津、剑桥大学模式兴建三一学院,三一学院成为爱尔兰的第一所大学。从外表上看,图书馆是一栋朴实敦厚的长方体建筑,走进二楼的“长厅”(Long Room),这里却出乎意料的高大开阔。两侧大型的木质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七八米高的穹顶,20多万册古老图书散发着幽静沉重的气息,让人不由得屏住气息。“长厅”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室图书馆。圣三一学院的图书馆是英伦三岛的四大版权图书馆之一。从1800年开始,每个出版社的每一本合法英文出版物,这里都会收藏一本免费缴送本。直到现在,这里每周都能得到1500多种刚刚出版的书、杂志、音乐集、报纸等等。

2011年5月,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爱尔兰期间在圣三一学院观看《凯尔经》
图书馆一楼展出的《凯尔经》,则是这里的镇馆之宝了。“你可以在其中凝视圣洁瑰丽之物的面庞,以奇迹的方式呈现;亦可以凝视福音书作者神秘的肖像,一忽儿生有六翼,一忽儿是四翼或双翼。你将在这里看见鹰,那里看见牛犊。这里是人类的面孔,那儿是狮子脸……如果你只是漫不经心地随便扫上几眼,你会认为它们是信手涂鸦,并非精心构绘。当一切皆极尽精细,你就见不到精细。但若你肯花费心思仔细看,用你的双眼洞穿其手艺的秘密,你会注意到这般有趣的细节,这样精致而微妙,这般紧密地簇拥交织,彼此拥叠,色彩如此栩栩如生,你将毫不犹豫地宣称:这一切绝非出自人类之手,而是天使的杰作。”这是《海波尼亚地形志》的作者、12世纪编年史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1184年在爱尔兰目睹《凯尔经》真容后发出的感叹。
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即使不具备任何宗教知识,光是看到色彩考究、图形极为繁复精密的《凯尔经》,就会惊叹于中世纪僧侣的艺术修为了。很多人在见到《凯尔经》真面目之前,以为这套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经书是个大部头。可是真正的《凯尔经》尺寸只有25厘米×17厘米而已,封面略大,也不过33厘米×25厘米。如此繁复和多彩的图案仅仅画在小巧的牛皮上,制作者的艰辛可见一斑。
制作《凯尔经》的僧侣们,居住在苏格兰西海岸外一个长5.5公里、宽2.5公里的弹丸小岛上。中世纪的书籍极为昂贵,因为需要用若干牛或羊的皮制成。拥有一份精美的手稿不仅为修道院的名声增光,还可以通过吸引参观的香客和学习的僧侣赚取收入,甚至得到慷慨的领主捐赠土地。据估计,《凯尔经》的340页牛皮纸至少取自185头小牛犊。这些牛皮还得用青柠汁或粪水浸泡后去毛,所以如果经书的制作时间紧张,所需小牛犊的数量可能数以千计。
那个年代更为困难的是对高级颜料的获取。在《凯尔经》的旁边有若干个小圆盒,里边展示着经书里颜料的来源。最为昂贵的深蓝色以天青石制成,而那个年代只能从阿富汗东北部的一处矿源获得。白色来自白铅和白垩;紫红来自地中海染色巴豆;有些颜料来自特殊的植物;据说一种特殊的胭脂红还得从一种珍奇昆虫怀孕的雌体中萃取。2009年制作的动画片《凯尔经的秘密》中,可以窥见僧侣们制作经书所需的磨练。

圣三一学院图书馆
从8世纪开始北欧海盗就沿着海岸线一路烧杀劫掠,尤其瞄准了没有城堡和军队保护又积聚了相当财富的教堂和修道院。这些异教徒对宗教毫无敬畏之心,将制作精美、耗费财富的经书也作为掠夺对象。《凯尔经》是中世纪经书艺术的一种代表,并且因为幸运地免遭维京海盗的掠夺或毁灭,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国宝。
在11世纪初,《凯尔经》和装盛它的匣子曾被偷走,小偷却干了“买椟还珠”的事情,拿走镶嵌珠宝的匣子,随手扔掉了经书。所以尽管匣子再也没有下落,这部珍贵的经书却保留了下来。
《凯尔经》的图像学融汇了基督教圣像传统与更古老的凯尔特民俗纹饰。所有首字母都被抽象成缠绕的花枝,纹路中又填满更细的纹路,有些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并且几乎没有一个首字母的图案是重样的。虽然中世纪的经书抄写员和画家的生活比较清苦,可是看到这些艺术性极强的创作,又让人感慨于他们内心藏着多么五彩斑斓的图景。直到今天,《凯尔经》里独特的纹饰,仍然是爱尔兰艺术家汲取创作灵感的来源。
文学大师出产地
比《凯尔经》更能体现爱尔兰特色的,是它出产的世界级文学大师。一个极少出远门的人与爱尔兰发生关联,最有可能是因为文学。在这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岛上,詹姆斯·乔伊斯、约翰·巴特勒、叶芝、奥斯卡·王尔德、萧伯纳等文学大师星光闪耀,以至于人们说:“爱尔兰对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与其幅员和人口是不成比例的。”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街景
文学大师在这里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都柏林的街头不时可见乔伊斯的身影,在市中心的伯爵北街,矗立着乔伊斯的雕像,他头戴宽檐帽,手持拐杖,有些玩世不恭地目视前方。当地人亲切地称这尊雕像为“手持拐杖的痞子”。6月16日是布鲁姆日,这是《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在都柏林街头游荡的日子。每年6月16日,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的乔伊斯“粉丝”会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布鲁姆日恐怕是世界上不多的以纪念一部艺术作品为目的的国际节日。
岛国偏居一隅,历史上的爱尔兰长期是移民输出国。发生在1845~1852年的爱尔兰大饥荒,使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口锐减近四分之一。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提供援助,经由一些爱尔兰港口转运的粮食也没有用来缓解饥荒的蔓延。除了因为马铃薯疫病而死去大量人口外,这次饥荒中约有100万人逃离爱尔兰,去海外谋求生存。大饥荒惨剧成为激发爱尔兰人更坚决寻求民族独立的一次大事件,在长达几百年的数次起义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国最终于1922年独立。爱尔兰在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在坚毅地寻求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文学最终成为他们最为举世闻名的一种标识自我的方式。
为了生存或发展,不少爱尔兰人年纪轻轻便离开家乡去英国或欧洲大陆,甚至美洲、大洋洲,一辈子只能在心中怀念“亲爱的老爱尔兰”。如何界定爱尔兰文学或爱尔兰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容易,因为不少作家大部分时间远离故土,比如乔伊斯,可是他们又毫无疑问地成为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
最能代表爱尔兰文化特性的作家,非叶芝莫属。叶芝早年的《凯尔特薄暮》,用诗人的笔法将爱尔兰民间传说、乡野故事娓娓道来,仿佛他刚刚从爱尔兰传统的“幻视”奇境中神游归来。叶芝早期诗作大多取材于凯尔特神话,试图以象征主义的艺术技巧构建一个超验的爱与美的世界。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叶芝因为他的浪漫主义诗作闻名,但是从叶芝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变化来看,浪漫主义只是诗人某个侧面的素描而已。

爱尔兰街头的詹姆斯·乔伊斯雕像
叶芝虽然主要是在都柏林和伦敦度过童年,他心中的故乡却是儿时经常度假的斯莱戈(Sligo)。斯莱戈郡位于爱尔兰共和国与英属北爱尔兰接壤处,如今作为叶芝的故乡和长眠之地而闻名。叶芝兄妹们在长假里拜访外祖父的房子“梅维尔”(Merville),这给他留下了一生绵长的影像。那栋房子“如此宽敞,总有房间可以躲藏”,一匹红色的小马跟着他,有一处花园可以溜达,还有两只狗身前身后地跟着他。叶芝的弟弟杰克作为爱尔兰最有民族代表性的画家,也终生对斯莱戈念念不忘。斯莱戈镇上有着迂回错综的安静街道,卡拉沃格河却放声喧哗,这里满是18世纪不规则的房舍和教堂,船只进进出出的宽敞港口边,四周围绕着起伏的田野和光秃秃的山巅。
今天走入斯莱戈镇,镇中心伫立着诗人神态洒脱而略为不羁的青年时期雕像,叶芝侧着脸庞望向左前方的中年时期画像,则挂在主路边高达几米的房屋墙壁上,十分显眼。一些有年头的餐厅或酒吧的门口贴着:“叶芝曾在这里讲话。”
“我将动身离去,前往因尼斯弗里岛/在那儿造间小屋,用树枝和筑泥/我要支起九排豆架,搭建蜜蜂巢/独自在林中空地聆听蜂鸣……我将动身离去,只因每日每夜/我听见湖水低声轻舔着湖岸;/当我站在大路上,或是灰色路缘/我听见它,在深深的心之内核。”叶芝早期的诗作《因尼斯弗里湖岛》,描述了一幅远离尘世的静谧景象,这座斯莱戈郊外的小岛成了爱尔兰文学中的著名岛屿,引得人们慕名前往。叶芝也将斯莱戈作为他最终的安息地,不大的教堂墓园里,叶芝的墓碑简朴干净,并不比周围乡邻们的惹眼,墓志铭上写着:“向生死投下冷眼/骑士们,向前。”
斯莱戈的田园和山丘给叶芝留下来丰厚的情感滋养。“马车上的鱼篮嘎吱作响/满载渔获到斯莱戈小镇出售/当时我的幼小心灵毫无裂痕/童年时带着鱼竿和假绳/我是区区小虫,我爬上磅礴的山脊/在那里消磨漫漫夏日。”叶芝早期的浪漫主义和神秘色彩显得轻盈奔放。但是随着逐渐卷入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再加上中年时期十余年的戏剧创作及舞台导演工作,叶芝更加关注客观世界发生的事情,作品创作逐渐走向现实主义风格。
诗人与民族认同
1889年,23岁的叶芝在贝德福公园的寓所接待了拜访者茅德·冈。根据诗人事后回忆,阳光洒在园中的苹果树上,而那位站在窗边的陌生女子面如春花,肌肤白皙胜雪,空灵宛如身后的花朵枝桠。叶芝从此陷入了伴随大半生的求而不得的恋情。

爱尔兰诗人叶芝
据朋友说,在陌生人面前的叶芝端庄而正式,有时会显得冷漠,藏在过度自矜的面具后面。在他喜欢并了解的人面前,他则比较放松,滔滔不绝。叶芝的一言一行总是带着彬彬有礼的味道,他签署支票或是穿上大衣的方式,都有一种慎重、一种几近教会的仪式性。“说到生活,我们的仆人会伺候一切。”他说。
都柏林流传着不少叶芝古怪行径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他向艾比剧场管戏服的女士借了一把剪刀,把他一件崭新的羊皮大衣剪了一半下来,就是为了不愿惊动一只趴在大衣上睡觉的猫。叶芝事后解释说:“那只猫正在神游太虚,如果把她叫醒非常危险。”
而年轻美貌的茅德·冈身上有一种炙热暴烈的反抗精神,她不仅反抗自身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英国陆军上校,母亲是一名英国侍女,更是积极投身于要把爱尔兰从700年的英国统治下解救出来的事业。茅德·冈热衷于暴力抗英,对于叶芝的追求,她说道:“他是一个像女人一样的男子,我拒绝了他,将他还给了世界。”叶芝不赞成平民的暴力革命,希望保持一个有产精英统治的社会,但也不满城市化对传统的侵蚀。叶芝笔下的爱尔兰精神特质,或者说叶芝自己的精神特质,称颂简单、宁静、自足、充满敬畏和神秘的生活。尽管叶芝并不懂爱尔兰语(与绝大多数爱尔兰人一样),但他的作品从爱尔兰的传统中吸取养分,他塑造的爱尔兰特质加强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叶芝被民众视为爱尔兰传统的代言人。
1902年,叶芝与格雷高利夫人合作的独幕剧《胡里痕的凯瑟琳》在都柏林的艾比剧院上演,轰动一时。爱尔兰的传说中,这个命运多舛的民族总是由一个可怜的老妇人象征,胡里痕的凯瑟琳便是这些形象中最著名的一个。她是爱尔兰母亲的象征,号召民族之子献身于对她至高无上的爱。
这部戏剧的巨大影响力让不少志士为浪漫的理想慨然赴死,而叶芝晚年每念及此,总是悔恨与疑惑交加。他事后描述复活节起义——“一种恐怖的美降生了。”对于自己的戏剧在革命理念中发挥的深刻影响,他发问:“现在我已老朽,疾病缠身/彻夜难眠/面对一个问题/却从未找到答案:/我的戏剧是否把人们/送向英国人的枪口?/我说过的话可有/挽救那家园沦为废墟?”
如今游览都柏林,无论是参观圣三一学院还是都柏林城堡,都绕不开爱尔兰与英国在历史上漫长的恩怨。比如英格兰的约翰王在13世纪初下令建造了都柏林城堡,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中,都柏林城堡成为历次起义的首要打击目标,因此成为爱尔兰人民族独立的象征。都柏林城堡里记录着爱尔兰人争取独立的艰辛过程,包括因为起草爱尔兰独立宣言而被英国人残酷杀害的七勇士,其中一位正是茅德·冈的丈夫。这里也记录着两个国家和解的过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11年访问爱尔兰,成为爱尔兰独立后首位到访的英国君主。

考尔德在他的罗克斯伯工作室
不过历史的沉重并不影响爱尔兰人乐观幽默的天性,嗜酒如命、巧舌如簧,即使一贫如洗也成天乐呵呵,这就是传统爱尔兰人给人的印象。爱尔兰人的口才颇有名头。这或许是因为它曾经长期作为一个交通不便的农业国,人们有大把时间一起消磨,尤其在夜晚和漫长的冬季,家里寒冷,大家喜欢聚到温暖的酒馆里长谈。这有点像咱们广大的东北地区,漫长的冬季使得人们长于唠嗑,滋生出了“二人转”和赵本山式的幽默。这样松散的气氛,让来访的人感到舒坦自在。人们豪饮着啤酒或啜着特色佳酿,醉心于诗歌和民谣,古老的诸神和精灵仍然活跃在人们的意识深处,注视着他们引以为豪、从未被割断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