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宇宙与天下——对当下科幻文学的一种考察
2015-12-02王冰冰
王冰冰
科幻文学近些年在中国的兴起与火爆,无疑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对于崇尚实用理性,科学意识、逻辑思维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中国而言,在科幻想象力方面的贫瘠原本是情理之中,中国电影在科幻这一类型上的缺失与尴尬便是最好的证明。因此科幻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勃兴不能不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刘慈欣、何夕、刘晋康、韩松等重量级的科幻小说家相继出现并大放异彩,实在是新世纪中国文坛上的惊喜甚或奇迹。其中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堪称中国当代文学界而非仅仅是科幻文学界的巨大收获,其内蕴之深厚,思想之深刻,想象之卓绝使其早已跃出通俗文学的行列,而具备可以与当下最为“精英”的文学文本一较高下的的实力。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科幻文学奇迹似的飞跃与当下中国“大国崛起”的时代转型之间似乎出现了某种颇具意味的呼应与互动,那么科幻文学的异军突起是否得益于特殊的时代契机,其兴盛是否包含着某种特定的时代内涵及意识形态症候?
一
王德威在评价晚清时期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潮流时,认为其间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是阐明了当时人们的政治愿景与国族神话(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自晚清以降,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如列文森在他的《儒教中国及现代命运》中的洞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代读书人面对近代化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经历的所有痛苦的思想蜕变均可以概括为放弃“文化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以期“在‘天下’的失败中夺回‘国’的胜利”(参见张旭东:《批评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6-177页)。从《新石头记》(吴趼人)、《月球殖民小说》(荒江钓叟),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晚清的科幻小说记录了这一历史轨迹与时代变局。此后中国对启蒙、现代及革命的自觉追求,都可以概括为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孜孜以求。而“天下”,则成为不得不抛入历史忘怀洞的、过时的“冗余物”。但成为时代“冗余”的“天下”却注定化身历史的“幽灵”,不停地试图回返,而其内部的革命能量也许并未耗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今日的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开始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间最为重要的是人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跨国化”或曰“全球化”趋势。在这日益全球的世界上,民族国家这一几个世纪以来坚不可摧的“想象共同体”似乎开始出现式微的颓势。一方面,资本不断加剧的多元中心及多国运动,创造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日常经验。在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面前,民族国家的权力似乎遭到了空前的削弱;另一方面。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却仍然牢牢依附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法律及政治基础(参见张旭东:《批评的踪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79页)。尤其体现在美国及西方强势国家仍然是资本全球流向的实际掌控者。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大国崛起”及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变化,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思考与启用“天下”与“天下体系”概念,这一定程度上是出自于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及“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的某种纠偏。对于“天下体系”的重新阐释的行为无疑暗含着对于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批判与对传统中国天下观合理性的论证,同时也成为“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的普适性思想实践。(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与此相应,对于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反思及对于全球化的批判,也出现在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中,在刘慈欣与王晋康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典型,这不能不说是发生在文化、文学及社会文本之间一次颇有意味的“耦合”。不同于刘慈欣在《三体》系列中一心构造“宇宙社会学”的野心,刘晋康的作品始终立足于“地球”与“人类”,可以说他以科幻的方式涉及了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构造“中国”认同的文化/政治议题。在他的长篇《生死平衡》中,王晋康在文本世界中复现与改写了发生于上世纪的伊拉克、科威特间的民族冲突与战争,让一个来自中国的落拓不羁的“江湖游医”介入这一场实际上由美国暗中操控的“石油之战”,且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平衡理论”彻底打败了蓄谋已久的现代“细菌战”,以此寻求中国文明与历史的独特性及主体性的表述。而在《格拉朗日墓场》中,面对着美国特工对于地球的叛卖,人类重新陷入核威胁的阴影这一危局,千钧一发之际是身为被劫持飞船船长的中国人鲁刚,率领他麾下的一群第三世界船员,毅然将载满核弹的飞船驶向太阳,用生命拯救了地球。可见刘晋康更为关注的是当下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世界上重新确立更具尊严性与崇高感的民族身份这一问题。他用戏剧化的方式将中国“主体”幻想置于文化的中心,在文本内部思考着第三世界民族未来的道路与前途。可以说在世界文化将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崛起的中国及第三世界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紧张地探索自我、他者与世界的过程,被当下的科幻小说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留存下来。面对当下发生的诸多政治/文化震荡,无论是持“文化自觉”论的学者,还是科幻小说家,都乐观地相信中国的文化转型将会对世界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批判西方中心的知识/权力系统的同时,重申中国的主体立场及文化策略,很大程度上应对着当下中国“大国崛起”这一现象。
在当今“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在变幻的国际环境中重新确认中国的主体位置,在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或主体空间的关系中,既不重复西方民族国家的霸权逻辑的同时彰显中国的主体性,“天下体系”已然成为建构合法性表述的一种文化资源(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刘慈欣在《人和吞食者》中曾借主人公之口引发对于“文明”的思索:“难道生存竞争是宇宙间生命和文明进化的唯一法则?难道不能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内省的、多种生命共生的文明吗?”而一种多元共生、更具包容性的文明体系无疑暗示着一种区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与帝国主义逻辑的主体立场与话语策略,为重新思考地球及全宇宙的生存伦理秩序与政治哲学思想提供空间与可能。而“天下”体系所尝试建构的正是一种包容族群多样性的实践样态,强调其内在的非均质性和多样性,以及如何造就一种多族群的平等关系这一政治构想。其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内部的历史与现实政治问题,还尝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构建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形态,从而可以成为引导当下全球秩序的乌托邦理想(参见贺桂梅:《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可以说当下科幻文学立足“宇宙”视角展开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及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与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与体系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耦合。
二
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其影响是全世界的,其间必然带出后冷战式的政治冲突,以及地缘政治的博弈,这一切也在科幻文学创作中有着症候式的显影。正如王晋康、何夕及刘慈欣都曾在小说的虚构场景中设想已霸权旁落、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对于新崛起的亚洲对手们的妒忌与防范。而在《三体》中,对于宇宙中“黑暗森林”法则的发现及宇宙社会学的建构无疑是最具想象力的段落,它带给读者惊心动魄的心理体验与智识挑战。那种彻骨的黑暗与残酷,令深谙“弱肉强食”这一丛林法则的人类相形见绌。但这样的关于宇宙最为黑暗绝望的想象,是否只是出于作者对于人性的失望?或者说黑暗森林的宇宙社会学是否只是“弱肉强食”的某种外太空加强版呢?《三体》虽然是立足宏大的宇宙视角,展开想象的翅膀,但不难发现其间潜藏的对于二十世纪诸多困局与悖论的思考。
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无法忘怀的历程,二十世纪是充满极端的暴力、恐怖、血腥,又充满希望、洋溢激情的特殊而奇异的时代。在《三体》中不难辨认出一种对于集体主义、强力政治回归的倾向,由此带出对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刘慈欣笔下的男性政治家们,无论是面壁者、执剑人罗辑,还是劫持星际舰队的章北海,都是一些强悍的、野心勃勃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性政治家或阴谋家。在面对强敌之时从不抱任何幻想,时刻准备着与敌玉石俱焚,他们强大的行动能力超越了多愁善感的道德。在刘慈欣看来,正是他们而非代表着爱与母性的程心才是地球及太阳系真正可能的拯救者。从他们身上,不难发现二十世纪那些曾震惊世界的革命家甚或集权者们的某些特质,那种在今日的“小时代”中踪迹难寻觅的强力、铁腕与远见。而作为“圣母”与人类最后希望的程心,在这些充满独裁者特质的男性身旁,却总是显出难以掩饰的苍白乏力,甚至她的妇人之仁不止一次地将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作为一部看似天马行空的科幻巨制,《三体》同时提示着着后冷战的困境,不露声色地彰显着那种经历过二十世纪的人类所不得不背负的徒然而沉重的遗产。正如在《全频道阻塞干扰》当中,刘慈欣在虚拟的未来美俄决战中,在科幻外衣下让交战双方回归最为原始的“肉搏”,不禁令读者回忆起前苏联卫国战争的悲壮惨烈,回忆起俄罗斯民族曾经为世界和平付出的巨大牺牲。其间刘慈欣这一代人对于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热爱、缅怀与哀悼,渗透在字里行间。而在《三体》中,面对宇宙强敌之时,大国间在联合阵线之下的隐形博弈,三体世界与地球之间基于宇宙法则形成的危如累卵的威慑平衡,都不难发现冷战的阴影与幽灵在暗自徘徊。对于人性弱点、政治内幕洞若观火的刘慈欣,怀抱着二十世纪的英雄主义情怀,拒绝一切田园诗般的浪漫与憧憬,而宁愿在“黑暗丛林”中选择一条用血污与残骸铺就的道路,试图用最后的冷酷来结束人类社会的一切冷酷。

应天齐《砖问——应天齐当代艺术展》海报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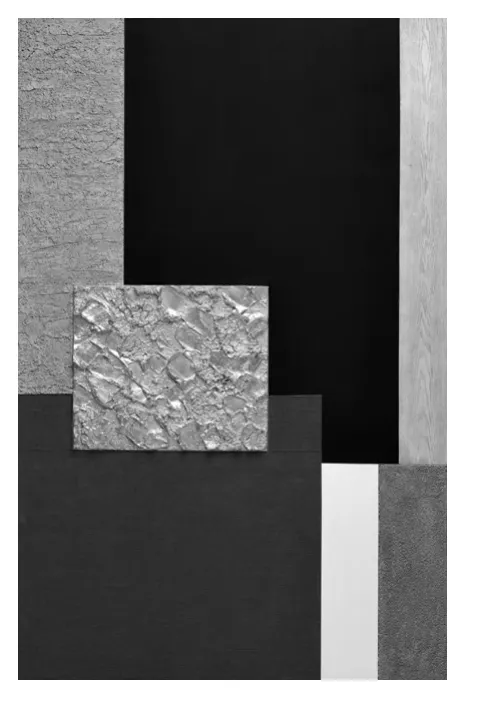
应天齐-《长安街之四》 综合材料 190×122cm2015
相对于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洞察与揭示,当需要建构一个全新的“宇宙”或曰“乌托邦”时,无论是哪一位科幻作家却都显示出某种力不胜任的无奈与乏力,即便深刻博大如刘慈欣也是如此,以致于在《三体》系列的终篇他只能将拯救的重任搁置于程心单薄的肩上。也许在宇宙经历归零重生之后,在一张白纸般的无辜世界,母性、爱、圣洁与无以伦比的责任感终将获得用武之地。詹姆逊在《乌托邦作为方法或未来的用途》中所说:“乌托邦不是一种表征,而是一种作用,旨在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超越这种局限,我们似乎再不能想象我们自己的社会和世界的变化。”(詹姆逊等:《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第78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想象力的匮乏正是后冷战情境的无意识流露。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共产主义理想及社会主义实践在全世界经历巨大的挫败及被持续地“污名”,人类从此不再试图触摸与思考任何宏大的命题,乌托邦视野已然闭阖与消逝。在这个意义上,今日科幻文学的勃兴也许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虽然微弱却可贵的希冀与可能,在一种新的历史/现实视野中重新想象与建构世界、宇宙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