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生活是诗的土壤,诗是我的生命”
2015-11-30叶介甫
● 叶介甫
臧克家:“生活是诗的土壤,诗是我的生命”
●叶介甫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孙荃、何嘉。臧克家1929年发表处女作,著有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诗论集等50多部。他的诗,富有时代精神、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在艺术表现上,朴素、精练、含蓄。
童年生活是诗的摇篮
臧克家曾说:“如果说,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极大的影响,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山东诸城西南的臧家庄,是臧克家的故乡,他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8岁时,他的生母便去世了;父亲是个神经质的人,仁慈、多感、热烈,感情同他的身躯一样纤弱,特别喜欢诗。臧克家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听父亲用抖颤的几乎细弱无声的感伤调子,吟诵着他同臧克家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
臧克家的祖父是一位板着铁脸,终天不说一句话的人,没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长恨歌》《琵琶行》。他的声音使臧克家莫名其妙地感动,他诗的热情燃烧着臧克家幼小的心灵。臧克家在《自己的写照》集子中曾这样回忆:“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
臧克家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而巧嘴的人,富于文艺天才。她常讲《聊斋》《水浒》《封神榜》《西游记》给臧克家听,还有那些仙女和凡人恋爱的富于诗意的故事……常引出臧克家的眼泪和幻想,像在心上打下深深的印记。
那时节,臧克家还不了解诗,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他蒙昧的心。
臧克家还有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六机匠,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是臧克家家里的佃户,也是远房的亲戚,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圣手,记忆力强,描绘能力也强,能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叶鲜枝地送到你的眼前来,好像展开一幅图画。他说故事往往用韵语和腔调唱出来,伴同着表演般的神态和姿势。他是用热情,用灵魂的口来说这故事,以安慰自己和别人。故事,就是他的创作,诗的创作。听的人,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里去。在他的屋子里,臧克家认识了许多灵魂;在他的屋子里,臧克家得到了盎然的诗趣;在他的屋子里,臧克家熏陶出一颗诗心。
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臧克家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他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这些,你可以在他的诗的内容上、形式上,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那么鲜明耀眼的佐证。在多少枝笔下,臧克家成了“农民诗人”。他爱乡村,因为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他爱泥土,因为他就是一个富泥土气息的人。

青年臧克家
青春热血孕育出诗的萌芽
1923年,臧克家进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那时,统治山东的军阀张宗昌对人民实行文化统治和武力镇压。他残酷屠杀革命者,怀抱“张”字大令的宪兵队日夜在街上梭巡。张宗昌的文攻武压并没有吓倒革命的人们。臧克家所在的学校校长王祝晨是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学习蔡元培新旧共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学校成了新生力量的滋生地。臧克家所在班的同学们,几乎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下课以后,有的人到工厂去了,有的人到大门口给民众讲演去了,有的人开会去了……
在反抗反动黑暗势力的同时,同学们还组织了“书报介绍社”,那里面的书籍杂志那么多,那么全,令人爱不释手。臧克家这时期新诗读得很多,穆木天、冯至、汪静之、韦丛芜……然而,撼动了他整个灵魂的却是郭沫若。有很长一段时间,臧克家生命的脉搏跳动在郭沫若的字里行间。他崇拜郭沫若,他从一本杂志上剪下郭沫若的一张照片贴在自己的案头,上题:“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臧克家时常同二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让风吹撒开他们的头发,高歌狂吟,像立在理想的王国里,向不醒的人间吹送他们诗的“预言”。他们也时常在大明湖上飘荡,身子互相偎依着,听小船冲开残荷,唰唰有声。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大家一面饮酒,一面狂吼,发出高歌,声裂如磐之夜。
对反动军阀的满腔愤慨,促使臧克家给当时《语丝》的主编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过了不久,这封署名“少全”的信,连同岂明(周作人)的复信一起被登在《语丝》上,还被加上了一个题目《别十与天罡》。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
这时候,臧克家写下了不少的诗篇。他写得多,全凭自己的大胆!他写得快,因为自己事前既不作绸缪的苦思,事后又不下功夫删改。“灵感”是他的唯一法宝,它一动声色,就在纸上“走笔”。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模仿时期”。他读了别人的诗篇,仿佛那里边涵蕴着的感情原来在自己心上就存在着一样,立刻就兴奋起来,也想以同样的内容自制一首。
臧克家走上新诗创作道路的时候,他的族叔、诗友——臧亦蘧(笔名“一石”),给了他极大的影响。臧亦蘧有个脾气,见了不足与谈的人,沉默木讷,但和知心朋友在一起,则高谈阔论,插科打诨。在封建气味浓厚的农村,他卓尔不群,狂傲不羁,用奇特的怪论和行动抵抗封建习俗,因此,这位族叔得到了一个绰号“四癫”。他的诗,直抒胸臆,毫无顾忌。臧克家说:“不遇见他(臧亦蘧),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新诗。没有当年的他,就没有今天的我。”不管族叔臧亦蘧怎样怪,怎样“癫”,“他是形体,我就是影子。”臧克家如是说。
每次学校放假时,臧克家常常和族叔跑到僻静无人的林边、崖下,去对坐半天。有时话多得使双颊发烧,有时默默地半天无语,听风号,听虫叫,听大自然神秘的语言。在春天,也远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阳的返照下,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张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诗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被黄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心的小船在诗湖中摇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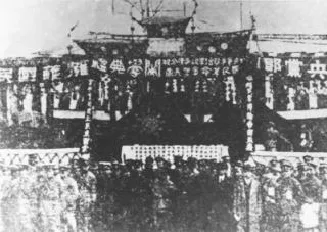
位于湖北武昌两湖书院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旧址
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明节,燕子新客似的刚刚从远方飞来,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灵感借了臧克家的手,在这个佳节的诗境里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中学生活还未结束,政治空气就变得更为紧张了。风传军队要来学校搜查,同学们半夜三更撬开地板,把所有带白话标点的书全部塞下去,用脚跺一跺,仿佛跺自己的心一样痛!信件、日记,仓皇中付之一炬。心,火一样地燃烧!
军阀反动统治的高压把臧克家和同学们仇恨的心磨锐了。恰巧,郭沫若的一篇新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落到了臧克家的眼底,给了他力量和希望。这样,投出“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的充满豪言壮语的一纸家书,臧克家便同几个朋友从寒冷中向着自由与温暖的江南奔去。
1926年的10月天,北国正是金风肃杀,万卉凋零,一片凄凉景色。而当他们踏上武汉的大地,却见大地一片葱绿,用青眼迎人,大家心里发问:“谁的手把宇宙割成了两片,南方是白昼,北方是黑天?”
1927年,臧克家考上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校址在武昌的两湖书院。大门两旁,一副对联“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字大如斗,震心耀眼。院内标语,引人注目,如革命鲜花,开满四壁。“今日的锄头,明日的自由”,这不就是鼓动人心的朴素的诗句吗?
索赔是一个既要求科学严谨,又要求艺术灵活的工程管理行为。索赔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标准答案,不同的人进行相同的索赔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由于索赔工作对施工企业的经济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索赔人员应注重知识的综合运用,不断学习、总结,将索赔工作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提升工程管理水平,为企业谋求更好的经济效益。
革命的空气像高涨的洪潮,严肃的生活刻苦而又紧张。这时节,臧克家的生活就是一篇雄伟悲壮的诗。
臧克家亲眼看见过人民伸出他们的巨掌,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吓倒了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了汉口英租界。臧克家亲眼看见过北伐誓师,十几万壮士用有力的步子走过阅兵台,歌声,那么整齐嘹亮,威武雄壮!一个铁的自信心,做了歌子和口号的内容。
多少伟大的场面,开拓了臧克家的眼界和心地。多少“巨人”的呼喊、行动,使得臧克家感到个人的渺小。理想的远景真灿烂,事业的担子真重!
臧克家曾经一身戎装立在黄鹤楼头,望着汉阳兵工厂的烟囱作豪迈的诗思(“像一支时代的喇叭吹向天空”);他曾经立在大江的岸上戍卫着森严的黑夜,隔江就是敌人,萤火闪耀着神秘恐怖的光,江潮像大时代的呼吸,又像自己的心一样不平地鸣吼;他曾经以天地为庐舍,野草做被褥,钢枪做枕头,露宿过多少夜;月光的天灯照着他们急行军,去包围敌人;稻田,一方方明镜似的偷描着山影、树影和时代的先锋——战士的身影。追击夏斗寅叛军,40天的“前敌”,飞过山,趟过水,在枪炮声里,在嘶喊声里,在呻吟声里,在风里、雨里、血泊里,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接近,一个铁的意志在执行。时代的大手在臧克家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革命画卷,臧克家,没有用诗句,却用子弹,做了战斗的一员!
臧克家并不责难自己这一时期没有留下诗。在这伟大的几年间,臧克家蓄积了无数的生活宝贵经验——诗的最有价值的材料。学习写诗不仅仅是技巧的磨炼,还应钻进人生的深海里去。技巧不过是诗的外衣,生活才是诗的骨肉,单从技巧上去求诗,你将永远得不到诗。
臧克家用生命去换诗,去写诗!

闻一多

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
诗,在生活的土壤中
1930年,臧克家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在这之前,他经历了革命失败的悲愤痛苦,逃亡生活的艰辛磨难,更加了解了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因此,在入学考试的作文《杂感》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他的恩师,著名诗人闻一多,正是从这一节《杂感》中认识了臧克家。臧克家向闻一多借来了《死水》,一读就入了迷,佩服得五体投地,大有对于一位令人心折的人物相见恨晚的心情。
闻一多的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读着它,仿佛能看见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热爱自然的炽烈的血心。
闻一多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严谨。他的诗,在技巧的磨炼上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浮浅的“自是”心,拉回乱放的野马,觉得新诗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因此,读了他的诗,臧克家把自己的一本过去的习作交给了火。
读了《死水》,臧克家觉得,过去自己像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今天,自己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他向闻一多和他的诗学习着怎样想象,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在以前,臧克家不知道什么叫想象,知道了,也不会用它。抓住第一个跑到自己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宝贝似的不放松,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隐喻、形象上去了。而不知道打开心门,让千千万万个想象飞进来。之后,苦心地比较着好坏,像一个吝啬的女人和一个小气的小贩把一个铜板作为这场买卖成败的关键那样认真地计较着。然后,用无情的手把所有的想象都赶出去,只留下最后的一个。因为,没有插着翅膀的想象,会永远把你的诗拖累在平庸的地上。
臧克家曾说:“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决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意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佛罗贝尔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写诗的青年都不应该看轻它。”这时候,每得一诗,他便跑到闻一多的家中去。这时他们像师生,又像朋友一样地交谈着。闻一多指点着臧克家这篇诗的优点、缺点,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些字下得太嫩。有一个暑假,臧克家把《神女》这一篇诗的底稿寄给闻一多看了,其中有一个句子臧克家最喜欢。闻一多的复信来了,臧克家心上的那个句子“记忆从心头一齐亮起”,果然单独地得了那个红圈。臧克家不禁高兴得狂跳起来。
臧克家拼命地写诗,追师,他的生命就是诗。推开了人生的庸俗,拒绝了世俗的快乐,他宁愿吃苦。看破了世事人情,臧克家才觉得事业是唯一“不空”的东西,它是一支精神的火炬,虽在千百年后也可以发热发光。一切皆朽,唯真理与事业同存。
臧克家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都是在不吐不快的情形下一字字、一句句地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他觉得仿佛天下的苦难都集中于一身,肚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像雍塞的淤泥。被压迫、被侮辱地生活在最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形象,乡村的大自然风光,地主官僚的丑态,一齐在臧克家心中鲜亮了起来,用它们的颜色,它们的声音,它们要求表现的希望打动他,鼓舞他,刺激他,使他把曾经看到过的,感受过的,统统化作诗。诗,是心头火焰的一个喷射口。
这一时期,臧克家写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这黑暗角落里的零零星星。臧克家正眼在瞪着人生,然而没抓住大处、要害处,只抓住了这一星点。虽是这样,然而,在象征诗风吹得乏力的时候,这也是能照耀现实生活的一盏小灯,给了黑暗中的人们一点光亮,一股生活的力。
1933年,诗人卞之琳在北平自费印了他的《三秋草》,他鼓励臧克家印一本诗集,臧克家便把新旧作品挑选了一下寄给了卞之琳,诗集取名《烙印》。闻一多为诗集写了序言,诗集式样、印刷等,一切全托给了卞之琳。闻一多、王统照及另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一次印了400本,这样,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
《烙印》出版不久,茅盾、老舍、韩侍桁诸先生在《文学》《现代》等杂志上写了评介文章,这给了臧克家很大的鼓舞力量。于是,他这个为新诗呕心沥血多年的文艺学徒,以“青年诗人”的头衔,与艾芜、沙汀等另外5位同志成了“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

抗战时生活在重庆的年轻诗人臧克家(前排右一)
这样,臧克家找到了“自己的诗”——也就是说,臧克家多年的血汗苦心终于铸造出一个结果——“风格”。
战斗的生活,痛苦的磨难,叫臧克家用一双最严肃的眼睛去看人生,并且以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生活,以强烈的火一样的热情去拥抱生活,以正义的界线去界开黑暗与光明,真理与罪恶。
臧克家找到了“自己的诗”,走了新诗的道路。他感慨地说:“这得要感谢家庭的熏陶、朋友的帮助、恩师的指点。然而,更重要的,这得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是诗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