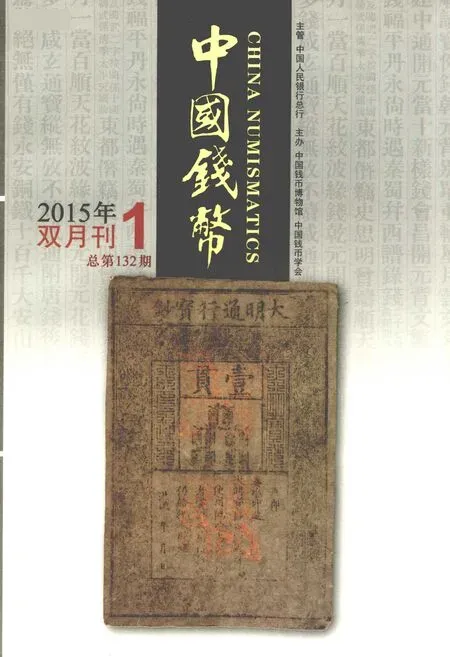地方志所见明末清初云贵地区钱币铸行
2015-11-27刘舜强袁凯铮
刘舜强 辛 岩 袁凯铮
地方志所见明末清初云贵地区钱币铸行
刘舜强辛岩袁凯铮
由于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财富的功能,铸行钱币是我国古代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其统治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更成为统治者政权合法性的象征。相比于中原,云贵地区略显偏远,地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以贝为货币,这不但见于地方文献:“昔日多用贝,俗名曰贝巴子……古者货贝而宝龟,至周而有泉,至秦乃废贝行泉……汉时钱贝并行……”①,还得到了一些学者更为详细论证,并证实直到明天启年间才几尽废止②。目前,对于明末清初时期云贵地区钱币的铸行状况还未见有人专门进行过系统整理,现以该地区这一时期的地方志为主要来源,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 地方志记载
查云贵地区方志,发现有关明末清初铸钱的文献很少,仅有一些零星记载,现摘录如下:
(1647年,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流寇至滇,沙定洲杀王锡衮以其众遁。张献忠死,其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走贵州。闻定洲据滇,诈称焦夫人之弟,以兵援黔国,屠平彝、交水、曲靖……可望知定洲走,即由宜良赴省,追各官印,铸大顺钱,设四城督捕,禁民问。行不窃语,夜不张灯,犯者族③。
(1647年,顺治四年)四月流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入滇,沙定洲遁走。初张献忠死,余党可望等入贵州。闻定洲据滇,诈称援黔国,兵屠平彝、交水、曲靖,知府宋文旦、知县陈六奇死之,执巡按罗国巘,声言预捣定洲巢,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怯,于十九日杀故詹事府正詹王锡衮于贡院,焚南城楼,遁走临安。滇民愤擒逆党阮韵嘉等送天波磔之。可望知定洲走,即由宜良趋省,追各官印,伪设四城督捕,铸大顺钱④。
(1647年,顺治四年)四月,本朝委知府萧元昭到任招安。初,张献忠死,余党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入贵州,闻沙定洲反,诈称援黔国兵入滇,知定洲走宜良趋省,追各官印,伪设四府,铸大顺钱,至 (1648年,顺治五年)戊子五月,艾能奇死,李定国擒定洲,孙可望以无名爵难以号召滇黔,闻明部院何腾蛟,瞿式耜等拥桂王子由榔,称号永历于粤西,遣人胁封可望为秦王,定国等素与可望不和,至此俞生怨愤矣⑤。
(1647年,顺治四年)可望、刘文秀、李定国与艾能奇皆僭称王,在籍御史任僎等又倡议尊可望为国主,可望遂置六部等官,以僎兼吏礼二部尚书,铸兴朝通宝钱,括近省田地及盐井之利,俱以官四民六分收取。各郡县工技悉归营伍,以备军资⑥。
(1649年,顺治六年)己丑,胡明桂王于肇庆称永历三年矣。孙可望称国主、千岁东平王。先铸大顺钱,至是,改为兴朝。修五华山紫禁城,大役民夫,人民死徙过半⑦。
(1651年,顺治八年)辛卯春,杨道来自粤西,出永历帝玺书,贼亦知跪读涕泣,传示滇南文武官,改年号,遵正朔,新铸永历钱,尊奉如宝,至是贼亦知有君也。未几帝颁诏,滇南并差官赍金,(1653年,顺治十年)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⑧
根据安龙出土的永历皇室墓志铭记载,顺治九年即永历六年,1652年,孙可望挟永历帝入贵州安龙,至顺治十三年即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随李定国离开安龙,前往云南曲靖⑨,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永历帝逃入缅甸,同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克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康熙元年十一月,1662年,吴三桂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
(1674年,康熙十三年)三月郭壮图开局省城铸利用钱⑩。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癸亥议于云南蒙自大理设局铸钱,巡抚王继文奏请蠲脩学校,振兴文教,正人心,以端风俗。诏许之。
二 各钱币铸行详情分析
综合以上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云贵地区政局十分动荡铸币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孙可望仅以张献忠大西军余部身份铸行了 “大顺通宝”钱,以东平王、“国主”身份铸行了 “兴朝通宝”钱,奉永历正朔铸行 “永历通宝”钱。此后,吴三桂政权铸行 “利用通宝”等钱。这几种钱币铸行有先有后,同时相互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大顺钱”
丁福保编撰的 《古钱大辞典》(以下简称 《辞典》)中有以下几条:
“顺治元年冬十月十六日,张献忠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悬顺民号帖,以大顺钱钉之帽顶。贼钱郭光润,精缀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贼下令,凡市镇民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
地方志中很多次提到顺治四年孙可望铸造大顺钱,但根据 《辞典》,大顺通宝原为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首铸;铸造该钱的原料主要为在当地收缴的铜器而非铜矿;制作精美并且似乎并没有通过兑换,而是通过直接发放的方式使其流入民间,要求民众必须佩戴在身。这种做法其实是利用铸造货币对其 “大西政权”进行政治宣传。顺治四年张献忠死后,其部下孙可望再次铸造大顺钱——这次铸钱的铸造规模应较小,因为紧接着其就又铸造了兴朝通宝钱。
2.兴朝通宝钱
地方志中所见的 “兴朝通宝”钱大部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只有一处所说为顺治六年。这与 《辞典》所说也不一致。后者这样描述:
“明史杨畏知传:永明王已称号于肇庆,而诏令不至。前御使临安任撰,议尊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三藩纪事本末:顺治四年,可望自称东平王,既至黔,设官铸钱。十四年,可望来降于王师”;“滇记:丁亥张献忠被诛于西兖,其义男孙可望率残兵由遵义入滇,三月至滇,遂由宜良入省。巡抚吴兆元等迎于郊外……任撰等倡议尊孙可望为东平王,铸钱曰兴朝通宝”。
由此,再综合地方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兴朝通宝钱的铸行时间有顺治四年和顺治六年两种说法,但 《辞典》中 《滇记》对孙可望铸兴朝通宝钱背景的描述,与地方志中对其铸大顺钱的背景几乎如出一辙,这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两种钱币的关系。
公元1647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确立了联明抗清的方针,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确立年号为 “兴朝”。而根据一些学者研究,孙可望在入滇后为了争取云南汉族官僚和土司的支持,确实废除了 “大西”国号,并许诺 “共扶明后,恢复江山”,而这是在其还未与永历帝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进行的,体现出孙可望对永历帝名望的利用。而为了保护民间贸易,在初入云南时便再次铸造大顺通宝钱,而后废除大西国号而改铸兴朝通宝钱,这也解释了文献中孙可望入滇后几乎同时铸造大顺钱和兴朝通宝钱的问题。
另据 《辞典》说,“此钱小钱径八分半,重一钱五分……。幕一分……此钱盖当十钱……重三钱八分……。幕五厘……此钱盖当五钱……重二钱六分……。幕工……此钱盖当二钱……重一钱四分……”。由此可见,虽然一些地方志中说兴朝通宝钱 “改自”大顺通宝,但此时的当权者孙可望远比之前的张献忠更重视新铸行钱币的经济功效——除当二钱外,还铸行有小平钱、当五、当十钱,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铸钱用铜供不应求的事实,但该钱铸行的真实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寻求支持。除此之外,兴朝通宝是典型的折银钱,是以铜作为银辅币的实例,是在白银广泛使用的背景下,货币流通领域以铜代银的现象。兴朝通宝的铸行,确立了清初折银钱体系,甚为重要。
3.永历通宝
关于永历通宝,《辞典》说:“三藩纪事本末: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孙。初封衡阳王,张献忠献衡州,王避于梧州。丙戌,总督丁魁楚等奉之监国。十一月,诸将立之,改元永历,以肇庆府为行宫,铸永历通宝。钱有大小二种,又有背上户字、工字、辅字、留字、督字、明字,背上下二星、背上定字又一星……”。
根据 《滇寇纪略》可知,永历钱应为南明桂王朱由榔铸造的 “永历通宝”。这条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永历通宝是顺治三年在两广地区首先铸行的,主要流通区域也在两广地区。其二,云贵地区的 “永历通宝”钱不同于两广地区的永历通宝钱,应当是孙可望 “改年号,尊正朔,新铸永历钱”。朱由榔于1646年 (顺治三年)十一月称帝于肇庆,因此永历通宝的铸造时间应在1646年11月之后。1651年 (顺治八年),孙可望拥永历帝,改正朔,在云贵地区铸造了 “永历通宝”钱,及至顺治十年,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其政权在云贵仍一直存在。
但是,实际控制云贵地区的孙可望和永历帝的关系一直不和:“(顺治)六年已丑二月孙可望要封永历”、“(顺治)七年庚寅七月,孙可望自称秦王”、“(顺治)八年,辛卯二月,孙可望自称国主”、“(顺治八年)三月,孙可望杀永历从臣严起恒、张载述、刘熹珍吴霖”、“(顺治八年)五月孙可望杀永历大学士杨畏知”、“(顺治九年)九月孙可望杀永历御史李如月”、“(顺治)十一年甲午二月,孙可望杀永历从臣十八人于安龙”;“(顺治十一年)六月,孙可望谋僭号不果,复如贵州”、“(顺治)十三年丙申三月,永历入云南”永历帝入滇是李定国一手导演,使永历帝从实际上逃脱了孙可望控制的安龙,这一举措得到了云南人民的热情响应,并将孙可望置于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顺治十三年)六月,永历招孙可望,不从”,而在这之后孙可望随后就于顺治十四年造反。根据地方志,永历政权铸行的永历通宝和孙可望铸行的兴朝通宝钱在时间上有重叠,同时前者对后者又有形制上延续的现象。不过,永历通宝集中铸行地区应在永历帝主要控制的两广,只有同兴朝通宝折银钱性质相同的背后为 “五厘”“壹分”两种永历通宝折银钱在云贵铸造。但永历通宝在云贵地区的流通状况远不如兴朝通宝钱,反映出清初十余年孙可望对云贵地区的实际控制
4.利用通宝、昭武通宝和洪化通宝
吴三桂进入云南后先后铸行了利用通宝和昭武通宝,其世孙吴世璠铸 “洪化通宝”,形成了独特的钱币体系。因此在这里做一并说明。
利用通宝
《辞典》收录文献中关于利用通宝的始铸时间说法不一,一说为康熙十二年末:“康熙癸丑十二月,吴逆以移藩据滇反叛,号大周,称帝于衡州,改元昭武,制钱曰利用通宝”另一种说法与地方志中相同,为康熙十三年:“国史:康熙十三年,三桂以滇铜铸钱,伪文曰利用”,虽然书上的内容自我矛盾,但词典也是收录的各家之言,因此我们还需参考更多文献进行分析。根据 《云南府志》:“十三年甲寅正月,吴三桂僭周王位,称周元年”还有一种说法为吴三桂初封平西王时:“张端木曰:吴三桂初封平西王,镇滇南,即山铸钱,文曰利用通宝”。虽然三种说法相异,但都明确了 “利用”一词为钱币名,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吴三桂建立大周后的年号。
张端木为乾隆年间人,其专著 《钱录》也离三藩之乱较近,因此所说较为可信。另据一些学者考证,吴三桂入滇后,由于各种原因云贵地区似乎并未大规模铸行清王朝本朝货币,而吴三桂为了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可能最早至康熙五年就开始铸造利用通宝钱那么在收复云南后不说为日后反叛做准备,仅仅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吴三桂选择自行铸造钱币也不是没有可能。
昭武通宝和洪化通宝
据云南 《云南府志》:“十七年戊午三月,吴三桂僭位衡州,伪号昭武”,时间上与《辞典》所载内容相互印证,昭武通宝应为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开始使用 “昭武”年号后所铸的年号钱。
《辞典》中记载:“钱币考:其孙世璠至贵阳,僭号,伪铸洪化通宝,重一钱三分”,而据 《云南府志》:“(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吴世璠僭位。世璠、吴应熊孽子也,三桂盗养于家,三桂死,胡国柱回云南,同郭壮图僭立之,伪号洪化”。我们由此得知,洪化通宝为吴世璠于康熙十七年 “登基”后所铸的年号钱。
而另据一些学者研究,吴三桂铸造的利用通宝钱为 “权银钱”,是受孙可望铸造的兴朝通宝钱的影响——兴朝通宝开辟了中国境内权银钱制度的先河,一直至昭武通宝、洪化通宝的出现才逐渐废止。
三 结论
综上,在清初云贵地区共见到大顺通宝、兴朝通宝、永历通宝、利用通宝、昭武通宝和洪化通宝钱。仅凭以上文献我们已可以窥见云贵地区的货币流通历史,初步得出以下两条结论:
1.大顺通宝、兴朝通宝、永历通宝的关系
顺治元年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时首铸大顺钱,但此流通并不广泛,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符号;朱由榔于顺治三年称帝,铸行永历钱,此时的永历通宝钱主要铸行并流通于两广地区;顺治四年沙定洲于云南造反,孙可望将其赶走后,先是在云南继续铸造大顺钱,旋即铸造兴朝通宝钱,以借支持永历帝 “兴大明”的名号维持自己的地方势力。除此之外,文献中 “大顺钱”和 “兴朝通宝”钱的铸造、推行者,或是提到的直接相关者无一例外为孙可望;而永历钱的铸行则均与永历帝相关,但是当永历帝进入云贵后,铸行永历通宝的幕后推手仍然是孙可望,反映出孙可望对云贵地区的实际控制力。
2.大周政权的钱币铸行史
清军攻克云南后,云南地区一直由吴三桂驻守,吴三桂曾于康熙二年请铸 “康熙钱”以恢复发展地方经济:“疏言滇省初定,请开鼓铸,应颁给康熙钱式”,并得到了清廷的许可,但不久中央政府收回了云贵地区的货币铸造权。后来康熙十二年吴三桂造反,建立大周政权并铸造利用钱,需要说明的是,“利用”为钱名而非年号,这一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开始以“昭武”为年号,铸造昭武通宝;十月吴三桂病死,十一月吴世璠继位,改元洪化,开始铸造洪化通宝钱。康熙二十年清军攻克云南省城,云南收复;之后云南地方官员立刻奏请铸造本朝货币,禁行前朝货币,云南地区应自此才开始较多流通本朝货币。但大周政权铸行的利用、昭武、洪化钱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民间流通,体现出了与云贵地区在货币需求上的适应性。
注释:
① ④ 范承勋、吴自肃:【康熙】云南通志,[缩微胶片],三十卷首一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1,5页。
② 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1,01,37页。
③ 张毓君:《中国方志丛书·第廿六号·云南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六年五月壹一版,116页。
⑤ 佟镇:《康熙鹤庆府志》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26-27页。
⑥ 冯甦:《中国方志丛书·第一四〇号·滇考·道光元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六年五月壹一版,392页。
⑦ 杨成彪:《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康熙罗次县志》,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126-127页。
⑧ 刘茝等:《狩缅纪事·明末滇南纪略·安龙逸史·皇明末造录》,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51页。
⑨ 龙尚学、房健:《安龙出土的南明永历皇室墓志铭》,《贵州社会科学》,1986,3:45-47页。
⑩ 同③,128页。
(责任编辑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