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盐道》对巫术的书写与展示
2015-11-25崔德全崔有第
崔德全,崔有第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论《盐道》对巫术的书写与展示
崔德全,崔有第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李春平的长篇小说《盐道》,首次自觉地表现了巴蜀一带盛行千年的巫术民俗传统。本文阐述了李春平对巫术的全面展示,并从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深入分析了《盐道》中巫术书写的价值,揭示了李春平对巫术书写的初衷。
《盐道》;巫术;书写;展示
2014年秋天,李春平长篇小说《盐道》的出版,打破了他近三年的沉寂。小说的出版,迅速引起了国内学人的关注。雷达说《盐道》“是一部具有纯正精神指向和历史文化内蕴的佳作”,它有着“民俗学与文化学的双重意义”[1]。本文认为,《盐道》的民俗学、文化学和文献学价值最集中地体现于小说在民俗描写方面的转型和“突破”,尤其是其对巫术的描写。在《盐道》中,李春平自觉地对巫术进行了全方位地展示。本文即尝试阐述《盐道》对巫术的书写。
一、《盐道》对巫术的全方位展示
巫术曾被称为魔术,是人类凭借对让他们感到恐惧和敬畏的神秘的大自然的一些神秘和虚幻的认识,创造的各种法术,以期能够寄托和实现某种愿望[2]。李春平对巫术的全景式呈现,是通过详细叙述几个典型的巫术事件来完成的。《盐道》为我们叙述了如下几个巫术事件:A.崔小岭向李兆祥拜师学艺,李兆祥向崔小岭全面地讲解巫术;B.李兆祥和崔小岭共同施法,救活了王国江的大老婆;C.王国江请崔小岭施法,“收拾那个在他卤孔里放石头的人”,后来,郑拐子家的盐锅炸裂了;D.李兆祥的邻居被棒老二抢了,李兆祥欲助其邻居咒死棒老二,而崔小岭却认为“土匪是咒不死的”,二人争执不休,最终导致师徒关系破裂;E.崔小岭在家做法,为两个精神不振的小猪“念咒驱邪”。除了上述几个较详细的巫术事件外,小说中还零散地分布着其他几次巫术事件。本文将围绕这些巫术事件,详细考察《盐道》对巫术的全面表现。
第一,《盐道》表现了巫术的神秘性。巫术的神秘性首先表现于巫师的神秘性。在《盐道》中,李春平对此进行了挥云泼墨式的书写。在事件A中,李兆祥向崔小岭讲道:巫师就是“通天达地的执行者”,就是人鬼神合一的全能智者,他有一种神奇的威力,他的职责在于“替神说话,传达神的旨意”。其次,巫术的神秘性表现在其表演仪式的神秘性上。巫术中的咒符、咒语和歌舞,在普通人眼里都是神秘莫测的。那些咒符怪模怪样的,普通人“根本看不懂”,“像文字又不是文字,说不是文字又像文字”。巫师背起咒语、念起咒诀来,像是在说梦话,“只有鬼神能听清”。跳起巫舞来,怪模怪样的,张牙舞爪的,阴风四起,心惊骨凉。李兆祥说道:跳端公就是“要跳出一身巫气,一团妖气来,要跳出恐惧,跳出厚重,要让人和鬼神都觉得神秘莫测”。最后,巫术的神秘性还表现在普通人对巫师和巫术法力的虔信和崇拜上。许多不明就里的人们,认为巫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王国江就是其一。当他看到崔小岭“成功”地帮助他收拾了郑拐子之后,他对崔小岭的“崇拜油然而生”。他“压低了声音,很神秘地对崔小岭说:‘你巫术那么高明,能不能让我不老?’”当崔小岭告诉他不能后,他又在想一些异想天开的事情:要唐幺妹生儿子等。钟宝镇的普通百姓也是这样:当崔小岭巫术学成回到老家后,钟宝镇的人们都知道了他在巫溪的那些神奇的故事,“他被传说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
第二,《盐道》表现了巫术的功利性。任何一种巫术,都有着针对性极强的现实功利目的,镇坪、巫山一带的巫术亦然。李春平在《盐道》中明确指出,尽管巫术的范围很广,活动形式也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事件B,王国江的大老婆在议论国事时突然倒下,不省人事,王国江请李兆祥和崔小岭师徒二人为其招魂。事件C,王国江发现他家的卤孔被人堵住了,卤水量减少了,他请崔小岭做法悄悄地收拾那个在他卤孔里放石头的人。事件D,李兆祥的邻居遭棒老二抢了,棒老二又抓不住,“就请李兆祥施行法术,把他们咒死”。事件E,崔张氏发现他家的“两个小猪精神不振”,崔张氏怕它们死掉,就让崔小岭专门给小猪做法以“念咒驱邪”。
上述四次事件,从巫术施行后的事态发展来看,除了事件D之外,看起来,巫术皆使人们心中的愿望得到了实现,需求得到了满足。事件B,王国江的大老婆喝了崔小岭化的九龙水后“起死回生”了。事件C,崔小岭施术后的第三天,郑拐子家的盐锅炸裂了。事件E,崔小岭为他家的小猪做法后,他家的小猪“一个个都长得油光水滑的”。李兆祥在给崔小岭讲解巫术的基本道理时,讲了一个他曾做过的一次法术,这次法术看起来也成功了。“去年腊月,巫溪一个女人生头胎,胎儿是逆生,女人生了一火烟只见胎儿的脚丫子,接生婆都急哭了,还是没用。”这家人从来不信巫术的,走投无路,跑去请李兆祥。李兆祥听说之后,就明白了,这个女人是让小鬼附身了。于是李兆祥化九龙水,念咒语驱魔除鬼。李兆祥将这次巫术的成功声色并茂地讲给了崔小岭:“咒语一念,小鬼驱散,只见一股妖风嗖的一声吹走了。一会儿,接生婆就看到了婴儿的两个脚丫子同时出来了,不到一火烟时间,娃儿就顺利出生了。”但是,巫术真的那么神奇吗,真的具有那么大的魔力吗?答案是否定的。
第三,《盐道》表现了巫术的虚妄性。“巫术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3]13巫术的无效,“不在于它对某种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事件程序的一般假定,而在于它对控制这种程序的特殊规律的性质的完全错误的认识”[3]47。随着巫术看似一个一个地应验,一个一个地将人们心中的愿望变成现实,将人们的空想变成实际,人们便开始对巫术的法力深信不疑,开始迷信和膜拜这种法术。正如《盐道》向我们展示的一样:在崔小岭“成功”地帮王国江收拾了郑拐子之后,王国江认为崔小岭是个“神人”,他对崔小岭的“崇拜油然而生”。实际上,巫术的施行与人们心中愿望的实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那只是时间先后顺序上的巧合,而王国江们却将“巧合”当成了“必然”。这种情况只有在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时才会产生。随着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发现巫术是虚妄的、无效的。《盐道》中,年轻一代的崔小岭和春儿对巫术的法力提出了明确的质疑。
在崔小岭化九龙水救活了王国江的大老婆之后,他还没有对巫术的效力产生多少怀疑。然而,在崔小岭因与小红分离了许久而想念她时,他就不明白了,“巫术是无所不能的,却偏偏没有一种法术可以湮灭人的欲望”。这是崔小岭第一次对巫术的法力产生怀疑。在崔小岭做法后,郑拐子家的铁锅爆裂,王国江心里暗自窃喜时,崔小岭却认为这是他“运气太好”,是“巧合”。其实,“铁锅早就破裂了,或许是在铸造时就埋下了隐患,只是没有发现而已。因为太厚,使用中没有出现渗水,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必然就会彻底爆裂的”。也就是说,即使他“不跳端公,不念咒语,那口铁锅照样也会爆裂”。此时,崔小岭对巫术法力的怀疑越发重了。只是,作为一个巫师,这样天大的秘密,“打死也不能说的”。其实,早在这一次做法之前,他业已明白“许多事情端公是办不了的”,那只是“人们夸大了端公的作用,也夸大了巫术的作用”。
崔小岭彻底揭开巫术的虚妄和无效是在事件D中。这一次,崔小岭彻底背叛了师傅教给他的作为巫师的精神信仰:“作为职业,崔小岭必须完全相信咒语的法力”。而“作为听众,崔小岭又觉得咒语的法力有些玄乎”,他认为咒语不能把无恶不作的棒老二咒死。为此,他还亲自跑到山上看看棒老二究竟有没有被咒死。结果证明了咒语的无效。
春儿和崔小岭的看法是一样的。当崔小岭向王国江述说他和师傅争吵的缘由时,春儿一嘴接过来,说:“哥哥说得对,咒语能咒死棒老二?鬼都不信!我们小时候,大人生气了,都骂我们短命死的,挨刀死的,砍脑壳的,不是一个个全长大了吗?要是都能咒死,细娃儿根本就没有长大的,早就全咒死了。”此时,连之前对巫术深信不疑的王国江也开始动摇了:“端公念咒语能不能咒死人,这个真难说。”
第四,《盐道》指出,巫术具有一定的宗教和科学性。既然崔小岭已经发现巫术是无效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做法为他家的两个小猪“念咒驱邪”呢?笔者认为:崔小岭为家里的小猪施法念咒驱邪已不再是纯粹的巫术,而具有了宗教的性质。“在许多世纪里和许多国土上,巫术和宗教相融合、相混淆。”[3]52“巫术是宗教的最早表现形态之一。”[4]上文已指出,任何一种巫术,都有着极强的现实功利目的。而巫术实现目的的手段,就是画符念咒配以歌舞,这实际上是“人类最早的符号操作。现代人对于没有把握的事,事先往往用符号来进行演习,原始人无意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5]在原始人眼里,该符号活动的意义是实用的。而对那些不相信巫术的人来说,那些画符、咒语,巫师的脸谱和歌舞,其意义不再是实用的,而是宗教的,或诗意的。当巫术仪式的实用价值被降解之后,其宗教意义和艺术属性则凸显了出来。而宗教,“指的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3]48。因此,崔小岭明知巫术无效,但依然为他家的两个小猪施法念咒驱邪,是为了让他母亲、也让自己感到安心,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抚慰。
在思想原则和认识世界的概念上,巫术与科学相近,而与宗教相反。巫术和科学“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这些演变是由不变的规律所决定的,所以他们是可以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3]47。巫术和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巫术对控制宇宙运行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是错误的,这才最终导致了巫术的虚妄、欺骗和无效。一旦人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是正确而合理的,那巫术就不再是巫术,而是科学了。其实,巫术和科学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有学者指出:巫师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4]。已有研究结果证明,今天的一些科学知识,像医学,其实源于原始巫术。“医学自巫术中产生,中国原始人所具备的一定的医药知识都与巫术活动有关。”[2]11《盐道》中的崔无疾就说:九龙水用在巫术中“驱邪镇妖”,只是它的一个功用,它还可以被用来“化食化骨”。
二、《盐道》中巫术书写的价值
《盐道》大篇幅地书写巫术,不是出于作者对巫术的喜爱和赞美,亦非借巫术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而是将巫术看作是巴蜀文化的重要内容加以呈现的。这一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客观书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一)题材内容上的价值
第一,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域。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艺术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巫术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也应该在文学中有所体现。应该说,在文学中表现巫术,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纵观中国文学史,描述巫术的作品比较多,如《诗经》《九歌》《搜神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妻妾成群》等。但那都是一些不自觉的呈现,也都是零散而琐碎的。而李春平则不然,他自觉地将巫术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文化现象加以展示,将巫术作为盐道上的民俗传奇加以书写。“小说中,巫术是最难表现的。难就难在要把巫术写得像巫术的样子,却又不能写得让大家看了都去相信巫术。”[6]尽管很难,李春平还是用了近40页的篇幅,为我们全景式地呈现了在巴蜀一带已经盛行千年的,类似于宗教仪式的巫术。如此大幅度地描写巫术,不要说是在当代小说中,就是放在中国小说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李春平的《盐道》对巫术的全景式呈现,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题材,拓宽了当代文学的表现域,为现代小说家的民俗创作辟出了一条蹊径。
第二,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巫术活动的发展演变史。巫术的起源有二:一曰人类的生存本能;二曰人类对大自然的神秘而虚幻的认识。巫术的衰落,其因亦有二:一则人类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深刻,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神秘虚妄;二则人类有了更加切实的实现愿望的科学方式。从最初人们认为巫术是全能的,到巫术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巫术被认为是无效的技艺,其间必经历了一段漫长且艰难的历史进程。这是一段渐进的历程,而对巫师来说,也是一个痛苦、无奈和不情愿的选择。巫师从骄傲的高耸的地位上被一步一步地击退,他们不得不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懊恼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他渐渐地发现“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3]55。
巫术的这一转变历程,李春平用文学艺术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这让我们感到异常欣慰。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文学家做到这一点。起初,李兆祥被众人“神”化,为自己能招到崔小岭这么个高徒感到欣慰,甚至有些妒忌这个徒弟。而当崔小岭将自己对巫术无效的认识“很为难地”告诉师傅时,李兆祥先是“非常吃惊”,接着“恶狠狠地瞪着崔小岭”,“脸色变得乌青”。李兆祥真的发怒了。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神坛被拆碎,神秘面纱被揭开,神奇本领被宣布无效。而这些,又都是他的高徒崔小岭干的,二人的师徒关系也就此破裂。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第三,用文学的形式保存了巴蜀一代的巫术文化遗产。在巴蜀一带,巫术的应用场合广泛:婚丧嫁娶、筑路修屋。施行目的多样:或除病消灾,或伤善害良。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或看相卜卦,或画符念咒,或招魂请神等。巴蜀一带的巫术不存在于历史文献中,而活泼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巫术也随之发生变化。如今,巫术的作用日渐淡薄,巫师的数量迅速减少,一度盛行的巫术呈现出迅速衰落消亡之态势。这一趋势已引起巴蜀一带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现已加大力度,对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进行保护和传承①据冉瑞铨撰文《巫溪与古老的巫文化》统计:“以民国三十年计,全县有23乡306保15.8万人。以古路乡第七保为例,该保有巫师3人,相命师2人,地理师1人,草医师3人,共计9人。若以全县306保计,不包括其他术士在内,就有2700多人。该乡镇有掌坛师,即有道士衣箱,经文挂图,各种响器者6家。一坛法事,一般7人。若以全县计,共有掌坛师138家,道士就近1000余人。若加上其他术士,全县将近5000人从事巫术活动,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30。”又据重庆日报2010年9月20日刊文称:巫溪“现在仍有上百名巫师在民间从事巫术活动,但年龄普遍偏大”。。李春平的《盐道》,将原生态的盐道人民生活和巴蜀巫术习俗呈现在我们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盐道》具有抢救和发掘、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功能。这体现了李春平作为一个文学作家的勇气和魄力,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地方文化守望与传承者的担当和责任,也体现了他扎实的文学功底。
(二)艺术风格上的价值
第一,《盐道》中的巫术书写,为小说增添了一种神秘奇幻的美感。小说中,大气磅礴、深幽雄奇的大巴山,弯弯曲曲、仄仄逼逼的盐道,豪气仗义的民俗风情,无不透露着小说的别样魅力。而神秘虚幻的巫术,则是这一特殊美感的突出体现。神秘虚幻的巫术,既真实地再现了巫术的基本属性,还原了那个地方的生活面貌,又为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层面纱吸引着读者进入其中,去切身感受品味巴蜀故国的奇幻与神秘。这是李春平的“镇坪盐道”小说所特有的艺术风格,它不同于李春平写农村、城市、官场题材的小说。这使得小说多了一些文化内涵,多了一些历史记忆,多了一些艺术上的纯粹。它的出现,标志着李春平小说创作的重大转型。
第二,《盐道》塑造了崔小岭这个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典型性格的深入刻画,是一部小说取得成功的标志,也是一部小说艺术魅力的有力体现。《盐道》在叙写“一段闻所未闻的盐道传奇”的同时,也刻画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性格。崔无疾的大义灭亲,王国江的知恩图报,春儿的因爱偷欢,崔大岭的断臂逃生,看到大儿子即将被抓时急得让自己老二媳妇用身体贿赂剿匪队长的崔张氏,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还不能说是《盐道》在人物塑造上的特殊贡献,这样的人物在其他小说中也可以看到。《盐道》的特殊贡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端公形象——崔小岭。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巫师形象,是第一个揭开巫术神秘面纱的人物。崔小岭的典型性不仅在于其端公的身份,更在于他身上体现着丰富的美好人性、人情:远离妻子时的相思幽怨,看到大哥竟然是土匪头子时的惊讶愤怒,大哥被熏死后的沉重感叹,对师傅教育之恩的感激以及与师父产生分歧时的坚定与愧疚。崔小岭这一人物使中国现代小说人物画廊更加丰富多样。
第三,巫术,不仅是《盐道》所表现的重要内容,还是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若崔小岭不学跳端公,他也不会和妻子小红长时间分离而饱受相思之苦,小红也不会冒险跋山涉水千里迢迢跑去与崔小岭相见,更不会出现二人相见时小红的喜极而泣和破涕为笑;无崔小岭学跳端公,就不会有后来的他帮助王国江收拾郑拐子,也不会有后来与春儿的数次交往乃至最终偷欢的事情发生;崔小岭若不学跳端公,镇坪县县府也不会请其选宅择日,崔无疾也不会让他给大岭选阴宅。若崔小岭不质疑巫术是否灵验,他也不会上山查看咒语是否已将土匪咒死,当然也就不会发现崔大岭早已是土匪头子。“这个情节设置精妙,机智地揭示了巫术的神秘和虚无,又顺理成章地把故事推向了高潮。”[1]因此,巫术作为《盐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仅具有烘托氛围、刻画人物形象的功能,还起着串联故事内容、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结语
李春平对巫术的书写与展示是站在文学家而非学者的立场上进行的。他并没有说巫术是封建迷信或腐朽文化,也没有站出来确切地告诉我们巫术是否灵验,更没有要求或指示我们信或不信巫术。他只是将原生态的巴蜀民间巫术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他在为纯粹艺术创作而努力,为镇坪盐道的文化建设而努力。正如李春平在《盐道·后记》中所说:“作家的任务不是要对某种现象去下结论,而是对生活状态进行艺术的书写和展示。”[7]这一“书写和展示”已足以让我们兴奋良久了。
[1]雷达.大道至简——长篇小说《盐道》的文化情怀[N].光明日报,2014-11-17.
[2]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4]弭维.巫术、巫师和中国早期的巫文化[J].宁夏社会科学,2009(2):133-137.
[5]朱狄.艺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11.
[6]耿翔.陕南镇坪千年古盐道系列专访:神秘都在一条路上[EB/OL].(2015-01-08).http://www.sxdaily.com.cn/n/ 2015/0108/c508-5597676-1.html.
[7]李春平.盐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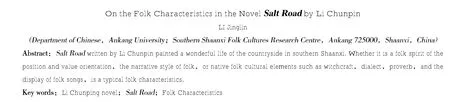
【责任编校 朱云】
I206.7
A
1674-0092(2015)05-0020-05
2015-06-30
安康市科技局项目“安康山水民俗文化研究”(10AK07-08)
崔德全,男,山东滕州人,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古代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崔有第,女,陕西平利人,安康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