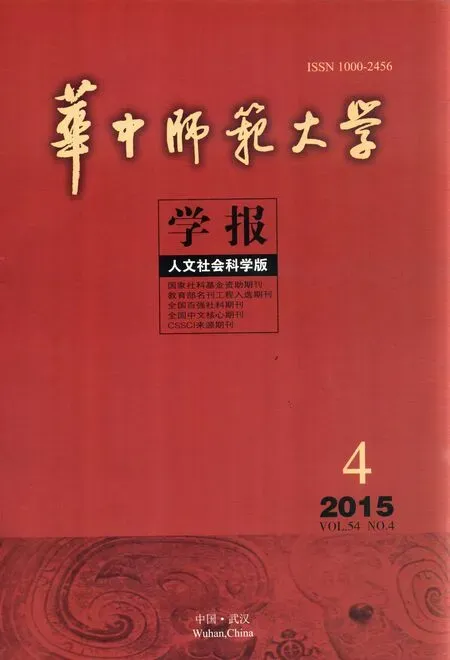从自治到动员: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
2015-11-22陶逸骏赵永茂
陶逸骏 赵永茂
(台湾大学 政治学系,台北10617)
一、引言: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
1920年代,作为日本政权的殖民地,台湾各地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使政治经济社会掀起汹涌波涛。多项冲突演变为各地“农民组合”所引导的组织性抗争。①而在“二林蔗农事件”影响下,农民组合进而串联为全岛的“台湾农民组合”。这场运动一度造成日本殖民体制统治危机。1927年,台湾农民组合举行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是农民运动声势最高峰。然而此后立场趋向激进,手段也日益剧烈。在日本政府大举镇压日本共产党之后的1929年3月,已具浓厚共运色彩的台湾农民组合也面临大肆搜捕,受到严重打击,并被迫转为地下活动。随之而来的是1930年代日本对台施行的“皇民化运动”,以及因应二战军工需求的加压汲取。自此台湾农民运动不再复见往日兴盛,民间反抗声浪一时也略为平息。然而,潜藏于历史脉络及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力量性质,从未遭到彻底铲除,从落入殖民前的清治末期,延续到光复后国民党政权,成为长期基层治理情境基础。
台湾农民为何具有如此行动意识与力量?如何解释当时台湾农民运动与组织的蕴酿、兴衰与遗绪?本文尝试追索台湾农民与殖民政权间冲突的社会起源。这些行动与事件尽管未能撼动殖民统治,然而无可否认,它不仅具体演示台湾民众反抗殖民政权的巨大力量,也在特定情境展现传统基层社会内生的治理性质。
二、问题与解释
日本殖民体制透过基层政权、警察与产业组织等制度结构,深广地涉入台湾基层事务,进行高压统治与资源汲取。农民何以在严密统治下萌发系列行动,甚至串联为广布全岛的组织,造成殖民统治的危机?且不论殖民初期台湾城镇士绅的反抗,事实上在1920年代前,以农民为主的官民对抗早已零星而持续浮现,只是并未演变为全岛规模的组织性动员。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并非突发偶然的事件,而可视为特定结构脉络下的行动现象。这个结构脉络自有因果逻辑,也牵动所衍生之现象形态。问题在于:1920年代的大规模组织性农民运动,其内在性质为何?动员形势及成员的能动性在何种结构脉络的基础上发生作用?
日本官方文献与学者为主的论述中,往往从民族、阶级、文化等政治共同体的集体斗争视角进行解释,强调台湾先进文化精英1920年代组织“文化协会”所启蒙扩散的、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如同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所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当中基于“民族主义”与“阶级意识”对农民运动的解释:“所谓‘生活威胁’一直不过是次要原因,过去此类问题也屡见不鲜,却从未采取争议形态。而自大正十二、三年(1923、1924年)时起,突然以此为主题,变成争议事件,其原因不得不归诸于农民的民族的或阶级的自觉,或是煽动者的介入。”至于煽动者是谁?当中说得明白,就是“文化协会在岛内的启蒙运动”。②同样作为日本精英,矢内原忠雄则较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他所谓“经济因素”事实上是“阶级经济关系”,因此在他的理解中,台湾农民运动是一场经济基础上的“阶级运动”。且由于殖民地社会的特征,因此“大体而论,民族运动即阶级运动,阶级运动即民族运动”。③这个解释与《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具有内在连系。亦即台湾农民运动本质是阶级的、民族的政治性行动。此类解释观点,我们可称之为“政治意识解释”。
然而“政治意识解释”不易处理许多农民在事件中的自主决策,以及运动后期激进化下的裂解与衰落。对于许多论者(特别是受日本教育的学者)蔚为共识的“政治意识解释”,台湾大学教授陈翠莲提出反驳。陈翠莲承认“文化协会”遍及全台的演讲活动固然对群众的权利意识具有启蒙作用,也确实对殖民当局的统治权威产生一定程度冲击,但她更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及“能动性”。她指出“台湾农民运动中的群众,其实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进一步将群众与精英的运动目标及行为特征加以分离,指出“知识精英固然有其运动目标,例如文化协会努力于改变殖民统治权力结构,农民组合领导精英醉心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但农民群众自有其经济动机与理性逻辑,在改善现实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决定如何采取行动”。④这种观点以先进阶级的“政治意识”与农民群众的“经济动机”共同解释农民运动。或可称之“以群众经济动机为主、精英政治意识为辅”的“分层动机解释”。
同样具有资源动员理论意涵,相较于“政治意识解释”,“分层动机解释”在考量文化精英、阶级结构之外,重视农民群众自主动机与理性逻辑,更能解释台湾农民运动的发生与演进,特别是台籍地主策略,以及基于特定经济诉求的抗争。然而将精英与群众区分理解,难以涵括农民运动群众诉求中具有的协商性、程序性、公共性乃至“自治性”先进成分。如1925年“二林蔗农事件”中派遣代表参与决策的要求,以及“竹林事件”中对于保管林的争议,都具有“协商自治”的性质。这很难说仅出自特定领导先进精英的“政治意识”;而以经济动机将农民群众一概而论,也不能解释1920年代之前,群众对于政治性组织宣传的长期接纳与酝酿,及随后自发动员的迅速参与及回应。对于农民运动其后的激进化、抽象化与萎缩,更只能由“外来精英所领导的农组日趋急进,造成农民大众的疏离”来泛泛理解。⑤事实上这可能只是基层农民社会基础内生的自治秩序与组织动员出现落差。是社会性质与动员形态的分歧,而未必是群众经济动机与精英政治意识的分歧。
换言之,各个精英与农民群众身上,其实同时存在经济理性与公共政治诉求的两种动机。而农民群众政治动机并非完全来自先进精英倡议,而早已存在于经济动机长期形构的“自治性”传统。两种动机的形成与组合,必须置于更为宏大的结构脉络底下理解。对经济利益的微观思路和政治意识的宏观思路,本文取乎其中,基于社群/组织行为假设,⑥采以产权与社群自治的中观思路,参酌动员性质,搭配外在政权体制形态的“汲取能力”概念组合,提出“社会基础-体制能力”的解释框架,而历史事件则贯穿其中。
三、产权自治性与动员
(一)产权与自治性
人生而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利”来自某件事物的“权利”运用效果。而对于财产物件的权利即为产权(property rights)。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以土地为例揭示产权性质:“我们也许能够说某人拥有一块土地,并且将它作为生产要素,然而土地的所有者实际上拥有的是一项权利,这项权利使他可以进行有限的行为”。⑦德姆塞茨进一步指出:“一组财产权利是附着在具体的商品或劳务之上,且正是这组权利的价值,决定了被交换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⑧任何一项财产所蕴涵的意义,实际上是“关于此项财产的权利”以及“此项权利所面临的局限”共同构成的组合。依此权利与局限性质,所能够透过行为选择获得的利益价值,决定了产权价值,也牵动行为决策。政治经济体制可视为由各种产权契约交易规则及决策行为组成的机制安排与体系结构。结构下的行为互动决定资源利益配置结果,并引导调整政治经济行为。政策执行及体制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产权安排体系的调整及治理过程。这个过程往往具有地方特色。清帝国或者日本殖民体制的统治决策,亦须面对地方内生的结构性质。一旦发生冲突,农民可能采取反抗,甚或动员成为集体行动与组织,尝试回应政权决策。对体制的压力取决农民关于产权的行为与社会基础,以及当下体制的决策情境。
产权安排的理念型当中,行为者依意愿运用及交换权利以获益。然而理想效率情境不易在真实社会出现,产权界定与配置往往在冲突与协调过程中逐渐达成。当产权界定与流转存在不确定性、甚至自始没有固定产权,各行为者对于资源蕴涵的租值(rent)便有诱因以各种手段竞逐,并且导致恣意夺取乃至暴力纷争的混乱状态。普遍寻租(rent seeking)的负面效应难免反噬产权利益,导致租值耗损(rent dissipation)。耗损可能延续较长时期,直到外力介入或者社群内部共同应对它所产生的压力,开始学习在耗损发生之际一齐进入一个公共性场域。在这场域中进行协商,进而建立某种共同认可的权威及秩序,以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产权契约,为彼此减低耗损。诺斯从产权契约协商的视角描述了制度演进过程:
相对价格的改变导致政治或经济交换的一方或双方,感觉在改变合约或契约之后,其中单方或双方的处境会较好,于是有人会试图重新商议契约。然而,因为契约是窝藏在规则阶层之中,不去重组更高层的规则(或违反某种行为规范)恐怕不能重新商议。这种情况下,能争得更强之谈判力量的一方也许会设法投下资源去改变更高层的规则。⑨
当社群内部能够自发进行产权规则重组,趋向稳定,就呈现为具“自治性”(self-governing)社群。自治性是产权过程在特定社群情境下的表现,且如费孝通所说“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⑩这种社群以地缘关系为初始核心。而这意谓一种社会状态:当个人或家户基于各自声称的产权,彼此冲突或合作,一般倾向在社群内部透过协商而非暴力方式解决,同享契约利益。以此规则共识与地方性叙事,⑪社群对内减低耗损、维持秩序,对外回应威胁、进行社群间协商合作、共同自治、必要时串联合并。这个社群边界与元素随着面对的情境性质变化而浮动,并且往往共拥某个地方权威如士绅、宗族长老、宗教象征等。传统社会中,政权体制决策一般尊重、认可、参照或咨询各地社群具体协商情境及地方权威意志,以处理基层事务。自治性社群无意冲击更高层的体制规则,但在互动中深受体制性质影响,并展现基层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当社群遭受政权体制的干预或汲取,会采取相应的行为或动员,尝试延续自治逻辑。当然,若体制力量强大而相应动员薄弱,社群自治性也可能斲伤。
(二)近代台湾的自治性与动员
关于晚清社会性质的文献汗牛充栋。罗威廉以“公共资金”、“公共事务”、“公共意见”,甚至“社会契约和所有权”的概念对应清末社会特征,并揭示极具限度的公共性现象;⑫兰金认为清末的公共领域是地方性的,而且核心的特征是管理,而非公共讨论;⑬黄宗智则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外,尝试提出“第三领域”概念。⑭然而,抽象的“公共领域”乃至西方“公民社会”相关概念存在过度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的危机,社群基于产权的“自治性”更适于理解特定情境。作为一个蕴涵现代性的概念,自治性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系仍相对缺乏关注,偶有借以理解清代地方社会形态者,⑮却罕有用于解释政治社会遭遇体制的转型与冲突。对于晚清基本已由移民社会走向在地社会的台湾,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殖民政权以现代化体制施加的汲取和渗透,则鲜明演示了这个过程。
具体而言,清廷治台最后数十年,台湾基层社会无论在城市乡村,其实都已出现某些社群自治性质。这些性质在长期冲突耗损与自发协商过程中积淀形成,农民运动无论基于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论的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或新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框构(framing)概念,都必须考量这个“自治性”社会基础。如赵鼎新指出:“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就是它们所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收的框架”。⑯自治性尚未形成时,行动形态因动员理念而异,同样带来耗损;而在自治性逐渐形成后,动员力量形态相当程度取决于动员性质与自治性社会基础的契合关系。这里所说动员性质便可纳入前述“政治意识”及“经济动机”的两种解释路径,并依行动理念的激进性(radical)高低区分。如表1所示。日本学者主流的“政治意识”路径强调理念激进性,但事实上农民运动激进化时已是强弩之末。而完全基于经济动机的冲突缺乏协商意识过程,难免表现为冲突械斗与纯粹利益诉求,也不符合1920年代农民组合的情况。“产权性动员”是动员与社会基础契合的状态,也成为运动兴衰的参照系。

表1 近代台湾基层社群的行动类型
社群动员形态又与政权体制的汲取渗透力量产生联结。日本殖民统治初期,曾借助基层自治性质获得经济社会的统治利益,但也旋即遭逢若干障碍。而1920年代面临的统治危机,未必是阶级或族群冲突,也不纯粹是利益冲突,而更倾向于体制力量汲取与渗入的过程中,与基层社群既有产权自治性基础秩序的冲突。冲突发展则与当下自治性与动员性质的契合形态有关。因此,必须考量政权体制的历史脉络与决策背景,参酌“自治性”和动员基础连结的不同形态,才能展现组织性冲突与体制的动态关系及兴衰逻辑。
四、台湾农民运动的社会基础与体制
(一)清治时期台湾
1.械斗的缓解与自治秩序的形成
清廷治台后,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基层曾在相当漫长的期间充斥各种暴力冲突,包括政治性叛乱及番汉间斗争,而以围绕土地财产的群体械斗特别频繁激烈。⑰然而到了1860年代,这种局面渐趋缓和。⑱至光绪年间(1875年后),大型械斗已经相当罕见。⑲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前,台湾农村产权与社群已有一定秩序,而主要立基于垦佃的“大小租制度”,呈现“一田二主”的特色:地方上有财有势的豪绅,向政府当局请领官地,取得开垦许可证明,成为创业的垦户或垦首,然后将土地交予佃户开垦耕作,借以收取“大租”;而佃户在获得耕作权之后,往往将土地租与其他佃户,进而收取“小租”。⑳这种具封建色彩的农地产权并非典型私有产权,然而在民众自发协商下却也逐渐形成运行有序的契约秩序,包括“隐田”及荒地的开发利用。正由于这套秩序的形成,以至于1880年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尝试整理地籍、消灭大租户以确立小租户的业主权时,遭到大租户激烈抗拒而未成功,尽管这种产权制度下,许多小租户经由努力,势力也有机会凌驾于大租户之上。但当时大小租户相当程度都已接受这种产权秩序,变动也只能是内生渐进的。
大小租制度存在于已开垦的土地社群,而未开垦或界定产权的林野更能显现自治性特征。由于清廷对未垦地缺乏管理,也未发展出相对应的地目,基层群众透过“缘故关系”契约形式就能对林野资源进行利用与配置,并稳定共享利益。这些林野资源显然也不是私有产权,但此时基层民众已透过自治性机制来避免曾经频发的冲突与耗损。尽管这个基层产权秩序里始终仍存在不平等与欺瞒的可能性,但无疑很大程度已脱离无序的丛林状态。日本统治前的台湾“土地所有形态虽错综复杂,但总算是勉勉强强完成了地主私有制”。在这种土地所有制衍发的商品经济关系,以及促进小租户抬头的趋势下,更使得经济结构逐渐转向小租户为中心的私有形态。而演化出的这套土地产权规范不仅在汉人社会当中落实,也逐渐为土著部落所接受。这种产权基本秩序展现一个特征:农民群众自发的民间组织与协商功能,成为处理私人及公众权利事务的一种习惯秩序,且常围绕村规民约或宗族耆老的公共权威,呈现相对独立有序的自治社群。其时中国基层社会“村庄有相当程度的独立,不管村庄民的新陈代谢,系具有永续的生命之有机体…对内而言,有村庄规约,拘束一般住民…对外关系,村庄不但与他村庄订立合约,或与之结盟,而且关于本村庄民与他村庄民之争讼,亦予以调处、裁判,或对他村庄请求处罚,救济…对政府关系,政府不但将村庄内事,委其自理,而且例如重要人犯之跟交,亦要求该村庄老大或全村庄民负责”。这种公共秩序形态的结构条件同时存在于台湾及大陆。黄宗智则指出:“两岸三个县(直隶宝坻、四川巴县与台湾淡水-新竹)的自1760年代至清末的628件民事案件中,只有221宗一直闹到正式开庭,由地方官吏裁决,剩下的几乎全都在提出诉讼后未闹到正式开庭,就在诉讼中途了结了。”他认为和解办法“不应被等同于正式法令的裁决,也不应被等同于非正式的社会/宗族调解,因为他们将正式与非正式的两种司法体制都包括到一种谈判协商的关系之中”。
而此种地权秩序的自治社群很大程度是地缘性的。正如前述费孝通所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陈其南则指出“汉人社会越是历史悠久而社会越是稳定,就越倾向于以本地的地缘和宗族关系为社会群体的构成法则”,进而以“土著化”理论,阐释汉人移民在台湾重建中国传统地方社会的过程。这个图景下,晚清台湾社会逐渐摆脱械斗与混乱,从农地产权制度中建立起一套深具中国传统社会特色的自治秩序。自治性社群自我管理协商地方事务,尊奉地方性权威,与其他社群竞争合作,拓展较为多元复杂的生产及商业活动,也面对不同时期政权体制的干涉汲取。
2.自治社群与体制的连结
协商自治秩序扎根基层社群,而与体制发生关联。清廷治台期间采取的是相对消极的策略,并未对于基层社会施加过多干预,这种态度虽然纵容许多械斗、匪乱、番汉冲突及激烈的产权竞逐,却为民间摸索协商自治秩序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而动乱冲突过程中透过族群政治操作,也对统治起了一定的安定作用。当然,清廷并非未曾尝试更积极涉入,特别在光绪年间,除了台湾贸易与战略地位更显重要,清廷自身也逐渐面临现代国家体制构建问题,需要更现代化的治理策略,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即为其中之一。只是对台湾的决策往往正因地方社群回应而未能获致预期成效。前述刘铭传整理地籍进行土改的尝试是个失败案例,另一个有力说明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构建运作。艾马克对“淡新档案”司法审判案例的研究指出,清廷在台法律体系的建立旨在整合社会中原本分散的团体,联结政府与社会,促进社会制度的形成。但如同黄宗智所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制度是在相对简单的小农社会基础上形成,却不易应付19世纪晚期淡水-新竹那般较为多元复杂的社会。当地民众往往不依从判决、诬告、采取各式各样的诉讼策谋手段,以及各种拖延伎俩。台湾基层自治发展逻辑不仅复杂多元,也延续了中国社会的“无讼”传统。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自有礼治传统,“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更麻烦的是,“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歹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王泰升也指出,艾马克所研究的许多案件足以说明官府态度的消极性,不能理所当然认为国家透过法律积极影响社会。可以想见,清廷大致还是扮演维持基本秩序的角色,使得晚清台湾基层呈现一种官方干预与民间自治回应彼此都“点到即止”的状态。这种状态加上免于晚清各地动乱的地域条件,构成趋向自治情境的优势。基于土地拓垦经营对秩序的需求,沿用大陆本土村庄社会结构的产权功能也更为显著。建省后清廷的行政法令,更与这些乡老乡约维系的公共权威彼此结合。这种由乡老乡约加上“社团自治”与“地方自治”的基层体系,因应基层社会需求、拥有社群秩序基础,与体制彼此相容,使台湾发展出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结构状态。
台湾经济社会的三个历史特性:重商性、早熟性、强韧性,正是在这种状态中逐渐形成。由于经济秩序趋向理想效率,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十几年,台湾已成为中国较为富庶的一省。经济生活发达丰裕程度不仅傲视国内,甚至不逊于日本的东京都。而当时基层民众的悠闲生活也催化“诗社”等人文性结社的出现。这些现象足堪表明,清治晚期台湾基层民间已有现代公共生活的萌生征象,并且来自协商参与的社会基础。这种特征趋势在台湾大致呈现由南向北、乡村发展蔓延至城市,最终反过来被城市发展所影响。
总之,在清朝治台的悠长时期,政权体制与台湾社会之间已逐渐寻得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状态,并呈现出社群的自治性。而在逐渐建立自治秩序并正式建省之后,“清国行政法”的温和介入更有助于社群秩序发展。行政条件已然趋向安定,加上高度持续的经济发展及精神生活萌芽,产权、商业之外更多层面自发产生自治性的政治生活性质,也就蔓生到更多群众生活当中,使他们更具有一种“参与政治生活的精神与性格”。这构成了日本殖民政权所面对的台湾社会。
(二)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
1.日据初期:汲取力量较弱
在产权秩序基础上,群众逐渐具有参与社群自治的意识,台湾农民基层社会因而可理解为“产权自治性”的秩序性质。这种性质下农民重视产权利益,同时也具备协商参与的自治性格。面对这种社会格局,日本对台殖民初期尽管遭遇同样来自群众性格的民族运动,但没有发生太多基于农民产权的冲突。一个原因是当时作为主要治理策略的土地调查,对民众产权自治秩序还没有太大冲击。叶荣钟便指出:“这样被没收的田畑,有自愿放弃者亦有因自己过失而招致的,数量可能不会太多,大量的收夺还是林野调查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政权殖民初期根本还没有能力去压制台湾基层民间的产权自治秩序。1904年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力量夺取台湾土著地主持有的整个土地,也占据不了太多土地。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尚未成熟,为了树立当前自身的统治新秩序,也忙于镇压‘土匪’,根本没有多大的力量可以投入台湾,开拓新殖民市场,而有‘一亿円出售台湾’之说”。尽 管1902年“台湾糖 业奖励 法”与1905年“原料采收区域制度”尝试由国家权力驱动糖业垄断资本,但并未打破台湾固有的土著地主制,也暴露出对台湾农村浸透力量的有限。
到了1908年,日本总督府以开发产业为由开始调查台湾竹林,直接干预资源安排,台湾农民的集体抵抗行动随之浮现。1910年官方将一片竹林让售给三菱会社,地方民众认为“竹林为祖先自康熙年间所种植、长久以来血汗培植的结果”,掀起反对运动,1912年更发生杀死三名日本警察的“林杞埔事件”。关于竹林的行动一直没有平息,也在1925年再度兴起成为农民组合的有力来源。可以说在“台湾农民组合”形成前,台湾农民都未曾放弃回应殖民政权对于产权自治秩序的干预,相对于1921年成立的“文化协会”,也具有相当的自主性。
2.汲取力度加强
另一案例是“退官土地纠纷”:台中大肚溪岸有一片为洪水所淹没、后来才逐渐浮现的土地。这片土地原本并不适于耕种,但是在一群台湾农民合力拓垦之下,使土地成为可供耕种的田地,并且预拟共同善加利用。当群众尝试向官厅办理登记时,屡次皆没有获得回应。直到1924年总督府裁并行政单位,将这片土地分给退官者(退职官僚),并且径自判定民众是“无断开垦”(未经许可开垦),否定民众长期的努力,直接抵触这些努力背后持续运行的产权自治秩序,也加剧殖民政权与社群的冲突。从这个例子能够看见民间自发协商产权的有效性,只是此时已不似清末消极官治下以民间协商就可以安排资源契约,而必须面对日本殖民政权在决策情境下的渗透汲取。除了1908年前后开始的直接涉入,日本1923年遭遇“关东大地震”,1927年发生“昭和金融恐慌”,社会动荡,失业严重,乃至二战临近,这些历史情境促使殖民政权对台湾的汲取渗透力度加大,与基层社会自治性的冲突也更为激烈频繁。表2进出口结构数据就能看出殖民政权对台湾经济涉入的程度趋势。

表2 日据时期台湾出口市场结构(%)
3.佃农争议与台湾农民组合
干涉与冲突是趋势,而组织动员随特定事件发生。较大规模抗争始自“蔗农事件”。“原料采收区域制度”和“产糖奖励法”等直接干涉手段的落实,限制了蔗农的出售区域,并由厂方单方面决定甘蔗等级与价格。在汲取加大的1923年,发生以二林、大城两庄长头衔,大城、沙山、竹塘、二林四庄蔗农二千余人连署,向台中州及殖产局提“叹愿书”的运动,并且获得一点补偿。而产权自治性社群力量,更充分体现在“二林蔗农事件”。1925年,不仅首先组织形成“二林蔗农组合”,并具体提出了两个面向的诉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及“在议定甘蔗收购价格时有蔗农代表参与”。前一个诉求具有经济动机,后一个诉求则很显然具有对公共事务进行自治参与的意识。而这个自治程序也是殖民政权处心积虑尝试渗透基层的重要部分。
各地自治社群很快被调动起来,地方农民组合的著名领袖大多还是地缘农业社群中的能人士绅,譬如二林农民组合的李应章,在参与文化协会活动前是二林当地的医师;凤山农民组合的简吉作为小学教师,在当时凤山地区是一位深受民众尊重的地方精英(local elites)。于是,台湾的农民能够迅速承接城镇“文化协会”的各种宣传策略,形成极具力量的农民运动,并集结成为大规模组织性的“全岛农民组合”。农民所处的基层社会基础,自始具有产权协商自治参与的性质。这源自清治时期历史脉络,构成台湾基层社会长期以来维系秩序的内生力量。而文化协会与农民组合,仅仅是在政权施力渗透的特定历史时点,扮演提供话语并引导回应的角色。这个角色体现固有的基层利益需求,同时也实践自治秩序的协商参与。台湾农民组合成立后,积极介入指导农民争议,并且在1927-8两年达到高峰。由表3佃农争议的数据特别能看出:
表3 1923-1931佃农争议与台湾农民组合

表3 1923-1931佃农争议与台湾农民组合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台北:创造出版,1989年,改编自陈翠莲:《精英与群众:文协、农组与台湾农民运动之关系(1923-1929)》,第116页。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介入/件数0/00/5 1/4 6/15 344/431 80/134 5/26
4.动员理念与社会基础的脱钩与退化
然而当行动与组织不断扩大,以及面对的政权汲取及压制力量不断加强,动员形式与规模逐渐超越社群自治参与诉求,也就开始脱离农民社群基层产权自治性秩序传统的性质功能。如此一来,所能获得的支持力量迅速消逝,进而尝试从理念更激进的组织寻求奥援,使农民组合在内部斗争后趋向“左倾”。毕仰高指出:自发性农民运动在意义上是狭窄的,充满自卫性。而且就算现状并不利于农民,这些自发性的运动,目标仍然是要维持现状。相反的,共产党的策略不但具有攻击性,而且目的就是为了要推翻当时现状。而当时共产运动在台湾发展土壤还比较贫弱,面对二战前日本殖民政权更强大的力量,难免走向分化衰微。其中部分成员到中国大陆开展事业,较著名的是文化协会与二林事件领袖人物之一的李应章(李伟光),参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的创建,并在1949年作为台盟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而另一方面,台湾基层群众一种出于产权协商的自治生活性格,也并非那么容易捻灭,而持续保有其自身潜能,存续于民间基层。这种活力遍及民间生活,在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之后,立即迸发而出。虽然因而催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冲突历史,但仍促使国民党政权以地方自治、农渔会信用合作社等更符应基层自治性的方式,来巩固对台湾的统治。长期脉络下,台湾基层社会、农民运动与体制力量的动态互动框架,呈现于表4当中。

表4 自治、行动与体制汲取-本文论述框架
五、结论
有别于强调民族、阶级、文化等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意识解释”,以及关注民间经济动力的“分层动机解释”,本文将农民运动置于台湾基层社会一个更宏大的政治史脉络当中考察,并在微观经济利益与宏观政治意识间,改采中观的产权与社群自治视角。这种视角下,基于比较历史分析以及立足基层的社群/组织行为假设,搭配前现代国家政权体制构建过程的不同形态,本文指出:由于产权协商的长期实践和扩散,台湾基层的移民社会在19世纪后半已逐渐脱离无序的械斗耗损状态,形成自治性社会基础,并在晚清对台消极官治及族群治理策略中趋于稳定。产权自治与商业发展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资源,将各拥财产利益的多元复杂力量融入公共社群的自治性秩序当中。当时许多台湾农民身上其实往往已同时显露私人与公共的两种动机,和当时大陆部分地区一样,已萌生现代发展的基础。
农民群众组织动员,实是源于这种社群的产权自治性与政权体制力量的冲突,而远远早于1920年“文化协会”等组织所号召的意识形态。自治性社群的土壤助长早期抗日运动,并在殖民政权强化渗透汲取时,即时提供民间组织的结社条件与宣传情境,乃至此后遍及全岛的农民组织。当政权体制汲取随着历史加强,大规模组织性冲突同时增加。当组织动员理念自然或被迫趋向激进化抽象化,就脱离社群的产权自治性质基础,也就难免走向衰微。基层社群产权协商所形成的自治性面对政权与历史情境,解释了日据时期台湾农民运动的激化与兴衰,也有助于理解国民党接收台湾前后,台湾各地层出不穷的行动。即使强力压制也从未彻底弭平,从而展现近代台湾作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性质──这种性质蕴涵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
注释
①“农民组合”即为农民团体、农民组织。
②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台北:创造,1989年,第42页。
③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林明德译,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4年,第229页。
⑥来自诺斯(Douglass North)1980年代以来在制度理论的努力。见刘瑞华:《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导读,载于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刘瑞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5年,第8页。
⑦Coase,Ronald.“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no.1(1960):44.
⑧Demsetz,Harold.“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no.2(1967):347.
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刘瑞华译,台北:时报文化,1994年。
⑪地方性叙事的概念来自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展现一种相对于帝国政权、基于历史与仪式而展现地方自主性的社群整合力量。
⑫罗威廉(William T.Rowe):《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杨念群译,载于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⑬玛丽.兰金(Mary B.Rankin):《中国“公共领域”观察》,武英译,载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⑮冯尔康:《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载于肖唐镖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⑯赵鼎新:《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更新和中国经验》,台北:巨流出版,2007年,第253页。
⑰这里所说的激烈是指手段,不同于前述“动员理念”的激进性(radical)。radical有时译为“基进”,具有“深入本源”的先进意涵。激进政治论述也不等同暴力政治主张。
⑱Larry J.Lamley.“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In Emily Ahern and Hill Gates eds.,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转引自艾马克(Mark A.Allee):《晚清中国的法律与地方社会-十九世纪的北部台湾》,王兴安译,台北:播种者文化,2003年,第41页。
⑲阎崇年、陈捷先编:《清代台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