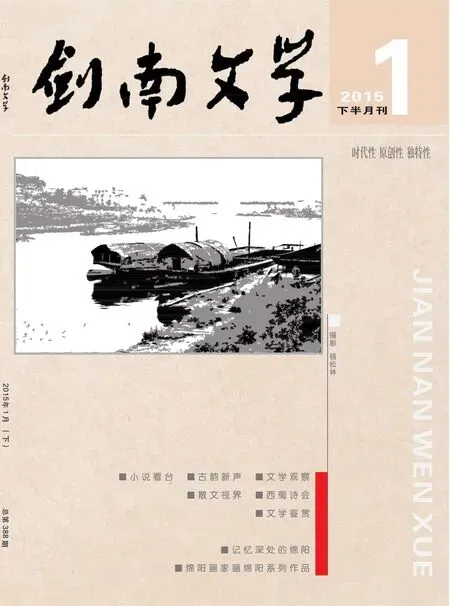采撷黄山
2015-11-22江剑鸣
■江剑鸣
从慈光阁上缆车,向玉屏峰进发,我们一直沐浴在黄山明媚的阳光里。我们同事一行五人,正好坐一辆缆车。我跟何万碧老师比较安静地观景,从车窗看出去,犹如在我们眼前播放自然风光片。曾小波老师、陈倩和廖美茜老师,面对黄山美景,激动不已,举着相机,远近高低前前后后地拍照。曾老师前年来过黄山,这次自然也就成了我们的义务导游。他主张步行,我不同意。老年人爬山,气喘气齁,非常吃力,还可能拖累别人。于是大家随我坐了缆车。
缆车缓缓上行,像在斜坡上一大片松树巅上缓慢飞行。脚下是悬崖与沟壑,旁边陡峭的岩石壁立。沟壑里尚没有晒着太阳,光线暗淡。偶有一缕一缕的烟雾,淡白色的,如丝如缕,袅袅娜娜,在沟底里漂升起来,从缆车旁边飘过,让人顿生如临仙境之感。莫不是神仙们的炊烟吧,虽说神仙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他们也要生火烟呀,不然,炼丹炉的火不就熄灭了?悬崖岩石泛着青黑色或者赭黄色,寸草不生,溜光溜滑,反射着阳光,轻轻地闪着我的眼睛。据说黄山曾经叫做黟山。那个黟字,至少有一半中国人不会读。那是个会意字,意思是说黑色石头多。在我眼里,黄山的确是丹崖黑石之山。山石上生长着沧桑而遒劲的松树——松树是黄山的标志,黄山似乎只有松树。那些松树多是两种形状,一种是笔尖宝塔形状,尖尖的树锋,长矛般向上,似乎要戳到缆车底部了。另一种是半边倚着岩石,倾斜生长在石缝里,另半边斜刺里长出长长的条干,仙人伸手般,伸着云枝,举着翠绿的松针花朵,向我们这些山外来客打招呼呢。
我一直生活在西蜀的崇山峻岭里,对于大山的喜爱已然深入骨髓。故乡在龙门山脉与岷山山脉交汇处,海拔从一千多米到五千多米不等,连成一片,构成了四川盆地的盆沿。都是页片岩石山,深切割型高山地貌,植被较好,但形状普通,毫无特色,观赏性不强,不适合普通游客光顾。近年来,地方政府也出大力气打造旅游,可收效一向不佳。我们常常从生活习惯了的熟悉之地,去一个陌生之地,登山,观海,丰富视野,开阔胸襟。比如,九黄山的卡斯特溶洞,黄山的丹霞地貌,海南岛的银白沙滩,就与故乡的景点有巨大区别。所以有人说,风景总在别处。如果说庐山是以秀美风光和悠久历史取巧,黄山则只凭雄伟壮丽取悦。如果说普陀山是小家碧玉轻敲木鱼的小尼姑,那么,黄山则是肩膀宽厚胸膛沉重的关云长。
利用暑假出游,是如今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八月八日,是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从缆车的玻璃上钻进来,映在何老师脸上,她的脸上便如同高级化妆师的大手笔般给化了妆,朱粉相间,浓淡恰宜。从屯溪古镇过来的路上,那个暑热啊,难受极了,热得人周身汗溽,心烦情燥。可随着缆车上行,身上就渐觉凉爽,心情也就愉快起来。自然环境真能够改变人的心情。俗话说:“山高一尺,土冷八寸。”黄山不愧是上佳的避暑胜地。远处山顶,有的被阳光照射,有的还没有照射到,明暗对比,绛皓驳色,矗立在蓝天下——蓝天似乎就是依靠那些高耸的山峰支撑着呢。我问曾老师,他说那就是玉屏峰,后山是光明顶。
这些年来,我经常旅游。许多中国人如今都走出家门,广泛地观察了解世界。这是社会进步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我的追求。年轻那会儿,我有精力出游,却无经济后盾支撑。现在勉强可以走得动,勉强可以挤出点小钱,我便走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放松我的心情,丰富我的生活内容。出于语文教师练笔的目的,偶尔也写写游记。我写不出徐霞客那样生动而详细的文辞,写不出郦道元那样准确而有力的考据。我也不想写成风景区旅游解说词。我没有义务为任何一个风景区写导游词。他们没有谁给我拿过一分一毫的卢布奖赏,倒是我自己掏了银子购买价格不菲的门票。然而,每到情绪所致,我还是会拿起秃笔,记录我的真实感受。初到黄山,这黄山灿烂的阳光,清亮的蓝天,壮丽的山峰,碧绿的松树和飘升的烟云,朋友般地欢迎我,我在心底里由衷感谢。我感谢伟大的自然。我要采撷黄山金黄的阳光,弱弱地植进我的文字。
下了缆车,走过一段崎岖坎坷的石梯,七拐八弯,我们到达玉屏楼广场。黄山是安徽的名片,那么这里就有黄山的招牌——迎客松。这是游黄山的必到之景,跟到北京必须到故宫到长城一样。石梯路上,游客众多,人来人往,摩肩接踵。要不是沿途的栏杆结实,还真的可能会被挤掉下去——掉进万丈深渊。广场上已经挤满了游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帅哥靓女,白发老头老妪,双髻少年儿童。天空湛蓝,丽日当顶。黄山的太阳与普陀山迥然不同。普陀山的烈日,似乎在皮肤上燃烧,灼得人头皮冒火,身上流油。黄山的阳光温柔婉约,让人感觉恰到好处。皖南的太阳普照大地,照耀着每一个人,照在我们身上,也映照进我的心里,晒得我身心中沾染的那些不良细菌无处可逃。广场上的人们,都背着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旅行包,都拿着相机或者手机,时刻准备着拍照留念。曾老师举着单反,看好背景,却没法给我们拍一张好照片,因为镜头里全是别人的头像——一张张偌大的脸或者一个个偌大的人头,艺术不艺术,都毫不犹豫地挤进你的镜头,令你猝不及防。
迎客松前的小平台上,人头攒动,如涌如潮,我根本找不到插足之地。人们一双双高举的手,手里举着各式不同的手机,对着迎客松。还有专业的相机,长长短短的炮筒子,对着迎客松。都想照一张与黄山名片迎客松亲密接触的好照片。挤啊挤,我好不容易挤到了迎客松前面的平台上,好不容易把手机焦距调到那棵世界著名的古松树上,在按下快门一瞬间,还是挤进了一个人的后脑壳。我居然都没有弄清那脑壳的主人是男是女是靓是丑。后来,照片发到微信上,好些朋友调侃我的技术差。我冤枉啊!哪里是技术问题哦,那完全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太多。我在黄山,真正体会到了人多的滋味。城市里人多,尚可理解。可这大山顶上,居然拥挤得我等弱势一族几无立锥之隙啊!
中国的名山大川,大都被僧道占尽。可是,黄山,除了山下有座慈光阁外,山上居然没有一座寺观庵庙,更没有香火和道场。黄山最早有过道士,古人皇甫大夫的诗里写过。开发旅游后,寺庙都搬迁下山了。这是黄山的独特之处,不像青城山峨眉山普陀山,真真假假的僧人游道,穿着僧衣道袍,穿梭于庙宇殿堂,香烟缭绕,骗人钱财。黄山的人文主要体现在摩崖石刻上。玉屏楼前后的大石头上,有许多摩崖石刻,书法或遒劲有力,或古朴沧桑,内容都是些赞美黄山的题词。可惜我不懂书法啊。同行的小茜倒是学习美术的,我以为跟书法沾点边。她在杭州时,还专门去中国美院门口留影,追寻美术大师刘海粟的足迹。中国古代的书画常常一体。可她说她学的是现代水彩,不懂书法。再好的艺术,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也就对牛弹琴了。在旅游途中,我发现许多人更钟情于人文景观,或者购物,或者烧香拜佛,单纯钟情于自然山水的人很少。黄山这些摩崖石刻,就是美好的人文景观。黄山,是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结合。倘若我稍微有点书画知识,我将会收获更多。
三年前去庐山,导游对电影《庐山恋》的推介声不绝于耳,指着地儿说这里是张瑜洗脚的地方,这里是郭凯敏坐过的石头。这次上黄山,导游又一直在介绍百步天梯。那是著名影星刘晓庆当年拍摄电影 《小花》“妹妹找哥泪花流”那场戏的地方。刘晓庆跪着抬担架,膝盖都磨出血了啊。那电影我看过N遍,那场戏我很熟悉。电影《小花》为黄山增辉添色。我随着人流往前走,崎岖的石梯路,时而上坡,时而下坎,斗折蛇行。挤在队伍里,不“随波逐流”都不行。终于到了百步天梯处,往下一看,那个陡峭啊,连目光都不敢久留,连飞鸟都会惧怕。倘若脚下一滑,滑过护栏,在悬崖下的几千米高空,就会有一只鸟人惨烈地飞下。人太多,有往有返,上上下下,太拥挤,任何一处也没法久留脚步,哪里还能尽情欣赏刘晓庆磨破膝盖跪着抬担架的石阶梯啊!本想拍照留影,无奈举不起相机。曾老师和何老师,被挤到队伍后面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星级相机如何发挥功能。
太阳早已经躲进了云层,云层暗淡而厚重。上山前,导游就说了,山上气候一日三变,甚至可能一天内体验到一年四季。他要求我们不要带雨伞。山风猛烈,撑伞反倒危险,谨防被刮下悬崖,化作一只悲催的飞鸟。他叫我们必备雨披。我们都买了黄色的雨披备着。有些游客购买的蓝色和白色雨披。山下的烟雾不断往上涌,此时已经不能用“飘”这个词语了。那团团滚滚的灰黑水汽,从我们身上裹过去,似乎要把我们裹进云雾里。天色越来越暗,正午的黄山,天地快变成一团乌黑的混沌世界了。
走下百步天梯,我们来到了一线天石梯,眼望着爬上几百步石梯,就可到达鳌鱼峰了。一块巨大的石英石搁在山顶,形似鳌鱼,瞩望着一线天梯步上络绎不绝的朝觐队伍。
一线天是地地道道的天险,两边石崖壁立,中间梯步仅容一人通过,头顶只现一线天空。石英石上凿成的几百步梯步,几百米高,几乎七十度地垂直,像一道通达天堂的梯子。天梯是单行道,只许往上攀登。我在底下望梯子上端,帽子都望掉。远远看去,天梯上一缕人流,慢慢向上蠕动。天色更暗了,像巨大的铅锅盖,直扣在我们头上。后边有人喊:“走快点,莫在陡梯上淋雨!”“暴雨要来了!”前边的人似乎听不见,依旧慢腾腾地蠕动,如懒蛇一般。我心里急啊,急啊!可只能干瞪眼,只能无可奈何地继续随波逐流。前边有白发苍苍的老妪,背着沉重的行囊,步履蹒跚。还有怀抱小孩的妇女,搂着小孩,吃力地攀登。如今生活好了,老人小孩都可以随便出来游山玩水,也算人们在同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暴风雨即将到来时,他们堵在前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急苦了我们在梯子下端的人啊。
突然,人们喊叫了起来,“暴雨来了!”有大点的雨滴打在我身上了。那雨滴之大,足有板栗那么大。我担心是冰雹,好在不是。噼啪——哐啷——轰隆!一声炸雷,又一声炸雷,就在我们头顶炸开。黄山打雷,与别处不同。别处打雷,一般先看见闪电。我们家乡叫做“扯火闪子”,哗啦一道电光闪过,几秒钟以后才闻雷声,响声沉闷。黄山打雷的响声,像是炸药摔在铁板上那般响亮,脆崩,干炸炸的。或许是黄山顶上,距离天空要近些,山上石头太多,巨雷砸下来,无遮无挡,所以声音特别脆吧。天梯上的人立刻快了起来。我距山顶鳌鱼峰只有百来步了。我赶紧从背包里扯出雨披,胡乱地往身上笼。脚下不敢半丝儿停顿,手拉着护栏,拼着老命往上爬。
到了山顶一块稍微平坦处,我一边喘气,一边把雨披捋伸展。身上已然淋湿。赶紧把手机往腋下藏,千万别把手机淋坏了啊!暴雨越来越大,简直不叫下雨,应该叫做倒雨。说倾盆而下,倾缸而下,一点都不为过。雨点打在脸上,像沙子,很疼。狂风也越来越大,呼啸着,猛烈地刮来,刮得人站立不稳。感谢导游劝买雨披。雨伞的确不适合黄山。烟雾和雨帘笼罩,看不清两米远的人和物。炸雷不停地爆响,干炸炸的,炸得地皮发抖。我甚至担心某一个炸雷就摔在自己头上或者脚边。风声,雨声,炸雷声,让人不得不胆战心惊。黄山顶上,鳌鱼峰前,这种独特的经历,独特的内心震撼,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啊!
后面的人继续往上涌,前边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哪里还有心情欣赏鳌鱼峰哦!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继续顶着暴雨往前走。前边是比较平缓的山路,全是石头阶梯,一直通往光明顶。但风雨如晦,看不到光明顶那个大圆球。一路上的人,没有谁不慌乱。路边雨水中,漂着有人扯烂了的绿色和黄色的雨披塑料布,那些塑料布可怜兮兮地躺在泥水里经历风雨,似乎在述说着主人的暴戾和遗弃。泥水里还斜躺着有人跑丢了的木拐杖。我拾起别人丢弃的一根木手杖,一路拄着走。有个美女,背着一个大包,从我身边挤过。她那雨披把前边笼严实了,后边却绊在背包上端。除了前胸,她周身全淋湿了。淡色薄裤,紧贴在腿上,几乎透明。看的人都尴尬,她自己浑然不觉。不知道先前看到的那白发老妪和那怀抱中的小孩,此时如何样了。老妪是否滑倒?小孩是否被雷声惊吓?我都自顾不暇,也只有在心里悲悯而已。
我走在最前边了。等不到曾老师他们,我就随着由陌生人自发构成的大队伍,无头苍蝇般往前跑。如果那只鳌鱼真有灵气的话,他该不会笑话我们这群自然美景的朝觐者吧?雷声不断,雨声不断,风声不断,像古代战场的军鼓,为我的奔跑呐喊助威,尽管我的跑姿十分狼狈。雷声震耳欲聋,撞击着我柔弱的心肺脏腑。狂风呼啸,撞击着我孱弱的身躯。暴雨如盆浇顶,清洗着我来自红尘的肌肤。旅游鞋里边已经装满了雨水,在我的奔跑中叽里咕噜呻吟叫唤。我拄着拐杖向前跑,一直跑,没有等他们。五人中我最年长。前几天在杭州,导游直接把我们当作了一家三代。我当然是长辈,曾老师何老师夫妇带着小倩小茜俩女儿。一路上,他们四人非常照顾我,其乐融融,真像一家人。我感激他们四个年轻人。去年,曾老师和小茜,就与我一同旅游过凤凰古城和张家界,也是一路对我照顾有加。年轻人精力充沛,他们旅游经验丰富。我相信他们会很快跟上来的。
跑过一段平缓的路,又跑过一段下坡路,到了白云宾馆的休息亭。亭子里已经挤满了躲雨的人,披着各色各式雨衣,红黄蓝白色俱全。他们跟我一样,刚刚经历了黄山雷阵雨。此时,雨已经小了些,风也没有那么猛烈了,雷也不再那么响亮,雾正在慢慢散开,天也要稍微亮些了。我挤不进去,只在亭子外边树下站着。
八月份的高山气候,真如小孩子的脸,阴晴变化,只在片刻间。风雨阴晴,本也自然。不一会儿,雨彻底停歇了。曾老师他们先后到来。经历了黄山暴雨醍醐灌顶般的洗礼,大家都是一副狼狈相。曾老师的相机包都湿了,他检查看相机是否淋湿,所幸相机还算没事。何老师和小倩小茜,三个刚刚“出浴”的美女,花容失色,几缕湿漉漉的头发,紧贴在额上,倒是别有风采。大家身上都在滴滴答答沥水,裤子鞋袜全都湿透。你看着我,我看着他,相视而笑。小倩惊奇地喊道:“一群黄山小黄鸭!”曾老师立刻翻出相机,咔嚓,给我们定格了一张黄山黄鸭图。
不管愿意不愿意,我都把黄山的雨水采撷进了行囊,保存在这张照片里。
吃了几口饼干,喝了几口饮料,小倩说这叫补充能量。把雨披收起来,装进包里,我们又往西海景区走。曾老师说西海景区是新开放的,他前些年来时就没有去过。西海景区的路很陡,从白云宾馆往下走,可以步行,也可以坐索道车。我又选择了索道车。老年人经不住煎熬。刚才的暴雨,我的惊魂尚未安定,脚下发软,一双鞋子水坨坨的,周身衣裳湿漉漉的,不便步行。尽管有不少景区的缆车类交通工具出过问题,但我胆大,还是要坐。许多人跟我一样,不愿步行,既有身体原因,恐怕也不排除心理因素。就跟马航阿航台航飞机连连失事,还是有许多人出行选择飞机一样。非常庆幸如今我有缆车索道车坐。遥想当年,徐霞客只能步行,甚至可能是手足并用地攀登。即使轿子,最多只能在山下坐。也不知道他坐过山上哪块石头,攀过哪棵树枝,爬过哪段悬崖。
天又放晴了。乌云开始消散,露出几块蓝天。远处光明顶那个大圆球,在阳光下闪耀着蓝光。那是一个气象观测装置,倒也成了黄山一个地标,一道人文风光景点。
西海索道车是小火车形状。索道背阴,只能看到远处山尖上染着阳光,染得金黄金黄。向下看西海山谷,却都还在一片浓浓云雾氤氲中。
索道车滑下谷底,我们好像又进入了另一派朦胧迷离的世界。走出索道车,四围陡崖,幽谷众多,岩石陡立,大大小小的瀑布,悬挂其间,白练飘荡,飞流喧豗,甚是壮观。瀑布下边一定是清澈的溪流,淙淙潺潺。满眼是云烟浓雾,分不清高低东西。刚下过暴雨的山谷,凉风习习,空气湿润,身上刚刚暖干的衣服,又被洇湿,就更觉得阵阵寒意。比起山下的酷暑和闷热,这也算一种享受。云雾是西海景区的主要景色之一。团状的,滚滚而来,絮状的,悠悠飘逸,带状的,缠绕着山峰或者裹绑在山腰。那些云雾,有的浓黑,有的灰淡,有的飘得飞快,有的原地踟蹰。梦兮?幻兮?这下可忙坏了爱好摄影的曾小波老师,他端着单反机炮筒子,上下左右,高低远近,找角度,调光圈,咔嚓,咔嚓。
西海大峡谷还是比较原始的生态。山谷里偶尔有几只小鸟飞过,传出几声鸟鸣,啾啾——啾啾。不清楚是什么鸟,能够在这样的仙境里幸福地翔集。还有阵阵蝉鸣,知了——知了。远远近近都有,声音时大时小,断断续续。偶闻几声蛙鼓,革哇——革哇。几只蜻蜓在亭子前飞来飞去,悠闲自在。有松鼠在跟前的树枝上自由自在地跳跃,置我这个大活人于不顾。一派热闹,反倒把西海山谷衬托得更加幽静。置身云雾中间,我直观地懂得了“如坠五里云中”和“云山雾罩”这些俗语。我想起了李白笔下的描写,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仙之人兮列如麻。我想起了郭沫若笔下天街的虚无与缥缈。我还想到了西游记中那些腾云驾雾的虚幻描写,甚至想到了孙悟空天上地下的快捷交通,和仙人们腾云驾雾时的飘逸衣裾。那是何等神奇啊!我是不是已经身处仙界了呢?那些笔陡的山崖,那些山岩上或者深壑里的松树,以及在树下或者沟里生活的麂鹿、野山羊、野兔、松鼠、松鸡、飞鸟、虫虫蚂蚁们,以及峡谷里的花草树木,是否都已然成仙了呢?
峡谷里烟云笼罩,水汽湿度大,洇濡我的皮肤,黏黏乎乎。空气格外清新,负氧离子丰富,令人心脾俱爽。新鲜的空气,吸进我的鼻喉,在我的心肺脾胃里巡游一番,将我五脏六腑里的污秽荡涤一空。湿润的水汽,沁过我的皮肤,透进我的血液,在我的脉管里巡游一番,将我在世俗红尘里沾染的肮脏清洁干净。这是多么高雅多么快乐的享受啊!伸手捋撷一把云烟,做成缥缈的纱巾,送给远方伊人,或者伸手摘一朵云彩,托风儿捎给远方伊人,这是何等惬意,何等罗曼蒂克啊!
在排云亭陡峭的栈道上,有返回的游客,手扶着栏杆,在石英石上凿出的和水泥浇铸的梯步上,倒退着下行。他们跋涉累了,脚走疼了。王介甫说过,世间的美景,往往都在险远之处。要想欣赏美景,必须要有志有力有外物相助。不付出代价,哪能欣赏得到?我这双被雨水泡白泡肿了的脚,也累得不想再动了。这里的人不是太多,路不是太拥挤。趁着陈倩廖美茜何万碧她们上另一处观景台去了,我便坐在亭子里,一边欣赏西海这滔滔烟云,遐想着云海中的神秘,一边脱下鞋子,拧出鞋袜里的雨水,让双脚透透空气。在美丽的风景区里,脱鞋子晾晒臭脚,大煞风景啊!哈哈,我做了一回不文明游客呢——好在,没人发现哦。黄山也不会怪罪我,因为我还要用我的双脚,去攀登光明顶,攀登飞来石,攀登天都峰,攀登莲花峰,攀登始信峰,去采撷阳光,雨水和云雾。
采撷黄山,装进我的土布旧囊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