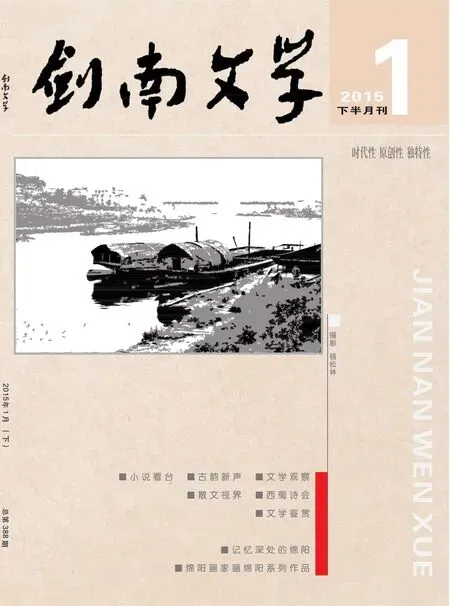论残雪小说中的意象
2015-11-22■吕晗
■吕 晗
引言:残雪是蜚声海内外的新时期先锋派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坚守着与现实对抗,与传统对抗的创作原则。她笔下的纯文学,既因为晦涩、恶心而令人“不忍卒读”,也因为直达灵魂深处而令人折服。长期以来,残雪文本在国内的解读都充满了争议。从意象分析入手研究残雪的中短篇小说,能够理解作者如何将大众眼中的日常现实变形为她笔下的那种癫狂状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早已由如火如荼转为悄然寂寞了,如今只有有限的几位作家仍在先锋派领域笔耕不辍,残雪便是其中耀眼的一位。
二十多年来,残雪小说的内在精神不断提升,思想追求日渐清晰,直指无穷尽的人的心灵世界。初涉残雪的小说世界,可能会因其错乱、压抑、焦虑、紧张以及对被害的臆想而止步,但当你深入其中,就会被作者对灵魂的深刻认识而震撼。残雪正是运用与众不同、含义深刻的意象来表现人性中癫狂的一面。
一、意象内涵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审美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和诗歌美学的重要概念,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固有元素。我国作为意象理论的发源地,长期把意象艺术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了系统的认识。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是作家的主观情感和客观景物交融互渗的产物,是作家传达情感、表现思想、升华意志的基本方式。它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主观的情、思、意、志,即审美主体;二是客观的景、象、物、境,即审美客体。一个完整和谐的意象,是意和象两个要素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感应、交流、契合的结果。残雪在创作过程中,充分把握意象内涵,广泛采用并列、对比、通感和荒诞等意象构建手法,使其作品呈现出无穷的魅力。
二、残雪小说中的意象
残雪小说堪称意象的世界。作者赋予一个个或和谐美好、或令人作呕的事物与众不同的含义,在提升作品思想深度的同时,增加了文本内涵的多义性,无意中给读者接受设置了障碍,给予读者广阔的理解空间,使各不相同的个性化解读有了意义。
(一)动植物意象
残雪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植物类意象,树、花、果等等都很常见。如《苍老的浮云》中,“楮树上的大白花含满了雨水,变得滞重起来,隔一会儿就‘啪嗒’一声落下一朵。”《天窗》中,“在冬夜里,我将细细地倾听那些脚步声,把梧桐树的故事想个明白。”《天堂里的对话(之一)》中,“那是一棵银杏在湖心水的深处摇摆,树上满是小小的铃铛,铃铛一发光,就灿烂地轰响。”残雪笔下的植物多得不胜枚举。
在《苍老的浮云》中,作者写楮树意在写其花和果,花和果是贯穿全文的一条微妙线索。如小说开头写到花香对人的影响:“一通夜,更善无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那香气里有股浊味儿,使人联想到阴沟水,闻到它人就头脑发昏,胡思乱想。”这种意象一直贯穿全文,使人无法摆脱:“楮树的花香弄得人心神不定……”“那些花儿开得人心惶惶的。”花香扰人的感受多次从不同的人物口中说出,每个人都深受其害。小说中的人物对果子的关注也很明显:“好久以来,他就盼望着树上的那些果子变红,因为他对她说过,等树上结出红浆果,大家就都能睡得安稳了。”在这部小说中,主要的植物意象是树,其中突出树的开花、结果等发展变化过程,以及这种自然过程中花香、红果与人物情绪的关系。
动物也是频繁出现在残雪小说中的一类重要意象,残雪笔下的老鼠尤为出彩。《苍老的浮云》中,老鼠频现,“天花板一角有许多老鼠在穿梭,爪子拨下的灰块不断地打在帐顶上。”《黄泥街》中,老鼠大举入侵人们的生活:“果然有一天,一只大老鼠爬到了床上,将她男人的耳朵咬穿了。”而在《母鼠》中,老鼠更成了主角,成了一家人生活的中心:“它静静地躲在我的鞋柜里头,根本就不危害谁的利益。不错,为了它,我常把地板弄得油迹斑斑,它的粪便也遗留在墙角,但嫂子并没有对我埋怨什么啊。不但不埋怨,她好像还很支持我养这只母鼠呢。”
在残雪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了鼠与人的三种关系。一是老鼠与人平等,动物与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互不干涉。如《苍老的浮云》中,“他不敢回头,像小偷一样逃窜。一只老鼠赶在他前头死命地窜到阴沟里去了。”这里的老鼠是更善无性格中卑微胆小因素的外化,他“像小偷一样逃窜”,老鼠与他的动作一致,也是“窜”,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更善无鼠一样怯懦的性格特征。二是人仰仗鼠,人们在精神上或生理上依赖老鼠,如虚汝华要依靠老鼠的咬啮声来缓解神经的剧痛,她自己也不停地咀嚼。三是鼠主宰人,人们对老鼠的存在敬畏不已。
残雪说:“不论小说中出现的虫还是动物,决不是现实中生存的虫和动物。因为那是我空想的东西。”残雪文本中的虫子、老鼠、蛇并不是先验地被设定为“丑”,它们只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随机出现在作者的潜意识建构的环境中。残雪曾多次强调孩童的眼光:“我就是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儿童的眼中没有所谓美丑,也没有社会化的世俗的东西。”“写这些动物是表现一种意境,写的时候无所谓美丑,用小孩的眼光,觉得奇特、有意思。”这说明了作者运用所谓的“丑”意象时的原则:只为遵循潜意识中的意境更好地表达思想、主题,而不管意象本身所传达的、早已被世俗规定的传统含义。
(二)器物意象
残雪小说往往以日常器物作为意象,镜子便是其中之一。《苍老的浮云》中,“我已经在后面的墙上挂了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可以侦察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方便极了。”《公牛》中,镜子更是频繁出现:“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镜子十分诡异:“我建议和他玩一种游戏,就是两人手牵手走进那些镜子里面去,我们把青虫打落在地上,朝着镜子外面吐口水。”
残雪在与文学评论家林舟进行书面访谈时说:“镜子的设置就是为了来审视自我的。”作者为每个人都设置了一面审视灵魂的多棱镜,在窥探别人的同时,也反射出自己的心灵。残雪文本也因此多了一柄直捣人类灵魂世界的利剑。
意象使残雪作品带上了寓言的特征。寓言式的作品能够打破文本在封闭状态下意义的确指,使寓意成为待挖掘的不确定物,让读者成为文本的主人。读者享有高度自由,反过来也赋予了残雪文本丰富的多义性,让阅读更有趣味。
三、残雪小说中的“意象”与“审丑”
残雪小说往往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压抑、焦虑甚至极度的紧张。这既是因为她没有采用传统的写作手法,淡化或抛弃了情节,放弃了对因果关系的交代,也是因为她使用过于繁密、奇特的意象让人难以理清头绪,更是因为她叛离传统的审美方式太远了。随着西方现代派思想广泛传播,大众对人性的理解愈加深刻:人性具有两重性,美丑并存、相互斗争,人的灵魂处于痛苦的撕裂状态。残雪的写作就处于这撕裂的空间之中。残雪将她的每个人物都视为一个矛盾着的个体。她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可是人性并非善恶两极,人性是一个矛盾,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有恶。”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残雪的作品难免会描写人性恶。
残雪用荒诞的意象、特异的写作手法与陌生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且奇诡的世界。她的小说仿佛一面镜子,反映出世界的荒谬、滑稽与可笑。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没有能力去改变生存的环境,那些崇高的、美丽的理想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对命运的终极关怀,充满了悲伤与忧虑,但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残雪的内心是那么热烈地渴望美,那么迫切地呼唤美,那么执着地追求着人类走出自身困境的崭新开始。小说对丑的大量描写正是对美的饥渴,小说中的荒诞正是对美好生活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