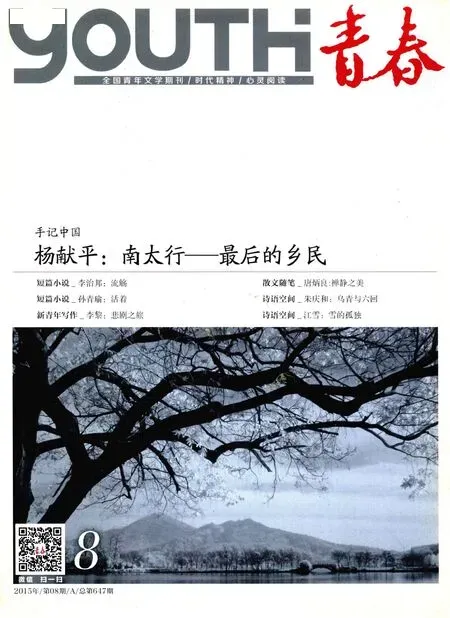悲剧之旅
2015-11-19李黎
李黎
一
下午两点,牛山坐地铁去高铁车站。他的双肩包里有如下物品:眼镜、换洗衣服、睡衣、干湿面纸、香烟、打火机、精装笔记本、《我亲爱的精神病人》(里面夹着一只红色水笔)、钥匙一串(上面还有一个U盘、车钥匙、名片、眼药水、市民卡、手机充电器、空杯、红茶、警用手电筒),当然还有钱包(内有身份证、现金两千元左右及多张银行卡、信用卡、消费储值卡和儿子幼儿园的门禁卡)。这些物品既满足了日常生活,也可以应付短途旅行。
他要去彭州,一是出差,二是为了见一见老同学程军。当年牛山和程军是死党,踢球打架逃课打游戏等都共同经历过。很多次,两个人如同情侣一样在深夜的操场上并排跑步并谈论各种话题。毕业时他们抱头痛哭,而后多年不联系。某天,牛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带着醉意说,老牛,我离婚了。
牛山愕然地问他,你是谁。
我离婚了,老牛。
牛山知道一定是熟人,大喊:你他妈的是谁啊,狗日的,快说!
老牛,我是程军。
我操,是你啊。
是我,老牛,我他妈的离婚了,哪天你来,我们喝酒,我离婚了。
他们最近一次见面就是在程军的婚礼上,距今十年。那是一次充满鸡蛋的婚礼:让夫妻双方额头顶着一颗鸡蛋来回走动,把鸡蛋塞进程军的裤筒里,然后新娘负责从另一个裤筒拿出来,把鸡蛋放在新娘的胸口让她夹住同时给别人斟酒……当程军反复说着离婚时,牛山看到了鸡蛋摔在地面,黄白相间的液体四处流淌的画面。
感情破裂了?牛山问。
破了。
后来,程军又一次带着醉意打电话给牛山,还是那句话,老牛,我离婚了,来喝酒。牛山有些烦躁,问道:你在哪,怎么感觉旁边好像很多姑娘。
你来了就知道了,我自己有一个场子。
什么场子?
皇家会所!一个姑娘大叫着回答牛山,牛老板你来嘛,我代表程总招待你。
还有我,还有我!其他几个人姑娘一起叫起来。
牛山有点激动,冷静地问:怎么招待我?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啦,我们有求必应,什么都可以的啦……一个来自南方的夹生口音回答,语气里带着必胜的决心。这让牛山很反感,他大声说一句:我喜欢看你们脱光了踢足球,你们行吗?
出现了一阵沉默。牛山喊,程军,狗日的,说话。
程军接了,带着醉意问,怎么样?
你是不是用免提了?
是啊。姑娘不错吧。
我怎么知道。哪天我去!牛山说。去之前告诉你。
当单位在彭州有事要处理时,牛山打电话给程军,问他明天有没有空。程军很冷淡,不断说你来你来,我来安排。他只是应付承诺之事,毫无热情,好在这也是确认。
地铁站里全是人,一排排乘客木然地走向等候区,他们似乎是为了证明生活无趣而存在的。但生活中有很多有趣的事在等着我们,比如去和程军喝一顿。牛山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出发了。老婆照例抱怨了几句。她不是反对,只是抱怨,抱怨没人一起吃晚饭,抱怨一个人带孩子,抱怨牛山总是在外奔波但是收入也就那么点,然后她开开心心地挂了电话。
地铁进站,牛山随着队伍挤上车,顿时淹没在脊背肩膀脑袋的汪洋大海中。他个矮、消瘦,很容易被人群淹没。牛山把双肩包放到胸前,抓着栏杆,身体随着列车的前行和人群的动荡微微晃动,一会前一会后,一会左一会右。地铁总在意犹未尽地跑,启动、加速、减速、停车,周围的面孔和服装在不断变化,姑娘变成大爷,少妇变成壮汉,本地学生的方言变成了遥远边疆的面孔。
老婆又打电话问牛山电烤箱的说明书在哪里。地铁里信号不好,几句话说得磕磕绊绊。牛山听明白后,没好气地说,就在那里。老婆哦了一声,利索地挂了电话。她知道那里在哪。
地铁继续往前,牛山用左手抓着栏杆,右手放在上衣外侧,算是保护着手机。随着临近高铁站,地铁里的人多了起来,牛山感觉自己被挤得往右倾斜了,他不由自主地伸出右手抓住栏杆。这时电话又响了,不大的声音传上来,伴随着震动。牛山非常烦躁,他知道这个电话还是老婆打来的,她大概没找到说明书。眼看下车在即,自己双手动弹不得,牛山决定不接,下车后再回过去。
下车后牛山长出一口气。车厢里太闷了,气味丰富,浓郁无比。牛山上下班都是步行,每天都路过百十家店铺和时代的变迁,也省去了公交地铁里人烟味油烟味。随即,牛山发现手机被偷了。
这让牛山陷入了同现实世界失去联系的恐惧,随即而来的是懊恼,刚才如果腾出手来接电话,或许不会被偷。这就是对最亲近的人缺乏耐心的恶果。整件事发生在几分钟之前,这几分钟的时间似乎还在眼前,没有走远,但也不会停顿和返回了。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去,过去的时间都意味着一种既成事实,它站在自己的对面,无法触及。
牛山一边懊悔,一边犹豫还去不去彭州,一边找公用电话。这同时发生的三件事让他精疲力竭,其实还要加上第四件事,就是后悔决定去彭州。那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摩崖石刻和古战场,也有当地人引以为豪的烧烤。这一切都要理性安排并且慢慢享受,自己匆匆前往,太追求程军承诺的酒色了。酒色破财,自己的手机刚买不久,价值四千。
牛山尝试借手机打电话,每一个被他挡住的人都拒绝了他。有的嘟囔着:你骗谁啊!有的说:对不起我没空。
牛山在车站值班室借用了电话,给老婆打过去,没有人,三次都是如此。在保安质疑的目光中,他赶紧递烟过去,再给同事打电话,接通后他说,帮忙在桌子上的名片夹里找到滕云的电话。马上就找一下,我等着。同事去找,牛山掏出笔记本和笔,等着记录。随后他打滕云的电话,幸好滕云接听了。牛山说,把程军的电话告诉我一下,我正在出发去彭州。
现在没有,办公室电脑里有,我现在在街道开会,回头我发给你。
发给我没用,我手机被偷了。我借车站的电话打给你的,马上就要去彭州了。
那你就别去了,赶紧去买个手机,办个挂失。
不行啊,我去彭州是出差,单位有事。说到这里,牛山发现去彭州要找的人也无从联系了。只能到了彭州再买手机,然后跟同事要相关电话。彭州一定要去,程军及其身边的姑娘们一定要见见,让手机成为一个插曲吧。
滕云想了想说,我大概一小时后回单位,我就把程军的号码存下来,你到了彭州随时打我电话。
牛山说,好,你回头有空给我老婆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手机被偷了。我刚才打了几次她都不接,发个消息也行。
滕云答应了。牛山挂了电话,再次向两位保安递烟、道谢,然后去办乘车手续。他从钱包里取出身份证和几百元现金,装在上衣口袋里,如此就不必总是把双肩包取下再背上。取了票,时间还宽裕,牛山带着绵绵不绝的悔恨和对自身愚蠢的恶毒诅咒在外面抽烟。眼前人来人往,他们这都是要去哪里?
二
牛山找到自己的座位,09排B座。A和C上面都坐着人,里面那个人正仰着头大睡,呼声大作,像往外吐着一颗颗发臭的豆子。C座是一个中年人,穿戴整齐,目光炯炯。他客气地给牛山让座,牛山把座椅调到最低,全身放松,闭上眼睛,唯有如此,才能忘记真实发生的事。
火车缓缓开动,随即高速向前,如同一颗射向山川湖泊的子弹,窗外的一切在扭曲变形,离人类远去了。
坐在他边上的人开始打电话。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因为靠得很近,牛山听到了旁边这位的每句话,也听到了电话那头的每一句话。
这里:是我啊,不忙吧。
别处:不忙。
这里:我也不忙,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你现在住哪?
别处:还是住在江北。
这里:每天来回跑?
别处:是啊,每天路上要花三个小时,每天都要早起。
这里:简直就是长途啊,你够辛苦的。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别处:没有哇。
这里:快找一个,老大不小了。你长得又不丑。
别处:没有合适的啊。我也想赶紧找一个。
这里:你是哪年的啊?
别处:1986的。
这里:我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还被催得半死。你怎么搞的哈哈。
别处:呃……哎,太失败了。现在又要过年了,哎。
这里:哈哈,是又要被逼问了。你以前交过男朋友没?
别处:以前有啊,去实习的时候刚分手。后来一直没谈了。
这里:干嘛分手。
别处:老是吵架,没有什么原因就吵了起来。后来他毕业了,去河南大学。他是河南人。
这里:一般而言,结婚一两年最容易吵架,恋爱时不该的,大家都很客气是吧,吵了就是不合适。你得再找找,不然奔三了。
别处:是啊,正在艰难地搜索中,但是总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这里:你也喜欢纠结啊,处着再说呗。
别处:哎,白羊座比较怪,注重感觉。我妈已经快对我绝望了。
这里:现在人长寿,她肯定能等到你出嫁。你注重什么感觉?
别处:我也说不出来,所以困难啊。现在也怕谈恋爱了。
这里:你不会是个那个,老处女吧。说这种感慨的人很多都是。
别处:是吧。选择一个人结婚就像选择一种今后的生活,想想都觉得恐怖。
这里:我猜对了哈。难怪老是吵架。结婚确实需要用心经营的,但中国人喜欢把它看成命的一部分。
别处:是哎,我就搞不懂为什么到这个年纪就非得结婚。结婚应该是水到渠成的。
这里:因为这个年龄是生育的好年龄,老人也快老了。
别处:看来找灵魂伴侣的可能性没有了。
这里:你这个太理想化了吧。还是先找到生活伴侣,再看看能不能进化成灵魂伴侣。
别处:估计那是不可能了。
这里:未必吧。总得有个开始,然后再慢慢升华一下哈哈。你要知道,灵与肉不分家的。
别处:真不分的话,那没那么多分手的和离婚的了。
这里:分手和离婚就是说明某处出问题了,往往还就不是灵魂。
别处:哦。
这里:触及灵魂的方式很多,语言、视觉、表演、财富、关爱、美食、性生活、异域他乡,但多数来自日常生活。你把这些都排除掉,纯粹追求灵魂它没由来啊,也找不着。
别处:(沉默一阵)哎,越来越觉得我这号的找不到对象了。
这里:哈哈你要转型升级。
别处:亚历山大。(牛山听了一阵恶心,他厌恶此类新词汇。)
这里:改天请我吃饭吧,我成咨询师了。
别处:行啊,这两天忙着搬家,等事情弄完。
这里:好的,搬进城啊。
别处:没有,还在江北,房子还是前几年买的。
这里:最好住城里,别和父母住。
别处:城里房子买不起啊。
这里:先租一个就是。
别处:我也看过不少,单身公寓太贵,合租又不方便。
这里:努力挣钱,空间和时间至关重要。
别处:存了几个月的工资都贡献出去了。
这里:什么意思。
别处:赞助装修了。
这里:哦,那你还得做好几年乖宝宝了。
别处:哎,是我主动贡献的。
这里:靠,你真好心。我请你吃饭吧,你都没存款啦。
别处:还留了一点私房钱。
这里:还是我请吧。
别处:那不行。
这里:好吧好吧,等我回去约你啊。
牛山把茶叶倒进茶杯,起身,旁边这位客气地站起身给让路,把电话紧紧按在耳边。牛山来到车厢接口处的开水供应处,往里加满开水,拧紧,随即进了厕所,小便,洗脸。出来后牛山不想回座位,不想再听到一个中年人用恋爱的口吻跟一个小姑娘说话。
广播响了,播报前方是南怀站,广播还说,因为停靠时间较短,请未到站的旅客不要下车。这似乎在提醒抽烟的人,他们纷纷走到车门边,烟拿在手里,准备出去过把瘾。牛山也决定下车抽根烟。
每个车门外都站着四五个人在抽烟。大家都谨慎而疯狂地抽着,使劲吸,腮帮子都瘪了。哨子声响了起来,火车发出嘀嘀嘀的关门声。牛山扔掉烟转身回车里,眼角的余光看到其他车厢有人正在往里走,这让他感到放心。一个人猛然间出现在牛山身前,手里拎着很多个箱子,吼着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差点耽误了……这个人连同一堆行李硬生生把牛山挤回站台,车门关闭。这时牛山看清楚,眼前是一个壮硕的中年妇女,面红耳赤,吃惊不小的样子。
火车缓缓开动,牛山大喊一声,停车,停车!无济于事。那妇女回头看看又迅速扭头走开,牛山冲过去抓住她的行李。
你把我挤下车了,我要去彭州的,我的包还在车上!
那女人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紧张。这只是短暂的,随后她大吼一声,谁让你下车抽烟,说了不要下车,活该你!说完她浑身一抖,把牛山的手震开,迈步往前走去。
牛山目送着她离开,转头,火车早已经毫无踪影。他的包还留在车上,包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件物件,它们会被人拿走,还是在审慎的旅客注视下由乘务员处理?这只可笑的双肩包已经陪伴他多年,以这种方式消失不见,既决绝,又可供想念。
牛山慢慢往出站口走去,浑身无力,被晦气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但他没有慌乱,身上有身份证和几百块钱,口袋里有一包烟一个火机,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里面装着红茶。这既满足了日常生活,也可以应付短途外出。
牛山还是决定去彭州,老同学程军以及那些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姑娘吸引力太大了。就让丢手机和丢包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插曲吧。
三
牛山摸索到售票处,在满是站名的电子屏上搜寻下一趟去彭州的火车。很多,南怀和彭州都是交通要塞。牛山放心地走到售票窗口,要买最近一班去彭州的车票。
六点钟的一趟有座位,之前的几趟都没有座位了。
我不要座位,能上车就行,牛山和售票员商量。
没有座位就是指没有票了,我这里不能出票。
牛山掏出自己那张车票给售票员看:我本来是从南京到彭州的,刚才停车的时候我下车抽烟,火车开动时我被一个急着下车的人挤下来,错过了火车。我要去彭州办事,现在这张票能不能再坐下一班车?
售票员思考了一会,用方言嘟囔了几句。牛山有点着急,补充说道,我可以坐后面随便哪一班列车到彭州,然后出站,不算逃票吧,只不过晚出站一会。服务员面带微笑,努力用普通话说:那你干嘛还要到这里买票呢?你应该一直站在站台上等着。
这算是肯定的回答。牛山愤怒地看着售票员。他对眼前的人没有什么意见,而是对眼前的事有意见。为什么我要出站,为什么站台上没有服务员,为什么刚才出站时没有人检票并提醒一下自己?
牛山转身,进到候车大厅,直奔检票口,径直走到木然的工作人员面前,掏出车票,把自己的情况和她说了一遍,带着恳求的语气说,让我过去吧,我上下一趟去彭州的车,这不算是逃票吧。
工作人员木然地看着牛山,最后冒出一句:重新买票去!
牛山耐着性子说:你看,我只不过是换了一辆车,没有多坐一站路啊,你让我进去吧。
重新买票去,高铁规定的。
牛山走近一些,看看空空荡荡的大厅,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一百元递过去说,这一百块钱给你,让我进去吧。
女人木然地看着他。牛山说,从南怀到彭州的票不过几十块钱,我赶时间。你让我进去吧。
你有病啊,重新买票去!木然的女人突然高声喊起来,充满拒绝诱惑和训斥他人的快感。
牛山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一共是五百六十元,他留下零钱,把五百元都给递过去。这么多可以了吧?我有急事,真的不是想逃票。
那女人又恢复了木然的表情,不看牛山一眼。
牛山突然也喊了一嗓子,给你一万块钱行不行?
那女人显然有些意外,一万元如同一团火一样让她的眼睛骤然睁大了,可牛山已经转身走了。
四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牛山捏着一张六点的车票。还有两个多小时。按照约定,六点不到牛山就应该到了彭州并电话程军了。牛山想着给程军打个电话。他从售票厅出来,站在南怀车站广场,看哪里有公用电话。
他首先看到了群山。南怀高铁站建在荒郊的丘陵之上,它前方是隐约的群山,此刻,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有一种神圣的光彩。牛山隐约记得,这些山曾经孕育过一位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影响的伟人,虽然伟人本身只是传说,虽然他在这里居住耕种是传说中的传说,但牛山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些山还曾经是无数战役的战场,那些战役构成了历史。但是眼下,这些山只是绿得发黑,毫无特色但散发着美感。它们有一副悠远的姿态,和时代的令人紧张的速度不相符合。它们被高速火车穿膛而过,毫无回手之力。
牛山决定去山里看看,哪怕只是山脚。他挥手招呼一辆出租车,然后和师傅咨询并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付200块钱,师傅带牛山去半山腰的禹王村,大约20分钟路程,等牛山考察一番后再负责送他回到这里。师傅答应借手机让牛山用,打几个长途。
一坐上车,师傅就把他的小而破旧的手机递给牛山。牛山给老婆拨电话,告诉她自己手机丢了,但没说背包丢失和半途下车的事,而是说已经到了彭州,借别人的手机打的。老婆抱怨了几句,非常严厉地告诫他注意安全,小心贵重物品。牛山让老婆帮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办个挂失。牛山还让老婆把滕云的电话发到这个手机上,本来记在笔记本上的,但此刻笔记本大概距离自己一百公里远了。
老婆答应照办。他们又闲聊几句,挂了电话。牛山一边看着四周的乡间景色,一边等待老婆的消息。车窗外的一切和在火车站看到的一切并无本质区别,贫穷。但这里看到的更为真切、新鲜。破旧的房屋构成了破旧的村庄,没有一个人影和猫狗鸡鸭,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很多大门上的春联只剩下粉红色的痕迹。偶尔出现的两层楼房和偶尔出现的土墙草房一样触目惊心,大部分的房子是带着夸张屋檐的平房,一排三间或者五间。偶尔出现的衣着破烂臃肿的小孩和偶尔出现的摇摇欲坠的老人一样触目惊心,村子里见不到青壮年了,他们都在遥远的战场上日夜奋战,不是保家卫国,是国家驱赶他们离开故乡,去远处觅食维生。
滕云的电话号码发了过来,牛山拨了过去。电话里,牛山告诉滕云,自己此刻身在南怀,手机背包都丢了,你把程军的电话发到这个手机上吧。滕云对此非常不解,劝牛山赶紧买票回南京。牛山推脱说,单位的事情必须要自己去彭州解决。
见劝说无效,滕云答应马上把程军的号码发过来,并关照牛山不要再误了去彭州的车。
出租车正往山坡上爬去,山路不算崎岖,铺着水泥,散发出政权的气息。两边的村子明显被拉长稀释了,三三两两的房子犹如哨兵一样守卫在半山腰。这里的房子更为破旧,而且显得冷清阴森,似乎自建好以来就没有人居住——大概也确实如此吧。
滕云的消息迟迟没来。牛山看看手里的手机,没电了。他问师傅,手机怎么没电了?师傅用方言回答,这个手机有点问题,常常在还剩一半电的时候就突然间全都没有了。
牛山把电池拆下来,再装上,试试有无可能再维持一会。但电池只够维持重新开机的,手机开机后不过几秒就嘀嘀两声,再度关机。这几秒钟里,牛山看到了有一条未读信息,但随着屏幕变黑消失了。牛山有些着急,手机已经没有反应了。
牛山有些恼火,问师傅有没有充电器,师傅说没有,说自己还有一部手机,要不要用?牛山看看师傅,没力气解释了。
他们在某个空旷的地方停了下来,最近的房屋距离他们大约五十米,这应该是村头了。前方是一大片开阔地,青山绿水,一层层随山势而上的稻田,稻田的尽头是树林,笔直密集,长势喜人,树林的尽头是蓝天,下午的温和的阳光把眼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层光泽。
牛山说,风景如画。
师傅露出一个木然而阴森的笑容,牛山递给师傅一根烟,然后说,还是麻烦你把那部手机给我用一下吧。牛山又一次打通了老婆的电话,告诉老婆,自己在南怀,在距离高铁站不远处的群山里在禹王村一带。老婆吓坏了,反复问了好几个问题,确认有南怀这么一个地方,确认牛山安全无恙,最后,她让牛山赶紧买票回南京。
没事的,去彭州的票已经买好了。六点整,不到七点就能见到程军了。牛山又说,刚才说到了彭州是不想让你担心。可惜刚才用的手机没电了,除了你我谁都联系不上,你赶紧再把滕云的号码再发到这个手机上面吧。老婆答应一声,牛山改口说,还是报给我,我背下来。
老婆把滕云的号码报给牛山。拨过去,占线。连续四五次,都是在占线。牛山想,等着吧。
滕云一直没有回电,牛山也没有再拨过去,打算到了彭州再联系。站在碧绿但显得荒芜的群山中,牛山突然对此次彭州之行产生了质疑和厌恶。这种感觉又蔓延到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己的一切都在此情此景下出现了莫大的疑问,像远处山顶和天空的交界处一样,不真切,不知道起于哪里,止于何处。感慨间,师傅递过来一根烟。牛山问他现在几点了。师傅挥挥胳膊,看看手表。四点五十。
从停车到现在,不过半小时。除掉打电话的几分钟,真正用于游目骋怀的时间很短。这只能算是对历史和人世的匆匆一瞥。但牛山觉得够了,高潮的时间一般不会长。他对师傅说,回去吧。车子发动,朝着山脚开去,牛山不再盯着窗外看,所谓的景色,新鲜感已经消失了,留在了再也不会涉足的身后。
牛山在车站外的超市里买了一包烟,早早来到候车室等候。那个拒绝让他上车的服务员还在那里,和另外两个同事聊天。牛山想走过去冲她晃晃自己手里的车票,但忍住了。一个倒霉的人何苦去冲一个陌生人耀武扬威呢,这不是羞辱别人,是羞辱自己。牛山觉得自己唯有等待,等待见到程军,等待回南京,让一切恢复常态,犹如伤口被缝合,伤痕逐渐淡去。
五
到彭州时是晚上七点。空空如也的肚子让牛山觉得精神抖擞,空空如也的双手让他显得非常潇洒惬意,他深感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太多的物件。或许这不现实,但这种身无长物的感觉确实很好。
彭州高铁站距离市区大约十五公里,最大特点是空旷,浓郁的夜色和浓重的雾霾让牛山看不清车站的全貌,只是跟着人群和指示牌往出租车候车点走去。大约走了一公里才到,等了十五分钟,牛山坐上出租车。
牛山对司机说,去鼓楼广场。那是彭州的市中心,去那里一定没错。随后牛山跟司机借手机。司机拒绝了,他带着几分凶狠说,没有手机!牛山说,我付你钱,就打两个电话,联系一下家里人和彭州的朋友。
司机说,你找公用电话吧,我没有手机。
牛山问司机,你知不知道皇家会所?
知道啊,新开的是吧。
牛山说,对,就去那里吧。
那不在新街口,那儿在城西,可远着呢。
就去那里。牛山不容置疑地说了句。这时司机的手机响了,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语气出奇的温柔,嘘寒问暖的,还不停地对着小小的手机点头哈腰。牛山扭头看着他,司机露出羞涩的表情,语气则更加温柔。
牛山听懂了司机五分之一左右的话,应该是未婚妻之类,虽然司机看上去至少四十岁了。未婚妻应该是在遥远的外地,因为他听到了“你来”“我去”之类字眼,还提到了好几次“娃儿”。牛山大致明白了司机为何不肯借手机了,放松下来,随着车子颠簸摇晃,他睡着了。
六
牛山醒来,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灯火辉煌的房间里。一张巨大的桌子堵在眼前,自己睡在一张宽大但是廉价的沙发上。他一睁眼,就模模糊糊地看到三四个人带着打架闹事的架势朝他走过来,程军熟悉但夸张的吼叫声随即升腾起来。老牛你醒了啊,你他妈的难道是跑步来彭州的,怎么睡成这个样子?
牛山摸索一下,没找到眼镜。他问,我的眼镜呢?
什么眼镜,哦,你戴眼镜的,没看到啊。程军继续喊着。他逼近牛山,拍了一下牛山的肩膀,又搂住刚才拍打过的地方,对着牛山的耳朵继续咆哮,夹杂着哈哈大笑:我等你老半天也不来,滕云给我打电话说是你手机丢掉了。可是手机丢了你怎么会火车晚点呢哈哈,后来又接到滕云的电话,说你被丢在火车站了哈哈哈哈。我就等着呗,我从五点钟就开始在这里等你给我打电话。老牛啊,这么多年你从来没主动联系过我啊,从来不打电话给我,连他妈的到了彭州也不打。
牛山插了一句:我来之前不是给你打电话的吗。
那不算,你到了彭州之后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坐上车子就直奔我这里。你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我正好在门口候着的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我的眼镜呢?
没看到,你们他妈的有没有看到?他扭头对其他几个人影喊道。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看到。一个小伙子说,大概是刚才从出租车里拖出来时给弄掉了。
你是不是跑来彭州啊,怎么睡得跟死猪一样,我让四个人才把你给弄到这里!你还抓着茶杯。
我怎么会到这里的,我不是在出租车上的吗?
是的,你是在出租车上的,那司机往老子门口一停,就坐在那里打电话,还大哭,不知道发什么疯。我正好在门口晃悠,伸头一看,是你狗日的,当时我就傻掉了。我过去把司机的车门踹开,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让他给送到这里的,他电话里谈着急事,说是未婚妻不肯结婚了,他活不成了。看见你睡着了,就想着打完电话再让你下车。
牛山哦了一声,程军接着说,太巧了,我看你狗日的是累惨了,让人把你弄过来,然后把司机打发走了。
我的眼镜呢?牛山大声问道。
都说没看见。程军说,实在太巧了,我正好在门口晃悠,不然哪能这么快见到你,如果我出去办事情,我们还见不着了。
牛山笑笑说,我眼镜没了,现在我都不确定你是不是程军狗日的。程军哈哈大笑,拍着牛山的肩膀说,但是我一眼就看到你了。你到底忙些什么事情了,在这儿还睡了这么长时间。
我睡了多久?牛山随口一问。
整整一天,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害怕你醒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