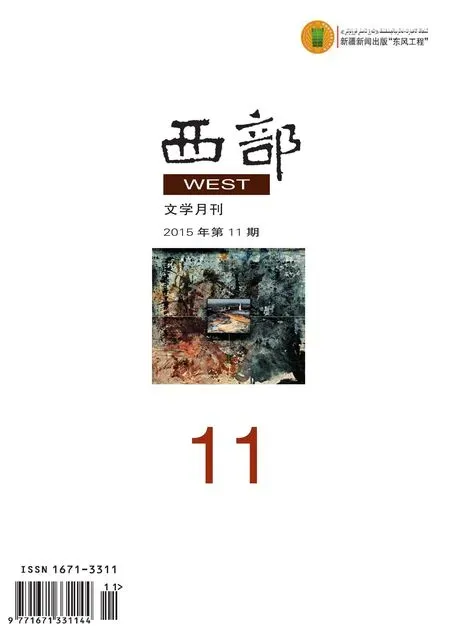敦煌意象
2015-11-19方健荣
方健荣
敦煌意象
方健荣
敦煌
敦煌。西域高地。
丝绸的古道飘在天上,一群神仙和一群凡人都依着心灵的呼唤风尘仆仆而来。
敦煌,盛大辉煌的城堡,坐落在漠海与天空相接的地平线边缘。天边的城堡,犹如残缺的夕阳,一个绝美的黄昏擦过一位游人身边。骆驼在充满东方情调的背景下走入天边。
金属质地,银子般闪亮的敦煌,被柔软的手抚摸,像抚摸一件古旧而美丽的玉器,这种感觉不是把玩,而是崇敬心情默默地流露,生怕一不小心失落在地会打碎的心情。进入敦煌,便一直把心稳稳地放在胸膛里,让这只鸟呆在笼中,让时间失去翅膀。多像一个朝拜者,敦煌以大佛、壁画、古建筑和你看不到却可以想到的许多力量吸引着你。不如让一匹马驮着,不问从何处来也不问到何处去,只横吹一支羌笛,任之悠悠于天地。
敦煌不是静物,但很安静。你可以感到衣袂飘飘的大智大慧者来无影去无踪。一只渡船漂在月牙泉上,水光映着山色。三危山在另一幅画里,九层阁是一个象征还是一个比天更高的启示呢!高楼飞檐,苍松翠柏,曲径通幽,而某个牌坊的红色柱子发散出一种不朽的光芒,细看,柱子上有岁月斑驳的蚀痕。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都处在心灵和生命最和谐的地域,处在一种宗教般神圣的状态。
敦煌不是风景区,传说和历史已经很是巍
峨了,飞天是梦幻的女儿,敦煌有精神世界里的那些洞窟,那些灵魂的居所。在地球的一侧,敦煌用佛教这根命运线串起了文化的珠子,这些珠子闪闪发亮,滚动在众人的指间。
青灯高擎在谁的手里,一定不是长跪者,我想,一定是默默无闻的开拓者。他们一寸一寸击凿着岩石,用生命调和着颜料,创作出富有感情,栩栩如生的形象,让自己的向往也处在灵魂的高地。
敦煌是有是无呢?而我企图挖掘出些什么?我感到无能为力了。
敦煌不需要说,那本名叫《敦煌》的灰色画册谁都可以买到,人们会产生一种什么心情,会不会说:敦煌不过如此。
天空
这里所具有的魅力不仅仅是外在的,我常常有一种神魂俱销的感受,似乎一切在一瞬间神秘而悠远起来。这时我深深地被内心里缥缈的想法吸引,达到了某个边缘,忽略了具体而真实的敦煌风光。我注意到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天空。
坐在沙粒组成的高大山体之上,身体是疲惫而柔软的,这时候看天,极富有情致。其实,天上会有什么呢?真正要看时它显出的博大蔚蓝似乎融化着雪一样的云片,似乎天空是丝绸,偶尔就从某个地方能看到抖动着的闪闪的光,这真是令人惊讶的错觉。静静的夏日黄昏,风吹走了鸟儿,天空永远是被水洗过的清明,不禁有纵身一跃的冲动。天很低,有时它却高,有时又自然垂下来,风吹时它飘动着,似乎就在我的身上。除了在这样的静谧里久久沉浸,我喜欢流云,被谁撕成丝絮状的流云,在蓝天的衬托下,更加洁白而轻飘了。它们缓缓而来,移过我的头顶,又缓缓而去。有时它们像一些生灵,似乎也为看到大地上的迷人风景而激动不安,因而天空显得越发空灵和诗意。默默地体尝这韵味,不知不觉天上缀满了星星。
我还常常听到一种声音,遥远的,像水从天边涌来,像一万只鸟儿扇动的翅膀,像一万匹骏马奔腾而过。这时候我的内心被擦得干干净净,像一个器皿一样置于天地之间,让所有的声音把它灌满,有时它承受不了,就让声音溢出来,钟鼓齐鸣般地回荡,我发觉我的身体、山体和大地都被这声音浮了起来,轻轻地像水上漂零的落叶。呵,天籁,我觉得我的生命里有一万种乐器,那些小小的音符从柔长的弦上飞溅而出,从沉默了很久的号角里奔涌而出,一瞬间把我击倒了。这时我的脚下是柔软的,好多花花绿绿的人踩着沙粒,每个沙粒里都包含着巨大的雷声,天空在每个人的胸腔里,振荡着骨节与品质,人们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似乎身上的一万双耳朵都经历了一次春风的洗涤,淋漓而痛快。
等一切声音消失之后,天空里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心情的水面也平静得找不到一丝涟漪,一丝波纹。而柔软的沙粒,还从指缝里流泻而下。没有风,绿洲上的树在干燥的阳光里静静伫立,一副希望者的深情形象。
天空不仅仅是你看到听到的那样,有时你不知不觉便走进它的怀里了。似乎无所依靠又似乎自由自在,这种大梦无边是古人也有过的吗?我们梦想进入的天堂,却原来是一种飘飘欲仙之感。敦煌是梦之所在。伎乐们翩翩起舞,脚铃手镯清脆悦耳,裙裳鲜艳美丽,她们飞翔,把我们的好多向往变成梦
的闪光。星辰暗淡,月光如雪,千万只猩红的花朵飘落在梦柔软的脚边,漫漫风沙的丝绸之路也成了飘带。敦煌似梦非梦,似醉非醉,美酒的芬芳阵阵飘荡,恍如隔世,在千年以前,把酒临风,激扬文字。这时我已进入一幅壁画,这种梦游是飘然于天地之间的,忘乎所以的,因而也是自然而然的。最好是在九月,这种梦之所钟的心情被一辆旅游车带到更远,因而你感到敦煌也是别具一格、动人心魄的。在玉关它是诗的春风,在阳关它是一匹马,在鸣沙山它是一缕缕皱纹,在莫高窟它是一颗星。这敦煌之梦,因而永远高高在上,它是天梦。
我久久地跋涉追寻,风尘仆仆在游人们的行列里,打动我的,是一束光,一种声,一个梦。敦煌的天,像来生的家,我飘泊的心,在无边无际中渐渐靠近。
沙粒
如此多的沙粒,一粒一粒堆积成了敦煌的早晨,一粒一粒流泻成敦煌的夜晚。当我一头扑向鸣沙山的怀抱,那满天满地的沙会让心灵落进一个无比远大的世界,这么多的沙粒,这么多的群山,绵延起伏,像一首柔长的乐曲,遥远无限。
带着亲爱的人,坐在一起一伏的骆驼上。那么多的人,从天南地北,悄悄地汇聚成了驼队的风景。在鸣沙山中,他们也仿佛是被风吹来的一粒粒沙,那么渺小,而心中的思念,又让他们温柔无限。这完全是诗意的境界,梦幻的天地,在这里,一切都纯净遥远,只有沙,只有摇呀摇的驼铃声,只有心儿,在风中发出来的轻微的欢乐。
沙地上是脚印,那么多的脚印,混淆在一起,没有人能够找到自己走过时留下来的。脚印与脚印连在一起时,仿佛是水波荡漾出来的海滩。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一片海洋思念一片沙漠,也许会吧!何况这是敦煌。
当我们攀爬着那巨大的沙山,一步一陷地向上,再向上,光着的脚在沙里的感觉是十分享受,仿佛身体与沙粒紧紧地相拥着,与它们一粒粒的交流、寸步不离。到达山顶的一刻,是豁然开朗的时候,天远地小,一览无余,这就是敦煌某个高处了。在鸣沙山上,举目远眺,是一生中快乐的事。坐在如刀刃般的山梁上,看远远的山上坐着三个人,仿佛几只鸟儿在天地之间。这是一个大境界,沙山绵延成了流水的篇章。波涛汹涌,高高的山丘与深深的峡谷柔和地挥洒成长长的线条,让人无从出入,无法言说。其中的奥秘只能在心中默默体会。山风吹过来,夹杂着沙粒打在人头上脸上身上,好爽快的感觉。大自然对人类是如此的多情,找到了亲近的自由,怎么会轻易走出这个神秘悠远的天地呢?
太阳落下去了,天地一派肃穆、寂静,那道晚霞像是一片光亮的伤口,一个英雄的光荣之伤,让我久久地凝望,沉浸在这远景之中。坐在山上,在高处只有自己,却不想别人,那么多的沙粒,像我内心的思想,一粒一粒地组成生命中最美的风景,组成了敦煌的巨大沙山。我有时候会想这里的沙粒也许是世上最小的沙粒了,这里的沙漠也许是世上最美的沙漠了,没有来过这里的人,永远不会有这静静沉淀在越来越黑夜晚里的感受。
捧起沙,让沙粒从手心里悄悄地流泻,一次又一次,不知有多少沙粒从命运之手中流淌。如梦如诗,沙粒,这小小的珍宝,包含着多
少人生的真理,让我捧在手上,捧在心上,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这回忆也像敦煌的那些细碎如尘的沙,永远在这沙漠里,风会吹出皱纹,吹掉皱纹,留下脚印,吹掉脚印,而那一粒粒的细沙,永远如往事一般,从我们的心上流泻着,沉淀着,成为一片沙漠的天地。
一粒沙,一粒沙,与敦煌紧紧挨着,仿佛脸上的一滴清泪,仿佛梦中疼痛的想念。
青灯
我看到青灯了。
我反复看着这盏陶制的灯,它似乎更适合我此刻触摸敦煌的心情。实际上,它不是静静地放在某个地方的,而是更适合于被人端着,随时走向黑夜。而我此刻更感兴趣的是曾经端着它一寸一寸凿击着黑夜的那些无名者。我已来到敦煌,面对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洞窟,我借助想象的力量抵达那青灯照耀的生命意境和沉默心灵了。
尾随的游人们如游鱼,从一个门里游出来,又从另一个门里游进去。他们走马观花,匆匆而过,许多人仅仅是看一眼,甚至连稍作思索都来不及,就又错开一次与古代艺术对话的机会了。带领他们并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的导游手持电筒,速度极快地从彩塑、壁画前走过,仿佛几千年就是眼前的一瞬间,然后一切又重归于沉寂与黑暗了。
在尾随者鱼贯而行的队伍里,领略那些绝美手笔留在岩石或泥土上的思想痕迹的时候,我眼前一亮闪出桔黄花朵般的古朴灯光和灯下以各种姿势艰难地勾画形象、涂抹色彩的无名画工。也许他们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工作的意义,更不会想到他们创造的劳动成果会让全世界瞩目。他们只想靠自己的技艺挣几个钱,然后打起行囊回趟家看看妻儿,尔后再端起这盏小小的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画下去。有时他们画着心里一些美好的想法,有时他们不知不觉把自己也画了进去。他们进入了一种神圣的生命状态,连自己也忘了。而他们又肯定为某件杰作感到特别得意过,因而自我欣赏一番。从英俊少年到白发老头,他们没有别的追求,唯一能让他们平静下来的就是左手的灯、右手的笔。他们的一生是平淡得不能再平淡了,像莫高窟前面的大泉河,从活泼的流动到最后的枯竭,而在生命的过程里似乎已经留下比生命本身更为悲壮的东西了。
翻开史书,可以看到敦煌这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中西方经济文化在此交流,但也不乏战争。也许那些无名画工正是不愿卷入战争才找到敦煌莫高窟这片清静之地,在这片乐土上从事默默无闻又乐趣无穷的工作。而他们的绘画也是那个时代侧影的真实反映。他们塑造的一个又一个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生动飘逸、富有生活气息。在这一幅又一幅绝美的壁画前,我们内心产生的是景仰是赞叹还是深思?
又看到了青灯,想起那些攀爬在壁面上勇敢地向着艺术领地拓荒的开拓者,他们那么真切地用博大的心灵营造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洞窟,营造着未来和明天。
我多想拥有一座洞窟,我想把心灵当作第四百九十三个洞窟,用印有飞天的洁白手绢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整个生命去开掘,而照耀我的,永远是一盏暗淡的青灯……
三危山水声
从白天到夜晚,走了一路,在石头间清澈激荡的水声响了一路,我们一直向上游去,而这条河流一直向下游流。这是三危山的一道山谷,天黑之后,我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就在草地上点起篝火,一边休息,一边补充体力。
离水很近,我两手抱住脑袋躺在一块石头上。山很高,星很亮,水声很大。这时候我才敞开整个身体、整个心灵,倾听到如此富有力量的水声,这种声音似乎包含着一种冲动,想冲刷一切,摧毁一切。在这山谷里,它流淌了多长时间?
整整一夜,这种声音像从心灵深处流淌而来,那么久远,让人心驰神往。一个人坐在水边的石头上,只听这水声,像生命猛然间透明了那样淋漓尽致,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倾吐衷肠,不夹杂一点儿别的想法,一切都是原始的、最初的。
当听着这水声的时候,自己便被自己融化了,自己便被自己感动了。
这种声音,让我体会到宁静、辽阔和深远,让我枕着它,整个夜晚都不想睡去……
禅定的微笑
多少次看到那尊禅定佛的微笑。每每看到,都会久久凝视,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还有身体和心灵,仿佛变得空空,没有一丝念头,只把内心和眼睛都交给了他。我静静地屏住呼吸,神色虔诚,似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一片静寂,连我的心跳声也听不到。
我沉浸在这样没有杂念和喧嚣的时光中,在一座敦煌的洞窟里。我的姿态是仰望着的姿态,我深切地明白,他还活着,一千多年的时光,他没有变老。在这么长的时光河流冲刷中,有多少花朵凋谢了,有多少星辰坠落了,有多少心灵破碎了,有多少过客化作灰烬了,他却那么柔和那么平静地坐着。人世间的那些伤、那些痛他没有感到吗?人世间那些丑恶和腐败他没有看到吗?他只是在一座小小的洞窟里,一坐就是一千多年。他的微笑,不知道感化了多少人,不知道照亮了多少心灵。他从来没有说过,也从来没有想过,他背靠着的墙壁上,有斑驳的佛光的痕迹;他的高高发鬓显示出生命的高贵,他的赭红色的袈裟,那些流畅的线条是多么诗意;他叠在一起的双手,多像人间那一双双善良的手;而他的眼光,一千年来竟没有染尘,那么清澈。他盘腿坐着,尽管他的膝盖也破碎了,而他似乎没有知觉,没有一点疼痛,他太安详了,他的胸膛里不过是泥土,他的身体不过是泥土,可他却活着。真敬佩那个塑造了他形体的工匠,是多么伟大的工匠,却没有留下名字。
今天有不少画家画过他的微笑,我的朋友高山不止一次画他。我好多次看到这微笑,除了震撼,除了凝视,我内心似乎一次次被净化了。
这是莫高窟第二百五十九窟北魏小小洞窟里的禅定佛,他身披袈裟,沉思的眼神,恬淡的微笑,像一道照亮内心的亮光。
这是最含蓄的东方的微笑,我又一次久久凝视。
大佛
终于感觉到这净地的神圣了。仰视一尊
大佛正襟危坐。
此刻,有无数朝圣者正沿着向西的道路而来,他们是抬着一颗颗高贵的头颅,凝视在大漠绿洲中高高矗立的敦煌。
四周静静的,这是一块有灵性的宝地,远离闹市,是彻底走向内心的大佛选择的山和水,是灵秀的凝聚。大佛背靠山岩,他的背景是精美的图案。你完全可以感到他是活的,目光平静地俯视尘世,修长的眉毛,下垂的大耳,平整的鼻梁,敦厚微闭的嘴唇。他的表情和蔼极了,肤色很有质感,连他身上的袈裟也似乎随着一阵清风就会衣袂飘然起来。
对这一切大佛似乎浑然无所知,也一无所求。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从他身边悄然远去了,大佛依旧在三危与鸣沙之间,而凡人依旧风尘仆仆地赶来寻找敦煌。
当我们坐着旅游车离开莫高窟时,那座九层阁像过电影一样翻开敦煌的一幕又一幕,而扉页上的大佛竟然是又熟悉又陌生,令人不禁凝然沉思良久。
大佛在哪里呢?大佛在心里吗?
像许多人一样,我许了个愿。敦煌大佛,一个美丽又神圣的谜,铭刻在我生命的洞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