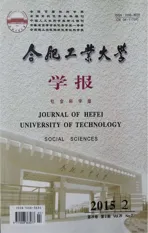结构·句式·意象——论穆旦诗歌的语言形式创新
2015-11-18黄倩倩
黄倩倩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南昌 330013)
中国诗坛自胡适尝试白话诗以来,一直把突破形式作为主要目标。胡适先生首开新诗风气,主张打破传统诗歌的窠臼,但是“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使新诗真正在文坛上立住脚的是郭沫若,但其在形式方面“素来也不十分讲究它。……只是我自己对于诗的直觉,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若是出于‘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人赏玩了”,所以他主张在诗歌形式上“绝端的自由,绝对的自主”[2]。但是由于对形式过于自由自主,新诗开始出现直白浅露、缺乏美感的弊端。闻一多清醒、理性地看到新诗发展中的不足,极力倡导新格律诗,提出“三美”的要求,从声音到视觉,从内容到形式对新诗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希望新诗走上一条规范的良性发展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发现格律诗不能满足情感宣泄的需要,因此他提出自由诗体,认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所谓形式,决非表面上的字的排列,也决非新的字眼的堆积。”[3]因此戴望舒融合中国古典诗歌之朦胧、法国象征主义之神秘,形成了精致含蓄的诗风。另辟蹊径超越这座高峰是穆旦等40年代诗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精致含蓄的风格不再适合于40年代战乱频仍的中国,同时标语口号式的呐喊又达不到诗歌的美学追求。因此穆旦吸收西方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与中国新诗的探索成果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诗歌语言形式。本文试图从整体结构、句式和意象三个方面探讨穆旦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创新之处。
一、穆旦诗歌的整体结构特色
闻一多“三美”理论中的“建筑美”要求诗歌要“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4]。陈本益先生进一步将建筑美划分为两类:“均齐形式的美”和“对称形式的美”[5]。前者指诗歌在句式、节式和体式上是均齐的,而后者则不要求每节诗歌的整齐划一,但是节与节之间的排列方式是一致的。在穆旦以前的诗歌大都属于“对称形式的美”这一类。虽然穆旦的诗歌也不乏对称之作,但是更引人关注的是那些看似“杂乱”的诗歌,这些杂乱的形式都是诗人独具匠心的设计。穆旦在诗歌整体结构上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诗体的交错、诗行切割和拟诗剧形式三个方面。
(1)新旧诗体交错 穆旦在《五月》中大胆使用了戏仿旧诗体和现代新诗体两种形式交错排列。第一、三、五、七、九节诗歌是戏仿古诗体,描绘古代美好的田园生活:“五月里来菜花香”、“布谷流连催人忙”、“落花飞絮满天空”等等。第二、四、六、八节的现代新诗体描绘四十年代的中国现实:“勃朗宁、毛瑟、三号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一个封建社会搁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里”,“流氓、骗子、匪棍,我们一起,在混乱的街上走”[6]。单纯描写现实生活苦难和虚伪的诗歌比比皆是,但是穆旦用两种诗体的交错让读者直接从视觉上感受到矛盾,并将古诗体和新诗体在诗歌形式上的对比、古代生活和现代生活的对比、诗体与现实的对比融合在一起,三重对比也使读者的感受不断叠加。
另外,如果细看穆旦所创作的古体诗就会发现,这些诗除了字数和句数外都不符合古诗体的要求。例如诗歌第一节:

平仄上并不符合七绝仄起式的要求,而且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并不符合古诗语言典雅的要求。穆旦正是用这种形式与实质自相矛盾的古诗体来衬托新诗体,凸显新诗体所表达的主题。
(2)诗行切割 穆旦在诗行切割上突破传统方式,扰乱了正常的语言秩序,这种独特的诗行切割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是破句断行。诗人经常将一句话割裂在两行中,达到扩大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例如《线上》:这时候,他一身担当过的事情/碾过他,却只碾出一条细线。诗人将“碾过他”与主语割裂开,在最后一句形成两个“碾过”的连用,“碾”一般指沉重的大型的东西,但最终碾成的细线却是微渺的。现代人从自然走向文明,但是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在不断丧失。人们所做的工作看似获得权威和声誉,实际上只是巨大工业链条上极小的一环。诗人通过破句断行凸显了“碾过”与“细线”之间的矛盾,表现出人生的荒诞和渺小。
二是破行断节,这种诗节之间的断裂既能凸显主题,又能让读者感到新鲜奇特。例如《控诉》:
我们看见,这样现实的态度
强过你任何的理想,只有它
不毁于战争。服从,喝彩,受苦,
是哭泣的良心唯一的责任——
无声。在这样的背景前,
冷风吹进了今天和明天,
冷风吹散了我们长住的
永久的家乡和暂时的旅店。
“良心的责任”诗人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将其放在下一节诗歌中,诗节之间的空行就好似良心的无声一样,无话可说,展现出人们在苦难和恶势力面前的软弱无能,完全没有抗争的觉悟。同时又将前后两节诗歌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软弱和麻木才使得苦难更加深重,就像“冷风”一样吹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穆旦的诗歌在诗行切割上所体现出的这些“标新立异”之处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形式的新奇,而是为了更好地凸显诗歌的情感与主题,表现出了形式与情感的紧密契合。
(3)拟诗剧创作 袁可嘉提出实现新诗现代化的方法之一就是新诗戏剧化,而穆旦创作的三首“拟诗剧”[7](《神魔之争》、《森林之魅》和《隐现》)正是对新诗戏剧化的实践。诗剧的形式允许一首诗中出现不同的角色,这样诗人就可以将内心的矛盾通过不同角色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神魔之争》中诗人用“神”、“魔”之争展现了人性的矛盾,用“东风”和“林妖”代表着永恒的生命和普通的人生,在四个角色的争论、独白、合唱中展现了生命的短暂、荒诞,以及众生的蒙昧无知。穆旦是真正通过角色形象来思考的诗人。
除了角色设置之外,穆旦还可以通过诗歌的内在结构实现戏剧化。以穆旦最受人关注的诗歌《隐现》为例,全诗分为宣道、历程、祈神三个部分,也就是戏剧中的三幕。第一幕宣道可以说是诗人内心痛苦的自白;第二幕历程,分为情人的自白、合唱、爱情的发现和合唱四部分,通过角色的语言来表现人生的历程;第三幕祈神,在经历了对社会、对人生、对人类历史的绝望之后,主人公开始向上帝倾诉,但上帝只是虚幻的安慰,“生命的源泉”永远不会流入“枯竭的众心”。
另外,穆旦还将戏剧化的手法运用于许多诗歌当中,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诗人直接将防空洞中人们的对白放入诗中,《从空虚到充实》则是设置戏剧性片段,借助戏剧化的手法从侧面反映诗歌主题。
二、句式的陌生化
穆旦内心丰富的痛苦和矛盾,使得他必须在诗歌中寻找宣泄的出口,所以他的诗歌自然而然呈现出许多矛盾、不和谐的地方,这就造就了穆旦的诗歌在句式上的陌生化。陌生化作为一种自觉的、明确的文学理论是由什克洛夫斯基在《论散文理论》中提出的,“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8]。穆旦自觉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当中,不让我们在习以为常的词语前流畅地滑过去,以艰涩的新鲜拉住我们的注意力,迫使我们打破思维和语言的惯性。这种陌生化的句式在穆旦的诗歌中主要表现为悖论、反讽和欧化三个方面。
(1)悖论式的词语组合 “悖论”一词原是西方古老的修辞学概念,西方“新批评”派干将布鲁克斯于《悖论语言》一文中提出“诗的语言是悖论语言”的论断,其特征为:“它把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紧密连接在一起。”[9]意指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却的确具备可行性的陈述。穆旦的《出发》可以说是充满了悖论的一首诗:
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
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
被大量制造又被蔑视
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底意义;
在你的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
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试看诗歌的最后两节,善感的心灵本该歌唱内心的哀喜,但是由于歌唱的内容与现实相反而成为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却得不到重视,而是被否定、僵化;紊乱却能够成为真理。这些悖论式的词语表面看来充满矛盾,但是联系诗人写作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就是现实的写照。战争带给人们巨大的苦难,但是在战争的年代个人的悲哀却是那么渺小。我们在这战争的世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将这些悖论当做是真理来相信,只能自觉地去承受苦难,才有可能得救。
悖论式词语的另一个作用是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例如《合唱二章》中“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干燥”和“卑湿”相对,却都是形容草原。实际上穆旦是分别描绘了草原在秋冬季节的萧瑟和春夏季节的旺盛,这样简单的四个字却展现了草原的季节变化,扩大了诗句的时空感。“多少欢欣、忧郁、澎湃的乐声”,用三种不同的情绪来形容乐声,为炎黄子孙的“勇敢、虔敬、坚韧”感到“欢欣”,为“辟出了华夏辽阔的神州”而“澎湃”,为人们的“痛苦、死难”而“忧郁”,这一句话虽是在形容乐声,却同时表达了诗人的三种不同感受,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
(2)反讽的运用 如果说悖论是直接将矛盾双方并置,那么反讽则是只出现一方,但是细读之下就会发现其与真实情况的矛盾,从而达到反讽的效果。穆旦汲取反讽的技巧,特别善于用语境的矛盾来颠覆语言的本意,使诗歌内涵更加含蓄。在《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有这样一节:
谁知道农夫把什么种子洒在这土里?
我正在高楼上睡觉,一个说,我在洗澡。
你想最近的市价会有变动吗?府上是?
哦哦,改日一定拜访,我最近很忙我站起来,这里的空气太窒息,
我说,一切完了吧,让我们出去!
但是他拉住我的手这是不是你的好友,
她在上海的饭店结了婚,看看这启事!
单独看这一节诗歌完全不知道诗人在表达什么,实际上这是人们遭遇空袭躲入防空洞后的对话。人们惧怕死亡,但又没有改变命运的觉悟,只知道暂时的躲避。一旦躲过了危险,就展现出冷漠麻木的本性。诗人通过语境巧妙地将诗歌的内容转变了,本来零散的对话,成为了讽刺的工具。
另外,穆旦还善于用轻松的语气表现重大的主题,用严肃的语气来写微不足道的小事,造成荒诞与严肃、轻松与沉重交错的复调效果。《退稿信》一诗是模拟编辑的口吻来诉说退稿的理由,“黑的应该全黑,白的应该全白”是对当时文学界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讽刺。“要列举优点,有一、二、三、四、五/只是六、七、八、九、十都够上缺点”。这里只是列了序号,根本未说明具体的优点和错误,明显是敷衍之词。第三节说“真人真事不行,假人假事也不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这些理由振振有词,实际上都是强词夺理,蛮橫无理的要求。诗人用严正的语气写的却是荒唐的退稿理由。
(3)欧化句式 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欧化现象是由始至终都存在的,所谓“欧化”,傅斯年说,“就是直用西洋人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10]穆旦诗歌欧化句式最鲜明的表现就是长句的增多。外语的语序与汉语不同,可以将修饰限定成分后置或者提前,方便了长句的使用。既可以突出主要信息,又可以给句子无限增容。穆旦诗歌中的长句比比皆是,《漫漫长夜》中一句话占用了七行:
那些淫荡的梦游人,庄严的
幽灵,拖着僵尸在街上走的,
伏在女人耳边诉说着热情的
怀疑分子,冷血的悲观论者,
和臭虫似地,在饭店,商行,剧院,汽车间爬行的吸血动物,
这些我都看见了不能忍受。
这句话中前六行都是同位语做主语,因为长句的使用使得穆旦可以将主语扩展到“梦游人”、“幽灵”、“怀疑分子”、“悲观论者”、“吸血动物”五类人。同时,在形容这五类人时也加入了大量的修饰成分,尤其是最后的“吸血动物”,用定语说明了地点(“饭店,商行,剧院,汽车”)、动作(“爬行”)和形状(“臭虫似的”)三个方面的特点。
另外,穆旦在写长句时,尤其善于通过英文语序中的状语后置现象来调整诗歌的节奏。例如《从空虚到现实》:
呵,谁知道我曾怎样寻找
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
当一阵狂涛涌来了
扑打我,流卷我,淹没我,
从东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
这一节诗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诗人将状语后置,先给出心灵的呐喊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从第三行交代事件的开始,第四行到事件的高潮,第五行忽然从顶点坠落,最后一行是最后的哀叹。这样的倒置使得诗歌的节奏一波三折,读者的情绪也在文字的牵引下不断起伏。如果按照正常的语言习惯,将第一二行移到最后,就是事情的起因、发展、结尾,是一条直线,缺少起伏。这就像是电影的刚开始先把男女主角的内心独白放在观众眼前,引起悬念,之后再慢慢叙说事情的原委。
三、现代化的意象
中国意象论起源于哲学,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意象运用于文学领域,《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1],说明构思时须将外物形象与意趣、情感融合起来,以形成审美意象。在西方意象论的基础是心理学,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指出“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感情的复合物的东西”[12]。虽然中西方意象论起源不同,但有一个共识:“意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融合统一,两者缺一不可。本文所探讨的穆旦诗歌中的意象,也是融合了诗人主观情感和意志的客观物象,是主客观的统一。穆旦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在意象的使用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化特点。
本文所探讨的穆旦诗歌中的意象,也是融合了诗人主观情感和意志的客观物象,是主客观的统一。穆旦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在意象的使用上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化特点,不管是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意象,还是苦难复杂的身体意象,其中都蕴含了诗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矛盾和痛苦,即使是古典诗歌中频繁使用的自然意象,穆旦也赋予它们现代生活的特殊含义。
(1)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意象 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给穆旦的诗歌提供了大量的新意象,这些意象和现代都市生活息息相关,诗人用这些意象展现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缩影,“报纸”、“汽车”、“公路”、“火炬游行”;并且进一步构筑出了现代人不同的生活方式,“电视”、“咖啡”、“百货公司”“八小时工作”和“办公室”。但是,穆旦对于这种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表现出了清醒理智的认识,看到了隐藏在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背后的冷漠和虚伪。在穆旦的诗歌中“八小时工作”不过是将人们禁锢在一个个小小的办公格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越来越冷漠。而“百货公司”被一个个“玻璃柜”分开,“店员打恭微笑,像块里程碑”,让人觉得虚伪。但是即使是这样“阴暗的生的命”,诗人仍然愿意面对两条鞭子的夹击,希望能抵抗住第二次“蛇的诱惑”。诗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短暂的物质享受只会带来另一种死亡,所以必须不断抗争,渴望接受苦难的折磨并改变这种虚假的社会现实。
(2)苦难复杂的身体意象 穆旦作为一个现代人,要打破传统的束缚,就必须肯定个体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穆旦通过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感受外界生活,让生活的痛苦和压力通过身体意象表现出来。穆旦笔下的“脸”是“厚重、多纹”的,“眼睛”是“干枯的”,“身躯”是“粗糙的”。但是身体的苦痛并不是生活的终点,在苦难之后往往都蕴藏着胜利的可能。例如《古墙》中“古墙”无疑是战争中满目疮痍的华夏民族的象征,诗人用身体意象来表现衰老,但同时精神却从不曾屈服。“当一切伏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的是坚忍的古墙”。
穆旦的身体意象中有一个是诗人最为赞赏的,就是“肉体”,“肉体”与其他身体意象不同,它充满原始的野性的力量,是诗人不断斗争的生命潜力,蕴藏着能量和希望。诗人在《春》中就开始意识到了肉体的存在,它像春天一样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同时又存在着危险,“暖风吹来烦恼”,满园的“花朵”成了欲望的化身。所以“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永远地迷惑着,所拥有的无限的能量和理想“却无处归依”。在《我歌颂肉体》中诗人是毫无顾忌的赞美肉体:“但它原是自由的和那远山的花一样,丰富如同/蕴藏的煤一样,把平凡的轮廓露在外面/它原是一颗种子而不是我们的掩蔽。”
(3)脱胎换骨的自然意象 在穆旦诗歌中,即使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自然意象,诗人也对之做了现代化的改造。中国传统诗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很多意象因为诗人们的频繁使用形成了固定的含义,尤其是自然意象含义更为确切。然而穆旦却给这些自然意象赋予了具有现代性的新涵义,打破了传统的固有观念。以中国传统诗歌最喜爱的意象“春”为例:传统诗歌一提到“春”不出表现春的美好或是叹息春的易逝,然而在穆旦的笔下春天是骚动不安的,《春》中既描写了春天的生机勃勃,又写出了年轻人像春天一样喷薄而出的欲望。这里的春天包含了欲望带来的苦与乐、悲与喜,当时年轻的穆旦还为这矛盾的欲望而感到茫然无措。而另一首诗《发现》中也使用了“春”的意象,“春”代表着合理的欲望,是应该被肯定和尊重的。诗人通过对“春”的礼赞肯定了欲望的存在,正是这些欲望唤醒了人们麻木的心灵。穆旦诗歌中这种突破传统的意象有很多,像是“风”,在穆旦的笔下几乎找不到和风细雨,基本上都是“狂风”、“巨风”、“暴风”、“冷风”,这个本属于中性的词语在诗人的修饰后就成为了黑暗、苦难、恶势力的象征。“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社会的黑暗和苦难随着风席卷了每一个地方,我们的祖先已经倒下了,而我们的孩子也要像我们一样慢慢倒下。
本文从诗歌的整体结构、句式和意象三个方面阐释了穆旦诗歌的创新之处。穆旦诗歌在整体结构上不仅大胆地将两种诗体交错排列,在诗行切割上打破固有的语言习惯,并进行了拟诗剧的尝试,将戏剧化手法运用于大量诗歌当中,这些独特的结构形式都大大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在句式方面,穆旦深受西方现代派理论的影响,大量使用悖论、反讽和欧化句式。这些陌生化的手法使读者感受到穆旦心中那丰富的痛苦和永恒的矛盾,与诗人的情感共同起伏。另外在意象的使用上穆旦也表现出对于现代主义的不断追求:用都市生活意象直接表现现代生活;用身体意象表现苦难,同时又从未屈服;在运用自然意象时打破传统诗歌的固有含义,而赋予其现代性的新内涵。正是这些语言形式的创新之处扩大了穆旦诗歌的艺术表现力,使他可以将民族的苦难和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这些丰富的内容都被融入到诗歌当中。
[1]胡 适.尝试集[C]//胡适作品集27.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23-25.
[2]郭沫若.论诗三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16-217.
[3]穆 旦.穆旦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37.
[4]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6-390.
[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203-205.
[6]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332-335.
[7]张卫中.汉语与汉语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02-105.
[8]刘 勰.文心雕龙[M].上海:中华书局,2013:320-327.
[9]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152-155.
[10]赵家壁.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5-7.
[11]陈本益.汉语诗的“建筑美”散论[J].当代文坛,2001,(1):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