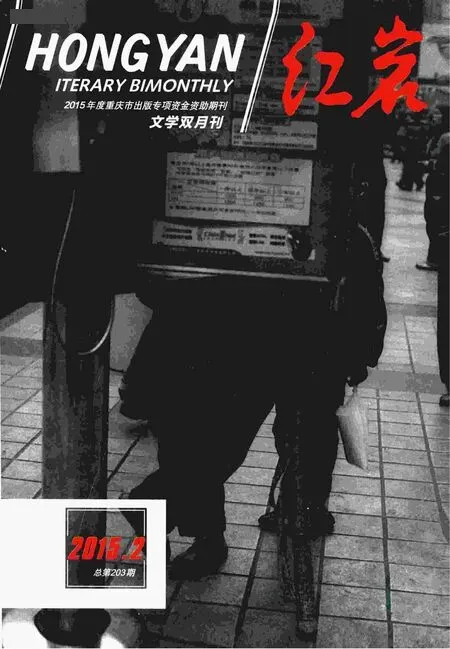“朝花”而“夕拾”中欢欣与悲怆相交织的童心之歌
2015-11-17王永祥
王永祥
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的时候,正是他思想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就个人而言,在北京和章士钊打官司、和现代评论派恶战一场、“三一八惨案”的刺激、和许广平恋爱关系的确定,再加上疾病缠身,鲁迅思想精神处于急剧的变化中;就社会而言,整个社会上革命势力汹涌而来,北伐势如破竹。军阀们个个自身难保,学者们也不能盘踞北京,纷纷南下自寻生路。文化人必须在生存和思想立场上作出明确的选择。寻找出路的鲁迅,到了厦门和人闹翻,到了中山大学,还是和学者、“正人君子”不能同流一气。在厦门的坟堆间照了相,在中大做了几个月的系主任,被革命的血惊得目瞪口呆的中年男人,无端地开始写回忆文章,真是让人难以索解。《朝花夕拾》的写作,用鲁迅的话说,面对“离奇”、“芜杂”的现实,“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回味童年时代可口的果蔬、重温人间的挚爱。鲁迅开始以更为复杂和开阔的成年人眼光审视自己的成长经历,将自我的成长经历与时代的关照结合起来,让我们看到文化、社会在鲁迅的成长中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迹。在某种程度上,《朝花夕拾》可看做鲁迅从儿时到“五四”前夕的自传,是我们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
1925到1927年间的鲁迅真是慌了神,但即使慌了神,毕竟是鲁迅,他要沉住气,不能乱了阵脚。但一个人如何能稳住阵脚,我想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回忆,一个人在无法理解眼前的事情的时候,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只能在回忆中找自己心里最可靠的东西来自我安慰。我想《朝花夕拾》的写作,鲁迅的心情也莫过于此。看他的《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就知道他开始找自己最熟悉东西来对抗现实。但《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鲁迅在观点上并无多创建,即使他自己说在刘师培的基础上阐释魏晋,我依然认为他没有超出刘师培。实在要说鲁迅有什么创建,那就只能说是同样的观点,鲁迅审视的视角和刘师培不同。刘师培出身经学世家,看不起民间;但鲁迅不同,虽也算士大夫家庭出身,但早已被排挤出上层,开始从民间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所以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虽然说的是上层社会的事情,但眼光还是和刘师培不一样,开始从民间、从个体的生活、生命感受中找解释的依据。这点就和刘师培很不一样,刘始终在考镜源流,不能脱离上层的气味,脱离文化的藩篱,而鲁迅开始从人的自然感受、生命状态来入手魏晋,所以虽然命题相似,但思路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说鲁迅从民间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民间的发现也看是在什么视角下去发现。民间在鲁迅看来是生命最为本真的呈现,但要将民间的本真呈现出来,需要破除观察者的思想藩篱,将自我观察的基点放在最为自由的生命状态中,而一个人生命的本真状态则莫过于童年了。换句话说,鲁迅是以成年人的在世状态,在回忆中慢慢复活了童年的生命感受力来书写《朝花夕拾》。童年的生命状态对一般人而言,只是潜在的、沉睡的存在。童年如何被唤醒,那是有待于一个人的人生机缘。也许一个人长大之后,童年偶尔会在他脑海中闪现,但不会升华为自我生命的精神原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人对童年在什么层次上理解,取决于他对人在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性的关照,一个人要如此关照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在世状态,知识性的东西是无法引导他到达如此境界的,必须在他成年之后陷入生存困境的时候,他才会如此选择。在中国更是如此,我们虽有信仰,但一般人并无宗教性的信仰。换句话说,我们从出生被抛入世界,中国人就陷入世俗的纠结中无法超越性地看待生命,他能对自己的生命来源做本体性的关照的,莫过于童年时代了。鲁迅在这三年中,之所以如此回溯他的童年时代,我们应该做如是观。我想这也是鲁迅开始写《朝花夕拾》最为根本的精神动力所在。
整体性地通读《朝花夕拾》,第一篇《狗猫鼠》虽然精彩,但掉书袋严重,显得过于生硬,映射人事纠葛的杂文笔法过重,换句话说,火气太重了,虽然精彩,但未到醇厚之境。《阿长与〈山海经〉》就不一样了,开始摆脱人事纠葛,思绪和境界渐入醇厚,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来得是那样自然深切,因为他在民间、在被文化异化的下层人的生硬外壳里,看到了生命中的纯朴和厚实,能让阿长容身的黑暗而仁厚的地母,让这个离家的灵魂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在了。其下几篇就是以地母般浑厚的生命眼光开始了对人世的批判。《二十四孝图》对道教化的儒道之孝的批判包含着对个体生命的肯定;《五猖会》和《无常》那是对民间游戏中自在本性的呼唤,可以和晚年的《女吊》参照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以一颗纯洁的童心对生活深情的拥抱,严师、祖母、大自然、同窗之谊、兴趣爱好皆是如此温暖人心;《父亲的病》不止是对父权的批判,和早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基调完全不一样,那是对父亲的理解——在悲悯意义上的理解,也是对童年毁灭之后的深情挽歌;《藤野先生》包含着在异域对另一种人格和生活状态的钦佩与反思,耻辱和敬佩交织的复杂已经撑破少年时代的梦想,真正开始睁眼看人世了,最后写到《范爱农》那更是对人的在世状态的沉痛书写。
在鲁迅童年的成长经历中,他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腐朽文化对童心之爱的扼杀。无论是《二十四孝图》对愚弄儿童的虚伪孝道的揭露、还是《五猖会》中,父亲对儿童好奇心的扼杀,以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儿童自由天性的追怀,鲁迅以自我的成长经历展示出阴暗文化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压抑。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是以儿童成长的视角来审视白话文以及这一语言变革中产生的新文化对人的成长的重要意义。相对于经过反复规训才能掌握的文言文,白话的自由和易于掌握,对儿童表达自我感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个体的语言能自由表达并被社会肯定,我们才能明白白话文对培养儿童的重要意义。相对繁难的文言,儿童爱美和好奇的天性只能从文言书籍中的插图画中得到满足。但就是这样的图画也充斥着虚伪的教化。《二十四孝图》中鲁迅以儿童真切的心理感受,揭露这些骗人把戏对儿童的扼杀。所谓“老莱娱亲”、“卧冰求鲤”、“郭巨埋儿”,都是以长者为本位,幼者只是依附于长者,儿童的个体独立地位自然不在承认之列。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以长者为本位的教化之道中,并不是以人伦亲情的真实感受为基础的,纯粹是以“孝”的美名为幌子,教给人们如何作伪。很多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教化的虚伪,但大家都在“孝”的美名下不敢将各自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鲁迅追忆儿童时代读了“郭巨埋儿”的恐惧,孝本来是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但反而让幼者感觉到长者的生存威胁着幼者的生存,长幼之间不但没有达到以“孝”维系亲情的目的,反而在虚伪的文化之下是敌对关系。因此他才会反讽“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这种借大义以扼杀弱者的文化传统并未随历史的变化而改变,而且成为一种文化惯性,依然存在于很多人的观念深处。很多接受新思想的所谓的“正人君子”正是以公理、正义等好听的名目掩盖着自己真实的人生体验,他们并未能替幼者和弱者说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伪善的文化传统,造成很多人在成长教化中习惯了做戏式的人生态度,并由此造成中国社会缺乏“诚”与“爱”,逐渐在成长中丧失了童心中本然的真诚天性,成了做戏的虚无党。在《五猖会》中,童心对民间赛会中自由精神的神往和父亲严厉的精神禁锢形成鲜明对比。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对父亲进行批判,而是对父亲之所以如此的社会文化根由的反思,面对社会对人的规范,即使慈爱如父亲的人,也难以抗拒,这就在更深的意义上揭示了个体在成长中所受到的伤害。与《五猖会》相对照,《父亲的病》又展现出儿子对父亲的伤害。被病痛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父亲,本渴望在最小的痛苦中能安然离开人世,但儿子在伪善的“孝”道迫使下,在大喊大叫中反而无端地增加了父亲所受的痛苦。
在鲁迅的童年记忆中,并非完全是文化与社会对童心的伤害,同时也有人间最为温情的爱。鲁迅拨开笼罩童年记忆的层层雾霭,将童心所体验到的最为纯真的爱一一流泻在笔底。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我们看到幼年鲁迅对长妈妈真切的爱。这是未经成人世界的利益、地位等世俗利害所玷污的爱。鲁迅正是因为这些爱,才认识到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身上最为朴素真切的善。和《社戏》等小说一起对照阅读,我们会认识到,在鲁迅对下层老百姓“怒其不争”的冷峻批判的背后,正是对这些被损害者的“哀其不幸“的温暖的爱,因此他才会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发出如此深情的呼唤,愿这些如长妈妈一样有着善良一面的闰土、祥林嫂、单四嫂们,在仁厚黑暗的地母中永安他们的魂灵。同样对方正而博学的寿镜吾先生严而不厉的可爱形象不能忘怀。寿先生手握戒尺,但不常用,对在学堂后花园中自由嬉戏的顽童他有祖父般的慈爱。同样的严师还有心胸博大的藤野先生,那种基于人类胸怀的人道之爱,在鲁迅的成长记忆中永久不能忘怀。所有这些人间的爱,构成鲁迅文学世界背后最为温暖和醇厚的底色,让我们明白鲁迅的精神世界,并不仅仅是匕首和投枪。
我们顺着鲁迅童年记忆中的爱和憎,能看到他一步步走出国门后的广阔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将《琐记》和《〈呐喊〉自序》等文章对照阅读,我们看到一个逃出死水一潭的封闭世界的少年,如何在阅读《天演论》、学外语的过程中打开自己的眼界,知道另一种文明对他的吸引以及他强烈的探索新世界的蓬勃精神。正是在他成长中日渐丰富的人生体验,撑破了原有文化对他生命力的束缚。鲁迅一代人的成长,并不仅仅是一己的逃亡和拯救,而是将自我的成长和整个民族国家的新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才有《范爱农》中对那些为新生国家付出生命代价的先贤们的深刻追怀。徐锡麟、秋瑾,还有《药》中的夏瑜,这些和鲁迅同时代的人,为了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他们并未死去,依然活在鲁迅的心中。同样,正直而难以与世苟合的范爱农的潦倒困顿的人生,就是对破坏先烈革命成果的敌人的最大批判。
作为一部记录鲁迅成长经历的散文集,从整体上来审视《朝花夕拾》,从童心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在社会与文化的视野中理解人的绝好例证,这个例证就是《朝花夕拾》所展示的鲁迅自我的成长经历,因为鲁迅是很真诚地以成人和儿童的双重视角审视、回望他的成长体验。在他对自我成长经历的展示中,我们看到文化、社会在哪些方面扼杀人,又在哪些方面温暖和救赎了个体生命。鲁迅在《狂人日记》末尾曾痛彻地呼唤:“救救孩子”。我们如何救孩子,要救孩子,必先对人有一个很全面深刻的认识,如果不能对孩子的内心有很好的理解,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就不是救孩子,而是扼杀孩子。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鲁迅正是以他切身的体验,让我们看到孩子内心的丰富和生命诉求。如果认真读《朝花夕拾》我们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特别是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而一旦我们达到对人的认识比较深入全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对我们的文化作出反思,也才能创造出更适合人性发展的新文化。
在童年回忆的另一端,《朝花夕拾》也可以看做是鲁迅在中年时代对自我生命的一次深情回溯,他为陷落的人而悲歌,也为在世的温情而感动。所有一切都会逝去,也许在某个时段,对自我做一次这样的回望并非矫情之举,那是一颗本真的心希望在艺术的游戏和幻想中,唱一曲欢欣与悲怆交织的歌,这也未尝不是一场自得其乐、也自识其痛的超脱而自由的灵魂漫游。我想这样的文字不是一般人写得出来的,那是一个童心永远不死的人、善永远以微弱的火苗在内心燃烧的人才能写出的。读《朝花夕拾》在某种程度上有读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悲痛感,斯世已往,何以挂怀;临文嗟悼,悲欣交集;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文字流传后世,莫过于对人心的安慰,能拥有这样安慰人心的文字的人,也愿他的魂灵在仁厚而黑暗的地母怀中永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