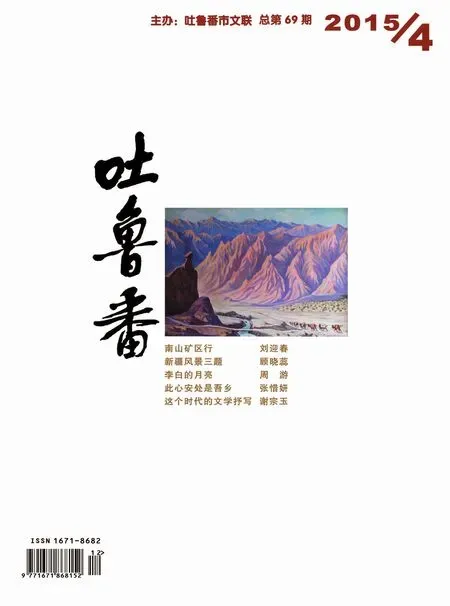把文字写进泥土里
——评刘奇叶长篇小说《论语》
2015-11-17聂茂
聂茂
把文字写进泥土里
——评刘奇叶长篇小说《论语》
聂茂
一直以来,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到当代作家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王安忆、韩少功等一大批赢得广泛声誉的作家,其代表作几乎都是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可见,农村生活的变迁和农民生存的心路历程是中国文学的“母地”和“福地”,其间蕴涵着无穷的创作灵感和取之不尽的素材。然而,当下农村题材作品的创作不容乐观,近年来也少有农村题材的力作问世,作家们写不好此类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对正在转型时期的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在我阅读到的文本中,不少作家虽然着眼于底层视角和个性化叙事,但在实际写作时,更多的只是在渲染农村底层生活的悲惨无助、愚昧无知,以及在此基础上抒发一点人道主义的同情而已。有些作家甚至是将“底层”作为题材、把“个性”当作标签,或者成为一种姿态,为“底层”而“底层”,却没有对于“底层生活”个性化的体验、独到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更谈不上灵与肉的撕裂与痛疼了,因而发表出来的作品只是在浅层意义上的重复,这种重复正慢慢演变成公式化和概念化而越来越受到读者的质疑和抛弃。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作家们的创作思想、精神追求和生活积淀是否准备好了?当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已成为相当严峻的现实要求,作家们对乡村及其农民生活的关注是否进入了宏观层面的自觉?当愈演愈烈的洪灾、频频发生的矿难,当乡村经济的贫困滞后、乡村现实蒙受的屈辱不公以及沙尘暴、民工潮、环境污染、土地和资源流失等越来越触目惊心的时候,作家们是否有过对当下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农村分配制度的利弊、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保护发生冲突如何妥善解决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深层次的思考?原本敏感于苦难意识的文学,如果看不到那些“现象”和“事件”背后的内在联系和深层系结,看不到时代大潮和商品经济中个体的人普遍出现的精神荒芜和灵魂苦闷,尤其重要的是,作家们不去花力气探究造成这种精神荒芜和灵魂苦闷的原因,却一味地以类似异乡人的他者方式对农村生活作旅游式的浪漫想象,那么,作家们要想使自己的创作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宏大的境界只能是缘木求鱼,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满足罢了。
令人高兴的是,一直在农村摸爬滚打的湖南青年作家刘奇叶笔耕不辍,近年来,创作并出版了多部颇具特色的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摆在面前的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论语》是刘奇叶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展示社会转型期中农村青年在事业与爱情的冲突中精神的漂泊、情感的挣扎和灵魂的灼痛。小说以我国开放以后穷壤闭塞的湘西南乡村为背景,在一环套一环的故事设计中,作者频频切换叙事场景,使霓虹闪烁、灯红酒绿的生活方式和珠江三角洲沿海开放城市的个人经验成为推动文本前进的动力。小说主人公任我行从小生长在湘西南一个小山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方面,他长期受到守旧的封建习俗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农村青年大多有的犹疑、自私、固执和蛮狠;另一方面,又由于有着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生活经历,较之都市里的青年男女,“农民”的身份符号使主人公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情绪和精神苦闷。为了释放这种情绪和苦闷,他通过各种手段,先后赢得了女人紫玲、燕妮、罗婕婕的芳心,但每一个女人都只能成为他的“过客”,成为他生活表层的情感慰藉和精神替代。正因为此,对于性格开朗、温顺善良的紫玲姑娘,任我行不止一次地拨动情弦,大有爱得欲罢不能之势。对于洒脱温柔、颇为高傲的燕妮,任我行又一见钟情,爱得难舍难分。而对于婀娜多姿、性感无限的少妇罗婕婕,任我行不计后果,一头扎入其中,像迷途的孩子,饱尝爱的酸甜和生活的苦辣。奇怪的是,任我行的每一次情感转移,看起来都是那么合情合理,并且每一次的离别都能得到被伤害的女人的理解和留恋。
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围绕主人公任我行的情感经历而展开叙事的,他与三个女人不同情感体验的关系,以及三个女人自身的情感挣扎和内心苦痛,连同湘西南乡村与沿海城市的时空转换,这些人物和时空就组成了任我行的生活现实和情感世界。有意思的是,小说虽然以任我行追求爱情与事业的起起落落为主线,但紫玲姑娘、燕妮和罗婕婕等也都有着各自的故事,且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各自的故事也是独立的,但又通过任我行集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农村真实生活的立体拼图。小说正是在这样网状般的社会关系中描述了任我行的“生命存在”,刻画出了这个湘西南农村青年的内心挣扎和情感煎熬,同时也通过他的主线折射出了不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从整体上勾勒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我宁愿认为,这个小说写的是生活,而不是故事。如果说故事像一条小溪,其脉络与转折比较容易把握,那么生活则仿佛一条江河,其内部有很多涡流,不同涡流的相互冲击才最终决定河流的方向,而要将不同的涡流及其冲击准确地描摹出来则要困难得多。
当然,这部小说也存在局部的粗糙和对主题的深刻性提炼不够的问题。刘奇叶似乎剑走偏锋,想走险棋,但我需要忠告的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推而广之任何作品——都不以篇幅长短论英雄,也不以篇名或书名的稀奇古怪决优劣,关键在于:你的作品是否体现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和艰难中的人性美,是否真正把新农村的现实生活转化成笔下的艺术生活,是否真正关注并体验变革时代农民的命运与灵魂的阵痛。质而言之,是否真正对农民的生活有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刻骨体验,是否真正对困境中的农民有着深切的关怀、深刻的同情、深情的尊重和深层的理解与表达,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让人欣慰的是,青年作家刘奇叶似乎一直朝着这方面试图做出自己的努力。
记得评论家蒋巍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末流小说中没有泥土;比较好的小说,是把泥土写进了书里;真正的优秀小说,是把文字写进了泥土里。”
我很赞同这个比喻。评论家吴秉杰先生对此解释说:把土地写进小说里的小说,总让人有写作的痕迹,能看到土墙上抹上了水泥,能看到人工的种种痕迹;优秀的乡土小说,洋溢泥土原汁原味的芳香,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文学作品使用。
我真诚地希望,写出了一批乡村小说的刘奇叶继续关注疼痛的乡村,继续用作品的方式抚慰梦中的美丽和如花一样开放的笑容,直到真正把文字写进湿漉漉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