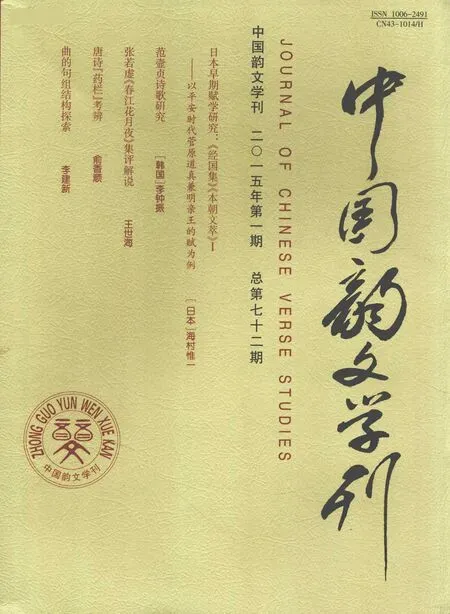论明末清初南北曲的演变
——兼论魏良辅和沈宠绥的曲唱理念
2015-11-14艾立中
艾立中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论明末清初南北曲的演变——兼论魏良辅和沈宠绥的曲唱理念
艾立中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度衰落的北曲在明末清初再次兴盛起来:一方面,北曲创作在复兴,北杂剧复苏,散曲的北曲曲牌激增;另一方面,北曲的演唱方法重新得到提倡。但北曲的复兴并未导致南曲的衰弱,南北曲都成为曲家常用曲体,二者功能的界限已经逐渐淡化。魏良辅改良南曲和沈宠绥振兴北曲在实质上都是复古,只是复古的理念不一致。
明末清初;南北曲
一 南北曲演变的原因
自明代中叶嘉隆时期梁辰鱼以来,南曲开始成为文人戏曲和散曲创作的主要曲体,特别是和梁辰鱼同时代的魏良辅改良昆山腔以来,演唱南曲之风迅速蔓延开来,这让一批酷好北曲、复古元音的文人们痛心疾首。早在嘉靖时期张羽曾说:“近时吴越间士人,乃弃古格、改新声,若《南西厢记》,及公余漫兴等作,鄙俚特甚,而作者之意微矣,悲夫!……且今之缙绅先生,既多南士,渐染流俗,异哉所闻,故率喜欢南调,而吴越之音靡靡乎不可止已。间闻北调纵不为厌怪,然非心知其趣,亦莫能鉴赏,其间故信而好者不多有之,大抵新声之易悦,而古调之难知,所从来远矣。”这是张羽在校对《董西厢》时所发出的一段感慨。作者感叹《董西厢》这部早期的北曲唱本正日益被忽视、湮没,积极把它整理出来,主要是针对北曲逐渐被南曲所代替的严峻形式而做出的抢救性工作。考察这段文字是嘉靖丁巳(公元1557年)秋,而梁辰鱼的散曲集《江东白苎》于嘉靖三十五年后刊行,即1556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梁辰鱼《浣纱记》和李日华《南西厢》两大传奇风靡海内。这些都说明了南曲裹挟着改良后的昆山腔正逐步代替北曲,并挑战着其他南曲声腔。和张羽同时代的何良俊也极力推崇北曲:“近世北曲,虽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
推崇南曲,贬低北曲的也大有人在,徐渭在《南词叙录》谈到:“有人酷信北曲,以至伎女南歌为犯禁,愚哉是子!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夷、狄之音可唱,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其实这更多是负气之辞。实际上,南曲的发展已经不可遏止。晚明万历时期沈璟和王骥德等吴江派成员,虽然还时时表示对北曲(更多是元代南戏)的崇敬,但在理论建构和实践上都在极力发展和完善南曲。他们在戏曲和散曲创作上大量使用南曲曲牌,编辑南曲曲谱,对格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尽管沈璟等人提倡古曲古调,但在实际创作中重辞藻,好典雅之风。正如任二北先生所说的:“沈璟之曲派,乃一面文字受梁氏之影响,而一面自己又专求律正与韵严。”南曲的兴盛、北曲的衰落成为晚明曲坛上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明末清初(这里的明末清初指天启、崇祯、顺治、康熙四朝)出现了北曲复兴现象。一方面是北曲的文学创作兴盛。曲家在创作戏曲和散曲时除了继续使用南曲曲牌,同时对北曲曲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散曲上。特别要强调的是,北曲的复兴只是相对晚明北曲极度衰落而言的。明末清初不少著名散曲家如施绍莘、徐石麒、沈谦、朱彝尊等等,他们部分甚至大量创作北曲。如朱彝尊的《叶儿乐府》除了一首【南商调·黄莺儿】,其它都是北曲小令。徐石麒《坦庵乐府》除了两首南曲套数,其它都是北曲。北曲在散曲中大量出现并非孤立,与此同时,北曲杂剧创作也呈现复苏。当时象沈自徵、凌濛初、尤侗、吴伟业、徐石麒等都有杂剧传世。当时吴江派沈氏族亲的一位女曲家叶纨纨还创作杂剧《鸳鸯梦》,沈君庸作序道:“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即国朝(明朝)杨升菴亦多杂剧,然其夫人第有黄莺数阕,未见染指北词。…吾家词隐先生(沈璟),为词坛宗匠。其北词亦未多。”晚明以来,杂剧选本也开始增多。自臧懋循的《元曲选》之后,明末又出现了像《盛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杂剧三集》等。不过,就整体来看,南曲仍多于北曲,到清中叶,南北曲已呈大致均衡之势。
另一方面,北曲演唱方法也在复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祁奕运鲜云小伶歌》诗云:“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无其精。老腔既改白字换,谁能熟练更还生。出口字字能丢下,不配笙箫配弦索。”又如清代章金牧《金谷悲》(其六)云:“伊梁弦索入云齐,旧本江南《水调》低。自学龟兹翻北曲,对人羞唱《白铜鞮》。”这些诗说明当时北曲的演唱处于从不绝如缕状态到再度复兴的状态,曲家对北曲的尊崇还一直延续至清代中叶,后面还将论述。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的寻绎。有学者已指出是缘于复古崇雅意识,正如曲学专家李昌集先生所说:“散曲本有‘文本’与‘歌本’的双重性质,一旦案头化,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文体’,这就使创作散曲时的‘择调’有了极大的自由,在元散曲的避世超脱精神又获得文人心理契合的背景下,晚明以来久已‘不唱’而鲜为人采用的北曲一体重新被文人起用,这一事实本身已在一个表面层次上映现了复古主义倾向”,“‘元曲化’的清散曲,其时代的意味,不在‘创造’,而在‘复古’。清初‘元曲化’一流散曲的出现,不是北曲自身活力的产物,而是因元曲这一已‘作古’的文学作为一种既有的精神范式契合了清初文人的某种心理。”尽管他说的是散曲,戏曲也不外如此。不过,他把崇雅意识产生的时间仅限定在清代不够准确,其实曲家的崇雅复古意识并非突然始于清初,明末已有较为明显的反映。北曲复兴除上述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明末清初文人对南北曲抒情写意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北曲在散曲和戏曲中的复苏,这二者不存在谁影响谁,而是共同受当时艺术观念的影响。正如明末徐翙所说的“今之所谓南者,皆风流自赏者之所为也。今之所谓北者,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这说明曲家意识到晚明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南曲已经不能满足多种感情的宣泄,邹式金在《杂剧三集》序云:“北曲南词如车舟各有所习,北曲调长而节促,组织易工,终乖红豆;南词调短而节缓,柔靡倾听,难协丝弦。”再次说明南北曲各有长短,北曲这一传统的曲体才被再次重视起来。
与此相应的是,自明代万历以来不少曲家开始反思南曲繁缛俗艳之风。比如凌濛初在《谭曲杂札》中说:“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状。盖其生于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崇尚华靡。……以故吴音一派,兢为剿袭靡词……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余,即人间一种真情话埋没不已。”他尖锐批判了梁辰鱼把南曲带入了雕琢靡丽的不良之境。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也批评道:“词曲入宫调,叶平仄,全以词意明亮为主。每见南曲艰涩扭挪,令人不解,虽强合丝竹,止可作工尺字谱,何以谓之填词耶。”还有人批评南曲缺乏精深的学理,如冯梦龙说:“然而南不逮北之精者,声彻于下,而学废于上也。”当时曲家正在寻找途径矫正南曲艰涩雕镂之弊,而一直被推崇但早已衰落的北曲被曲家看中,充当曲体、曲风变革的利器。
清中叶凌廷堪在《与程时斋论曲书》中精辟地总结了南北曲盛衰的原因:“虽然北曲以微而存,南曲以盛而亡,何则?北曲自元人而后,绝少问津,间有作者亦皆不甚逾越闲,无黎邱野狐之惑人,有豪杰之士兴取元人而法之,复古亦竭为力。若夫南曲之多不可胜计,握管者类皆文辞之士。彼之意以为吾既能文辞矣,则于度曲何有。于是悍然下笔,漫然成编,或诩秾艳,或矜考据,谓之为诗也可,谓之为词也亦可,即谓之为文也亦无不可,独谓之为曲则不可。”他把二百多年来南北曲的演变概括了。不过,清初以来北曲命运和南曲一样,常被用来写考据、艳情之作,北曲的复兴更多是表层的、形式上的,元代和明中叶北曲中的豪放泼辣、率直纯朴的精神内涵早已丧失殆尽。
第二,北曲昆腔化后,南北曲体正在趋同。魏良辅在《曲律》中提出:“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虽然南曲和北曲的演唱技巧、声情上仍有区别,但改良后的昆山腔以字声行腔,这就导致南曲曲体与北曲曲体走向趋同。王骥德《曲律》“论过搭二十二”中说:“或谓南曲原不配弦索,不必拘拘宫调,不知南人第取按板,然未尝不可取配弦索。”明末清初,南北曲体趋同之势更明显,如沈自晋《南词新谱》卷十四【黄钟·点绛唇】曲下注曰:“此曲乃南吕引子,不可作北调唱……今人凡唱此调及【粉蝶儿】,俱作北腔,竟不知有【南点绛唇】及【南粉蝶儿】也,可笑。”又在【二犯江儿水】曲下注明:“此曲本为南调,前辈陈大声诸公作此调者甚多,今《银瓶记》亦作南曲唱。不知始自何人,将《宝剑记》诸曲唱北腔,此后《红拂》、《浣纱》而下,皆被人作北腔唱矣。然作者元未尝以北调题之也”;李玉在其所编订的《北词广正谱》里还第一次列了北曲中与南曲格律相同的曲调。如正宫内的【金殿喜重重】、【怕春归】、【锦庭芳】等曲调,皆注明“与南词同”,还在【番马舞西风】、【普天乐】、【锦庭芳】三曲下注云:“以上三章一套,断属南调,北有其目,而缺其词也。”因北曲无相应的曲文可选,故李玉以南曲为范文,这正说明了南北曲体趋同已经成为了曲学家的共识。
正因为南北曲走向趋同,所以南曲可以用北曲的旋律演唱,只要在旋律中加入乙、凡二音,即7和4两音,如《铁冠图·别母》有一【南越调·小桃红】用了北曲中的“乙”音,表达了苍凉悲壮的心境。《长生殿·惊变》中【南扑灯蛾】加入了凡音(即简谱中4),在委婉中透出一种活泼。北曲也可用南曲的旋律来演唱。在《玉珏记》第二十九出中,有如下的叙述:
(丑)大姐,央你唱一套马东篱《百岁光阴》。(小旦做北调唱介)(丑)我不喜北音,要做南调唱才好。(小旦)也罢。(唱)【集贤宾】光阴百岁如梦蝶,回首往事堪嗟。……
可见昆腔改革后,只要遵循依字声行腔,从理论上讲南北曲是可以换唱的,但实践中还不多。南北曲的通融性还表现在板式的变化上存在一致,正如《康熙曲谱·凡例》中说:“然亦随宜消息,欲曼衍则板可增,欲径净则板可减,欲变换新巧则板可移,南北曲皆然。”
沈德符《顾曲杂言》曰:“今南方北曲,瓦缶乱鸣,此名‘北南’,非北曲也。”沈宠绥还认为当时的北曲:“名北而曲不真北也,年来业经厘剔,顾亦以字清腔径之故,渐近水磨,转无北气,则字北曲岂尽北哉?”这一切正如俞为民先生所言:“从曲体上来说,无论是南曲,还是北曲,两者都与以前的南曲、北曲产生了差异,故从这点上来说,经过魏良辅对剧唱昆山腔加以改革后,南曲与北曲产生了交流与融合,昆山腔所唱的南北曲,不仅北曲已非以前的北曲,而且南曲也已不是以前的南曲了。”当然,曲体的演变对剧唱的影响也渗透到了清唱的散曲。
第三,曲家的欣赏个性和创新意识。艺术规律昭示艺术家,一种文体如果臻于完善,并成为严格的法则,就会对艺术创作和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当传统的艺术规范束缚了艺术家自由表达情感时,体制的扩展、改造和重建就不可阻挡了。晚明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就有曲体的创新,如第47出《围释》曲牌构成是【出队子】、【双劝酒】、北【夜行船】、北【清江引】、【前腔】、北【尾】,【前腔】本为南曲所有,却引入北曲。明末清初由于昆唱北曲已经成熟,部分曲家在南曲中引入北曲只曲,如阮大铖《燕子笺》第20出:【南越调】【水底鱼】【前腔】【北双调】【清江引】。吴伟业《秣陵春》第6出:【南仙吕】【青歌儿】【光光乍】【皂罗袍】【前腔】北仙吕【骂玉郎带上小楼】【前腔】【南仙吕】【掉角儿序】。李渔《凰求凤》第8出:【北双调【青玉案】【前腔】【南正宫】【玉芙蓉】【前腔】【前腔】【前腔】。
如果说上述曲家的创新还局限于文体上的,那么明末松江地区著名曲家施绍莘(1588—?)则将文体创新和音乐演奏方式名副其实地结合起来。施绍莘在套数《春游述怀》的跋云:“予雅好声乐,每闻琵琶筝阮声,便为魂销神舞。故迩来多作北宫,时教慧童,度以弦索,更以箫管叶予诸南词。院本诸曲,一切休却。”可见,施绍莘偏好北曲弦索音乐,也不废南曲,这促使他在音乐上积极革新。在他很多散曲中,都在体现着南北曲文体和音乐上的创新。比如他的套数《旅怀》,曲牌构成是【南仙吕入双调·二犯江儿水】、【前腔】、【沽美酒】、【幺篇】、【清江引】,前面两曲牌是南曲,后面三曲牌是北曲【双调】,而且前两曲子是押“尤侯”韵,后面三曲子是押“江阳韵”,这种套曲模式明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南北合套,而是作者的一种创新,为的是配合北曲弦索音乐的演奏。又如他的《四景闺词》【北双调】,曲牌构成为【八不就】、【前腔】、【前腔】、【前腔】,四支曲子分别押“庚青”、“萧豪”“尤候”“皆来”,作者在后面写到:“此等词本被弦索,须带肉麻,当在不文不俗之间,方入词家三昧。右词似亦梦见一斑者,每花月之下,令两童以三弦箫管,凄声度之,宛然一燕赵佳人,攒眉酸涕矣。”《弦索词》的曲牌构成为【北南吕·骂玉郎】、【前腔】、【前腔】,也是南北曲牌融合。不过,由于这一创新更多是对于传统南北曲合套规律的天才式的破坏,而并未建立一种严谨的规范。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内,正是昆曲曲律成型的重要的时期,施绍莘的艺术创新只能是个别的实践,而不能被曲家广泛接受。
施绍莘《旅怀》所附陈继儒的跋中还论述道:
吾松弦索几绝统,近来诸名家,始稍稍起废,然不久便散逸。……子野避地空山,绝迹城市,日撰新声,令宗工名手,商榷翻度,差为弦索兴灭继绝。时时率诸童过予顽仙庐,丝竹嘈嘈,随风飘扬,村姑里叟,皆负子凭肩而听,亦山林快事也。
又有王季长的评点:
王元美谓北曲多词情,南曲多声情。子野以南词韵语作北词,且箫管弦索,合而翻度,宜其声情词情,洒洒倾听也。
由上观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明末以来弦索北曲的复兴也并非是施绍莘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时代风气在发生变化,陈继儒说松江地区“近来诸名家,始稍稍起废,然不久便散逸”,证明当时有人力图恢复北曲,但效果不佳。后面要提到的明末清初著名曲家沈宠绥和冯梦龙便是恢复北曲弦索的代表人物之一。
自魏良辅改革昆曲后,昆曲的主要乐器由箫管和鼓板承担,弦索乐器居次要地位,而施绍莘“箫管弦索,合而翻度”与昆曲的演奏方式虽貌合但神离。施绍莘在套数《花生日祝花》后的《乙丑百花生日记》一文中叙述道:“予时有歌童六人,善三弦者曰停云,善琵琶者曰响泉,善头管及搊筝者曰秋声,善及箫笛者曰永新,善阮咸吹凤笙者曰松涛、霓裳。于是各奏其技,称觞而前。每进一杯,歌小词一解,而丝竹之音,从而和之。”这是一支规模虽不大、但乐器比较完备的家乐,箫管乐器和弦索乐器都有,但作者把乐器的主次顺序分得很明白,先弦索后箫管。这说明施绍莘家乐的主要乐器是弦索,符合他对北曲的审美喜好。除施绍莘之外,明末清初还有一些曲家投身北曲表演,据徐珂《清稗类钞》“音乐类”记载:“(顺治康熙时期)疁城(今上海嘉定)陆君旸(陆曜)初尝学吴弦于吴门范昆白,得其技。已而尽弃不用。以为三弦,北音也。自金、元以降,曲分南北,今则有南音而无北音,三弦犹饩羊也。然而吴人歌之,而只为南曲之出调之半,吾将返于北,使撩捩之曼引而离迤者,尽归激决。”显然他对当时流行的缠绵委婉的吴音即昆腔并不欣赏,出于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他推崇激决奔放的北曲,这其实是以复古为创新的艺术表现方式。
二 沈宠绥和魏良辅的复古实质
尽管明末北曲出现复苏,但依然有人对其忧心忡忡。著名吴江籍曲律专家沈宠绥《度曲须知》“弦律存亡”中对北曲的演变作了如下阐述:
若乃古之弦索,则但以曲配弦,绝不以弦和曲。凡种种牌名,皆从未有曲文之先,预定工尺之谱,夫其以工尺谱词曲,即如琴之以钩剔度诗歌,又如唱家箫谱,所为浪淘沙沽美酒之类,则皆有音无文,立为谱式者也。慨自南调繁兴(经魏良辅改良的新声昆腔),以轻讴废弹拨,不异匠氏之弃准绳。况词人率意挥毫,曲文非尽合矩,唱家又不按谱相稽,反就平仄例填之曲,刻意推敲,不知关头错认,曲词先已离轨,则字虽正而律且失矣。故同此字面,昔正之而合谱,今则梦中认醒而惟格是叛;同此弦索,昔弹之确有成式,今则依声附和而为曲子之奴。总是牌名,此套唱法,不施彼套;总是前腔,首曲腔规,非同后曲。以变化为新奇,以合掌为卑拙;符者不及二三,异者十常八九。即使以今式今,且毫无把捉,欲一一古律绳之,不迳庭者!
与此相似,吴江派著名曲家冯梦龙在传奇《双雄记》叙中提到:“说者又谓:北调入于弦索,南调便于箫管。吴人贱弦索而贵箫管,以故南词最盛。是又不然。吴人直不知弦索耳,宁贱之耶?若箫管是何足贵?夫填词之法,谓先有其音,而以字肖之。故声与音戾,谓之不协,不协者绌。今箫管之曲,反以歌者之字为主,而以音肖之,随声作响,共曲传讹,虽曰无箫管可也。然则,箫管之在今日,是又南词之一大不幸矣。”
可见,沈、冯二人对魏良辅改良昆腔都持保留态度。他们批评魏良辅将北曲改成按平仄演唱的方式是背弃了按谱唱北曲的传统。在我们看来,魏良辅和沈宠绥、冯梦龙的理论区别主要在于如何看待南北曲音乐和文字孰重孰轻。沈、冯二人虽强调字声,但把乐器的旋律和声调抬到了最高的地位,文辞的演唱是从属于音高、旋律以及音乐风格,而魏更强调对文字平仄本身的把握:“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务得中正,如或苟且舛误,声调自乖,虽具绕梁,终不足取。”
然而,就曲文和音乐的关系上来看,沈宠绥在《度曲须知》批评魏良辅之流云:“但正目前字眼,不审词谱为何事;徒喜淫声聒听,不知宫调为何物。踵舛承讹,音理消败,则良辅者流,固时调功魁,亦叛古戎首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沈、冯在复古,魏也在复古,魏和《尚书·尧典》“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中国早期音乐理想有渊源关系,目标比沈、冯更久远。唐代元稹(字微之)的《乐府古题》序云:“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长短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往往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显然,元稹认为,在音乐和文辞的关系上,汉乐府存在两种方式,一种和沈、冯二人提倡的依乐腔唱词、填词方式相符,一种和魏良辅提倡的依字声唱词、填词方式吻合。北宋时期,依乐声填词的创作方式却遭到个别人的质疑。北宋王安石指出:“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今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倒置甚矣。”王安石和王灼其实是遵从上古诗歌的创作和演唱方式,和沈、冯二人的观点正好相反,我们不难看出,晚唐北宋以来都是先有曲子或曲谱,然后填词。乐器演奏和音乐旋律决定了作词和唱词的方式,并成为自晚唐和北宋时期词作和演唱的主要方式。《碧鸡漫志》卷二中曰:“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一解(曲),即为填词,故周集中多新声。”
又如苏轼的【醉翁操】自序云:
琅琊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音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南宋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对上面这段逸闻还有发挥:“方补其词,闲(崔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这两段逸闻反映了一个问题:北宋同时出现了依曲作词、依字声作曲的现象,但在当时文人看来,“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说明靠字声的把握来度曲总是不如靠对音乐节奏和旋律的把握来得自然。
这一方式还影响到元曲即早期北曲的写作和演唱。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开头提到:“每病今之乐府有遵音调作者”正好说明当时的元曲大部分还是依乐曲旋律和乐器伴奏行腔,明代还有曲家以此法创作南曲。如明初朱有燉在【南南吕·楚江情】《春》的序中云:“迩者,闻人有歌南曲【罗江怨】者,予爱其音韵抑扬,有一唱三叹之妙。乃令其歌之十余度,予始能记其音调,遂制四时词四篇,更其名曰【楚江情】。”考察朱有燉的【楚江情】的平仄及句式和原南曲【罗江怨】有所差异,显然这并非是依字声作腔的,而应该是依乐曲音高旋律来制曲。至于北曲和旋律的配合要求更严格。又如沈德符《顾曲杂言》记载:“老乐工云:‘凡学唱从弦索入者,遇清唱则字窒而喉劣。’”这都证明了弦索乐器对于演唱北曲的重要性。从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所谓的按音乐行腔过渡到按字声行腔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正如路应昆先生所说的“然而‘文从乐’到‘乐从文’的过渡很漫长,曲乐内部的不同种类也各有不同情形,并非步调一致,不同做法长期处于交错混杂状态。”
显然,沈、冯二人期望的古音的写作和演唱方式远自晚唐、北宋依乐填词、依乐唱词,近承元至明中叶北曲的创作和演唱方式。沈宠绥在《度曲须知》“弦律存亡”中具体论述了字声和弦索乐器的配合:“而欲以作者之平仄阴阳,叶弹者之抑扬高下,则高徽须配去声字眼,平亦间用,至上声固枘凿不投者也。……以故作者、歌者,兢兢共禀三尺,而口必应手,词必谐弦。”这和前面提到的苏轼的做法是相通的。当然沈宠绥上面讲究的以词配乐细化到四声,其实也有依字声行腔的成分,但这种腔格是不能违背乐曲旋律的。
和沈、冯以词配乐的做法相反,北宋末年特别是南宋出现了以乐配词、依字声唱词方式。宋代词人在配乐填词或演唱的同时就逐渐严格字声,如李清照《词论》中说:“诗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他们讲究四声与乐曲旋律的应和,但主要着眼点还是乐曲本身,字声安排妥当,可以帮助乐曲旋律更美听。至于依字声唱词形成的原因,“是由‘由乐以定词’所决定的文辞‘字声’伏涵着音乐基质反生出的歌法,是‘依字声成歌’古老形式在一个新层次上的返归,是一种自觉化、艺术化的‘依字声成歌’。”南宋王灼《碧鸡漫志》是主张先有文字然后谱曲,稍后词人姜夔所谓的“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张炎的“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这和魏良辅提出“箫管以工尺谱词曲,即如琴之勾、剔度诗歌也”意义一样。比魏良辅更早的周德清《中原音韵》也特别讲究“明腔、识谱、审音”,把字的四声及阴阳提到一个极高的位置,对后来北曲昆唱的依字声行腔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初,朱有燉是比较鲜明地反对以乐定辞的代表人物,他在散曲《咏秋景引》的序言中云:“其时,已有李太白之【忆秦娥】、【菩萨蛮】等词,渐流入腔调律吕,渐违于声依永之传,后遂全革古体,专以律吕音调,格定声句之长短缓急,反以吟咏情性,求之于音声词句耳。”要补充说明的是,明中期所形成的依字声传腔的主流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的音乐才华在逐渐退化。
从声乐变迁的角度来看,我们最后可以得到三点启示:第一,魏良辅的改良昆腔并没有“叛古”,而是在复古。他的本意是借古老的“声依永”模式来改造南曲,使其按字声行腔,至于北曲后来的命运是魏良辅始料未及的。第二,宋代开始的所谓的曲唱复古与否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主流艺术理念与非主流艺术理念之间的摩擦互动。非主流艺术理念希望回到主流,而主流艺术理念不愿边缘化。宋以前,“声依永”和“永依声”并行不悖,二者无争论。当“永依声”成为主流理念时,便遭到持“声依永”理念之人的批评,反之亦然。魏良辅批评“永依声”之时,正是南曲依字声传腔模式尚在社会边缘之时。而沈宠绥对魏良辅的批评,一方面是缘于魏良辅改良昆腔导致北曲唱法走向衰落,另一方面是已成为非主流的“永依声”曲唱理念对主流的“声依永”的理念的一次反击。反击的武器仍然是“复古”,但沈宠绥缺乏先秦圣贤经典作为证据,只有宣扬金元以来的北曲依弦索乐器演唱的传统。可贵的是,他清醒认识到这是声乐变迁的必然结果,不可勉强,只能适应。第三,“永依声”和“声依永”并非完全对立,宋代词人在以乐声定词的同时就逐渐严格字声,他们讲究四声与音乐旋律的应和,沈宠绥讲究的以乐声定词细化到四声阴阳,其实也是在提倡“声依永”的理念。
[1]张羽.西厢弹词序[A].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二册卷五)[C].济南:齐鲁书社,1989.
[2]何良俊.曲论[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徐渭.南词叙录[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三)[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任二北.散曲概论(卷二“派别”第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5]沈君庸.鸳鸯梦序[A].叶绍袁编.午梦堂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8.
[6]夏咸淳校点.张岱诗文集(张子诗秕卷之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章金牧.莱山诗集(卷七)[C].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Z].济南:齐鲁书社,1997.
[8]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9]徐翙.盛明杂剧·序[A].沈泰.盛明杂剧初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影印本,1958.
[10]凌濛初.谭曲杂札[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M].1959.
[11]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2]冯梦龙.步雪初声集序[A].谢伯阳编.全明散曲(册三)[C].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十二)[A].续修四库全书(册1480)[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14]魏良辅.曲律[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5]王骥德.曲律[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三)[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6]沈自晋.南词新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7]李玉.北词广正谱[A].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刻本(册1748)[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18]毛晋编.六十种曲(第九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9]王奕清主编.康熙曲谱[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0]沈德符.顾曲杂言[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四)[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1]沈宠绥.度曲须知[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五)[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2]俞为民.曲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3]谢伯阳.全明散曲[C].济南:齐鲁书社,1997.
[24]徐珂.清稗类钞(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5]冯梦龙.双雄记叙[A].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卷十一)[C].济南:齐鲁书社,1989.
[26]元稹.乐府古题[A].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册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7]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册一)[Z].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唐圭璋编.全宋词(册一)[C].北京:中华书局,1965.
[29]施蛰存、陈如江编.宋元词话[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0]周德清.中原音韵[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一)[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31]路应昆.文、乐关系与词曲音乐演进[J].中国音乐学(季刊),2005(3).
[3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册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吴道勤
I207.24
A
1006-2491(2015)01-0081-07
本文是2013年江苏省重大项目基金项目《江苏戏曲文化史研究》(编号13ZD008)阶段性成果。
艾立中(1976- ),男,江西景德镇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戏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