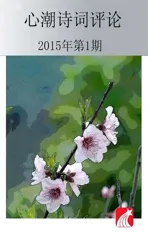回荡百年的悲愤绝唱
——晚清词人叶衍兰、梁鼎芬眼里的甲午战争
2015-11-14巴晓芳
巴晓芳
回荡百年的悲愤绝唱——晚清词人叶衍兰、梁鼎芬眼里的甲午战争
巴晓芳
甲午战败之时,岭南词人叶衍兰、梁鼎芬以此为题材,各写了十首菩萨蛮。词作记录了战争的前后过程,抨击清廷上层的腐朽,哀悼阵亡将士,充满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当时事件、 人物多有品评,自成一家之说。作品用笔曲折,表达含蓄隐晦,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一、岭南唱和——叶衍兰与梁鼎芬的《菩萨蛮》
叶衍兰(1823—1897),字南雪,号兰台,广东番禺人。清代官员、书画家、词人,为清代词坛“粤东三家”之一,人称“南词正宗”。咸丰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户部江西司主事、贵州司员外郎、云南司郎中,官至军机章京。请疾归里,主讲越华书院。
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授编修。历任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曾因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后应张之洞聘,主讲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院。辛亥革命前有反帝主战思想。后任溥仪的毓庆宫行走。诗词多愤世之作,与罗惇曧等人并称“岭南近代四家”。
甲午战败,当时已72岁高龄的叶衍兰,深感于时事艰难,愤懑于心,遂填《菩萨蛮》十阕,抨击时局,全国传诵。梁鼎芬早年曾随叶衍兰学词,与叶家三代均有交往。当时也身在番禺。估计当时二人对战败之事议论颇深,所见略同,一时兴发,故有同题同体之唱和。叶词标题即《菩萨蛮·甲午感事,与节庵同作》,梁词当为和作,标题为《菩萨蛮·和南雪丈甲午感事》。
因为二人均写到了马关条约的签订,所以,具体写作时间应该是在1895年,即马关条约签订之后。
此组菩萨蛮唱和,影响颇大,尤其叶词,据说一时“全国传诵”,但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谈到叶词时说:“此几首词《秋梦庵词集》未载,词意显露,当时似有所讳。”可能是文人同好间传播,未敢张扬。今天资料但凡介绍叶衍兰生平事略者,无不提到“甲午感事《菩萨蛮》十首”,可见其影响。梁鼎芬的和作论者较少瞩目,可能由于梁不仅是诗人,也是学者、书法家、藏书家、高层幕僚,此词在其诸多成就中不算特别,但并不影响其词在词坛上的地位。尤其唱和的集成力量,更增加其影响力。朱德庸《岭南历代词选》,选叶衍兰6首词,录入此组菩萨蛮5首;选梁鼎芬10首,录入此组菩萨蛮4首。叶恭绰《全清词钞》仅录叶衍兰词作19首、梁鼎芬词作20首,但二人的10首菩萨蛮均悉数选入。
二、悲愤词笔——别样的历史记载
(一)勾勒了战争的过程
一百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改变了双方的历史,改变了自古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仰视,也打破了中国对日本的一向傲慢。这是一直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人尤其难以接受的血的现实,他们不能忘记,战争是怎样发生的,更难以容忍战争发生时朝廷的应对。二人词作对战争的全过程,做了几近完整的记录。
记录战争的爆发:叶词之一“锦帐醉芙蓉,边书不启封”;之二“浊雾起楼兰,边风铁骑寒”;梁词之四“无端横海天风疾,龙愁鼍恨今何及” 、“边书”、“边风”、“无端横海天风疾”等,均指战争的爆发。
痛惜战争的惨烈:两词人对战争的发生经过均有记录,叶词之五“淮南赴召牙璋起”;之三“海蜃驾长空,寒涛战血红”、“淮南”句,指李鸿章奉旨迎战。
对战败的悲叹:叶词之三“寒涛战血红”;之八“青燐飞不断,惨惨虫沙怨。江上哭忠魂,同仇粉将军”;之十“卅年竞铸神州铁,水犀翻被蛟螭截。雷火满江红,伤心骇浪中”;梁词之一“开径见飞红,惊呼是梦中”。
对战争后期求和的无奈悲叹:叶词之七“乘槎空挂席,未采支机石。青琐点朝班,琵琶出塞难”,前两句指张荫桓出使日本议和,日本嫌他分量不够,拒绝接待。后两句指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出使日本求和。这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注定是一场屈辱的出使,故以“琵琶出塞难”喻之。梁词之九“峨峨一舰浮东海,春帆楼约千年在”,点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造成“此恨竟无期,寻春岁岁悲”的千古遗恨。
对战争结局的悲观苦闷:叶词之十“长城吾自坏,添筑蠮螉塞。廷尉望山头,思君双泪流”;梁词之九“此恨竟无期,寻春岁岁悲”;之十“冤禽填海知何日,芳怀惹得秋萧瑟”,表达了词人悲凉的心境。
(二)鞭挞了清廷统治腐败荒废国政
鞭挞腐朽的清廷统治者,表达了词人的沉痛之情,这是二人词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二十篇作品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上层的骄奢淫逸、荒淫腐朽。清廷对边防大事,先是漠不关心,后是惊慌失措。如叶词之一“华筵歌舞倦,帘外流莺唤。锦帐醉芙蓉,边书不启封”,同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之二“琅璈钿瑟瑶池宴,素娥青女时相见”;之四“凤窠群女颟顸舞,缠头百万输无数……醉眼太迷离,双双金缕衣”,对慈禧等醉生梦死、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作了无情的揭露。
梁词之二“霜文翠照横晨夕,流杯巧镂桃花石。亭馆极蝉嫣,清风也费钱。 西园莺燕好,拾翠春争道。杨柳袅千丝,谁言非盛时”,其园林楼阁的铺排豪华,让人想起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一片歌舞升平、盛世华章。而词人的点睛之笔也在这里:“谁言非盛时?”将前线的惨败置于此虚幻的“盛世”背景下,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之三“曼延更奏鱼龙戏,骖鸾仙子青霞帔。各自唱回波,纤儿奈汝何。 繁声香旖旎,天也胡为醉。东去望扶桑,麻姑泣数行”;之八“璇宫夜半惊传烛,西头势重貂相属。桃宴酒酣时,春残那得知。 搴芳情绪各,不念花开落。庭院这般荒,有人空断肠”,统治者只看到眼前“酒酣时”,却不理会外面的“春残”。
(三)批评谴责朝廷重臣、高级将领贻误大局
这在梁词中,尤为突出。本来李鸿章就是当时朝廷清流派的攻击目标。梁鼎芬早年曾弹劾李鸿章,被慈禧太后斥为“妄劾”罪,被连降五级。这里不排除梁对李的某种旧恨新仇,如之五“钦䲹违旨谁能捍,狐狸狐搰成功罕。几队狭邪儿,暑寒犹未知”,差不多是骂人了。并算起了十年前弹劾李鸿章的旧账,之十“莫忆十年前,肠回玉案烟”。以李鸿章在清廷的地位、作用和他对中日双方政局及军力的了解,李之主和,比清流派一味主战,很难说哪个是更好的选择。甲午战争的结果也证明主战派的自大与幼稚。
梁词之九“峨峨一舰浮东海,春帆楼约千年在。叔宝是何心,真成不择音。 通人眉语妙,岂避旁人笑。此恨竟无期,寻春岁岁悲”,马关条约,乃城下之盟,本来没有谈判本钱,此时的李鸿章,已是百身莫赎,任何人前往,也不可能取得更好的谈判结果。何况日本人根本拒绝其他人的谈判资格。这里抨击李“通人眉语妙,岂避旁人笑”,恐怕有点过分。
比较而言,叶词对李鸿章的批评比较客观,既指出李鸿章不过是受命慈禧旨意的执行者,之六“汤网总宏开,和羹宰相才”,是否“汤网”只能是最高决策者才能制定,作为宰相的李鸿章充其量不过“和羹”而已。也点明了李鸿章的难处及在清廷中的砥柱地位,先是受命被迫勉强应战,之五“淮南赴召牙璋起”,后是受命出使日本求和,之七“青琐点朝班,琵琶出塞难”。
词人还抨击了贸然求战而贻误战机的朝廷大员,如叶词之九“向阳花木都肠断,青鸾望绝音书远。鵷鹭忒知时,春情听子规。
鸣珂金紫焕,赫赫麒麟楦。簪绂乐升平,终军漫请缨”,指不懂军事的吴大澂乘时投机,轻率地自请出征,虚骄恃气,卒至误事。之五“清人河上乐,卿子谁偕作”, 讽刺宋庆等清军将领作战不力,弃师而逃的可耻行径。
(四)讴歌了为国捐躯的将士
对奋战牺牲在前线的将士,词人则进行了诚挚的哀悼和由衷的赞颂,基调沉痛、悲凉。叶词之五“大漠阵云昏,凄凉烈士魂”,之八“青燐飞不断,惨惨虫沙怨”,明确肯定:牺牲的将士,尽管化为渺小的虫沙,但他们的精神不死,青燐之光,永远闪耀不断。这是对死于国难烈士的一曲赞歌。之十“雷火满江红,伤心骇浪中”,对牺牲于惊涛骇浪中的阵亡将士,表达了深深的哀悼。
(五)表达了对国势危殆的担忧
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这是中国刻骨的耻辱与巨大损失。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与悲痛,对国家的前途,无不表示深深的忧虑。词人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种心情。
叶词之二“泪眼望斜阳,关山别恨长”,梁词之八“庭院这般荒,有人空断肠”,分别以“泪眼斜阳”、“荒芜庭院”,比喻此时国家局势的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不约而同地,两人都在最后一首词中,表达了对国家惨败的痛惜。叶词 “卅年竞铸神州铁,水犀翻被蛟螭截”;对复仇前景的悲观,梁词“冤禽填海知何日,芳怀惹得秋萧瑟”;对光绪的思念,叶词“廷尉望山头,思君双泪流”;梁词“无谓过浮生,思君空复情”。
(六)反映了高层对战事的态度
不可否认,战争期间,清廷也在尽力商讨对策,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叶词之五、之六、之七,分别写到了开战的准备、对将士的奖赏,以及外交的努力,还写到了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上疏请罢慈禧生日庆典的舍身谏言,梁词之七“绿章次第通宵写。不敢负深恩,身危舌尚存”。但谏臣泪干而不得答复,“沧海亦成枯,当筵泪更无”。
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失败的态度如何呢?二人词中也有反映,叶词之九“簪绂乐升平,终军漫请缨”,指吴大澂因指挥不力造成大败被革职,表明朝廷在追究责任。梁词之三更透露了慈禧的心态,“东去望扶桑,麻姑泣数行”,此二句学者均解释为:对于海战的惨败,连神仙麻姑也不免伤心流泪。然而,麻姑既不是著名神仙,也跟日本没什么关系,此说就显得突兀而莫名其妙。窃以为,在中国文化中,麻姑首先是以女寿仙面目出现的,“麻姑献寿”是广为人知的民间文化符号。甲午战败恰恰与当时的女寿星有关,慈禧为做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之事举世皆知,颐和园长廊还有麻姑献寿的彩绘画像。所以,此处应是以麻姑暗喻慈禧,这样解释才合理。
最后,愤怒谴责了日本的挑衅与侵略。叶词之二“扶桑东海树,移种荒崖去”;梁词之六“无端横海天风疾”,表达了对日本无端挑衅、悍然侵略、无耻敲诈等行为的正义谴责。
三、时事入词——“词史”的艺术特色及局限
(一)词中的历史
诗词写作,无非抒情、叙事、写景、状物,作为诗言志的产物,尤以抒情为宗。即令写景状物叙事,也往往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记事寄怀。两组二十首菩萨蛮以“甲午感事”冠名,若不是如此重大的时事题材,若不是深深刺痛了词人心灵,以致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词人断不至于兴起十首组词的浩繁工程,且与词友同作,让词这个通常只表现小题材,多为“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文学形式,承担起重大题材的使命。这是对清初以来词坛逐渐明朗的“词史”主张的一次有力回应和生动实践,是镌刻在词史上的重要词章,辉映在词史上的二十颗闪亮星星。
两组菩萨蛮,出自两位高手,各有千秋。比较而言,叶词似乎稍胜一筹。一是内容更丰富,涉及面更广泛,十首词几乎是对甲午战争整个过程的全面扫描。二是对历史大事件的看法上,立场更为冷静和客观,在大局的观察上更成熟。如对李鸿章的作用就不是简单的批评指责,对主战派也不是片面的赞扬,对他们的草率应战也有批评。三是艺术上,更含蓄内敛,情感的抒发也更冷静。含蓄、委婉、蕴藉,本是词的本色,二人词大体均符此旨,而梁词个别篇什,或失于直白(如之五),或纠结于个人恩怨(如之十),如前所述,也许是意气用事,结果以意害词,影响了词的整体风格。在十首词的内容分配上,叶词更有次序,从战事的起因、过程、失败、反思,大体按事态的发展顺序进行结构。梁词则缺少这种有序的逻辑结构。
鉴赏二十首菩萨蛮,可以感受到当年黄海的惊涛骇浪,京畿的咫尺狼烟,对于朝廷的腐朽与惶恐,大臣的吵嚷与偏执,词人则只有发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无奈悲叹。两组词篇幅不长,但因其内容的独特性,从而成为一页别具一格的历史——词史。今日读来,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如在眼前。
关于“词史”问题,清代词学大家的“词史”主张、晚清词人的“词史”意识,如今有不少学者论及,其概念、外延与内涵,其意义、地位与作用等等,此处不一一列举。既然有“诗史”一说,“词史”一说的“合法性”自然不成问题,学界对此已有基本共识。
具体到清词,具体到叶、梁这两组词的词史地位如何?清词成就之高,已有公认,刘梦芙认为:“词虽历元、明而衰靡,但到有清一代,又出现中兴的繁荣局面,名家辈出,灿若群星,足以抗衡两宋。”这是纵向比较,或许不错。但是横向比较,特别是将清词的“词史”与同一时代的“诗史”进行比较,恐怕就不容乐观。重大题材入词,固然突破了传统的狭小藩篱,壮大了词的阵容,提高了词的地位,但是若以“史”的标准来衡量,还远不如诗之于“史”的分量。只简单地求证一下即可:有多少人从清词中读到了历史,多少人从叶、梁菩萨蛮中看到了甲午战争?而我们从诗中读到的历史比比皆是。这里的原因何在?
(二)体裁的局限
一是词牌繁多的局限。诗的体裁形式相对简单: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加上古风,体裁大略不超过十种。而词的体例多达一千余种,常用词牌也有上百种之多。如此之多的词牌形式,固然增加了表现的多样性,却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也严重影响了传播效果,不利于普及。
二是曲笔的局限。比喻、用典、含蓄、隐晦等曲折之笔,是词人常用的修辞手法。且看叶、梁两组词,二人均是大学者,满腹诗书,笔下词章,无处不用典,一地的书袋子。有的地方用典、暗喻叠加,更显隐晦。如按照谭献对词人的三类划分,二人当属“学人之词”。在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庙堂政事莫测高深,江湖恩怨外人难道的大背景下,要读懂这二十首词写就的“甲午战争史”,确要下一番考证功夫。不是专业人士或有特别研究之需,恐怕很少有人下此功夫。
含蓄、隐晦的曲笔,本是词的一大特色,一种特有的文学艺术美,但是一旦作为“词史”,词的首要功能诉求,恐怕就发生了变化:不是抒情而是叙事,不是艺术鉴赏而是历史记录。然而,曲笔的表达就带来了阅读理解的问题。其比喻象征等种种隐晦曲折的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不仅不再是美的要素,反而成了阅读的障碍。比较一下作为诗史、明白如话的杜诗“三吏三别”,韦庄的《秦妇吟》,今人对它的阅读理解,没有一点困难。这是诗词本身表现方式区别带来的理解差异,词承担“史”的先天局限使然。就此看来,“词史”恐怕也就只能局限于小众圈子,不大可能走向大众,当然也就局限了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关于词在这方面相对诗的局限性,有不少论及。学者马大勇说:“与诗相较,词因婉曲多讽,尤宜于承载个人情怀的文类特点,其记录‘大历史’之功能稍显逊色。”(马大勇《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心潮诗词评论》2014年第2期)
(三)观察的局限
如果以词史来看这二十首词,公允地说,它们大体反映了甲午战争的基本轮廓。叶、梁二人作为词史的记录者,指点江山,褒贬是非,月旦人物,充分表达了作为历史观察者对时局的分析,做出了一系列价值判断。
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些观察或许失之于片面;有些判断可能不一定准确,如对主战派主和派的褒贬。
和与战孰利孰弊,后人也许认识更清醒一些。然而有一种舆论氛围,好像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以此占据道德高地。如主战派文廷式曾奏劾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谏阻和议,以为“辱国病民,莫此为甚”。这种以战为荣,以和为耻的思想也体现在词中。叶词之五“烽火已漫天,何时着祖鞭”,何尝不是对主战者的鼓励。梁词更是对主和派痛加谴责。
值得一提的是,文廷式是梁鼎芬的好友,其主战思想必然影响到梁。词中对文等人充满赞扬(之七),对李鸿章多有苛责乃至嘲骂,这里恐怕就包含某种个人的恩怨。
但是“和议”是否就是辱国呢?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总结甲午战争时指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6月第87页)对主战派主和派的历史功罪作出了评判。
陈寅恪先生的学生石泉从晚清政局纷争的角度谈甲午战争,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思考:“晚清自太平天国后,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对峙,中央由清流与后党为主,地方以湘军淮军为首,四方势力相互制衡。至甲午之战,清流逼迫湘淮军出战,借日本削弱地方势力,却不料战争兵败如山倒,连带自身亦遭到排斥。我们不妨大胆猜测,甲午之战实际为慈禧一手策划导演,先用清流逼迫李鸿章就范,然后因战争失利先罢黜李鸿章,再排斥清流党,最终将权柄收回己手。”(三联出版社《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同历史学家的煌煌巨著相比,几篇词章当然不是一个量级。这种局限不仅存在于词史、词人,也存在于诗史、诗人。毕竟,诗人词人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时间老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充分肯定这两组《菩萨蛮》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它的“词史”地位,它特殊的镜子作用,它的历史认识价值。
(作者系《湖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