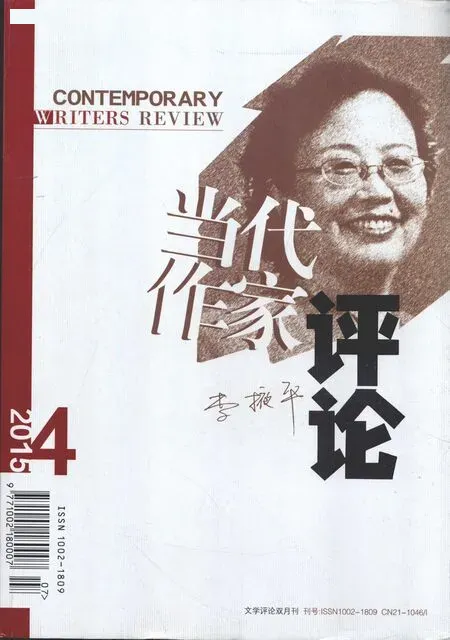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
2015-11-14安德鲁霍布里克史国强
〔美〕安德鲁·霍布里克 史国强/译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化
〔美〕安德鲁·霍布里克 史国强/译
在《中产阶级的暮光》(The Twilight of the Middle Class)一书中,我提出要“辩证地阅读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世界观所指不仅是中产阶级的特权,还有这种特权的空虚:痛苦地发现你没有外力,在世上无法通行。”更明确地说,我要强调的是,朝着后现代主义转向时,作家们对白领工作(作家身份也在其内)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所取的姿态——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等写作风格大不相同的作家也在其中——不是非要精巧地推出没有污染的个人风格,而是要渲染在形式上与制度一同来临的、威胁中产阶级个性的压力。因此我们发现后现代派不再关注个性化——比如,在品钦(Thomas Pynchon)的《万有引力之虹》(一九七三)里,徒有其名的主人公斯劳斯洛普(Tyrone Slothrop)是如何发散后消失的——并将非个性化视为设想中机构人(organization men)人格发散(depersonalization的相伴物。我还提出,后现代派吸纳类型元素,将类型视为“泰勒化的”(Taylorized)、程式化的脑力劳动形式,对这种劳动形式,作家们无法拒绝,只能亲身经历。
撰写此文时,我知道还有欠缺的地方,尽管我说不好其中的原因。我仍然以为,就如何理解后现代主义与类型的关系,还有不少话要说,尤其要顾及后来的作家如莱瑟姆(Jonathan Lethem)、迪亚兹(Junot Diaz)、埃根(Jennifer Egan)等以不同的方式接纳类型形式(更少的自我意识,更少的精英成分,往往是更多的快乐)。不过,论及后现代与类型的关系,我描述过的、我在这里正在描述的不是简单的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后现代主义的晚期形态:比如,在《名字》(The Names)(一九八二)里,德里罗(Delillo)的侦探惊悚故事或灾难片《白噪音》(White Noise)(一九八五)是何等的平庸。但这里要指出的是,菲耶德勒(Leslie Fiedler)一九七〇年撰文《越界——弥合差距》(Cross the Border—Close the Gap)——这里的差距指高低文化之分——在详述“后-现代主义”这一范畴时,作者描述了当时的当代作家与他们借用的大众类型之间明显不同的关系:
他们选取的小说形式是……尽可能地摆脱艺术和先锋,远远地离开内省、分析和做作;因此,一方面不受抒情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受自以为是的社会批评的影响。这不是对他们感到恐惧的市场的妥协;相反,他们选择的类型所受大众媒体剥削最深:显著者如西方的东西、科幻小说与色情文学。
这并不是当下作家与类型小说之间真正的关系——请注意,后来的作家们正是为了抒情性和社会评论才转向大众类型的,这也是指出不同之处的方法之一,不过,上述引文确实在暗示,在一个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不如说是黑色幽默的时期,颇有抱负的美国作品在其同族堂兄那里发现的倾向是反系统(anti-systemic),而不是系统。这方面品钦在《对抗时日》(Against the Day)(二○○六)里从高高在上的后现代派朝着类型管理员的转向,与其说是转变,还不如说是一次迟到的抵达。
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把后现代主义当成二十世纪末美国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读,不过,当人们希望以辩证的方式来思维时,我描述的仅是辩证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大众类型造成的个人风格堕落,后者也是泰勒化脑力劳动的物化产品。另一方面是移位的美学对这种无产阶级化的抵抗,在类型转向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化与之相伴相生,无政府、低俗、市场驱动是其表现形式。如默里蒂(Franco Moretti)所说,如果小说一再借助“低俗”的形式更新自己,那么,从后现代时代一开始,大众类型就以拙劣的文字形式提出了榜样,以此来对抗形式上的完美,与这种完美相连的是习俗化的现代主义。与此同时,大众类型还代表着堕落的脑力劳动的发源地,后来这种倾向变得越发地明显,最终后现代主义也经历了习俗化的嬗变,披上了现代主义精英的价值。面对这种普遍倾向,个体作家早晚能发现他们不是站在等式的这端,就是站在等式的那端,当然这种站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还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既要厘清中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又要提出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
如此梳理战后小说就更为重要了,因为后现代批评史与其说是要分析一场连贯的运动,不如说是要表达对文学历史范畴的渴望。所以,读詹姆逊(Fredric Jameson)那部集大成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九九一),就要将其视为伟大现代主义者的绝唱,因为他的演出居然从现代主义已成定论的失败中发现了几分成功。这位批评家还就现代主义进行了最为成功的描述,这不是偶然的,如贝斯特(Stephen Best)和马库斯(Sharon Marcus)所说,詹姆逊的著作《政治上的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一九八一)恢复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学说的地位,他们的学说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强调“症状”或深度阅读,当时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反深度(anti-depth)的思潮所撼动。
然而,我们在这里才能发现,后现代主义与战后美国中产阶级之间或许存在着最诱人的关联。因为,要是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姗姗来迟的话(到目前为止,后现代主义的欲望不可避免地落空了,没能继承现代主义那身斗篷),那么战后中产阶级也是如此。的确,这个中产阶级与昔日中产阶级的种种显赫,有人说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足的后-现代。我们发现流亡哲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著作《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中,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说法有过论述,他的论述不仅发表得早,而且颇有影响。弗洛姆一开始就指出,“在过去几个世纪令西方文化大放光彩的骄傲与乐观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派生出的对“物理能”(physical energy)的拥有,已经在一个时代里宣告完成,因为“生产问题——过去困扰人们的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不过,作为胜利的源泉,这一成就又造成了一种局面,其中的——
现代人感到不安,越来越感到困惑。他们劳作,他们进取,但他们对自己的活动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种徒劳感。他们驾驭物质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但他们在个人生活和社会方面却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为征服自然找到了新的、更好的方法,但他们却深深地陷入这些方法构成的网络之中,失去了目标,而这目标才是他们的意义所在——他们自己。
弗洛姆指出,当代人对这种危机作出了回应,其方式是“返回希腊人的启蒙、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已经占领的地方”,以“国家的要求,以伟大领袖身上那些神奇素质引起的热情,以强大的机器和物质成功,作为其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的出发点”。上述所列各项清楚地表明第三帝国对弗洛姆思维的重要,虽然他也间接地提及中产阶级现代性的特点,其表述方式在其美国继承者们那里,将变得格外重要。弗洛姆指出,在十八、十九世纪里,“稳定的世界、稳定的财产及稳定的伦理让中产阶级成员有了一种归属感、自信和骄傲”,但当代中产阶级的特点被“市场方向”所左右,“希望走在前面的”个人“要使自己适合庞大的组织,他扮演所属角色的能力是他的一份重要资产”。
战后评论美国中产阶级,凡著名者都继承了弗洛姆的观点:当代生活标志着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方现代性时期的断裂。如里耶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九五○)就描述“外指”(other-directed)性格类型如何从之前的“内指”(inner-directed)性格类型演变而来,就从他昔日的老师弗洛姆那里借来不少东西。里耶斯曼以人口模式划分性格类型,其要素是人口的相对增长,他按出生率和死亡率把社会分开,在生死人数大体相等的社会里,“指向传统”的性格类型占大多数;“从十七世纪开始的西方社会”人口激增(内指);与战后美国相同的社会,低出生率再次造成低生长率(外指)。这种披着决定论色彩的分类法广遭诟病(还不是因为其后出现的婴儿潮),里耶斯曼在一九六一年版的序言里又将其大部分收了回来。然而,不太明显,也不太被人注意的是,这种三分法正好适合将西方历史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里耶斯曼明确指出,内指的性格类型“在西方社会历史中”有着示范作用,这一“西方社会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同出现。其特点是个人移动增多,资本迅速积累(伴之以惊人的技术转向),还有不停地扩张:商品和人口的扩张,及开发、殖民、帝国的扩张”。里耶斯曼指出,因其他方向的崛起,这个社会“此刻正在消亡”。其他战后分析家对萎靡的中产阶级所作的判断,其结构虽然不如里耶斯曼的历史三分法复杂,但也足以使中产阶级与其发挥能动作用的现代形成对照。怀特(William H.Whyte)以新的当代商业社会伦理对抗新教伦理,“崛起的中产阶级”借助新教伦理充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急先锋;米尔斯(C.Wright Mills)将白领劳作的新世界比作“经典自由主义的时代”,后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小企业家的大批存在”,他们生活的社会“没有封建传统,没有官僚国家”。
等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另一些美国思想者开始研究解决中产阶级没落的方案,后来证明他们的方案很有影响。据他们的说法,“通过加速自然进程,‘传统’社会将走向显然以美国为榜样的开明的‘现代性’”,美国致力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现代化,其努力将使中产阶级美国人拾回他们失去的能动作用。实现这一设想有两种方式,一是提供场地,重振美国企业,使用美国的专业技术,二是改变所谓第三世界的国民,把他们变成美国的代理人。
第三世界的说法最早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家索维一九五二年在《观察家》(L’Observatear)上正式使用的,这一说法提出的概念是指(法国版的)中产阶级现代性在当代的继续:“因为那个第三世界,如(法国的)第三等级,被无视,被剥削,被唾弃,所以也想有所成就”虽然索维注意到第三世界作为冷战战利品的角色,但他同时提出,第三世界也能形成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同时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如当年法国政治现代性发生时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贵族和僧侣的世界。继发轫者塞泽尔(Aime Cesaire)之后,索维修改了马克思,提出第三世界(不是无产阶级)将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其方式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再现资产阶级革命,借此引发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就是积极意义上的后现代。
这是更生之后的后现代,通过现代化的概念,新生的后现代将被讨论后现代如何没落的美国话语所吸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现代化理论出现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比较政治学社会关系研究委员会和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里耶斯曼提出上述历史设想的前后,杜鲁门也确定了以援助促发展的冷战战略,其实里耶斯曼已经提到了参差不齐的发展,一些国家仍然停留在以传统为指向的前现代模式上:
半数以上的人口出生在高增长国家或地区:印度、埃及和中国(最近几代人口激增),此外就是中非没文字的民族,部分中南美洲,事实上,还有工业化没有波及的大多数地方,那里死亡率是如此之高,要是出生率跟不上的话,人口就得死光。
在这种语境下,论述人口增长的语言(日后里耶斯曼又推翻了)听上去更像关于发展的话语,这种话语源自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之后是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再到今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代化理论的聪明之处是,选出一系列问题——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如,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剥夺问题;从战略角度,如,不使那些国家落入苏联的阵营——再把这些问题变成解决另一些问题的方案,如失落的中产阶级能动作用。
罗斯托(Walt Whiteman Rostow)一九六〇年出版的《经济增长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可谓现代化研究的圣经,这部著作提纲挈领地概括了上述转向。罗斯托原为经济学教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与肯尼迪相识,因助其竞选,一九六一年进入政策规划团队,开始从政,后来又成为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斯托明确地提出了“起飞”模式(model of “take-off”),以此来对抗苏联模式,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出现“经济发展的力量不断扩张,逐渐占领社会”,“增长变成社会的常态”。他把外交政策上遇到的难题变成解决中产阶级萎靡这一国内危机的方案:
在这两种问题之间——军备竞赛和满怀渴望的新兴国家,这方面的问题与当代外交密切相关——对技术上更为成熟的北方社会来说,还存在着更为紧迫的任务,虽然消费者商品与服务乃至大家族在讨我们的好,但我们最好还是把注意力放在紧迫的任务上,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知道,世俗的精神麻木——或无聊——能不能被征服。
美国外交政策还要顾及“无聊”,对这一绝妙的提法,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罗斯托显然是以弗洛姆的方式在说话,他指出,美国人成功地走完了现代化过程,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当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失去魅力之后,还怎么办?孩子呀,无聊,三天的周末,月亮,或制造出新鲜的、内心的人类边疆,以此来替代昔日匮乏造成的压力?”罗斯托自问自答,为“雅加达、仰光、新德里、卡拉奇、德黑兰、巴格达和开罗,还有沙漠以南阿克拉、拉戈斯和索尔兹伯里的人们的困境与烦恼”,提出了化解危机的方案。罗斯托接下来说:“要理解上述关键地点在发生什么,创造性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这话表面上是在论述他自己的理论模式,但暗指战后社会批评一再重复的话题:白领组织人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所缺少的正是“创造性想象力”。要是将(罗斯福的)新政视为专业管理阶层最后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个阶层的成员为着社会利益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结果又造出来一个资本集中的世界,瓦解了战后中产阶级的能动作用——那么,罗斯托的书是在告诉我们,或者可以把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视为生产物料管控,其目的是在国外施加影响——这一外交政策终因越战和“伟大社会”蓝图的褪色而宣告结束。
后来罗斯托因其顽固地支持越战为人所知,也因此为人痛斥。虽然现代化理论已经收场,但罗斯托为复苏中产阶级的能动作用将视线投向国外,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拥护冷战或国家权力,还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知音。我们在米尔斯对古巴革命的描述中也能发现罗斯托的转向,米尔斯的《古巴革命》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各阶段》同年出版。其时《白领》(White Collar)已近出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米尔斯的书越写越悲观,《古巴革命》的到来是在宣布“西半球一次新的开始”,是开拓精神在加勒比的继续。虽然在卡斯特罗的问题上米尔斯与肯尼迪政府南辕北辙,但他与之也有相通的地方:第三世界现代化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复苏提供的不仅仅是想象的也是实用的空间。米尔斯与这个中产阶级打了招呼,他为撰写《古巴革命》采访了古巴人,下文大概是被访者们共同的声音:
因为你们那么有钱那么强大,你们有资格决定怎样对待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国家。你们的选择是重要的选择。所以你们现在还是一个边疆。你们才能问人该怎样生活;你们不必为生存挣扎。是的,你们还在边疆上,美国佬,要是你们想要的话。边疆对于你们——你没发现吗?——首先,在你们的南边,在你们的东方。美国佬,那里是饥饿的世界,是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世界。但首先,大概,都应该纳入美国的政治经济。
“新边疆”三个字自然是肯尼迪政府的标志,是肯尼迪的讲稿撰写者和罗斯托依据他人的描述生造出来的短语。肯尼迪和现代化理论家们把发展当成旧中产阶级开拓精神与新中产阶级专业技术的无缝结合,米尔斯与他们相同,他把古巴人“革命的幸福感”描绘成“一次新开始”,不仅仅对古巴人是如此,“对你们(美国人)”亦复如此——因为北美人“不也曾经……朝气蓬勃”嘛。
先把政治话题停下来,我们还要指出米尔斯是如何以不和谐的声音来表现《古巴革命》的,书的开始与结尾另作他论。第一章的第一句“我们古巴人知道,你们以为我们都是被一小撮共产党领导的”,要是这句话对我们来说感到格外刺耳的话,那就说明米尔斯在古巴发现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精神,还有一种写作风格。米尔斯的上一部书《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要找到一种适合“我们时代历史现实和政治事实”的写作形式。一旦“严肃文学在众多方面退化成一门小艺术”,无法完成自身的角色,社会学的写作就将分裂开来,一边是泛泛的大理论在风格上造成的毛病,一边是限定在“认识论的方法问题”之内的“抽象的经验主义”。虽然米尔斯名正言顺地被读者视为韦伯式的集权批评家,但他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走得太远,居然提出美国和苏联在集权方面出现的“后现代高潮”,促进了“历史进程中人的能动作用”,至少在精英分子中是如此,说那些机会之所以没有抓住,原因是“在西方社会为人们创造历史闪现希望的意识形态,已经没落,而且正在崩溃”。如果我们把上述推论理解成对集权社会制度日趋没落的回应(以上是米尔斯在《白领》和一九五六年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等著作中描绘的画面,其目的是断定,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在知识分子如何在制度下工作,如何书写制度,尽管他们要受到制度的束缚),那么,古巴就办到了旁人办不到的:既送了他一个权力分散的历史样板,又告诉他如何撰写这个样板。《古巴革命》听上去有所不同。说古巴人的好话,米尔斯借此丢下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批评,转而以第一人称复数的散文来歌颂,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革命的写作风格:“我们并不是重建古巴社会,因为这里没什么值得重建的。我们在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从上到下,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国家的新生。”
这种风格的转变为《古巴革命》赢得了地位,不仅在美国社会学史上,在美国散文史上也是如此,原因是这部作品预见了从讽刺到情感投入的转向,后来菲耶德勒在一九七〇年才将这一转向定性为新式美国写作的一大特色。如同菲耶德勒描述的那些作家,米尔斯也在借用被神化的边疆和非殖民化的第三世界,以此为出发点,来对抗战后美国上上下下变了性(denatured)的世界。但米尔斯让开了原始主义(primitivism)和令人不安的暴力——菲耶德勒认为这两者与上述新式散文也有关联——所以选择米尔斯为这种散文写作的代表才有价值,不去选择垮掉派的人物或梅勒(Norman Mailer),尽管他们平时被引用得更多。越战后之后的菲耶德勒在“游击队暴力”的幻想中发现了第三世界的反抗,反抗指向“一无灵魂、二无人性的官僚国家”,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反抗与他所谓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理性和政治事实领先性的捍卫”有着明显的不同。不过,抱有相同理想的米尔斯要在第三世界为社会与风格的新生找到更为乐观的,哪怕是浪漫化的源泉。对米尔斯来说,第三世界现代化所做的也是菲耶德勒眼里暴力的、前现代的第三世界对这种现代化的抵抗。米尔斯可能担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僵化的社会学和官僚化的社会相伴相行,其实,小说家和批评家在二战之后就开始为小说领域出现的相同现象感到痛苦了,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小说从二十世纪初的辉煌状态漫无目的地坠落下来,如同从中产阶级手里坠落的历史使命。但如我们所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左右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的现代化理论家和公务员,已经开始为冷战制定新战略,要把新兴国家变成美国中产阶级找回其能动作用的场地。在风格方面,美国写作对这一转向有所表述,但总的来说与作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无关。
米尔斯是个未必合适的例子,我选择他来说明一种新风格,不仅是因为他明确地指出了新风格与美国现代化政策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原因:他既拥护肯尼迪政府,又拥护与第三世界革命相伴的浪漫化的政治,他在两者之间徘徊,他的政治立场清楚地表明,现实政治与这种感情结构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如同社会学家关注社会学家如何写作,米尔斯让我们看到,歌颂他国人民的真实性(我们一般将其视为文学上的身份政治),是如何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与后现代主义一同发生的。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原因既有政治的,更有美学的。
【译者简介】史国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安德鲁·霍布里克(Andrew Hoberek),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英文教授,在《中产阶级的暮光》(The Twilight of the Middle Class:Post-World War II American Fiction and White-Collar Work)之外,还著有《后现代主义与战后及之后》(Postmodern/Postwar—and After)和科幻小说《沙丘》(Dune)等作品。
* 文章选自Postmodernism and Modernization,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57.3& 57.4 Fall/Winter 2011,后收入Daniel Worden, Jason Gladstone与Andrew Hoberek编辑的POSTMODERN/POSTWAR--AND AFTER,该书即将由University of Iowa Press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