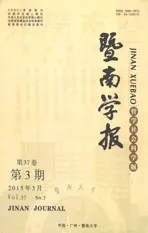魏校岭南毁佛述略
2015-11-14林有能
林有能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 广州 510050)
岭南佛教行进至明朝,有两件事影响较大:一是魏校毁佛;二是憨山兴佛。兹就前者略作陈述。
魏校(1483—1543),字子材,苏州府昆山县人,因居苏州葑门之庄渠而自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移疾归。嘉靖初任广东提学副使,次年丁忧服阕,后补江西兵备副使,改河南提学。嘉靖七年(1528)升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次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嘉靖九年(1530)七月致仕,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年六十一,谥庄简。《明史》、《广东通志》、《粤大记》等均有其传。
魏氏学宗胡居仁,工诗文,著有《周礼沿革传》、《周礼义疏》、《郊祀论》、《春秋经世》、《大学指归》、《奕世增光录》、《官职会通》、《体仁说》、《魏庄渠粹言》、《巷牖录》、《庄渠遗书》、《庄渠诗稿全编》等。
魏校于正德十六年(1521),作为按察司副使督学广东,次年丁忧辞归,寓粤虽仅年余,然因其大毁淫祠寺观、兴建社学书院而见诸史籍文献。嘉靖三十七年《广东通志》卷二十民物志一《风俗》说:“习尚,俗素尚鬼,三家之里必有淫祠庵观。每有所事,辄求祈谶,以卜休咎,信之惟谨。有疾病,不肯服药,而问香设鬼,听命于师巫僧道,如恐不及。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始尽毁,而痛惩之,今乃渐革。”郭棐《粤大记》曰:魏校“乃大毁寺观淫祠,或改公署及书院,余尽建社学。……自洪武中归并丛林为豪氓所匿者,悉毁无遗。僧、尼亦多还俗。”屈大均《广东新语》云:“吾粤督学使者,在嘉靖时有魏公校者,……大毁寺观淫祠,以为书院社学,使诸童生三时分肄歌诗习礼演乐,禁止火葬,令僧尼还俗,巫觋勿祠鬼,男子皆编为渡夫。”
魏校所毁之“淫祠”何指?《礼记·曲礼》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在古代,“祀”“祠”互通,因之,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界定:“中国古代,淫祠通常是民间不合国家祀礼的宗教信仰的总括性指称。”“所谓淫祠,就是指与朝廷所编纂的祭祀典籍(祀典)里所记载的祠庙,即与通称的正祠不同,未被祀典登录的祠庙。”说白了就是国家政权对“神权”的垄断。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屡有禁、毁“淫祠”的规制和举措。明代也不例外。洪武三年颁布了《禁淫祠制》:
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祀天地,祈福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犯分莫大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于是中书省等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祭灶,乡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厉郡厉之祭则里社自为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祇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扶鸾祷圣符咒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
《大明会典》也规定,社稷山川风雨雷神、帝王忠臣烈士等“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祇”,各级官吏均要祭祀,“其不安奉祀之神”一律禁止祭祀,违者杖八十。而所谓“不安奉之神”,即《大明律》所列的“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对这些人“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类似的律例禁令还有不少。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多受传统儒学所浸润,在国家政权“独尊儒术,罢默百家”的客观政治背景下,其禁毁“淫祠”乃顺理成章之举。所以在明代广东,比魏校更早毁淫祠的大有人在,如吴廷举于弘治二年(1489)官顺德知县,颁《禁淫祠条约》,毁“淫祠”不遗余力,在任期间,顺德“通县计去淫祠二百二十五所”。嘉靖时丁积任新会县令,“其不载祀典之祠,无大小咸毁之”。
魏氏之毁淫祠,涉及面很广,凡是官方不认可的寺、观、祠、堂等均为所毁之列。这里的“淫祠”虽无特指佛教之庙宇,然佛教自汉东来华夏,经千百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融合,已和中国本土的道教一样,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宗教,虽有别于民间信仰、祖先崇拜、圣贤祀奉等,然其内容及仪轨却又深深地渗透于各种民间信仰中,换句话说,中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信仰很难与佛教划清界限,比如在岭南嘉应地区流行的“香花佛”,到底是民间信仰还是佛教就难以辨清。有学者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往往被官方视为危险的邪教和异端”。所以,在毁淫祠的打击中,佛教的发展乃至生存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难怪英国学者科大卫在评论魏校毁淫祠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时,特别提到了佛教:“明代的反宗教活动,往往牵涉地方庙宇和佛寺两方面,魏校这一次亦相同”。而以魏校的言行观之,似乎他骨子里就有尊儒恶佛的潜在意识,清人檀萃就直言:“庄渠视学于粤,恶佛氏,必诋之”。
那么,魏校之毁淫祠到底对明代岭南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窃以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毁“淫祠”中毁掉了不少佛教道场,把佛教寺庙改为社学和学院。
魏氏在粤时间不长,到底毁了多少佛教寺庙无法统计。从地域上看,首当其冲者当是省城广州。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魏校发布了广州城内捣毁淫祠及改淫祠为社学的命令:
照得广城淫祠所在布列,煽惑民俗,耗蠹民财,莫斯为盛。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当职怵然于衷,拟合就行,仰广州府抄案委官,亲诣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于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厂者,改建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南社学七区。
这七个区社学多由佛道寺观改造而成,具体情况是:石头庙巷的定林寺改为中隅社学、番禺县衙门西的真武庙改为东隅社学、城西西市街的五显庙改为西隅社学、南门外褥子巷的西来堂改为南隅社学、城北顺天门街的大云寺和小府君庙改为北隅社学、南门外永安桥西的大王庙改为东南隅社学、西城外蚬子步的小天妃宫改为西隅社学。
而城外粤秀、白云两山上的佛道场所均被易为书院。“照得粤秀山一城之镇,故有观音阁,今改而新之,崇奉宋广东漕宪周元公遗像,顺民心也。山之左为迎真观,右为悟性寺。因并废之,塑奉程淳公正公遗像。南有仁皇废寺,塑奉朱文公遗像,即其旧扁更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四书院。迎真观之左有天竺寺,改为崇正书院,合祀四先生。”关于白云山的状况,屈大均则有详述:“白云之山有三寺,中曰白云,左月溪,右景泰,盖山中之三胜也。嘉靖间,三寺既毁,于是泰泉黄公,以景泰为泰泉书院,铁桥黄公,以月溪为铁桥精舍,甘泉湛公,以白云为甘泉书院。自作《白云记》,谓‘仙变释,释变儒。’王青箩读而嘉之曰:‘其变之终于正矣乎’,遂书‘白云三变’匾而揭焉”。
而在省城外域,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只要其触角所及均必受其损。魏氏曾令“髙明县教谕李士文,四会县教谕林启,增城县教谕易文彬,新会县训导萧浚,从化县教谕唐仁,新宁县训导倪廷玉,分诣各乡通查,一应淫祠尽数拆毁,收贮材料变卖地基兴建社学。”在博罗,延庆寺因近泮宫,当地儒生翟宗鲁以扰书院而告诸魏校,要求迁寺,得魏氏允准并欲推而广之。屈大均《广东新语》记此事云:“翟一东先生宗鲁,初为诸生,以博罗延庆寺逼近泮宫,上书督学魏公校曰:‘风鸱不并树而栖,兰棘不同林而植。今泮宫实厌招提,庠声嚣于梵音,青衿杂于在袱,非所以息邪反经,崇儒贞教也。徙寺他所,以其地广学宫便。’魏公从之,谓此议可行于天下。”檀萃的《楚庭稗珠录》亦云:“登峰书院故延庆寺也。康先生茂园视博篆,念罗阳湫隘,以寺为书院;别建寺院之左,移佛像居之。夏木千章,重阴交翠,晚钟动寺,曙鸟啼林,吟声梵声,东西唱和,亦天皇寺之画图也。寺故在泮宫之东,明嘉靖时,邑诸生翟宗鲁请于魏庄渠,校徙之登高,致僧讼于阙,事几不解。庄渠视学于粤,恶佛氏,必诋之,故宗鲁之言易入。”
在粤西雷州,魏氏令当地官员将“境内淫祠及废寺观,尽数折毁,以祛数百年之惑,变卖地基收贮材料以兴社学,凡可以便民者,从宜为之田粮入官,其师公师婆火居道士圣子人等,俱令首官改正,追出袈裟、法衣、神像、经箓之类,当官烧毁”。
在粤北韶州、南雄等地也有毁寺观改为社学的现象。甚至六祖慧能的道场南华寺,魏氏也欲拆毁,只因地方官员劝阻和僧众的力争才未得逞:“(魏校)出巡韶郡,欲入南华山拆六祖寺,时得郡守后尚书周厚山公解乃罢。”寺虽幸免拆,却把六祖衣钵砸碎。(这点下文将详述)
在拆毁佛教庙宇的同时,魏氏把寺中佛像,尤其是铜铸佛像熔毁变卖,以作改铸先贤遗像的资本,如在广州他令广州右卫指挥李松为监督,将佛寺的铜像熔化卖掉,以此为本钱铸造先贤遗像:“广州右卫指挥李松,督同武生黄泽、黄节将佛寺铜像镕卖,赁工修塑立先贤遗像,查取淫祠神位座案炉瓶钟鼔应用”。在粤西雷州,把“天宁寺铜鼓并各寺院铜皿,送学镕铸祭器,以绝怪诞”。
中国的佛教,特别是禅宗至隋唐时期出现繁盛的景象,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丛林道场的形成,个人的头陀苦行游方变为僧众集聚习经修行。所以,寺庙道场是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载体。而魏氏毁寺观,无异于削挖佛教的根基。
第二,强令僧尼还俗或集中管理。
魏氏在毁淫祠、摧毁佛教道场的同时,设法削弱信众的队伍,具体措施有:一是把持有度牒的僧尼集中于光孝寺,由僧纲司统一管理。在对佛教信徒的管理上,明代沿袭度牒持证制度,持有度牒之僧尼由僧纲司的僧官统一管理。明代广州的僧纲司设于光孝寺,所以,魏氏令僧侣中“持有度牒者归属城内的光孝寺”。佛事活动须经官方认可方能举行,违者依律治罪。二是强令没有度牒的佛教信徒还俗:“近我皇上一新政化,大启文风,淫祠既毁,邪术难除。汝四民合行遵守,庶人祭先祖之礼,毋得因仍弊习,取罪招刑。”……“禁约之后,师长、火居道士、师公师婆、圣子、尼姑及无牒僧道各项邪术人等,各赴府县自首,各归原籍,另求生理买卖,故违者拿问如律治罪。”此后“民家只许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隐藏邪术者,访出问罪,决不轻恕”。
一个宗教能否存在和发展,其信徒的众寡将是决定的因素。魏氏强令僧尼还俗,或集中管束度牒僧众,直接的后果是削弱了佛教信众的队伍和基础。
第三,没收寺庙田产,或充归社学、书院学田,或拍卖。
岭南佛教发展至明清时期,各地寺庙基本有自己的田产,作为道场日常运作和住寺僧尼供养的经济来源,同时也是中国佛教禅农并重的特色。如六祖故里国恩寺在明代的寺田达一千八百亩。南华寺的田产,除了在韶州域内,远在新会、南海、番禺等地也有。但在魏氏看来,佛教寺庙田产非自身所置,而是民众布施之果,既然拆毁这些庙宇,其田产就必须收回或改为学田或拍卖,让这些寺僧再也不能不劳而食。因而颁令云:“各处废额寺观及淫祠有田,非出僧道自创置也。皆由愚民舍施,遂使无父无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祸于无穷。本道已行各处,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者,尽数拆除,因以改建社学。今岁适当造册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为社学之田,是除生民无穷之害而兴无穷之利也。仰抄案回府着落,当该官吏照依案验内事理即便行,仰各县通查废额寺观及淫祠之田,清出归官,召人佃种,分拨各社学供给,师生就择佃人看视,社学有余则量拨儒学,册内明白开注,仍总立碑学宫存照,以防侵占,绝奸欺,随田粮差,各随土俗议处,明白呈夺,以为永久之利,其清查完日,各造册缴报,俱无违错,抄案依准缴来。”
这一政令的施行,使这些未获官方认可的寺庙田产惨遭厄运,如万历《新会县志》云:“各寺田嘉靖二十二年(1543)皆以奉诏变卖,每寺田或留少许,以供香灯,或尽卖之。所全者,惟光孝西禅二寺之田而已,今按光孝之田,万历元年(1573)筑外城,僧送出变卖,后城工完,有未作价而白食其田,上不纳粮,下不输租,寺僧屡以为言,竟委之而矣,此不可不清理也。”在粤西雷州,“广济寺乃系私创,宜毁以灭迹,其寺田改为学田”。雷郡最大的佛教寺庙天宁寺,为免寺田全被没收而主动献出大部分:“天宁寺僧一人而占田三十六庄,影射差役,坐享厚利,蠧国殃民,司政教者所当治也。庸僧不通内典,不守清规,本当尽数入官,既告愿让田二十庄为学田,姑示宽容,僧死毋俾他僧接管以崇异教,每大礼习仪宜于学宫展教,慎勿于寺中,俾复得以借口兴建”。
寺庙田产被没收变卖,对一些豪强望族而言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纷纷争夺抢占,明人严贞在《重修龙山寺记》曰:“(国恩)寺有田一千八百亩,多为豪猾所噬,余粢不得入于寺,以故缁锡少聚。”《曹溪通志》也有南华寺田产被豪势蚕吞的记录。而豪族显贵承买寺观田产者,当推南海之霍韬,《石头霍氏族谱》载:“大宗祠地原系淫祠,嘉靖初年,奉勘合拆毁,发卖时,文敏公(即霍韬)承买建祠。嘉靖初年,又奉勘合拆毁寺观。简村堡排年呈首,西樵宝峰寺僧,奸淫不法,奉准拆寺卖田,时文敏公家居,承买寺田三百亩,作大宗蒸堂。”嘉靖十一年(1532),广东按察司佥事龚大稔曾就此事弹劾吏部尚书方献夫和詹事府詹事霍韬:“夺禅林攘寺产,而擅其利,在二臣犹为细事。甚者若仁王寺基已改先儒朱熹书,而献夫夺之以广其居。”
佛教田产,除了部分由僧尼自己耕种外,大部分往往是以租种的方式来收取钱物,从而维系日常的用度,包括庙宇的修葺及僧尼的生活等,因此于佛教道场及住寺僧众而言,寺产是其生存和壮大的经济基础。魏氏没收佛教寺田,就是削弱了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第四,把佛经列为禁书,禁止流通。
魏氏把佛经列为禁书而禁售,虽鲜见于珠三角地区,然在粤北,却有严厉政令:“书铺当禁之书,一曰时文蠧坏学者心术,二曰曲本诲人以淫,三曰佛经,四曰道经煽惑人心,先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责取各铺并地方总小甲邻佑结状,如再发卖前项书籍重治以罪,再不许开,书铺仍大书告示张挂,关隘去处,不许从外省贩卖前项书籍私入广东境内,不时差官盘验以诘奸弊”。从这一政令可见其把佛经等列为禁书。为了防止这些“禁书”流通,采取如下措施:一、禁止出售;二、书铺及甲邻具结承诺不售,违者治罪;三、各书铺张贴禁书告示;四、省边境设关检查,以防“禁书”流入粤境。在粤西,一经“追出袈裟、法衣、神像、经箓之类,当官烧毁。”
佛经,乃佛陀之言说,集中了佛教的义理,系佛教三藏之一,称为经藏,佛教皈依者必诵、必修之课。魏氏将其列为禁书而禁售、禁读甚至烧毁,堵死其传播的渠道,从而削弱信众对佛教义理接受的基础。
第五,魏氏之反佛行为,最赫然者当是砸碎六祖惠能大师的钵盂。
据《韶州府志》云:“衣钵自达摩所传者,明为魏校所毁。”关于此事,明末清初名人笔下或褒或贬,议论纷呈。黄宗羲《明儒学案》云:“先生(指魏校)提学广东时,过曹溪,焚大鉴之衣,椎碎其钵,曰:‘无使惑后人也’。”《郭青蝟集》曰:“万历乙酉,予入韶州至曹溪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形,而宝色无光。”《蒿庵闲话》云:“六祖衣钵,传自达摩,藏广东传法寺。衣本西方诸佛传法器,钵则魏王所赐。嘉靖督学使者某焚碎之。”清初张潮编《虞初新志》所述更为详尽:
南华寺六祖钵,非金非石。魏庄渠督学广东,遍毁佛寺。至曹溪,索钵掷地,碎之为二,每片各有一字,视之,乃“委鬼”也。庄渠异之,寺因得不毁。
崇祯中,有彭举人某,病中梦至一官府,其神冠冕坐堂皇,状如王者。闻胥吏传呼魏校一案。须臾,有一官人,峨冠盛服而入。其神问:“何以毁曹溪钵?”答言:“吾为孔子之徒,官督学校,在广东所毁淫祠几千百所,岂但一钵?”神云:“闻钵破中有魏字,如此神异,乌可以为异端而毁之?”答言:“魏是予姓,既数已前定,虽欲不毁其可得耶?”神语塞,揖之而出。彭病痊,为人言如此。
清人檀萃游历黔、湘、粤等地,将所见所闻笔录辑成《楚庭稗珠录》,内有明人梦中魏氏碎钵细节及时人讥讽汉主夫人和魏氏歌谣:
庄渠视学于粤,恶佛氏,必诋之,故宗鲁之言易入。毁祠庙甚多,而曹溪之钵竟被捶碎(太鲁莽)。至崇祯间,有彭孝廉某病,梦至官府,神被服如王者,闻胥吏传呼魏校一案,须臾一人峨冠盛服入,神问“何以毁曹溪钵”?答曰:“吾为孔子之徒,官督学校,在广东毁淫祠几千百所,岂但一钵?”神云:“闻钵破,中有‘魏’字,如此神异,焉可以为异端而毁之?”答云:“魏是予姓,数已前定,虽欲不毁,其可得耶?”神语塞,揖之而出。庄渠诚辣,然千年异物,一朝碎之,能无孙家虺瓦吊之讥乎?近时罗孝廉天尺善于言之也,歌曰:“西来本是无一物,达摩之钵胡为哉?大庾岭头争不动,獦獠米熟归黄梅。紫金色吐毫光现,驯龙法水六时变。汉家公主号平阳,凤辇来游纤指玷。指痕触处如初月,上弦补完晦又缺。女娲之石炼不成,赐庄特代金条脱。公主奉佛心何虔?降王一去失山川。此庄万古属公主,毋乃佛力人争传。我来曹溪独访古,守钵人传有猛虎。谁知猛虎终无权,西来法器沦荒圃。岭南使者玉尺方,能将色相还空王。一声棰响钵不见,宝光飞上南华殿。”
对魏氏之所为,檀萃给予严厉批评:“大毁寺院,至碎曹溪之钵,无理取闹,宏奖风教固如是乎?”因魏氏后人早折及官运有阻,时人窃议乃碎祖钵之果报,其本人也心怀悔意:“(魏校)出巡韶郡,欲入南华山拆六祖寺,时得郡守后尚书周厚山公解乃罢,在郡庠中碎其衣钵,翁源太平寺亦在毁中,住持真广赴京奏辩,乃复奏中亦言其毁寺衣钵,校后起北祭酒。时世宗再幸太学,校以侍讲言动失体,调太常寺少卿。致仕家富,惟一子已爱而夭无嗣,闻其后亦有悔于心云”。
但魏校有否碎毁六祖钵盂?清初平藩重建南华寺祖师殿,其存库法宝中有“钵盂一个”,附文曰:“谓魏提学击碎金漆固,惟露一片约寸许,非铜铁瓦石,盖四天王所献如来者”。如此说属实,则钵盂只是损坏些许,不致碎毁无存。新编《曹溪通志》所列寺藏明代文物中就有铜质钵盂一个。
魏氏砸六祖惠能祖传衣钵,无论是全毁还是损坏,不管时人是褒是贬,窃以为,此举本身就是偏激至极。祖传衣钵是教界的至尊信物,菩提达摩从印度携来中华六传至岭南的惠能而成就中国的禅宗,是岭南乃至中国佛教之幸,何以对这一圣物之不敬,此其一;其二,佛教来华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调和、融合而成中国禅宗,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唐宋以降,多少文豪大家、硕学鸿儒受到禅学的影响,宋明理学、陆王心学均不可免。魏氏为饱读诗书之儒者,何以容不下佛教禅宗这一圣物?所以,魏氏之为,不可饶恕。
魏校岭南毁淫祠,虽有“驱邪扶正”、“扬正气”等褒扬之辞,然其对佛教道场的破坏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却是明显的,有明一代,岭南佛教的脚步迟滞不前,至万历年间憨山大师抵岭南,才肩负起中兴佛教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