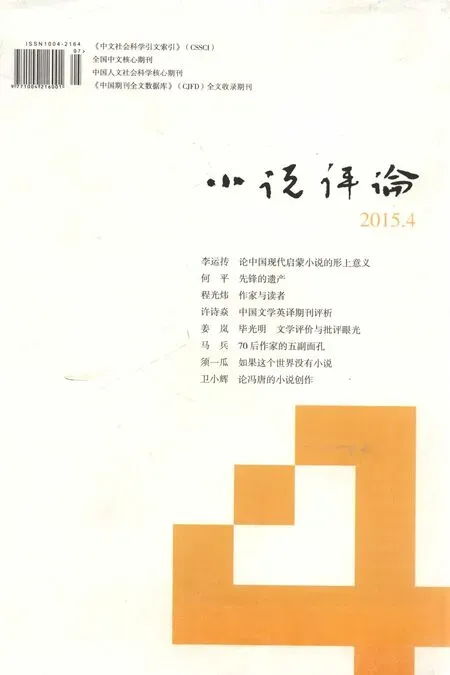论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
2015-11-14景俊美
景俊美
论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
景俊美
关仁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是其书写农民问题的代表作,较为集中地表现了农民的现实处境与命运起伏。作者在关注社会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艺术呈现中,寄寓了多年的艺术探索与理性思考。立足于乡土大地,关仁山举重若轻地直面“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他的中短篇小说与其长篇互补呈现,映射着他在捕捉生活、探寻人性的艺术创作中的写作理路。小说《日头》在跨度近40年的时代书写中展示出对乡土中国的深度探寻,是贴近生活而又超拔于生活的新时代史诗。时代变迁、社会问题及纷扰而杂乱的种种事件背后的文化意蕴,是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小说描写了冀东平原日头村的历史变迁,金、权、汪、杜四个家族几代人的利益角逐与灵魂博弈构成了《日头》缠绵纠结的关系图谱。土地所有权、农村劳动力、农产品的出路以及农村贫富分化、土地流转等“现实问题”是小说关注的焦点。作者通过“问题”展示“追问”,在寻找农民出路的同时充溢着艺术的瑰丽。
一、虚实相间的叙事手法
《日头》作为关仁山“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显示出艺术探索上的日益娴熟。作者在比较自己的三部作品时也曾指出:“‘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有改变。《天高地厚》生活气息浓厚,写得比较瓷实,缺少一些飞翔的东西;《麦河》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有了一些变化,以一只鹰的两次蜕变为隐喻,形而上的思考多了一些;《日头》更注重虚实结合,魔幻的东西更多,虚幻的东西和哲理意味更足一些。”
《日头》中作者设置了两个叙述视角,一是敲钟人汪长轸,小说中又叫老轸头。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有着普通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勤劳、本分与坚韧,以及固执、保守与狭隘。其身份的特殊性赋予了故事的传奇色彩,他既是日头村的“当家人”权桑麻书记的亲家,又是日头村的民间思想者金沐灶的“准岳父”。情感上他站在金沐灶的一边,而生活中他又不得不妥协于他的亲家。老轸头的视角不是以一种外在的视角来观察,而是日头村人直接在场的内在视角和乡土生活逻辑。国家和民族命运关键的历史转折在日头村的映射大部分通过老轸头的视角得以展开,他的视角整体来说是客观的,但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之形成互补的另一个视角是“畸形+奇幻”的毛嘎子。能在天上飞的毛嘎子以儿童的视角构成强大的“本我”内核。这一视角拥有着原始的活力与狂放的意绪,并构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人性呼唤。毛嘎子的直觉让我们自问:“我是谁?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是我自己,而不是我的肉体的延续?”毛嘎子与日头村既有联系又有脱离,他曾在这里出生又因飞翔而成为一个日头村的“局外人”,他在天空中以超脱的姿态议论、抒情,见证着日头村的兴盛与消亡,借助对日头村这一“故乡”的怀念与质疑产生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灵魂叩问。虚构是一种精神。从小说的整体寓意看,与其说是毛嘎子在讲故事,不如说是日头村的故事在讲述一个畸形的毛嘎子的来、去人生。
尤为有意义的是,两个人物在特殊的时刻可以彼此沟通,而众人却听不见;呈现出智者不用声音也可以对话,众人不能理解、更无可领会的象征与隐喻。小说中毛嘎子还有许多特异功能,比如他每到十五月圆就飞回村里,落在树林里一颗菩提树的树顶上;他具有根据星宿的闪光给人解梦的功能;他在天上找到了一个无人的仙境叫云顶;他从红嘴乌鸦的孤单中看到了自己命运中的影子等等。小说构筑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人物,他的存在使得小说具有一种魔幻般的形式感,其哲理思考也便在这种真与假、实与虚的交互中自然呈现。
诚然,所有的叙事传统都是建立在语言系统之上的。作家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手法,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取舍,更是叙事立场的识别。《日头》拥有着大地诗学般的生命质感,在鲜明的现场感中展示时代生活的宽广度;同时,又游刃有余于魔幻的叙事手法,以艺术特有的空灵感交织出转型乡土的困惑与生机。关仁山在《日头》中充分展开的叙事立场,是民间的、反思的和文化的。老轸头这条实线以民间的立场游走在日头村的家家户户,他虽然怯懦,但他发自内心的善良与真诚让金沐灶、杜伯儒、权桑麻、汪树等日头村村民都由衷地认可并接纳他。金沐灶是反思的,他所关注的是文化种群的共同命运,因此他深入乡土社会的内部结构,用思想的手术刀剖析国民根性与人性根底,在不断追寻中进行着灵魂的叩问与形而上的思考。毛嘎子与日头村的文化象征——状元槐、魁星阁、天启大钟等则是文化的。这些看似“不经之谈”的存在给生活以希望、让精神得自由,是小说抚慰灵魂、滋养心性的亮点。
语言的叙事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宿命般的故事与大量反智性的人物是日头村独特的人文景观,更是作者进入人类意义空间的通道。优秀的作家必然以最高的意蕴展现人类的思考,魔幻或者说寓言是这种展现的最好表达。如此,小说以新的光亮照耀人类的理解力,既克服偏见,又不至于引起无谓的敌意与争辩,更重要的是它让艺术更接近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美中不足的是,老轸头与毛嘎子的两条线索多数处在平行状态,在结构上也是彼此分离的。这也许正是作者的用心也未可知,但它确实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难度,让作品面临“脱离”大众的危险。
二、直面现实的人物形象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为金沐灶。作为一个农民形象,金沐灶不是一个所谓的“新农民形象”,他身上流淌着更多的传统,他也有他自身的缺点与不足,甚至在生命的历程中屡屡受挫。这个人物超越其他农民形象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有文化深度的“农民”,在家庭、社会、时代遇到问题时,他能够不断求根问底去探寻原因。在面对大是大非时,他一直秉承的是一份公心。尽管他也疯狂和执拗过,尤其是在火苗儿嫁给权国金之后,他与火苗儿曾经做过超越一般人的疯狂,不过这疯狂与执拗事实上正是他遵从内心中的“真”而体现出来生命挚诚。
金沐灶也曾进入“官场”,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披霞山乡副乡长。但是他当乡长后没有变成少人味儿的“聪明人”,而是顶着极权政治与垄断资本的双重压力为民众求福利。他帮村里招商引资想出路、为村民推销日头村的优质大米、指导农民建大棚等等,为的就是能够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金沐灶也办过企业,他所开的铸铜厂获得了丰厚的财富积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个人财富的获得,他在看到厂矿给村里带来“繁荣”的同时,深刻地忧虑着环境破坏与资源消耗等现实问题,他甚至忧愁为什么厂矿的繁荣不能给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因此他对老轸头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金沐灶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小说中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答案。但是金沐灶试图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中找到农民真正出路的探索却是真实而可贵的。他为重建魁星阁一辈子未婚,他将被权桑麻逼疯的大学生汪树挽救后,又接纳了吮吸空巢老人尸液的孤儿……金沐灶的身上涌动着思想的亮光和人文的关怀,他既脚踏土地又仰望星空的求索,代表着社会与时代的良心。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关仁山就是要写这样的中国人,他们的坚韧与拼搏、他们的心性与尊严,指明了中国的未来。小说中我们看到,金沐灶一步步地超越自己、寻找理想的过程,是艰难而又寄寓希望的。他懂得从善如流、能够接纳不同的声音。小说中的他因受到儒、释、道以及基督的影响,在魁星阁的最终建造中做出了整合宗教的“荒唐”行为,但是这个荒唐的行为是一种自然生长,是金沐灶在绝望中希望,在希望中存向往的真实选择。
权桑麻这一形象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他的出现映射着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生态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有冲天的胆量。这胆量让他活出了人模狗样,这胆量让他成为日头村的天,这胆量让他成为一个村的“精神象征”。人们恨他、恐惧他,但又觉得离不开他。于是,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他的儿子权国金啃一啃他的那根骨头,一切棘手的问题便“迎刃而解”。权桑麻这个人物形象本身涵盖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史,他知道利用所谓的“民意”与“民心”去做他想做的事。文革时期的争斗、开矿山的主意以及与袁三定争夺利益等几次大的社会事件他都利用了民意,于是他屡试不爽地赢得了胜利。
权桑麻的形象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农村基层的真实写照。这一人物形象的确立是作者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中最要害问题的敏锐书写,也是作家探讨农民问题的作品中最大胆和最直接的“现实主义”。农民的问题决不是单一的问题。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权桑麻这种投机钻营且胆量大的“积年老狐狸”反而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权利空间,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掌控者,意味着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不仅仅是道路宽敞、拥有钞票、住上高楼的外在形式的变革,而是应该尊重普通民众对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的自由选择,是让农民活得有希望、有尊严、有精神追求的内在信仰的获得。
小说中权桑麻建立的农民帝国是一个集专制、严密、混乱、愚昧、迷信、短视、功利、破坏于一体的封闭体系,而他所构建的资本、权力、“土豪”三位一体的利益格局则是中国社会利益链条的象征。只要这样的人还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成果就会变味,老百姓就不会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果实。面对这样的体系与如此强大的利益格局,中国农村现代化若想取得成功,必然要解决制度的、人的以及文化上的种种问题,否则三农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民不仅不会是社会与土地的主人,反而会成为迫害他们自身的帮凶。
三、叩问灵魂的思想力量
构成优秀小说的要素有很多,除故事性与可读性外,故事背后的思想与文化含量是决定小说品相的内核。换句话说,好小说是灵魂的逆光。从小说构思看,关仁山在《日头》中下足了功夫,他以文化立题,以哲学定魂,以思想贯始终。
《日头》中激荡着多种文化的碰撞。乡村政治文化、社会伦理文化、自然生态文化以及宗教道德文化等不同文化在这里交织、聚集,形成了千百年来的农民文化性格及典型文化基因。传统乡土社会即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并建立起来的族群社会,说它好也好坏也罢,它都代表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社会转型将固有的传统打破,原有的文化既面临浩劫也面临重建,这是乡土中国史无前例的价值命题,更是当下社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根基所在的文化与外来的文化之间必然是需要互为补充的,但这互补的衔接点何在?小说探寻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诚如保尔·利科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对于思想观念和表达方式具有有限的能力,恰恰是使用我们‘自己的’范畴中的思想财富的解释本身,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的’范畴。也许在‘自己’和‘其他’之间的这一张力打开了通向重要发现的道路。”关仁山在小说中设置了积淀着我们“自己的”深沉历史力量的血燕、红嘴乌鸦、状元槐、魁星阁、天启大钟等文化意象,将神话故事与现实生活、文化符号与精神意义进行合理对接,展示了中国农民寻求精神出路的努力及其所可能追寻到的方向。
晨钟暮鼓,以召百灵。小说以钟之“十二律”与二十八星宿相衔接的方式结构全篇,暗含着深沉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章节布局。首先,十二律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并含蕴着二十四个节气,是日头文化的真实写照。所谓“节好过,年好过,日子不好过”,说的正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天熬日子的苦难人生。但是具有悖论意义的是,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苦难却铸就了生命的华章。农民以巨大的隐忍建构起自身的社会秩序,社会制度与民俗风尚在日头升与日头落的平凡日子里一点点累积,最终形成一种精神力量与哲学命意。小说中汪老七的死也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他对银杏树下妻子骨灰的守护,他临终前对儿子汪树的嘱托却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其次,“十二律”构成了乡土中国的文化秩序。《周礼》中所谓“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说的正是乡土中国的思想核心。《左传》亦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强调的便是中国以农立国、以天为大的社会秩序与精神崇尚。所以,凡是内心有担当的中国人,必然怀着难解的忧患和繁复的向往找寻中国农民的真正出路。天启大钟开启的金家血脉在小说中担此大任,当金世鑫护钟而亡、要续文脉的嘱托埋下了他儿子金沐灶的人生命运,这命运伴随着他的不断追问得到一一化解。这里,天启大钟不仅是一个物的载体,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钟声可以警万里,钟声还可以惠十方。当小说在钟声鸣响中埋下问题的时候,也便在钟声的悠长中浮起了生命的意义。
时代呼吁作家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日头》中关仁山借金沐灶之口提出的“农民主体观”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焦虑,他让我们看清浮夸的政绩观与恶意资本联手之后的利益陷阱。而“谁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的问题的提出,更是直接而尖锐地将农民的现实境遇摆在读者面前。生活从来都离不开生命的追问与沉思。谢林认为,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不再拥有家园,故而终始不能摆脱被遗弃的痛楚。正在经历着的社会转型让乡村文明几近崩溃,多少人望着“回不去的故乡”哀叹却愿景模糊。“寻路中国”似乎正在经历一个西西弗斯式的悖论。当下,中国农村的土地荒芜、生态失衡、道德沦丧、强力拆迁及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突出,追问并解决上述问题是人类认证自我的必然历程,其难度也许超越当代人的视野,但是在反思种种事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与制度根源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勇气与担当。小说既展现了现实的矛盾、文化的纠结与历史的撕扯,更以悲悯与温暖跃现生命的希望。关仁山的《日头》在打通艺术与现实、传统与当下、人生与理想的维度里,展开对乡土中国中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命际遇与精神状态的书写,寄寓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深刻的反思精神。平凡者未必平庸,众人的喜怒哀乐可以铸成民族的生命之河。只有重视普通民众,中国乡土社会的未来才不会塌陷。
景俊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注释:
①茅盾:《英文版〈茅盾选集〉序》,参见丁尔纲编:《茅盾序跋集》,第2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②关仁山、张继合:《关于〈日头〉和“农民三部曲”》,《河北日报》2014年9月12日。
③ [美]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第130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④关仁山:《日头》,第2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第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⑥杨立元:《〈日头〉:对当下农村境况的一次逼视》,《博览群书》2014年第12期。
⑦[法]保尔·利科:《导论》,见[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第20页,郑乐平、胡建平译,顾晓鸣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⑧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下)》,第1731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⑩Shelling,The Philosophy of Art,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