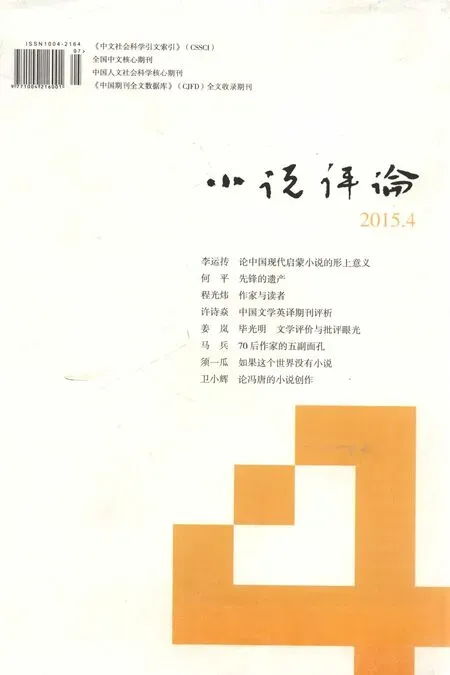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启蒙小说的形上意义
2015-11-14李运抟
李运抟
论中国现代启蒙小说的形上意义
李运抟
启蒙主义与启蒙文学都有形而上思想,即某些特定价值观念。启蒙意思是“用光明驱散黑暗”以求理性生存,理性就体现为价值取向。欧洲文艺复兴以理性反对愚昧、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性自由抗拒禁欲主义,欧洲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天赐”、“法律平等”,就都是形上思想。中国五四知识界呼吁“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也是价值取向。启蒙在人类思想史有进步意义,却不断遭受现实阻击。中国启蒙的现实遭遇就相当坎坷。反对和质疑因时而异有各种说法:如阶级革命解构五四启蒙的阶级论;启蒙并没改变中国的失败论;启蒙不宜中国的国情论;市场经济时代的启蒙过时论;启蒙只是文化精英的悲天怜人等。换言之启蒙思想常常得不到社会认可。但不难发现阶级论、失败论、国情论、过时论和精英论有个共同倾向:即以启蒙实际遭遇为依据,带有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谈启蒙当然离不开现实,但不能陷入功利得失。很多人谈到中国启蒙与民众有距离,尤其农民不理解,需要启蒙而无感觉,恰恰说明启蒙面对的是深层文化心理。无论传统启蒙还是现代启蒙,因为是思想洗礼的“务虚”,所以不同政治革命或经济变革容易立竿见影。而且启蒙不仅是让人接受知识与文明,还要让人对合理事物产生敬畏之心,这就更为不易。
中国社会启蒙之路曲折,启蒙文学却相当顽强。小说为启蒙文学重镇,从鲁迅经典小说始,中国现代(包括当代)小说启蒙意识延续至今,成为不同小说时代亮色所在。包括以赵树理方向代替鲁迅方向的解放区,赵树理本人也有“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启蒙意识,《小二黑结婚》可谓标志。新时期文学启蒙重演更是证明。人们通常认为1980年代文学都与启蒙有关,1990年代文学则告别了启蒙。事实上个人化写作时期启蒙小说并不少。如新反思小说《洗澡》、《走向混沌》、《踌躇的季节》、《中国1957》和《乌泥湖年谱》,包括稍晚些的杨显惠“夹边沟系列”,启蒙性批判都比早期同类作品更深刻。《国画》、《沧浪之水》、《欲望之路》等官场小说也批判了封建特权;《羊的门》、《米》、《日光流年》更是国民性批判力作。中篇如《山里的花儿》、《向上的台阶》、《镇长之死》、《白棉花》、《道场》、《黑风景》、《棺材铺》、《预谋杀人》等同样属于启蒙小说。新世纪底层叙事既有新工农主义民粹思想,也有继续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启蒙性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可谓比比皆是,也涌现了很多代表作。甚至可以说优秀小说家都有启蒙情结。但如同评价社会启蒙,评判启蒙小说形上思想也存在政治取舍、权力态度、主流褒贬、民众接受等问题。研究启蒙小说形上意义就是要避免成王败寇的功利性,看其思想价值究竟如何。由此有三种时代文学现象可作为标本分析,即阶级革命文学的拒绝启蒙、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演和市场经济时代的误解启蒙。
一、阶级革命文学的拒绝
启蒙成为五四知识界共识,首先与欧洲启蒙思想有关。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等都有欧美留学经历,接受了相关思想资源;前期创造社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都是留日学生,也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影响。包括留日的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亦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主义”多舶来,启蒙主义亦然。而如同所有舶来主义,启蒙也存在本土化问题。很多人谈过新文化的矫枉过正,泼脏水倒掉婴儿问题确实存在,但事出有因。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是不动传统的技术主义,新文化运动则恰恰要清除传统文化弊病。当有人谴责《新青年》全盘否定传统,陈独秀就用了“不得不”的排比句来反驳,即“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教、旧伦理、旧政治、国粹、旧艺术、旧文学,是为了维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新文化矫枉过正,确实是封建传统太顽固。包括之前梁启超这种改良思想家,其实也激进。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功能抬至“治国平天下”,显然也矫枉过正。
民国时期有三种主义文学最重要,即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和阶级革命主义。从形上思想的现实遭遇看,启蒙还是获得知识分子普遍认同,但民众接受有限;自由主义属思想“奢侈品”,国共都不喜欢,遭遇最尴尬。阶级革命主义最实用,有广泛社会基础。启蒙者(包括鲁迅)并非赞同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者几乎都赞同启蒙。因此启蒙的真正冲突主要发生在启蒙主义与阶级革命主义之间。
五四文学革命引领者,陈独秀更多考虑社会政治,胡适注重文学史、语言与文体问题,鲁迅集中反思封建文化危害,国民性则成为突破口,鲁迅也成为五四启蒙文学第一人。针对“爱排场的学者们”总是设些汉族发祥时代、发达时代、中兴时代的“好题目”,鲁迅认为“直截了当的说法”只有两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奴隶时代”说法如同《狂人日记》斥责“吃人文化”,有些偏激却一针见血。它们确实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文化体现。鲁迅给许广平信中多次谈到国民问题,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国民性批判是对辛亥革命后国民精神的忧虑,但阿Q、祥林嫂、爱姑、九斤老太、华老栓、赵太爷、七大人、假洋鬼子、康大叔、红眼睛阿义等系列典型,确实呈现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众生相,如精神胜利法、愚昧怯弱、欺软怕硬、看客心理、从众心理和膜拜权力等。鲁迅批判对象还包括知识分子。鲁迅同情迂腐善良的孔乙己,为生计随波逐流的吕纬甫和“时代孤独者”魏连殳,更为涓生和子君这种新时代青年鸣不平,但最讨厌貌似新潮而实际腐朽的读书人。如《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自诩新派人物,骨子却是虚伪道学。国民性批判在鲁迅其实是长期思想结果。1908年发表的《魔罗诗力说》极力推崇英国诗人拜伦,认为其浪漫主义体现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启蒙思想与现实精神。鲁迅还指出“若夫斯拉夫民族,思想殊异于西欧”,而十九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叹其美伟矣”,则也是得于“魔罗诗力”影响。所谓斯拉夫民族“殊异于西欧”,确切说就是专制与民主、开放与保守的差异。
阶级革命文学的拒绝启蒙,则从革命文学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的前27年文学。
革命文学首先是以阶级革命解构五四启蒙。与太阳社成员提倡革命文学不同,后期创造社反启蒙的突变耐人寻味。如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宣称“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鲁迅也成为攻击目标,阿英(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批评阿Q形象已无时代意义,麦克昂(郭沫若)干脆斥责鲁迅为“封建余孽”和“双重反革命”。革命文学反启蒙有两个支撑:一是认为启蒙是资产阶级或有闲阶级产物,而无产阶级天然先进。其理解“劳工神圣”其实狭隘。蔡元培曾认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运转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显然更合理。二是革命文学希望以暴力革命的“现实解决”替换务虚的“思想解决”。这点是关键。夺取话语权而反对资产阶级启蒙并不奇怪,断定无产阶级天然先进显然主观,成仿吾们未必真信,但相信暴力革命很快见效则无疑。出于革命现实需要而拒绝启蒙,在解放区文学更突出。毛泽东曾推崇鲁迅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讲话》则认为“鲁迅笔法”只适合针对“黑暗统治势力”而不能用来对付人民群众。其实毛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早不以为然。1939年11月7日毛给周扬写了封信,认为“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族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信中还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但政治方面则农村比城市先进。延安以“赵树理方向”替代“鲁迅方向”就是从革命现实需要出发。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就体现了这种意识,文章对赵树理方向有三点概括:很强的政治性;创造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新形式;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其实言“民族新形式”也是利于革命宣传。总之是强调文学为政治和革命服务。应该承认毛泽东比提倡启蒙的知识分子更懂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民,工农革命也确实改变了中国。这种历史事实更强化了阶级革命对启蒙的拒绝。
二、新时期为何“启蒙重演”?
关于新时期启蒙重演原因,李泽厚有个观点非常流行:即革命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压倒了启蒙,建国后又放弃“补课”,从而导致五四启蒙中断。这确实不假。但这种现实却恰恰反映了对启蒙思想的错误理解,没有真正认识到启蒙意义。不管现实形势如何,都不能成为放弃启蒙的理由。作为正视封建危害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启蒙,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就文学启蒙看,即使救亡时期也并非不能。前面说过赵树理有“夺取封建文化阵地”意识,而初去解放区的丁玲,其《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是如此。小说所写贞贞不幸被日本鬼子抓去糟蹋后,村人关注的不是贞贞悲惨遭遇,而是失身的“不干净”,甚至有种种流言蜚语。揭示这种封建贞节观及农民心理就有启蒙意识。包括为延安妇女处境鸣不平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也显示了启蒙性批评。东北是中国最早沦陷区,萧红不写正面抗战的《生死场》所揭示北方小城民众的封闭保守,包括后来《呼兰河传》,都有国民性思考。这类作品实际利于救亡而非反之。关键还是对启蒙的认识。革命压倒启蒙,建国后放弃“补课”,都是本身就拒绝启蒙。拒绝启蒙留下很多思想问题,还导致种种荒唐的现代迷信。后者实际是新时期启蒙重演的关键原因。“分田分地真忙”后,封建文化是否随之改变?鲁迅担忧的国民精神是否真的变成了“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真正的事实恰恰很不理想。
中国现代迷信其实与封建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救星思想导致的领袖一言堂,一风吹的权力膜拜,“根红苗正”的血统论,大跃进“放卫星”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文革中“读书越多越反动”的以无知为荣,全民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所有这些现代迷信都与封建专制文化有关。不仅一般工农群众成为现代迷信的国民基础,知识分子改弦易辙的开始“一是忏悔,二是歌颂”, 对现代迷信同样推波助澜。比如老舍就将否定旧我发挥到极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由此像《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这些名篇也不值一提。正如杨绛《洗澡》描述的,知识分子不管情愿与否,都争先恐后加入思想“洗澡”。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有试验性,柳青《创业史》却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农业改造的史诗性运动”,而且“千年万年长”。真正状况如何呢?胡平曾谈到浙江省情况:浙江省1954年有农业生产合作社3800个,第二年发展到55000个,膨胀15倍。由于合作化运动盲进,造成农村人心浮动,干群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等严重问题。这种情况很多省份都存在。即使不怀疑柳青真诚,至少有盲目迎合。大跃进后农村饿死很多人,但文学还是莺歌燕舞,良知完全不见。知识分子丧失自我带来什么?晚年巴金一针见血:“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李泽厚认为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完全消失了自己。他们只有两件事可干,一是歌颂,二是忏悔”。问题在于他们为何接受残酷思想斗争?为何看见是非颠倒还推波助澜?人们常常批评极左路线,问题并不在于“极”的程度,而是它们究竟推行的是什么。
正是这个根本问题上,新时期启蒙小说的思考就很发人深思,它们揭示的极左思潮恰恰多是封建幽灵和现代迷信。其中有两个方面最能说明问题:即权力专横与国民愚昧。
公共权力状况很能显示社会思想。即使“忠良落难”模式的《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风泪眼》、《芙蓉镇》、《绿化树》等早期小说中,也能看到借助极左的封建家长式权力。新反思小说《洗澡》、《走向混沌》、《踌躇的季节》、《中国1957》、《乌泥湖年谱》和杨显惠“夹边沟系列”,更深刻揭示了革命名义的权力迫害。人人自危、人人互危以及“受虐者施虐”现象触目惊心。文革题材,无论宗璞《蜗居》、《鬼域》、《我是谁?》和李国文《危楼记事》的“怪诞”,还是《飞天》、《桑树坪纪事》的纪实写法,都凸显了现代迷信的权力膜拜。柯云路《黑山堡纲鉴》呈现的黑山堡完全是个封建王国。开放时期又如何呢?权力问题在《新星》、《浮躁》、《古船》等改革小说中同样醒目。《浮躁》中当金狗劝告雷大空不要和巩宝山们纠结时,雷大空回答是“要长远着想,就得靠政治势力”。所谓政治势力就是官场权力。新写实小说中平民与权力的纠葛成为普遍主题。《新兵连》、《单位》、《官人》、《一地鸡毛》、《风景》、《特别提款权》、《单身贵族》、《少将》、《纸床》、《黑洞》等都质疑了权力膜拜。批判封建家长式权力的启蒙作品可谓举不胜举,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蒋子龙《农民帝国》就刻画了一个现代乡村土皇帝郭存先形象。李建军认为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出现空前严重状况,郭存先就是个“新国民”典型。但郭存先成为郭家店人民“大救星”这种典型土皇帝,其实与全球化现代化没有因果关系,倒是与封建专制有根本关联。这种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中出现的“现代迷信”实际是封建迷信。
权力专横与国民愚昧是事物两面,互相依存也互相强化。权力封建化专制化需要愚昧迷信的文化土壤,否则难以产生更不能畅通无阻。国民愚昧正是基础。《班主任》将谢惠敏愚忠归咎“四人帮”,启蒙深度与鲁迅《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无法相比,但还是触及国民愚昧。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啊!》、《鬼域》、《危楼记事》等文革题材作品的启蒙则明显深刻起来。如果说“忠良落难”模式的反思小说对国民精神审视非常缺乏,改革小说在质疑权力时对国民精神则思考较多,尤其《古船》这样的深刻之作。寻根文学文化取向较复杂,但提倡者韩少功肯定是启蒙派。有意思的是韩少功原是想寻“优根”而重塑民族精神,实际创作却集中揭示“劣根”。《爸爸爸》中白痴丙崽得到鸡头寨全体村民顶礼膜拜,被尊为“丙大爷”,体现的完全是愚昧麻木的文化形态。《女女女》同样如此。优秀作家的思想深处还是难忘启蒙。新写实小说呈现的平民与权力的纠葛中,平民既不满权力滥用,但又往往顺从权力甚至纷纷加入权力游戏。值得注意的无论新写实还是其它流派作品,膜拜权力的国民涉及多种类型。《瑶沟人的梦》、《山里的花儿》、《向上的台阶》写的是农民顺从权力;《风景》、《白涡》、《单位》、《官人》写的是知识分子向往权力;《灰色迷惘》写的是工厂选举的权力游戏;《少将》、《夏日落》和《城市的灯》写的是军人的权力追逐。关于乡村权力与国民关系的书写,李佩甫《羊的门》可谓具有经典性。呼天成成为呼风唤雨的“东方教父”就与村民愚昧相连。如呼天成病入膏肓时,呼家堡人忧心忡忡的是“如果呼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活呢?!” 呼伯想听狗叫,老闺女徐三妮突然跪下学狗叫,于是众人效仿,“黑暗之中,呼家堡传出了一片震耳欲聋的狗咬声!!”这一幕实在深刻,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昭然若揭!阎连科《瑶沟人的梦》、《日光流年》、《受活》等也是出色的启蒙文本。其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就非同寻常:镇长驾车压死了人,竟然好些人想替镇长坐牢。因为“做了镇长恩人”会得回报。于是镇长心腹李屠夫精心挑选四个人,采取拈阄方式,谁抓到有黑猪毛的纸包谁就去“做镇长恩人”。《柳乡长》中柳乡长带领青年男女“进城致富”的方式是男的做贼,女的做小姐。如此现代荒诞剧,映现的只能是封建权力阴魂不散与国民愚昧仍然严重。
关于先锋小说的“先锋意识”及先锋作家转型后的思想变化有种种看法,但就反叛传统而言,批判封建文化与反思国民精神至少是个重要主题。而莫言、残雪、余华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最有一贯性。不管批评家们如何理解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都无法忽视其启蒙立场的突出与坚守。其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第四十一炮》、《檀香刑》、《生死疲劳》和《蛙》几乎都贯穿了启蒙意识。残雪从早期《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黄泥街》到后来的《突围表演》和《匿名者》等,呈现出“永远的先锋”,而有些怪异偏执的现代姿态中却始终保留了对现代国民精神传统因袭的揭示与批判。余华小说,无论前期的暴力与死亡,还是转向后的《细雨中的呼喊》与《活着》,尤其重返先锋的《兄弟》和直面现实问题的《第七天》,余华的苦难书写都在质疑生存荒唐与国民精神,实际都含有启蒙意识。苏童和格非转型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如《妻妾成群》、《米》和《人面桃花》等,反思传统和探求真相同样体现了启蒙意识。至于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小说或女性主义写作,批判封建文化、传统道德和男权主义就从未停止,明显继承了五四女性文学启蒙传统。
三、市场经济时代的误解启蒙
认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告别了启蒙是种流行看法。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鼓噪更助长了这种观点。市场经济时代是否需要启蒙,严格说是个伪命题。启蒙是针对不合理而言,不管什么不合理,只要存在就需要启蒙。启蒙问题会有变化,启蒙思想也要更新,但这种思想洗礼会永远伴随人类。世界启蒙可以分为传统启蒙和现代启蒙:前者针对的是传统专制,如王权、教会、神权与相关政治和道德等;后者针对的是现代社会问题,如官僚主义、新极权、知识分子犬儒化,大众的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等。所以哈贝马斯、萨义德们强调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公共角色。福柯曾激烈批判传统理性,晚年则注意到了传统启蒙价值,也是意识到了后现代理论的解构偏激。国内有“后启蒙”之说,也是看到现代启蒙问题。
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告别启蒙,更重要的是要看中国市场经济实际情况如何。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以政治控制经济,市场经济则被视为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实行计划与市场并行的双轨制,活跃了经济的同时,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也不断出现。1990年代加快市场经济步伐,但权力寻租并没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腐败成为严重社会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反思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制度问题时指出:“根据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但“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要看看近年中央反腐(包括与国际合作追捕海外贪官)公开报道的案件,就能说明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腐败多么触目惊心。高官腐败、小官巨贪、官场窝案、职业犯罪比比,不拿白不拿的心理,如此等等虽与制度缺失有关,但根本还是国民精神问题。将权力关进法律笼子里,从制度控制腐败当然需要。但不敢腐败还是属于被迫。如果从思想与心理首先拒绝,即自觉抗拒腐败,这才是现代公民意识体现。中国官员腐败多家族犯罪特征,包括子女利用父母权力、夫荣妻贪、裙带风等。当年林语堂《吾国吾民》就指出国人多“私民意识”而缺乏“公民意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典型的“私民意识”。官二代的权力寻租,富二代的骄横,星二代的奢侈,都是缺乏对社会负责的基本公民意识。
市场经济时代中国乡村违法犯罪有种群体现象。如曾全国闻名的河南“造假村”,导致大量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拐卖人口是古老罪恶,农村也成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多发地,参与者还多是已为人母的女性,其泛滥导致全国多次严打;广东揭阳有个“制毒村”,村支书、村长和少数民警形成保护伞,很多村民靠毒品致富;远的不说,就以2015年4月央视《经济与法》关于国内电信诈骗活动的系列报道,参与者的年轻化和广泛性就令人匪夷所思。如广西科甲村被称为“电信诈骗村”,很多村民加入,还形成钓鱼、刷卡、取现、望风的诈骗链;湖南双峰县电信诈骗活动则可谓天下奇闻,据被抓者交代有几万人加入。电视还展现了双峰很多颇为气派的独立房,竟然是电信诈骗赃款所建。缺乏谋生技能又不愿吃苦的农二代犯罪已成为社会问题。据报道很多拿到土地转让金的农民不是去再创业,而是纷纷参与赌博,甚至想靠赌博致富;从公开报道看,每年公安部打掉的涉黑团伙和各种犯罪团伙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个。面对如此国民精神问题,启蒙过时论不是曲解现实就是想当然。
我们面对的国民精神问题,其实更多还属传统启蒙。当代启蒙小说中,批判权力专制和国民性的作品就为主要。如陈世旭《救灾记》中,群众遭遇天灾的不幸与权势人物仍然享乐形成反差鲜明的官民图;梁晓声的《民选》和《沉默权》则通过乡村直选村委员会的荒唐和普通农民的悲苦无告,揭示了乡村家族势力的严重;毕飞宇《玉米》中村支书王连方在位时欺男霸女,王连方下台后一些村民就强暴玉米姐妹,连年幼的玉秧和玉秀也难逃厄运。这种疯狂报复,由奴化的“羊”变成凶残的“狼”,其丑恶与现代文明完全背道而驰。严歌苓《谁家有女初长成》和胡学文《飞翔的女人》描述的拐卖人口,方方《奔跑的火光》讲述的英芝难逃夫权,都是现代乡村国民精神悲剧。锦璐《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的悲惨生命,就和其父赵五重男轻女有直接关系。香火意识还导致赵五的自私卑劣:当愚昧无能的赵五看到被小拖拐骗回来的何前英和装了半桶米的米桶时,心满意足的他不由赞扬女儿能干了,却毫不思考女儿的惨痛代价。如此作孽的“国民”,能够“告别启蒙”?
吴敬琏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制度问题时还提供了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一个基尼系数(贫富差距)情况:公布的127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有94个,高于中国的有29个(27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而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超过国际公布的0、40警戒线。由此可知基尼系数高的多为发展中和贫困国家,越穷而贫富悬殊还越大,确实耐人寻味。很多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国家都出现过宣告“苦难结束”的新时代狂欢节,结果大量事实证明执政者的美妙许诺只是好大喜功。马尔克斯为此曾非常愤怒。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愤怒陈述了《百年孤独》问世后10多年间拉美的种种独裁暴行:五次战争和16次军事政变,两千万儿童不满两岁夭折,前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实行种族灭绝,遭受政府迫害而失踪12万人,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三个中美洲小国任意杀人,等等。国家与民族精神状况确实不是政权的成王败寇问题。当今恐怖主义猖狂,恐怖分子通常有狂热信仰,但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2015年初肯尼亚大学发生恐怖袭击,造成146名大学生死亡,恐怖行为禽兽不如。即使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国家,种族歧视也难以解决,无论白人黑人都需要种族平等的现代启蒙。不是说人们不懂种族平等意义,而是缺乏敬畏之心。中国很多腐败官员是高学历者,能说会道,怎么不懂腐败可恶?知法犯法就是缺乏敬畏良知。而启蒙就是要将公平正义在人们灵魂中扎根。还有种现象值得注意:思想发达的民族与国家也会出现极端野蛮的疯狂。丹纳认为德国是个擅长“创立形而上学和各种主义的国家”,“爱好抽象和高级理论的德国人”总想创立“包罗万象的哲学”。而德国也产生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这些有重大影响的世界哲学家。但正是这个思想发达的德国曾变成法西斯国家,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反人类行为丧心病狂。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同,但至少都看重人道生存,尤其康德关于“善良意志”与“道德自律”的论述。参加纳粹党且赞同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海德格尔有些特殊,但他也希望人类能够“诗意的栖息”。人类思想启蒙不仅是个漫长过程,也是拯救人类灵魂的精神工作。无论过去的“黑暗”还是现代的不公,只要存在不合理就不能放弃启蒙。这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经的思想洗礼。也正如此,我们对中国现代启蒙小说的形上意义要予以充分肯定。
李运抟 广西民族大学
注释:
①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②《灯下漫笔》,《鲁迅选集》第二卷,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两地书》(八),《鲁迅选集》第四卷,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魔罗诗力说》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08年《河南月刊》第2号和第3号,署名令飞,是体现了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代表性文章。
⑤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纪念协约国胜利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后《新青年》、《新潮》等刊发此演说时就定题为《劳工神圣》。
⑥黎之:《关于首次发表毛泽东致周扬的信》,《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⑦老舍:《生活,学习,工作》,《福星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⑧胡平:《1957苦难的祭坛》,第53页,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
⑨ 巴金:《真话集》,第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⑩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第249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⑪李建军:《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⑫⑬吴敬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新华文摘》2009年第1期。
⑭《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获奖演说全集》,马尔克斯部分,第686、68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⑮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第146页,安微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