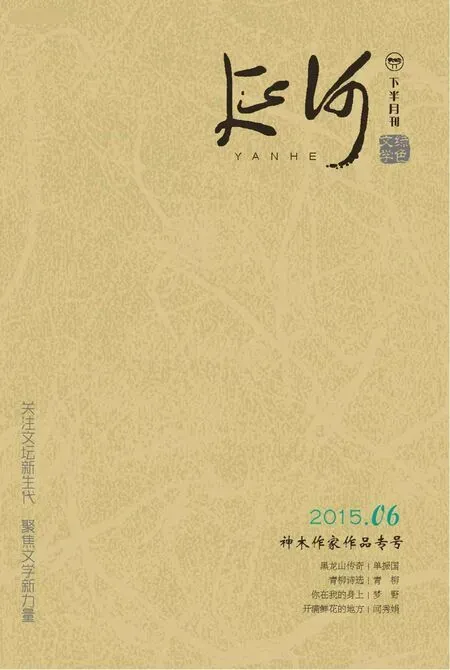我只想写出一点一点的痛来
2015-11-14青柳
青 柳
我只想写出一点一点的痛来
青 柳
阅读过我诗歌的人或许能发现,在我的诗歌写作中,对于“钝刀”一词的使用最为频繁。几乎在我的每一首诗歌中都能发现一些棱角分明的词,这些词在表述中让我着迷,在我的写作中无限地接近我生活的隐秘部分。
其实每一个诗人在写作中,都会有无意识地迷恋与剖析自己生活中隐秘的一些东西的习惯。这种神秘的东西,有可能是诗人的故乡,也有可能是诗人的亲人,还有可能是一位对自己影响最为深刻的作家,而我则将我生活的一些经历作为我写作的主要泉眼。作家自身的这些东西的特质构成了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言传方式,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的场域。
我现在生活的县城,离我出生的村子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这是在油路修通了以后。在油路还没修通之前,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来县城,就得早早地起床,走五里路去班车必经的道班等车。那时候的车少,一天的班车就那么一趟,你误过这趟车,就意味着你要误过进城的时间,就得等到第二天了,再早早地起床去等,上一天耽误去的时间与你往返走过的路,已静悄悄地隐匿在村子的岁月之中。
在村子里生活那么多年,村子里的一切都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我们村在山上,所谓山上是我们农村人用来区别与河流远近的关系的一个词,与其对应的是川里。生活在山上意思就是你所有的地只能靠天来浇灌,而川里则可以用窟野河的水来灌溉。这一年,你按照自然的各种规律,在地上安种上了,这一年雨水充沛了,你将会丰收;而这一年遇到了大旱,那么这一年将遇到灾荒,有时候这种饥荒会连续几年发生,在我的记忆中这种事情真实地发生过。直到十四岁我才由于上学而离开我们的村子,所以对于农村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为我理解乡村的生活储备了能量,给了我在后来的写作中直抵乡村的内核提供了便捷。乡村的一切都以一种缓慢的方式从始至终地交替更新着,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或许是乡村这种推进的方式影响了我,在我的性格里,我是属于“慢”的一个人,从对待事物和写作的态度,我都是不到万不得已而不去紧凑地完成的这样一种性格。这种慢我更多地理解为笨钝,而这种笨钝是与生俱来的,具有不可重塑性与复制性,是一个人内心的丰富与博大,体现为对事物的爱与宽容。这体现在我的诗歌里,表现为对事物体验的敏感和细腻,我喜欢将在捕捉到的东西上找到突破口,并用一些铿锵有力的词表达出来,我喜欢那种坚硬与锋利的表达带来的快感,更愿意寻找两个事物之间潜在的关联的神秘性。
我写的第一首诗是一首关于赞颂红旗的打油诗,那时候我上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写诗的意识,是在日记本上简单地写下的。现在已经对这首诗没映像了。我开始大量地练习诗歌写作是在上了高中之后,遇上不喜欢上的课,便只顾自己在下面写了,那时候每天大概能写那么一两首,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这一阶段是我写诗歌的练笔期。我对生活的这种笨钝,使我比别的人持续的过程要长一些。我真正地开始有意识地写作是在我大学毕业进了西安高压开关厂以后开始的,在西安高压开关厂我们是工人,工人就意味着在上班的时候有干不完的体力活。而制造高压开关主要以铁、铝和铜为工作的开展对象,每天与一些铁器打交道,在慢慢的那个适应过程中,身体的创伤感是不言而喻的,加之大学刚刚毕业,对生活的不适应,使我在内心里聚集了过多的怨愤,那种钝刀割裂一样的感觉正一点点深入到内心,我便开始大量地写诗歌,我的第一本诗集几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当然第一本诗集不仅仅是关于在工厂工作的,反而我在工厂工作的那类东西写的更少,我将那些东西掩盖起来,不愿去触碰。我更愿意在下班之后去观察我们所处的生活场所的那些人们,那些和我有着紧密关系的瞬间,激发了我那段时间创作的主要灵感,但我深知道那些时候我写出了生活反射给我的痛,这种感受或许与我远离他乡有着密切的关系。
几乎我的诗歌都是这样来的。我写下了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瞬间,写下了我对生活的体悟,也写出了我对生活中事物的情感。那些年,我的诗歌几乎是随时随地的,在好大一部分诗歌中能找到那些事情准确的地点和发生的方式,而几乎是我对这些事物的直接感受构成了完成那些诗歌的整个情感场域。
在西开呆了3年之后,2009年我回到了故乡神木,正好那一年开始,神木的煤炭资源给神木这个小县城带来了爆炸式的发展,我经历了那个爆破式的发展的时期,我也看到了蓬勃发展之后,借贷危机给神木带来的信誉的丧失,这种丧失集中地表现在我所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并且表现为诚信体系的崩盘,而这些在我的生活中时刻萦绕的事情,给我带来了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与反思。而正是这些年间,夹杂在这些瞬息变换的事物之间,让我更多地关注了苦难,更多地关注了生活中的弱势群体。这与我对生活的慢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与我的亲人们在这种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我对生活的阅读给我带来了更为接近我的内心的表达方式。我表达了对亲人们的爱,也写出了我内心的酸楚。
责任编辑: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