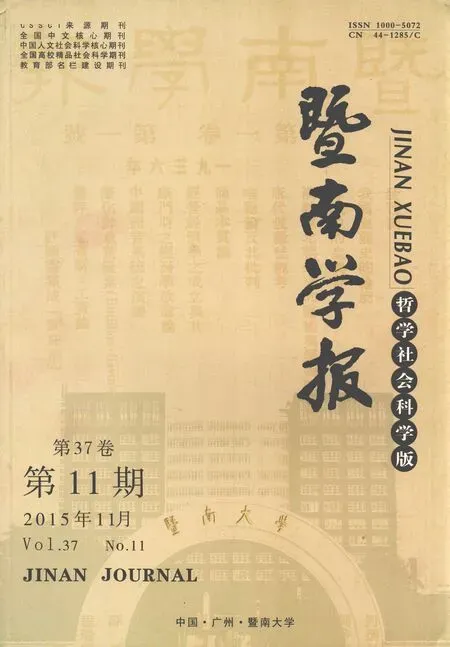论叔向的文学成就
2015-11-14来森华
来森华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论叔向的文学成就
来森华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
前人早已提及叔向文学家的身份,然学界对其全面、深入的研究至今阙如。据考证,叔向至迟生于公元前593年,至迟卒于公元前514年。叔向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学活动、文章、文论三个方面:诗学活动主要分引诗以明事、诗歌篇章的阐释、诗意的领悟三类,尤其对《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阐释对后世解《诗》影响较大;在文章层面,主要分书信和辞令,一篇书信结构完整、情辞俱佳;辞令又有外交辞令与论谏辞令,皆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就文论而言,主要是对于言辞的一些看法与观点,如辞尚得体与畅达、信而有征、言不僭礼、言重于貌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通识性。叔向相关的文学素材,多注重德行与礼数的彰显,塑造出一位具有君子风范的文学家形象。[关键词]
叔向; 诗学活动; 诗歌阐释; 信札; 辞令; 言辞观叔向,春秋末期晋国公族成员羊舌肸之字,又字叔誉,因封地在杨(今山西洪洞县一带),故又有杨肸、叔肸之名。其父羊舌职,叔向四兄弟当时皆出仕晋室,时称“羊舌四族”, 叔向排行第二。晋悼公时初任公子彪之傅,彪即位为平公,叔向继续任傅、上大夫等职,后又事昭公。著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名正直无私的廉吏,孔子评价其为“古之遗直也”;另外他又有卓越的外交才干,屡次单独或随从出使诸侯、应接来使,为江河日下的晋国维护着残存的霸主威严,与时下著名的子产、晏婴、叔孙豹、季札等人均有外交往来。
叔向虽与子产、晏婴、叔孙豹等人几乎同处一时,然史籍对于其生卒年并未明确记载。笔者在勾勒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拟将其作以大致的推测与界定。《左传》载叔向事止于鲁昭公十五年(晋昭公五年,公元前527年),而昭公二十八年(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秋羊舍氏被灭族时并未提及叔向,这就暗示出叔向当卒于此期之内,至迟不晚于前514年。《说苑·敬慎》载曰:“韩平子(按,韩宣子韩起之子韩须)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云云。’”可见叔向至少活了八十岁。故大致推测为:叔向至迟卒于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至迟生于晋景公七年(前593年)。
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人物表》将叔向与鲁国叔孙豹、吴国季札、楚国左史倚相等一起归为“文学”一类,又彰显其文学家的身份。然学界对于叔向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对作为文学家的叔向进行全面、专门的研究至今阙如。笔者不揣简陋,试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挖掘相关文学素材,将其文学成就从诗学活动、文章、文论三个方面作以力所能及的梳理与探讨。
一、卓于诗学
关于春秋时期赋诗、引诗等相关诗学活动,学界广有所涉,成果颇丰。笔者依《左传》《国语》《晏子春秋》统计,叔向无赋诗活动,引诗凡9处,另外其对于别人赋诗或有篇章字句的显性训解,或有诗意的隐性领悟。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叔向诗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兹择要作以专述。
(一)引诗以明事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叔向因栾盈事受到牵连而被囚,有人劝其不归附范宣子而获罪不明智,叔向却引逸诗之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以对,认为不介入大族之争当为明智。此事过后,乐王鲋来见叔向答应为其求情,然叔向深知其为人,入不搭理,出不拜送;人们又怪叔向,叔向却言能解救自己者为祁奚而非乐王鲋,并引《大雅·抑》中诗句“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赞扬祁奚,认为其是正直之人。
《昭公二年》记载,鲁国叔弓回访晋国,晋国国君先是派人行郊劳之礼,叔弓表示承受不起如此重礼以辞谢;而后又让其入住宾馆,叔弓又卑让以辞。叔向认为叔弓知礼,具有忠信与卑让的高尚品德,遂引《大雅·生民》之句“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以明叔弓之德行。
另《昭公元年》《昭公六年》《昭公八年》《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叔向亦有引诗以明所言之事,就此提过,不多辞费。
(二)诗歌篇章的显性训释
春秋时期外交场合赋诗、引诗的用诗过程,从另一视角看就是一种不自觉地诗歌阐释过程。然而在这种君子风雅当中,为了使不同阶层的更多人领会诗意,一些熟谙诗意之君子往往会自觉地对其中的字句、篇章等进行不同程度地训解。拙文《论春秋时期的〈诗〉文本阐释及其特点——基于〈左传〉〈国语〉中“赋诗”“引诗”的探析》对此有过一些不成熟的见解,可参。实际上,春秋时期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既是诗歌应用过程,又是诗歌阐释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诗歌传播过程。而在此过程当中,叔向对于《周颂·昊天有成命》全诗与《大雅·既醉》第六章的训解尤具代表性。
《国语·周语下》记载,叔向聘问于周,在发放礼币的过程中轮到单靖公,靖公虽然宴享简便但对叔向颇为敬重,处处不僭越礼数,并在宴会上为其奏《昊天有成命》。宴毕,靖公的家臣送叔向,叔向对其言到,单靖公家族将会兴盛起来,在引用古史之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所奏《昊天有成命》的诗意进行了通盘训解,最后又引用《既醉》第六章并亲自训解后以证单靖公家族必将强盛的预言。便于理解起见,兹将叔向诗歌训解部分引于下:
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而称昊天,翼其上也。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
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单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单若有阙,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他矣。
叔向对于《昊天有成命》一诗的说解,对于后世解《诗》影响深远,《毛诗正义》曰:“此篇《毛传》皆依《国语》。唯‘广’、‘固’二字郑(按,《郑笺》也。)不为别训而破以同已,则是不异于毛,但意不必有。‘感生之帝’与郑小异,今既无迹可据,皆同之郑焉。”另外,在征引叔向说解全诗内容的基础上,继而曰:“是全释此篇之意也。古人说诗者,因其节文比义起象理,颇溢于经意,不必全与本同,但检其大旨,不为乖异,故《传》采而用焉。”孔氏明确指出了叔向训解此诗对于《毛传》的深远影响。朱熹《诗集传》亦云:“《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以此证之,则为祭祀成王之诗无疑矣。”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亦云:“考叔向说是诗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昭文昭、定武烈者也。’二后指文武,则成王自指周成王无疑。”可见后儒对于此诗诗旨的理解,多不出叔向。
“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为《既醉》第六章,关于其训解,《毛诗正义》虽未明确指出其依于《国语》叔向之辞,然《毛传》训此章中“壶”字为“广也”,孔颖达认为还是受到了叔向解诗的影响,其曰:“王肃云:‘其善道施于室家而广及天下。云云。’王肃据彼文以述《毛传》,彼言‘壶者,广裕民人’,故以‘壶’为‘广也’。”很显然,王肃进一步阐释诗意也是参于叔向之辞。
(三)诗意的隐性领悟
对于春秋时期的诗学活动,学界往往更多关注赋诗、引诗本身及对此的评点等现象,然有一种现象亦不可忽视,即通过对诗意的领悟完成对赋诗者意图的把握。领悟得当,大国或许化干戈为玉帛,小国或许求得生存之机;如若无法领悟或领悟不当,轻则于己受辱,重则于国蒙难。此种对诗意的领悟,具有隐性特征,彼此心照不宣、悟而不解,与赋诗、引诗一样,这同样要求参与者具备很高的诗学素养。
《国语·鲁语下》记载,各路诸侯在晋悼公的率领下讨伐秦国以报复栎之役的失败,到了泾水边诸侯都无渡江之意。晋国叔向到诸侯间斡旋,见到鲁国叔孙豹便说:“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叔孙豹回答道:“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回来后,便召集掌管舟、马的相关人员,说道:“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处隧,不共有法。”果不其然,“联合国”军出发时,鲁人、莒人先渡河,其他诸侯的军队从之。这次战役虽然最后因联军内讧而以失败告终,但是起初叔向对于叔孙豹所赋诗意的领悟可谓切当。《左传·襄公十四年》对此事亦有记载,互有详略。
《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齐、晋两国修平,在大隧会盟。出于政治利益,鲁国的叔孙豹作为外交使臣在柯会见晋国赵宣子,见到叔向,赋《载驰》第四章以表鲁国欲借助大国力量以自我救助,叔向听后便知对方意图,遂以“肸敢不承命”以对,答应救助鲁国。
另外,《襄公二十六年》叔向亦先后两次对齐国国弱、郑国子展的赋诗意图准确领会,从而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
二、工于书信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此年三月郑国子产铸刑书,此事在诸侯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且多有非议,叔向亦致书于子产曰: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贤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此为春秋时期活跃在诸侯之间的两位外交家间的一份书信,虽属私人信件,但其中涉及的却是时下重要的政治事件。信中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动之以制,晓之以理,明之以利害,道之以古训,表明了对于郑国铸刑书一事的不赞成。此篇虽依附于史传,然首尾完整,单独亦可成篇,同时句式整齐、情辞俱佳,具有一定的文章与文学价值,是一篇优秀的应用文,在春秋时期的文书中具有文体代表性。子产对此有回信,与叔向立足于“礼”的深远目光不同,其答复表达了对于铸刑书一事的现实考虑。
三、娴于辞令
宋真德秀《文章真宗》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门,可见人们较早就注意到了辞令的文章价值。近来,学界对于在形态上隶属于史传叙事一部分的辞令的文体价值进一步挖掘,如赵逵夫先生说道:“行人辞令是先秦时代具有文体学意义的散文,对后代散文、辞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行人是我们研究先秦尤其春秋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与文学思想的一个新的视角。”就此问题,新近亦有研究性论著不断出现,如陈彦辉《春秋辞令研究》、董芬芬《春秋辞令文体研究》等。
《鄘风·定之方中》之《毛传》有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有此九能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史通·叙事》亦言:“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参以叔向曾任上大夫一职,辞令方为其职守之一,称其娴于辞令并不为过。在相关史传典籍中,叔向亦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辞令,且屡屡出彩于外交场合,此分外交辞令与论谏辞令两大类简要述之。
(一)外交辞令
《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昔日,诸侯在朝会晋国虒祁落成归去时心存二心,叔向主张示威于诸侯。到了此年晋国欲结盟而齐国不想参与,晋国国君便派叔向将此事告于周天子之卿刘献公,在得到对方的支持后叔向如齐请盟,对方却以“诸侯讨二,则有寻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寻?”为由认为晋国寻盟师出无名,早有所备的叔向遂对曰:
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问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自古以来,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兴。晋礼主盟,惧有不治;奉承齐牺,而布诸君,求终事也。君曰“余必废之”,何齐之有?唯君图之。寡君闻命矣。
齐国早已看出晋国寻盟的真实动机,故当叔向表明来意后直接道明不愿结盟的原因。得到周天子支持的叔向不卑不亢,首先采用排比和顶真的修辞手法,气势磅礴,使得示威于众有礼可据、师出有名;进而说明此举意在彰明天子之制,使其政治目的进一步神圣化;接着将其上升到天下存亡之攸关的高度,将晋国寻盟的举动美化;最后自然地道出齐国的不是,并将决定权抛给对方。叔向此段外交辞令显然是经过事先精心筹备,词采并茂但不失声辞俱厉,齐国听罢惧而结盟。为了政治利益而告之以言辞并顺利地使得对方顺从,由此不难窥见叔向作为一名优秀外交家的卓越言语才能与文章本领。在剑拔弩张的政治与外交面前,词采斐然的辞令犹如糖衣炮弹将对方轻易击溃。
《昭公十年》记载,晋平公卒后,诸侯之大夫如晋吊唁,安葬完毕却不听劝阻执意要见晋国新君,足智多谋的叔向以辞婉拒,其辞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当时晋国新君未立,而其仍是时下名义上的霸主,各国大夫们此时提出见新君必各怀政治目的,叔向以上辞令于情于礼不可谓不得体,但又不失实用,最后皆无辞以对,既维护了晋国霸主的所谓尊严,又未直接伤害外宾的脸面。
(二)论谏辞令
《国语·晋语八》记载“叔向贺贫”一事,叔向贺词为典型的论谏辞令之一。叔向见到韩宣子,宣子忧患于自己的贫穷,叔向却向其道贺,宣子不解,叔向遂对曰:
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诸侯亲之,戎狄怀之,以正晋国,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假贷居贿,宜及于难,而赖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难,而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一朝而灭,莫之哀也,唯无德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叔向从正反两方面以晋国上层政治人物为例,最后道明宣子应该以栾武子为榜样,学习其简约、乐于清贫的德行,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德行之不至,而非苦恼于物质之匮乏。整篇文辞条分缕析,引古喻今,说理透彻,终以一反问句收尾,在点明主题的同时又显现出论谏者委婉陈辞的语言技巧。
另外,《晋语八》记载叔向对韩宣子问于秦、楚二公子之禄;《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灵王诱杀蔡灵侯及其随从卿士,楚公子弃疾率军围攻蔡国,韩宣子问楚军能否胜利,叔向借之以论德;《昭公十三年》记载韩宣子问楚国子干归国后能否成功,叔向借之以论政,云云。这些议论文辞主题鲜明,言辞恳切,囿于篇幅,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四、重于言辞
先秦尤其春秋时期,尤重言辞,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关乎言辞的普遍性认识与评论。《尚书》有“嘉言”“谝言”之分,另《周书·毕命》中康王告诫毕公为政之道时提出“辞尚体要”,即为政者言辞要尚实。据《左传》所载,叔孙豹将“立言”与“立德”“立功”一起称为“三不朽”。《周易·文言》中孔子有“修辞立其诚”之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提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言辞观点;《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又有“辞达”之说。尤为重要的是,言语更是作为“孔门四科”之一,作为孔子教授与评价弟子的一个重要方面。
叔向在外交话语中亦不乏言辞之论,兹列举如下,并作简要析论。
(一)言辞尚得体、畅达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鲁襄公卒后,子产辅佐郑简公出使晋国,晋平公以鲁襄公去世为由,不予接见。子产将诸侯宾馆的墙全部推翻然后让车马进入,晋国的主管官员士文伯前往问责,孰料子产据礼以对,当时晋国执政赵文子听后觉得子产所言极是,并派士文伯前去道歉。遂有“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引诗出自《大雅·板》,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言辞辑睦则民众团结、协作,言辞有条理且畅达则民众安定,叔向引此以证子产之辞得体、实用。赵逵夫先生主编《先秦文论全编要诠》节录此事并题曰《子产有辞》,说道:“从叔向对诗句的感悟中还可以看出时人以言辞的得体、条理、畅达为上。也能够想见出当时的人们对语言艺术的重视程度。”得体、有条理、畅达的言辞可以说是当时一种普遍的体认与追求,孔子所言“辞达”即是。
(二)“君子之言,信而有征”
《左传·昭公八年》记载,晋国的魏榆这个地方在石头上出现了言辞,晋平公问师旷何故,师旷详细作答,认为系人为所致,并非石头天然出言。遂有“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是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先秦文论全编要诠》亦选此篇,题曰《晋侯问石言》。叔向所论主要提出了君子之言与小人之言的区别,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即真实而有依据,如此方祸怨远离己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征”,即信口开河、毫不凭证,如此就会祸怨上身。很明显,叔向于此是要突出师旷信而有征的君子之言。
关于言辞要有理据的道理,叔向于《昭公九年》亦有提及。周朝甘大夫襄与晋国阎嘉争夺阎之田地,周天子派詹桓伯陈辞于晋,叔向听罢对晋国执政赵宣子提到“且王辞直,子其图之”。杨伯峻注曰:“直谓有理,曲则无理。”言辞要有真实性,可谓春秋时人一种近乎通约性的认识,《国语·晋语五》即载宁嬴言曰:“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胡可渎也!”言辞华而不实如晋大夫阳处父者,不但初欲追随者宁嬴悔而知返,就连妇人如伯宁之妻者亦会将其视为话柄。
(三)言不僭礼
《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曰:“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叔向此段关于言辞的评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则是说言辞要大方、让别人明白;深层次的含义无外乎如其所言“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即言辞要合乎礼仪,失言、失容貌即失礼。
而关于言辞要合乎礼数,叔向亦不乏专论。《昭公十五年》载曰:“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叔向认为周王失掉最根本的礼数而数举典籍,滔滔不绝之言既失礼又无用。
其实,当时亦有言辞以合礼的论点,如《昭公二十六年》载曰:“闵马父闻子朝之辞曰:‘文辞以行礼也,子朝干景之命,远晋之大,以专其志,无礼甚矣,文辞何为?’”春秋晚期虽然“礼崩乐坏”,然在时下君子的眼中,言辞依然不能僭越礼数。
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史料证明其中的渊源,但在叔向主张言辞不能僭越礼数、闵马父所言“文辞以行礼”的言辞观念中依然不难觅得后世儒家诗学及文论的些许痕迹,如《毛诗序》即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当属于同一理论范畴。
(四)言重于貌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祁氏、羊舌氏被灭族后田地被瓜分殆尽,其中派贾辛任祁大夫,上任前向魏献子道别,魏献子为之讲叔向言重于貌的故事以激励贾辛。叔向曾经出使郑国,鬷蔑容貌丑陋,然因“一言而善”而得到叔向的赏识,并引同样貌丑的贾大夫射落野鸡方博美人一笑的故事鼓励鬷蔑勿因容貌丑陋而自卑,其有言曰:“今子少不扬,子若不言,吾几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二人随后就如彼此已经很熟悉的老朋友一样,相见恨晚。从此处记载足以说明春秋时期对于作为内在修养的言辞本体的重视程度远胜外貌,诚如前引宁嬴与阳处父的故事,纵然初因外貌而从之,也会由于言辞华而不实终而离之。
韩高年先生《春秋时代的文章本体观念及其奠基意义》一文提到:“发为言辞与撰制文章是春秋时期人的能动性得以发挥的重要手段,所以重视言辞、语、说、命、论等篇章的功能、并进而探讨其言说与撰制的规律,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气。他们提出的种种观念和范畴,是最初形态的文章本体论,这些观念和范畴,奠定了中国古代文章理论的基础,是很多重要的文论范畴的源头。”此说将春秋时期的言辞观念等上升到文章本体论的高度,充分彰显其文论价值,对于更好地理解时下言辞观念启发良多,而叔向的一些观点可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证实与完善。
五、余论
通过以上析论,就叔向文学成就而言,在诗学活动中尤以对诗歌的通盘阐释对于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而在书信、辞令方面亦显其卓越的言语才能与文章本领,在文论方面所发表的对于言辞的相关看法也是对于春秋时期普遍重视言辞的印证与呼应,是“最初形态的文章本体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叔向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往往重视德行与礼数的宣扬。换言之,德、礼几乎统贯叔向思想,对其进行细致归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与树立这个鲜活的文学家形象。宣扬德行层面,如前引《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叔向引《诗》句“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称赞祁奚正直之德;《昭公二年》叔向引《诗》句“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赞扬叔弓,并认为“夫子近德也”;《国语·周语下》载叔向在训解单靖公所奏《昊天有成命》一诗,认为其是“《颂》之盛德也”,并由此而上升到单靖公的德行层面,赞其“俭敬让咨,以应成德”,“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晋语八》所载“叔向贺贫”故事,在其贺词中叔向建议韩宣子当学习栾武子的德行,真正值得苦恼的不应是贫穷,而应是德行的匮乏;云云。另外,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叔向与晏婴就当下各自国家普遍存在的道德衰败现象有过专门讨论。依据以上典型例证,可以发现叔向宣扬德行主要体现在个体修养上。而在宣扬礼数层面,如前引《左传·昭公六年》所载叔向给子产的书信中以礼为立论点,提出其铸刑书的后果是民众“将弃礼而征于书”;《昭公十年》载叔向依据礼数力拒执意欲见晋国新君之各国来使的失礼行为;《昭公十五年》载叔向听完籍谈出使周王室后的报告,认为周王已经两次失礼,并提出“礼,王之大经也”;等等。另外,在叔向的其他言辞中亦不乏对于礼数的专论,如《昭公二年》叔向引听闻之言“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认为“辞不忘国”“先国后己”的鲁国叔弓是知礼之人。综上所举,叔向关于礼数的彰显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知礼君子方能依礼处理内政外交。概而言之,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叔向标举德与礼,一方面展现出叔向高尚的人格情操与君子风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末世中君子们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而呼唤礼与德的回归以救世的普世情怀。于此,更为我们塑造出春秋时期一位具有伟岸人格和博大情怀的鲜活的文学家形象。
还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从史传中挖掘的相关文学个案素材终归是依附于史传这个母体,那么难以避免的是相关的文学素材之间就会出现交叉的现象,如书信、辞令中引诗以明事,发表言辞观念时亦引诗以证,云云。
以上仅为对作为文学家个案之文学成就的叔向的一次尝试性探索,而随着辞令等文学现象对后世文学影响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文学成就当有更大的空间可供挖掘。另外,就其生卒年亦只能大致推定,至于具体的时间只有期待新材料的发现。
[责任编辑吴奕锜责任校对王桃]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批准号:11&ZD103)。[作者简介]
来森华(1986—),男,藏族,甘肃卓尼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收稿日期]
2014-09-26[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15)11-01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