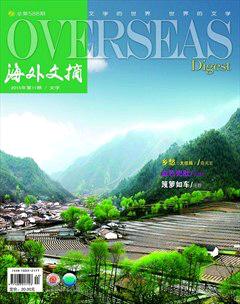篾箩如车
2015-11-13
篾箩如车,这是朦胧感觉。因为随父母来到乡下是一个月色的夜晚,好像没有一丝寒冷,凭记忆不是夏天,就是春秋了。这种记忆中的感觉,至今印象很深。记忆中,我是坐在父亲肩担着的篾箩里来到乡下的。因为那时连一辆木制的双轮车也没有,肩担手扛加步行是习惯的生活方式。父亲担着两只篾箩,一只里面是我,另一只是大我一岁的姐姐。两只篾箩里盛放着父亲许多心爱的文学书籍。后来才知道这些书籍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等。到我懂事时,这些书籍都已泛黄,因而父亲又用“牛皮纸”作封面保存下来。现在父母新居的书柜里还整整齐齐地放着这些“宝贝”。
坐在摇晃的篾箩书堆里,小手紧紧抓住篾箩的边沿和绳索,别有一番似同坐车的感觉。一路上在晃动中数着繁星点点,至于后来是怎样的感觉就一点也回忆不起了。我想,可能是年岁小,在这幸福的摇篮里可能是睡着了。当然就不知道当晚在乡下时的景况,包括见到何人、住在哪一户农家了。
60年代初随父母下放农村来到递铺公社的梅园村。这个村的村名多次更改:双友村、梅园村,现在又在梅园、狮子山、方家上这三个村的基础上合并后又称之为双河村。何以起此村名?因为三个村的腹地流淌着西苕溪的两条支河,所以用之“双河村”也很确切,百姓们也不去争名,可说是“和谐之村”了。
我在梅园村长大,后来在村里很荣幸地参加了全国首次地名普查,也弄清了梅园村的来历。通过走访老农和一些长辈,我在那次地名普查的表格上写上了这样的语句:多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小河,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别是上游受常年奔涌而下的河水冲刷,后来逐渐变成了一条宽阔的溪流。当初,溪流的两岸梅树遍野,春天时可谓“山花烂漫”,人们就习惯称这里是梅园。早年这里又没有桥,人们靠摆渡往返于两岸,到递铺镇上又是必经之路,大家都叫这里为梅园渡。于是,行政村建制时,“梅园村”的大名也就非其莫属了。
父母何以要下放到农村?说来话长,暂且避之。父亲本是递铺人,祖父祖籍是安徽徽州。父亲1949年9月参加工作,后来在分水县粮食局工作,接下来分水又与桐庐合并称为桐庐县。由于工作的缘由认识了桐庐籍又在一个系统工作的我的母亲。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国弱民穷,为了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父母凭着青春热血毅然向组织报了名。据母亲早年时常这样说父亲:“你说下放好,到乡下养几只鸡,生些鸡蛋,种些蔬菜,兼上几个生产队的会计,就能过上好日子,我是被你骗到农村来的。”其实,下放农村后,劳动强度大,体力又弱,工分不多,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是极其艰苦的。在生产队里还成了头号“倒挂户(倒欠户)”。我曾记得有几个年头过除夕,还是乡亲送来了几斤猪肉才过上了年,那是特别地辛酸,但心里还是温暖的,因为周围有许多真诚相助的人们。
有了这段困苦的岁月,我对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倍感珍惜。想想自己或多或少混出个人样,也不怨言。但自己只能与自己的纵向来比,也就坦然了。
母亲何以说到农村是“受骗”呢?其实,母亲是1949年8月参加工作的,如果不“青春热血”来到农村,早已够上“离休干部”的资格。想到此,母亲怎不痛心疾首,懊悔莫及呢。如今,母亲仅拿几百元一个月的生活补助费,要与离休待遇相比可谓大相径庭了。也难怪母亲动不动就唠叨不停,尤其是年老多病的晚年,想想当年17岁参加工作时的意气风发,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父亲的下放还是另有原因的,后来听母亲唠叨中得知是“右派”什么的。但事实是刮到了一阵错划“右派”之风。当时,父亲一夜成了县里的“大诗人”,墙上贴满了父亲写的诗词,任意加以“润色”,并成了国宝大熊猫,日夜加以“保护”。而且没收了父亲的诗稿,至今父亲对此痛惜不已。特别是其中有一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写的长诗———《胜利的旗帜在飘扬》,也从此消失了,而今已不能回忆起来。虽然这个“错划”当年就得到了纠正,但负面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父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获得了重新扬眉吐气的舒畅日子。我母亲是经过父亲再三劝说才同意随父亲一同到农村去的。所以,后来母亲一直责怪父亲。
父亲下放时选择的地点即梅园村,是父亲的首选。听父亲说,当时选择何处随自己的意愿。据父亲说,日本鬼子侵占中国时,递铺沦陷。那时父亲随爷爷奶奶逃难于梅园。因为梅园有个自然村叫木橡园,那里有成片的小竹林,木橡园当然还有在竹林中长着的橡子树。在躲难时,把竹子弯成居住的小房子。日军飞机轰炸百姓房屋,躲在竹林里就安然无恙。
在避难的日子里,爷爷、奶奶和父亲就认识了当地不少好乡亲,有的成了莫逆之交。乡下人听说父亲下放选择于此,当然是热情欢迎。日后几十年在农村生活的日子,方方面面都得到众多乡亲们的关照,把这段美好的回忆永远留在心里。
如今,每当我在那里看到了乡亲们的篾箩仍很亲切,心中就会涌上坐在篾箩里的那份甜蜜。它不是车却胜似车,因为它牵连着在乡下与朝夕相处农民朋友的那份情结,那份怀念和那份别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