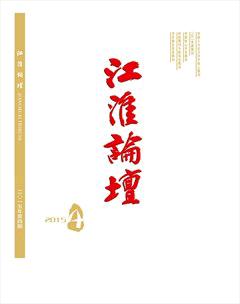十年磨剑,终成名器
——读朱万曙先生《徽商与明清文学》
2015-11-02唐明生
唐明生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十年磨剑,终成名器
——读朱万曙先生《徽商与明清文学》
唐明生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朱万曙先生的《徽商与明清文学》是一部研究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力作,呈现出研究视界的聚焦性、立论基础的坚实性、研究向度的立体性等特点。
《徽商与明清文学》;研究视界;立论基础;研究向度
日前,朱万曙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清文学”的最终成果《徽商与明清文学》[1]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项目自2004年申报,到2011年结题时被评为优秀,到最终成果2014年出版,历时十年,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为学界奉献了一部研究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力作。
在朱先生之前,关于明清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有部分论述。如邵毅平先生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2],就将中国古代文学中商人题材与商人形象的塑造进行过全面的梳理;陈书禄等学者从士商关系的转变或“士商契合”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文学的转型等问题。明清两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得到不断扩增,这一社会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乃至文学的变化,这种变化,以往的文学研究未曾给予充分的注意。朱万曙先生的《徽商与明清文学》恰恰就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通过徽商这富可敌国而又遍布全国的商帮和明清文学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来立论的,乃填补徽商与明清文学关系研究空白之力作。
《徽商与明清文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徽商与明清文学生态,包括徽商的崛起和“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徽商与明清文学传播、徽商家族与文学传统、徽商与明清戏曲、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等六章;下编主要探讨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包括徽商文学创作的蔚起、徽商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价值、明代文学创作个案、清代文学创作个案等四章,另外还有绪论、结语和两篇附录。如果说上编在具体探讨明清文学生态变化,阐释徽商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下编就是徽商在明清文学生态变化中所起作用的具体例证与实践。整部书征引雅博、论断精审、逻辑严明、浑然一体,体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聚焦的研究视界:通过代表性强的徽商透视商儒互动对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影响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生产与交换之后,就诞生了商人和商业。商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又被称为“商贾”。何谓“商贾”呢?汉代的《白虎通》曰:
商贾,何谓也?商人之为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谓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
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贾。[3]
从这个对商贾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商贾所独有的特点在于流通、便民、求利,也可以得出商人在整个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人阶层也不断扩增。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就记载了明代正德前后社会上对待商业态度的变化:“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应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4]何良俊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后,进入商人行业的人数越来越多,经商已经成为农、工之外的又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工,商人阶层较之以前是成倍的增扩。另外,曾经担任过嘉靖、万历朝重臣的张翰在《松窗梦语·商贾记》中描绘了大江南北各地商贾异常活跃的情形和地域特点:“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便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5]
在全国各地的商人群体中,徽商是不容小觑的力量:
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6]42(明.王世贞《赠程君五十叙》)
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6]213(明.万历《歙志》卷十《货殖》)
如果前一句说的是徽州人对经商的热情以及徽人从商的比例,那么后一句则告诉我们徽人经商的活动区域极其广泛,徽人经商的足迹不仅遍布许多都市大邑,而且也深入到一些乡镇,从省到府,从府到县,从县到乡镇,可以说,遍地都洒下了徽商辛勤的汗水与足迹。
明清时期的商帮很多,历史学界有“十大商帮”之说。但作者为何选择徽商来探讨商人与明清文学之关系?这是因为相对于其他商帮,徽商有着“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故而从徽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当时明清文学生态的变化,更具有代表性。
循此思路,朱万曙先生在本书中首先探讨了徽商之于明清文学生态变化的关系。上编六章,从徽商的故乡徽州文化传统入手,首先论述了其与其他商帮文化性格的不同,以此为基础,分别论述了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与文学传播、徽商家族的文学传统以及与明清戏曲的关系,其着力点集中于徽商的崛起对明清文学生态的影响。例如,徽商由于“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较之于其他地域商帮,与文人的交往更频繁密切,书中详细考察了诸多徽商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对文化的崇尚姿态,特别以哈佛大学所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为材料,考察了明代徽商方用彬与当时文士们的交往情形,分析了他与文人交往的动机和效果,并进一步分析了文人对商人的复杂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正是由交往而发生的态度的变化,带来了文人书写商人态度的变化,商人形象不再仅仅是追逐金钱、充满铜臭气的,而是有文化追求的。这就是徽商对文学生态影响的结果。正如朱先生所言:“这种商儒互动或士商契合对于文学思想和创作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50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7]明清时期,因为商人阶层的扩增,商人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明清文学中,商人生活也必然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对此,本书第六章《明清文学中徽商题材的创作》也进行了探讨。作者首先对大量的徽商传记进行了搜集和分析,具体而细致地阐述了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动机与宗旨、徽商传记中徽商形象的建构、徽商传记中的文学价值。这既是将徽商传记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整体观照,也是聚焦徽商领域,探讨徽商的兴起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作者还将目光投射到明清的白话小说中,从《三言》、《二拍》、《西湖二集》、《杜骗新书》、《石点头》、《贪欢报》、《一片情》、《醉醒石》、《生绡剪》、《十二楼》、《豆棚闲话》等小说集中梳理出关于徽商形象的描写,用表格的形式将徽商出现的回目、活动地点及对徽商的描写都一目了然地呈现出来,从而见出了这些小说作品中徽商的“贾而好儒”、乐善好施而又贪念女色等性格特征。徽商成为小说的形象,同样是文学生态的变化。
纵观此书,我们可以看到,探讨的都是明清文学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变化都和“徽商”有关。这种聚焦讨论的方法虽然是管中窥豹,但呈现给读者的却不是一个斑点,而是一个宏大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变革时代的文学全景,是一个发生着变化的文学生态的文学图景。
二、坚实的立论基础:新文献的发掘和利用
有关徽商的研究资料和文献,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张海鹏、王廷元等先生就编纂了《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一书,为众多研究者征引。但是,朱万曙先生研究的是徽商与明清文学的关系,必须挖掘新的资料文献,才能有新的突破。纵观《徽商与明清文学》,可以发现,其所引证的史料非常详实。这些史料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新公布的资料的利用。如哈佛大学所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经由陈智超先生整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于这批珍贵的资料,徽学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而朱万曙先生借以考察手札的主人方用彬与文士交往的情形,以作为徽商与文士交往的个案。又如鲍廷博的《花韵轩咏物诗存》,刘尚恒先生在《鲍廷博年谱》中已经有所研究,朱先生则从文学的角度给予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列为本书附录的《近代徽商自传小说<我之小史>》一文关照的《我之小史》小说文本,也已经王振忠先生整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学界似乎也未曾注意,朱先生则对其给予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述。
第二类则是朱万曙先生的自我发掘。这类材料更多,也更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对无论是从事徽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者,都是全新的资料。例如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率滨吟社录》,反映了明代休宁率口程氏家族诗会情形,朱万曙先生借以考察徽商家族文学。又如对晚明时期活跃于杭州文坛的汪然明,以往的学者乃至像陈寅恪那样的学术大师都曾多次提及,但并未发现关于他经商的记载,朱先生从清代延丰编纂的《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中找出其传记,其中明确记载他“业盐桐江”;至于对汪然明本人的创作以及对其家族文学传统的梳理,则充分利用了汪簠所编的《从睦汪氏遗书》。再如对明代徽商文学创作的概述,作者从李梦阳的《空同集》中找出了他为鲍弼、佘育、郑作等徽商的诗集写的序言,从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找出其为徽商吴汝义写的《吴汝义诗小引》,从胡应麟的《少室山房集》中找出为徽商吴德符写的《吴德符诗序》,从许国的《许文穆公集》中找出传其同族商人许文林的《竹石先生像祠记》,等等,通过这些资料,作者大致勾勒出明代徽商文学创作的面貌。同时,他对程诰、方于鲁、江春等徽商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无不显示对新文献的挖掘和利用。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整部著作中,朱先生共引用材料492种(不包括重复使用),这492种材料中,大部分是家谱、方志,还有许多碑铭,以及诸多藏于国内外图书馆的善本等。这些珍贵文献很好地佐证了徽商与文士交往的记录,生动地体现了在商人阶层扩增的情况下,明清文学生态发生变化的过程。
三、立体的研究向度:宏观的论述、微观的实证与文学批评相结合
在朱万曙先生的大作中,体现了宏观的概述和微观的实证相结合的特点。如上编第二章《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中,著者先用一例个案即徽商方用彬和文士交往引起,通过介绍徽商方用彬其人、从方用彬与文士交往的信札看其与文士的交往、看他和文士交往的动机和效果来着手。这是具体的徽商与文士交往的个案,之所以选择这一个案,是因为方用彬是一个有心人,他精心保留了和文士交往的七百多封信件,这是实实在在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记载了方用彬这个徽商与文士交往的诸多细节与心理。在这一个案基础上,作者又将徽商作为一个总体,从宏观上探讨了他们对文士的崇尚和利用、对文士的关心和帮助等。交往是相互的,只有相互的交往,才能更加促进交往的频繁,为此,作者又用了一节,专门探讨文人对徽商的复杂心态及其观念的转变。这样微观和宏观相结合,就将文士和徽商的交往作为一幅立体图呈现于读者面前。这种立体构造图,直观、多角度、多层面地呈现了徽商与文士的交往,使读者对其之间的交往一目了然,增强了立体透视感。
再如下编的四章中,前两章是概述在宏阔的明清文学生态视阈中,因为徽商参与文学创作给文学带来的变化,并且对徽商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后两章则分别探讨了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与清代徽商的文学创作。这完全是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通过宏观的描述概括其特点与价值,通过微观的实例来论证宏观的判断,这样,有理论,有实证,理论和实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互相印证和补充,很好地说明了徽商和明清文学生态之间的生成、发展、变化关系。
作为研究徽商与文学关系的著作,除了注重史实的描述和考证以外,本书也时时注意开展文学批评,这在下编《明清徽商的文学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例如第二章分别从“文会与唱和:商人创作之情景”、“山水与田园:商人创作之审美意识”、“寂寞与孤独:商人创作之生命意识”、“追忆与寻觅:商人创作之情感书写”四个层面分析了徽商创作的特点。特别是对商人创作个案的研究,作者一方面搜寻资料,考证其生平,以做到知人论世,另外一方面则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分析,努力发现他们的哪怕是一点点的贡献和特色,如明代曾经受到李梦阳指点的徽商程诰,文学史上虽然没有他半点地位,但作者引录了其长达230句的《发蜀中东归黄山乃述南北游历留别云巢王子》一诗,指出它“大约是文学史上最长、涉及游历之地最丰富的旅游诗”,“像这样以本人亲身游历为素材并且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诗作,在一般的文人那里反而很难觅见”。[1]265再如,对汪然明诗歌,作者指出其多以“绮丽”为风格内容,而且往往和女性关系密切。对于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作者认为“与他的商人生活有关,和晚明时期‘尚情'思潮也有很大关联”。[1]331凡此,都体现了本书文学研究的立场。
朱万曙先生的大作《徽商与明清文学》在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商与明清文学“的最终成果结项时获得“优秀”等级,国家社科基金办在对这项最终成果作介绍时,曾评价道:
安徽大学朱万曙教授主持完成的《徽商与明清文学》,从“好儒”的文化性格、徽商与明清文人的交往、徽商与明清文学的传播、徽商家族与文学传统、徽商题材的创作等多个方面,对徽商与明清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该成果研究视角和方法新颖,不仅将商贾、徽州区域文化与文学相结合,乾嘉朴学等传统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文献整理与艺术批评相结合,而且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鉴定专家认为,该书资料翔实,分析细致,且多有发明和创获,是一部徽商与明清文学交叉研究的力作,填补了徽商与明清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480
这既是综合鉴定专家意见后的评价,也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评价。作为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其中“多有发明和创获”自不待言。我想,无论是从事徽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的同仁,应该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收获的。
[1]朱万曙.徽商与明清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东汉]班固.白虎通(卷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2.
[4][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111.
[5][明]张瀚.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4.
[6]张海鹏,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G].合肥:黄山书社,1985.
[7]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M].吕荧,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21.
(责任编辑黄胜江)
I206
A
1001-862X(2015)04-0173-00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唐明生(1976—),湖北谷城人,文学博士后,湖北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戏曲与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