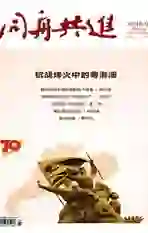由现代版《农夫与蛇》想到的
2015-10-30苍耳
苍耳
一
几乎所有寓言都不免有武断、说教的意味,因为最后的寓意必须直白地说出来;但寓言提供的故事场景足堪回味,其内涵总是大于其寓意。在现代,将古代寓言隐喻化、泛政治化,或将正在发生的事件与寓言联系起来,放大、影射社会的多个方面和多个层面,这在现代人似乎已习以为常了。
以前读到报上的一则小新闻:湖南隆回县雨山镇和平村村民李炳元,有一天放牛回家时,见到雪地上蜷缩着一条冻僵的眼镜蛇。李柄元忙将蛇捉住,见蛇没死,便喜滋滋地把蛇带回家泡酒喝。回家后,李炳元让七岁的儿子抓住蛇尾,自己抓住蛇头,一点点地把蛇塞入玻璃坛子。由于坛口较小,加上用力过猛,坛子被压碎了,眼镜蛇冲着李炳元右手就是一口。这一口不仅让李炳元命悬一线,而且让他意外地成为当地晚报的新闻人物。记者评论道:这简直是《农夫与蛇》的现代翻版!在记者看来,无论从事件的开端还是结果看,二者确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想捂暖冻蛇,另一个是想泡酒喝而已。
这似乎触及到寓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譬如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一直被延伸到政治层面上的不分善恶,姑息养奸,并围绕“费厄泼赖”是否应该实行而展开论争。钱钟书在早年一篇读书随笔中说,小孩子是不宜看寓言的。当然这是一种反嘲说法。他认为小孩子是否适宜看寓言,主要取决于成人造成的现实是怎样的。不妨说,伊索也只提供了一个蓝本,其后的人们不自觉地参与到这个寓言的创构中。
二
传说伊索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但从这则寓言来看,他不太像奴隶。他竟不理解一个农夫拯救一条冻蛇的行为。为了让寓意更自然地说出来,他让农夫自己去“痛悔”:“我可怜恶人,不辨好坏,结果害了自己,遭到这样的报应。”但伊索那个时代,是神话而非宗教鼎盛的时代,伊索得出那样的结论自然情有可原。
我想,这个农夫并非不知道蛇有毒,但他对一条濒死生命的怜悯,战胜了利己与自卫的本能——这正是他与兽类区别开来的标志。怜悯包含怜惜和同情,是人性和良知的要素之一。它没有民族性、阶级性和集团性,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具备之,而怜悯的对象可以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即便是窃贼、战俘、凶犯、死囚。从生命本体的意义上说,所有物种和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等值的,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所赋予的价值,这正是人道主义的基础。在现代世界,立法中已有“反人类罪”,即借助种族、战争、宗教、政治、阶级等名义实施屠杀同类的行为。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既出现过以人性论抹杀阶级性的观点,更出现过以阶级论抹杀人性的畸形理论和历史时期。中学时学鲁迅的《文学和出汗》,当时就心存困惑,只是不敢说而已。梁实秋和鲁迅各执一端:梁实秋认为“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鲁迅则反驳之,认为:“‘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在我看来,文学既可以通过直接描写来呈现简单的人性,也可以通过阶级性曲折地表现复杂的人性,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冲突。阶级性非但不表明人性的消泯,恰恰是人性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衍生出的反向表征——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往往如此。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性或阶级划分有助于被压迫、被剥夺的一方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合乎人性的,马克思理论的进步意义正在于此。但一些阶级论者看不到或否定它下面的人性基础,主张以兽性手段灭绝另一方,其违背人性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俄国十月革命后,如果说枪决尼古拉二世尚可找到理由,那么屠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两个尚未成年)难道也有理由吗?但阶级论者振振有辞:既然尼古拉二世一家是统治阶级,那么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也属于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
所谓怜悯,其实正是人性根基上绽放的花朵。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俄罗斯的思想特征时说:“他们没有西方那种对于冷漠的公正的崇拜,对他们来说,人高于所有制原则,这一点决定了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对于丧失了社会地位的人、被欺侮的与被损害的人的怜悯、同情是俄罗斯人很重要的特征。”原始蒙昧年代的农夫见到毒蛇,即用工具击打之也并不奇怪。但只有当第一个农夫见到冻僵的蛇后生出怜悯之心,才表明这片大陆上生存的人群有了新的质的提升。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将恻隐之心视为人类“性本善”的证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前提之一,便有赖于这种人性的根本觉醒。在古代中国,“连坐制”是从法律层面将怜悯斩草除根,株连九族的残酷无情,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在“阶级性”支配一切的年代,怜悯也被当作“人性恶”加以批判,只要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就可以无情打击。那时候,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得经过阶级性这个大熔炉的炙烤和过滤。以杜甫为例,杜甫确实写了不少“描写臭汗”的诗篇,但最终还是被排到“大地主”的队伍里:“……杜甫是个大地主。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我屋上三层茅,据我所知,四川贫民最多一层草,他有三层草,大地主无疑,邻村的革命小将拿走他的茅草是革命行动,我们应该为之欢呼。”(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只见阶级性,不见人性,甚至连人的气息也没有。这远比被毒蛇咬一口更可怕了。
三
对照一下古希腊那个农夫,他明知冻蛇有毒,对自己有威胁,却不加考虑地“把它拾起来,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用暖热的身体温暖着它”,在我看来这已不止是怜悯,而是不计后果的悲悯了。至今看来,这个悲悯的古希腊农夫仍是伟大的,他不但因捂暖冻蛇而丧失了生命,而且在伊索的笔下再死了一次!这正是它震撼我的原因。
在日常语境中,“怜悯”与“悲悯”常常被混为一谈,二者其实存在很大差别:
其一,悲悯比怜悯要博大得多,它不是出于一种可怜而做出的施舍,而是一种平等的、自觉的痛惜与大哀。即便不幸的对象不在眼前,也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卢森堡在《狱中书简》中写到一匹被抽打的马:“……卸货的时候,这些动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已经筋疲力尽了,其中那只淌血的,茫然朝前望着,它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里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个眼泪汪汪的孩子一样……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着我,我的眼泪不觉簌簌地落下来——这也是它的眼泪呵,就是一个人为他最亲爱的兄弟而悲痛,也不会比我无能为力地目睹这种默默的受难更为痛心了。”缺少悲悯情怀的人,不可能写出这种痛彻骨髓的文字。
其二,怜悯和悲悯具有共同的人性基础,但悲悯的理性根须扎得更深更广,即任何生命个体都可能犯错、误入歧途,都可能因环境畸形、文化冲突、社会不公造成人格扭曲。因而当施暴行为——他戕和自戕的惨剧发生后,当社会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后,作为他的同类,对误入歧途的生命怎能没有一点痛惜?对本来可以良善地活着的罪人怎能没有一点黯然哀悯?对同样可能步其后尘的同类(包括自己)怎能不反躬自省?
其三,怜悯的方式可以不危及自身,而悲悯的付出则是不计后果的。农夫将冻蛇“揣进怀里”,正是不顾危险或不计后果的。反观伊索的结尾,狗尾续貂地让农夫“痛悔”一番,显然是一种“作假”。一个农夫绝不会傻到连毒蛇能致命也不知的地步。农夫既然明知,“痛悔”又从何而来?
四
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和慈善教育的国度,悲悯的稀薄是不奇怪的。近年来,他戕或自戕的悲剧呈暴增之势,原因在于心理畸形、精神病态、患抑郁症的人,近些年是愈来愈多了。
问题是,当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被发现后,他慌不择路地跳入河里,围观者可以心安理得看着他慢慢淹死,而不去施救。因为看一个小偷淹死,良心似乎不会受到谴责,甚至还有一种报复的快感。高尔基记载了革命期间的一件事:“士兵们拖着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要把他扔进莫伊卡河里淹死。小偷浑身是血,脸被打得一塌糊涂,一只眼睛被打得流了出来。一群孩子一路围观着;后来,其中的几个孩子从莫伊卡河边回来时,一边单脚跳着,一边兴高采烈地叫喊:‘淹死了,淹死了!这是我们的孩子,是未来的生活建设者。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观念里将变得十分廉价,然而人——不应该忘记这一点——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东西……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不合时宜的思想》)
若干年前,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事件,韩国学生赵承熙开枪打死了32人,随后饮弹自尽。在接下来的悼念仪式中,被害者亲友点燃的却是包括凶手在内的33根蜡烛,之后在校园草坪上安放的悼念碑也是33块。不少悼念者在赵承熙碑前留下纸条,有的写道:“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也有的写道:“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及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牧师祈祷说:这里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他们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这大概就是《圣经》所言:“别人告诉你们,爱你们的邻人,恨你们的敌人。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马太传》)
对一个凶手的宽谅或悲悯,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这与追求社会正义的观念相冲突。无端伤害或剥夺了别人生命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并受到惩罚,这是对的。社会正义是一把刻度精准的法制之尺,而悲悯则属于一种宽恕仁爱的宗教情怀。二者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既不能互相混淆,也无法相互替代。
我们发现,所有参与泄恨与声讨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自己排除在“人性恶”之外,似乎自己对恶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于是,怀着最大的仇恨来实施或关注对人犯的审判和惩罚,甚至“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无意识地将自己正义化、纯洁化,并不断滋生着一种戾气。“正义”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应该有边界,尤其应该避免自由的网络言论滥用“权力”,否则,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新约?约翰福音》中,当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来,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砸她。人类从野蛮和蒙昧走来,且不说什么原罪,人性本来就不完美。而所有的人格缺陷也并非先天形成,追究下去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社会或历史的根源。只要社会存在非公正和非正义,那么人格变态、人性扭曲就不可能绝迹。
五
如果从寓言中冻蛇的角度看,它未尝没有它的道理。蛇有冬眠的习性,农夫遇到那条蛇也许正处于冬眠状态。农夫将它捂暖,等于将它从冬眠中唤醒,从而改变它亘古的生存方式。这无异于致其命于死地。蛇并没有招谁惹谁,它出于本能,“用尖利的毒牙狠狠地咬了恩人一口”并不奇怪。人类与万物(包括蛇)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处在相克又相容的依存关系中。那个农夫多少有点“好心办坏事”的意味。
人类自诩为“万物的灵长”,总是居高临下地“以我观物”,以功利的眼光看待万物,因而将它们分出“益虫”和“害虫”,乃至将阶级性扩展到整个自然界。上世纪50年代全民大规模“除四害”的运动,便是其中的一例。在那个年代,虎豹豺狼作为“统治阶级”被明文规定可以猎杀,即便像麻雀这种“小害虫”也在全民扫除之列。
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中认为,人的伦理观念是按照三个层次来发展的。早期伦理观是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后来是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第三个层次:人和土地的关系。而土地,不光是土壤,还包括气候、水、动物和植物,它们与土地组成一个互利平等的共同体。利奥波德指出,人应当改变在土地共同体中征服者的面目。但利奥波德不知道,改变“征服者”的面目,缺乏悲悯之心是不可能做到或做好的。著名的“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几任队长都倒在盗猎分子的枪口下。然而,在这一英雄集体里,后来却有八名队员私售没收的藏羚羊皮,中饱私囊。他们将自己视为另一种“征服者”,因而有权私分这些“战利品”。说到底,他们保护藏羚羊,并不是出于伦理的自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悲悯”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祛除“征服”心态。在中国乡村,施用化肥和农药几乎天经地义,如同农夫习惯了与毒蛇打交道,中枢神经已慢慢麻木了。如果一个农民按土地伦理行事,那么他将面临减产和村民的嘲笑。联合国世卫组织曾建议中国控制使用杀虫剂,每年中国有28万人自杀身亡,其中半数以上是喝杀虫剂,在农村更为普遍,且大多为妇女。至于杀虫剂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更难以估计。江苏泰州市高港区某地曾发生过万只飞鸟突然从空中坠亡的怪象,那简直是一场惨不忍睹的“鸟雨”。显然,食物和水源受到毒害,这是造成大面积中毒的根源。
卡夫卡在《一只狗的研究》中,借狗的视角提出一个看似荒诞的命题:“土地从何处获取我们的食物?”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世人总是千方百计从土地那里获得食物,何尝给过土地以“食物”?这个问题恐怕世人连想都没想过。但一只“瘦弱的小狗”想到了。由此可见,一直标榜“天人合一”的我们,从未真正将土地也视为一个完整的、能呼吸的生命体。因为我们只有一点可怜的怜悯,悲悯压根儿就没有。
六
回到前面一则报道。对湖南农夫李炳元来说,事情远没有像《伊索寓言》那样戛然而止,记者写道:李炳元痛得惊叫起来,忙将蛇打死,然后用嘴从伤口处往外吸毒液。刚吸了几口,他的手和胳膊就开始发紫,嘴也开始麻木,脸色惨白,呼吸困难。儿子见状,哭喊着跑到邻居家中报信。当医生到他家时,李炳元已处在休克状态,手肿得像一个大馒头,呈青紫色。医生迅速对伤口进行清洗包扎,在伤口周围涂上解蛇毒药粉,服用解蛇毒药片,并套上呼吸机。过了一会儿,李苏醒过来,随后急救车迅速将他送到县医院,被注射一针“抗蛇毒血清”。大约半小时后,他清醒过来,第一句话便是:“我真不该这么贪呵!”一个卑微而渺小的中国农夫,终于从现代版的《伊索寓言》引伸出一个新寓意了,仿佛他真的成了寓言的注释者。
鲁迅说:“人类究竟是可怕的东西。就是能够咬死人的毒蛇,商人们也会将它浸在酒里,什么‘三蛇酒‘五蛇酒,去卖钱。”(《而已集?“意表之外”》)然而,跟那些大贪官小贪官相比,李炳元不是囤积居奇的商人,也不是油光满面的食蛇族,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说的是心里话,不像古希腊农夫临死前还被伊索强加一个“痛悔”。圣哲卢克莱修说:“一人之美食可为他人之毒药。”李炳元相反,他想泡毒蛇为药,却成了毒蛇之美食。
我忽然觉得,也许真有一种超级而虚无的毒蛇存在着,它原本被关闭在玻璃坛中,然而那坛子终究像潘多拉盒子一样被打开了。这注定了类似西绪弗斯的命运。即使真有一个农夫捉住它,并试图将它重新装进那个坛子——然而事实上已不可能了。你可以说坛口太小,或者坛壁太脆薄,也可以说那蛇太狡猾,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双刃的悖论,一个沦陷与救赎相互循环的隐形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