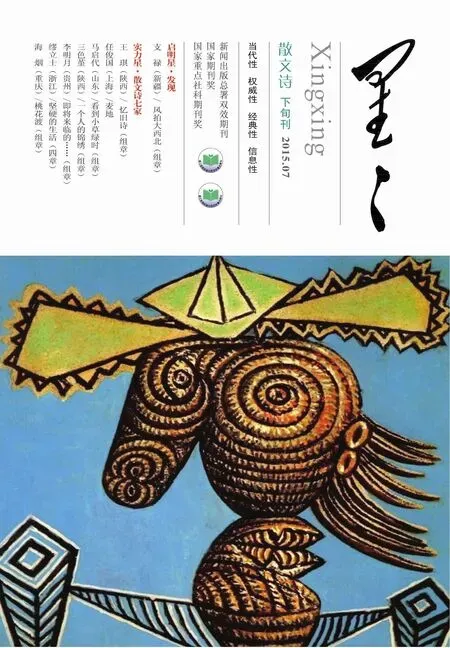高粱红了
2015-10-27徐晓
徐 晓
高粱红了
徐 晓
一
时候到了。我从远方赶来看你。
胶河的水已不再清澈,河岸却一如从前,像个挺拔的将士。
城楼上的枪眼尚在,而那些曾经鲜活的人事,随着战火的硝烟四散而去,也隐匿了声迹。
一波波晶亮的水纹在周身穿梭往返,一排排白杨树像死亡那般沉默和静穆。
终于,我于暮色时分抵达东北乡。
这该是你盛装相迎的时刻,那些深沉的红色,是你多年前的嫁衣。
而你在笑,你枝头上摇摆的穗子在笑。它们饱满而结实,像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娃娃。
你是该笑的,你那令人晕眩的姿色,覆盖了前来探望你的人的眼眸。
我的眼眸是疲倦的,亦是喜悦的。
于是我确信,脚步没有抵达的地方,就是一个迷;视野没有碰触的角落,就是遥远的梦。而那未知处的丰茂,永远在前方招手。
比如此时的你。
二
像北方任何一个村庄一样,平安庄隐于大地的腹部,静谧,古朴。
仿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安详地卧着。
而莫言旧居,就是一双洞穿世事的眼睛,寂寂地在时光流转中笑看人间。
是的,寂寂地。任凭屋外成片的林木枝叶,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不问世事。不谙世事。
喧闹的永远是人心。大师,一直躲在时光的暗处,抿着嘴笑。
刹那间,尘封在泛黄书页中的记忆开始绽放。
镌刻在儿时印象中的场景浮出水面。
朦胧中,一个受苦伶仃的瘦孩子,蹲在泥地里,捧着一块热红薯,惊恐地望着来来往往的大人。
那是黑孩,是豆官,是罗小通。是所有在苦难中长大的人们的童年印记。
越来越近了。我终于踏进了院子。
满怀虔诚。但我并不急于表达。
质朴的房门,简陋的居所,古旧的摆设。
一个农家小院,一口缸,一盘磨,一小块菜地。
几串红辣椒,懒洋洋地挂在墙上。
天地不言。
犹如美,一种稚拙不事张扬的美,陈旧的美。
被岁月淘洗得干干净净的美,与生俱来的美。
三
立于苍茫的田野,就像立于世界的中心。
有一只鹰倏地从头顶飞过,扑闪着翅膀,慢悠悠地飞过村庄,飞过田野。
它要到哪儿去呢?它从哪里来呢?是飞向它的家,还是它所向往的远方?
你看,不只是我,也不只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前赴后继地赶来看你。还有它。一只来自远方的鹰。
其实,世间的一切生灵,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会千里迢迢地赶来。
不论是乘飞机、坐火车、开轿车,还是坐轮船,亦或是自己走来,自己爬来,自己飞来,自己游来。
不需要你的同意,更不需要你的邀请。
他们到高粱地里,挑挑选选,掐几穗穗子带走,再到大师家的小院里,拔几棵绿油油的小萝卜,放进包里,再往边上随便一站,咔嚓几声,你便此生长在了他们的镜头里。他们的后人也会仰慕你,生生世世。
对你的情谊,都是自发的。因此你并不必背负人情债。
我想,你该是欣喜,还是悲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