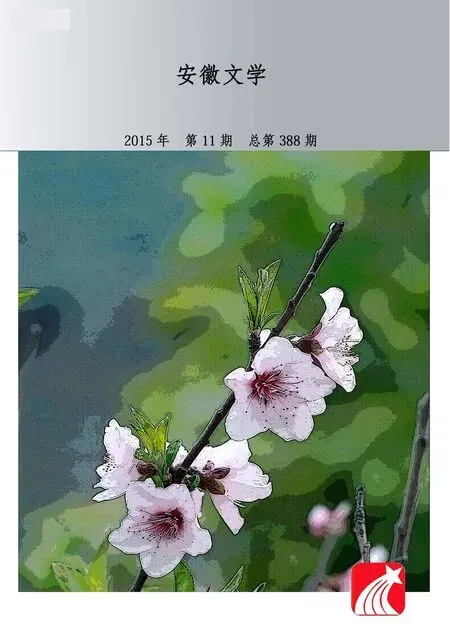福克纳意识流作品的开放性结构:长句的运用
2015-10-26刘蜀云
刘蜀云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福克纳意识流作品的开放性结构:长句的运用
刘蜀云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美国南方作家的代表福克纳以大胆的实验性手法将意识流小说创作推向了巅峰。本文拟以其两部意识流杰作《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为例,分析作家如何运用兼具连续性和包容性的长句来构建意识流小说的开放性结构,从而展现绵延不绝的内心生活之流。
福克纳 意识流小说 开放性结构 长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南方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深陷于传统与变革尖锐的社会冲突之中。美国南方作家的代表福克纳凭借前所未有的大胆手法和具有开放多元性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再现出那一时期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现实生活。其丰富的创作背景和多元的艺术技巧早已使他的意识流作品载入文学的史册,而其独特的开放性结构无疑也是使其作品大放异彩的重要原因。这种开放性特征无论在他的句子结构中还是意识流作品的整体叙述结构中都展露无遗。
一、题材决定长句的使用
在句法层面,福克纳复杂难懂、不断延长的句子如此引人注目,因而在为他赢得声誉的同时也招致不少批评。沃伦·贝克曾给他冠之以“一位极富独创性和多才多艺的文体家”[1]53的名号,但他也同时指出,“没有哪一位能与之媲美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像威廉·福克纳一样因为自己的文体而被如此频繁或严厉地批评过。”[1]53其文体导致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因其在语法、标点、句子结构等方面无视逻辑和规则所致。对福克纳而言,文体不过是作家用来达到其艺术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正如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时所说:“文体可以是变化之流动性的一部分……文体必须随着作家试图讲述的内容而变化。”[2]279
因此福克纳长句的使用是由其题材所决定的,即他所极力描摹的人物内心在绵延不绝的钟表时间中自由流动、彼此融合的心理状态。福克纳自己曾解释道:“……没有人是他自己,他是他的过去的总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将来的总和。而长句则是将他的过去,也许还有他的将来融入他现在做某件事的那一时刻的一种尝试……”[2]84这种“把一切都用一个句子来表达”[3]的尝试使得他能够“凝结某个瞬间,并同时探寻它的全部复杂性。”[3]他一直在试图表达内心超验的感受,描绘意识那种种联想性的、分析性的构成成分,而正是意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组成部分使现在这一时刻延伸到了无尽的永恒。
他努力的成果便是那冗长的句子,句子中包含了多种多样却又彼此关联的成分,例如对意识的对象的观察、记忆、推测、解释和修饰等等。到此为止,表面上看起来无穷无尽的长句也许是“作为小说工具的语言所最能接近意识本身的复杂瞬间”[1]62-63的形式了。在他的意识流名著《喧哗与骚动》中,对康普生家的长子昆丁的一段意识的描述对此做出了充分的说明。昆丁在圣诞节回家的旅途中遇到一个老黑人,当火车渐行渐远,他扭头凝望老黑人的身影时,不禁对黑人的行为方式陷入了沉思。
“列车拐弯了,机车喷发出几下短促的、重重的爆裂声,他和骡子就那样平稳地离开了视域,还是那么可怜巴巴,那么有永恒的耐心,那么死一般的肃穆:他们身上既有幼稚而随时可见的笨拙的成分也有与之矛盾的稳妥可靠的成分这两种成分照顾着他们保护着他们不可理喻地爱着他们却又不断地掠夺他们并规避了责任与义务用的手法太露骨简直不能称之为狡诡他们被掠夺被欺骗却对胜利者怀着坦率而自发的钦佩一个绅士对于任何一个在一场公正的竞赛中赢了他的人都会有这种感情,此外他们对白人的怪癖行为又以一种溺爱而耐心到极点的态度加以容忍祖父母对于不定什么时候发作的淘气的小孙孙都是这样慈爱的,这种感情我已经淡忘了。”[4]
昆丁自小生活在南方,黑人作为他家乡南方的一部分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他对黑人非常了解,也对他们有着某种深厚的情感,对黑人可悲的境地以及黑人和白人之间奇异的关系洞若观火。对黑人身上矛盾个性和处事方式的观察及分析全被囊括进了一个句子,而正是这个长句将昆丁过去数年来的体会、记忆与眼前旅途中碰到老黑人的那一刻连结了起来并糅为一体,于是“此刻”便延伸到了漫长的过去。
二、扩展意象的插入
在人物陷入沉思默想或是对故事情节进行阐释的时候,福克纳也会把幻想或是扩展的意象插入人物的思绪或是话语中的一个句子里。当这些人物对事件进行冥想,或竭力描述细节,或是提出一个又一个假设的时候,他们的迟疑和臆测则会为读者提供一个对现实本身的神秘莫测、难以理解的视角。福克纳的另一部意识流小说《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仑家的二儿子达尔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常使他能看透别人的内心,因而被周围人所憎恶,甚至被视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达尔通过自己的“内心之眼”对已死去的母亲的容貌的描述颇富弦外之音,“手”这一由遗容延伸而来的意象被赋予了生命和思想,因而产生了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感。
“它在枕头上像是绿锈逐渐增多的铜铸遗容,只有一双手还有点儿生气:那是一件蜷曲的、多节的静物;具有一种已筋疲力尽然而还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品性,疲惫、颓衰、操劳尚未远离,仿佛这双手还在怀疑安息莫非果真来临,正对这中止状态保持着支棱着犄角的、小心翼翼的警惕,认定这种中止不会久长。”[5]56
尽管福克纳的语词之流滚滚向前,源源不绝,有时甚至让人有接不上气的感觉,因而招致啰嗦的批评,但他的“语词链”在他分析入微、详尽缜密的文体中似乎自有一席之地。这一系列词语,以其特有的形式,非但不累赘,反而经过精心的排列,达到了一种累积的、渐进的效果。尽管看起来过长,它们却往往是高度压缩的表达方式。以长句为特征的所谓累赘迂回的文体并不会像有些人所宣称的那样,破坏叙述的节奏和重要性,相反,却成功地将经验的多个侧面呈现出来,并使意义以逐步、持续和更为丰富的形式揭示出来。
三、长句带来的阅读体验
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所展示的那样,有时长句中所包含的意义极其丰富,再加上晦涩难解,读者不得不面对一直要去搜寻和阐释真正意义的挑战。此外,令人目眩的句子长度常常令读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读者难以确定单独悬垂的动词的主语,或是一直重复出现的第三人称代词究竟指谁,后者在达尔关于他的兄弟朱厄尔的内心独白中十分典型。在小说《我弥留之际》第四十二章达尔的独白部分有一段关于朱厄尔的神情和动作的描写:
“他脸上又出现那种木呆呆的神情了;那种冒冒失失、狠巴巴、血气很旺、直僵僵的神情,仿佛他的脸和眼睛是属于两种不同木头的颜色,那种不对头的浅色和不对头的深色。……他已经走回到马身边去了,正在把马鞍卸下来,他移动时,他那件湿衬衫服服帖帖地裹在他的身上。”[5]171
全章出现了三十八个第三人称代词“他”,有的是指大儿子卡什,有的则是指朱厄尔,却从始至终都未出现朱厄尔的名字。读者只能根据前文提及过的朱厄尔的呆滞神情以及他酷爱马的特点来推测此处是对朱厄尔的描写。也正是透过不断重复使用的这个冷冰冰的代词“他”,读者才窥见达尔对深得妈妈喜爱的朱厄尔的嫉妒和仇恨,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提起,而长句中所包含的对朱厄尔神情和一系列动作的详尽的描写却又向我们展示出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朱厄尔的达尔对他十分关注的矛盾内心。
四、结语
总之,包罗万象的长句表面上仿佛在读者的阅读之路上设置了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障碍,而所有障碍事实上都指向同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形式和思想都保持流动和未完结的状态,可以说,一直处于运动中和未知的状态,直至(句子的)最后一个音节尘埃落定。”[6]福克纳运用长句所创造的连续性和包容性正是他意识流作品开放性特征的体现,他所追求的其实是一个没有停顿的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现在”这个瞬间,或是由一个瞬间向另一个瞬间的就如生活本身一样持续绵延却又难以察觉的流动。
[1]Warren Beck.William Faulkner’s style.Robert Penn Warren,ed.Faulkn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6:53,62-63.
[2]Frederick L.Gwynn&Joseph L.Blotner,eds.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M].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84,279.
[3]MichaelMillgate.TheachievementofWilliam Faulkner[M].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9: 286.
[4]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91.
[5]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56,171.
[6]John T.Matthews.The discovery of loss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Harold Bloom,ed.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The Sound and the Fury[M].New York: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