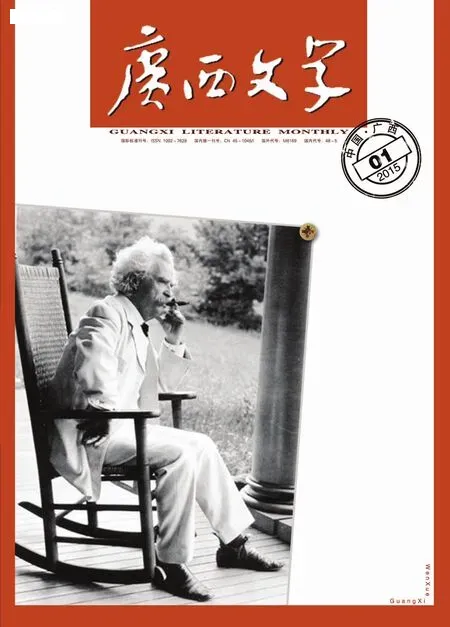两间风雨忆秦似
2015-10-22刘振娅
刘振娅/著
热爱生活吧!热爱文学吧!再不要徘徊,再不要低泣了!昂首高歌,迈步向前吧!
我认识秦似,要比给他当学生早得多。1953年,大哥叫我从家乡河南转学到南宁铁路小学五年级。这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作为优秀少先队员的代表和市里其他代表一起,到省政府见作家,接见我们的就是秦似。见作家,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那天,我们都穿得很整齐,男队员白衬衫、蓝裤子,女队员白衬衫、蓝裙子,佩戴红领巾和少先队委的标志。记得我是大队学习委员——三道红杠杠,好不神气!我们一个个天真活泼,朝气蓬勃。秦似对我们这些未来的小主人特别热情。开始,我们还有点紧张,规规矩矩地坐着,问一句答一句,过一会儿就无拘无束了。我们叫他秦伯伯,一个个又是拍手,又是唱歌,又是朗诵作品。我向他朗诵了我的作文《可爱的祖国》,他高兴得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连声说好,让我坐在他身边亲切地问长问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刚读完一个学期,大哥便又匆匆忙忙把我送回老家,连夏令营也不让参加。那时参加夏令营是有名额的,要经过层层挑选,南宁铁小总共推选两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又是去桂林。在老家就听人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很向往,不能去,觉得很可惜,也很无奈。我在家乡读完小学、初中,考上高中,直到1958年才又转学到桂林读高中。说也凑巧,1960年我考进广西师院(现在的广西师大)中文系,就有个副主任叫秦似。秦似这名字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甚至有点亲切感,因为他可是我平生所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呀。这些年我虽然没有再见到他,没读他的作品,可那年“六一”儿童节的记忆却历历在目。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莫非他就是我所见到过的作家秦似吗?是的,他就是那个秦似。听说还是因为写了什么作品受了批判,不让当省文化局长了,到中文系教书的。
不久,在开学典礼上我看见他坐在主席台一侧,不说也不笑,活像一尊菩萨。他胖,比别人占的地方宽,容易辨认。我觉得眼前的这个秦似和记忆中那个谈笑风生的秦似有点不像。后来,我又知道,他就住在离我们教室不到百米的平房里,我多么想去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朗诵《可爱的祖国》的少先队员啊!然而,我迟疑了,因为这时的我,已不是七年前那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年。1957年那场扩大化了的运动也把我这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卷了进去,在家乡,因为同情被错划的班主任受了处分,成了政治上“有污点”的人。自那以后,许多人用另一种眼光看我,对我失去了信心,认定我不会再有什么前途……倘若我去找他,他问我当年的优秀少先队员,这几年有什么进步,我该怎样回答他?我能说得清楚吗?假如我照实说了,他能理解我么?假如不能,彼此无话可说地尴尬着,或者言不由衷地敷衍几句,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不对他说实话,岂不是蒙骗老师?那样我会心安么?岂不又要增添一层愧疚?如此,倒不如压根儿不见,压根儿不说!大学四年,我竟一次也没有去拜访过他。我们离得这么近,但却始终隔膜着,没有任何思想情感的交流。印象中,秦似平时走在校园里,双眼常似开似闭,有一种睥睨的神气,令人不敢冒犯,因此,我也从来不跟他打招呼。

秦似写给作者的亲笔信
到师院与他最早的一次近距离见面,是在中文系学生所办刊物的编委会上。那时我是系《东风报》的编辑、院《大学生之声》的编辑兼美工、60级《汉语拼音报》的主编。那时候,除院刊《大学生之声》是毛笔字手抄的大字报之外,其余几乎全是黑板报。60级《汉语拼音报》,其实就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编辑的一块黑板报,特色是全用拼音文字书写,锻炼大家练习拼音而已。系《东风报》虽然只是一份黑板报,但在桂林市颇具影响,《桂林日报》刊发的不少好文章就是直接从这上面选上去的,从这块园地里还真走出了好几位广西著名作家。秦似很重视这份系报,他主张办出特色来,并鼓励我们说,不要小看黑板报,当年我做学生时就是从校办小报锻炼成长起来的。会后,我们查阅资料,知道秦老师十六岁在玉林读高中时就已经在当地报纸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参加编辑香港《循环日报》的文艺性副刊,读大学时担任学生会进步刊物《呼声》主编,1939年到贵县中学教书,做《贵县日报》副刊编辑。二十四岁的他,作为自由撰稿人向大报投稿,被夏衍看中,认为他“仿鲁迅笔法,可以乱真”,约他到桂林见面。他做了《野草》的编委,第二年任该刊主编。在中国文学史上,《野草》被称为中国杂文史上的一座丰碑,五个编委中夏衍、聂绀弩、宋云彬、孟超,哪个不是名震文坛的大家?秦似名列其中,应该是广西父老的骄傲。《野草》团结了一大批全国著名作家,并得到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的支持,成为它的撰搞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6年,秦似去香港继续办《野草》……了解到老师的成就,同学们对中文系的师资力量也刮目相看了:啊,原来我们身边还有这么有名气的老师!顿时增添了几分信心。
他给我们讲诗词格律和古典文学,时间都不长。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班讲《红楼梦》,堂上,突然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也没听明白他问我的问题,便站起来盯着课桌头也不抬地回答说:《红楼梦》的人物,我最喜欢三姑娘探春,她很有见识,有志向,是这群脂粉队里的另类。查抄大观园,那个狗仗人势,生怕天下不乱的林之孝家的仗着王夫人的势力,威风得很,姑娘小姐们都怕她,探春就敢当着王熙凤的面给这个奴才一记耳光,打得真痛快,真爽!我觉得就像六月天喝了雪水,真过瘾,真解气!这位三姑娘当时就能看出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单从外面是杀不绝的,多足之虫,死而不僵嘛,败就败在自己人窝里斗,多有胆识!当家理财也是一把好手。可惜她是庶岀,不受器重,她的出身决定她不能发挥作用。可见庶岀的未必就不如正出的,贾府那些正出的公子小姐,地位虽优越,有哪个能与探春比?……
正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发挥我的“探春论”时,感觉有人在背后偷偷拉我的衣襟。抬头看看,大家都用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冒犯了老师,便立即停止。再看看讲台上的秦老师,似乎并没有生气,他什么也没有说,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我就坐下了。我想,倘若做大学生时我能给他留下一点什么印象的话,那便是这次课堂提问了,有些怪怪的。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叫我,向我提了什么问题。过去曾听说秦似批评人很不讲情面,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就轻易地摆摆手让我坐下了。
大学毕业后,我又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而又艰辛的路。走出校门,便被送到农场改造。“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学校暂时同意我回到桂林,打算把我们这几个在1964年毕业时按“反动学生”处理的60届学生跟“文革”以来囤集在学校尚未分配的62届、63届一同分配。那时已经是我到农场改造的第五个年头,看不到任何希望,前途渺茫,心情黯淡,又身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钩虫病、贫血,身体十分羸弱,又值动乱,平时就蜷缩在宿舍里看书,除了到指定的地方劳动之外,不参加任何活动,也不与别人交往。
有一天,一位同学到我的住处来告诉我,他到中文系去看批斗会,所有有名气的老师都被带到台上,一个挨一个地低头站着,一个“学生”上到台去,二话不说,依次照着每个老师的脸扇一耳光。扇到秦似的时候,他反抗了,瞪着那“学生”说:“有理说理,你为什么无故地打人?” 那“学生”说:“你敢跟我说理?再赏给你一记耳光!”听到此,我的心笃地沉了下去,感到一阵眩晕,我的那些被称作是“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们都在遭难呵!我想到那位年逾七旬,头发脱落成为童山的系主任冯振教授;想到那眼睛起了翳,行走不便还在编《中华词典》的王永华教授;想起那位身体瘦弱、治学严谨的彭泽陶教授,那位精力充沛,在课堂上引证外国文学经典如数家珍的贺祥麟教授,还有那位被埋没在资料室里的著名老作家林焕平教授……想到许许多多我熟悉和尊敬的老师。这些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着教育这块园地,如今却在忍受着凌辱!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此刻,我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悲壮的敬意,我从此对秦似那睥睨的神气肃然起敬起来。在大家都默默地忍受暴虐和无理时,他却反抗了!尽管这反抗招来的是加倍的凌辱,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识时务,但他毕竟出声了。
人们常说,一个长期在逆境中生活的人,会变得桀骜的。从此以后,只要在校园里看到秦似,我都主动地迎上去跟他打招呼,向他问好,表示我的敬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给老师一点微弱的安慰吧。他仍然很胖,冷天穿一身蓝色中式衣服,又宽又大,走路的时候仍然目不旁视,两手交叉在袖筒里,托在胸前成一个“U”形,眼睛半开半闭,似乎有点睡意朦胧。每当我向他问好时,他便睁开双目注视我并向我点点头,但彼此从不停下来交谈。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祖国的春天。1978年,我那位被错划的班主任得以平反,重新走上教学领导岗位。第二年,我也收到县团委签发的红头文件,大意是:刘某某同志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同情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师某某某被开除团籍,现决定撤销其处分,恢复团籍,恢复名誉。1980年,自治区教委、计委、人事厅等三个单位下达文件,为我们这批学生落实政策,我得以平反,享受到与同届大学毕业生转正定级的同等待遇。我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觉得有很多话要说。我想到了那个在暴虐面前要跟施暴者论理的秦似,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还填了一首词《永遇乐·赠秦似老师》:
遥寄尺书,中原赤子,述师徒谊。二十三年,风狂雨骤,打得苍松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应不负苍天意。到中年,忧愁总怕,等闲岁月归去。炯阳出谷,驱寒送暖.普照神州大地。“四化”征程,中华鹏举,更爱春光丽。日新月异,万千气象,一派昂扬意气。看高天,穿云破雾,百翎熠熠。
这首词用普通话声韵适律,这在当时还很少见(当时写格律诗通行用平水韵,填词用词林正韵,允许写旧体诗“双轨制”是近些年才逐渐被接受的,即可以用“旧韵”的声韵适律,也可以用普通话的声韵适律,不过要注明是用“新韵”)。我当时只是觉得把隔膜了二十多年想说而又终于没有说的话说了,感到轻松,却没想到他会回信给我,并且写满了四张稿纸。他在回信中说道:
我很追悔,为什么当年在学校时,我竟没有伸出一个同情之手!没有一声必要的慰问。但的确如你所说,即使我那时了解到你的情况,也只能是爱莫能助……倒不如
“相忘于江湖”反倒干净。但你那时曾对我这个老师有所理解,有所爱护(哪怕仅仅放在心里),有所怀念,这使我深深感动。我为你这些年来的遭际暗洒一掬同情之热泪,为你今天的得到重新在祖国明媚的春光中生活而万分欣慰!希望你热爱生活吧!热爱文学吧!不要徘徊,再不要低泣了!昂首高歌,迈步向前吧!
从信中我还得知,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出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其实就三人),他随同巴金从瑞典访问回来,已经直接晋升为教授(自他1959年调高校任教,二十年间一直被当作无职称无级别的普通教员使用,现在总算还他一个公正)。1981年三联书店隆重出版了聂绀弩、秦似的杂文集,是对这两位老作家的重新肯定,被人们看作是文学界拨乱反正的一项成果。“文革”后他身兼多职: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广西作协副主席、广西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西语文学会会长、广西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等。我觉得他最倾注心血的还是在广西的语文教学上,用功最勤的还是他的教学、研究与写作。办刊物,出杂志,都要耗费他许多精力。虽然他是个大忙人,但对我寄给他的词却改得很仔细,不但指出所有不当之处,还一一作了旁批,并且说:
你有诗人的气质,也善于遣词造句,可惜对词牌不大熟悉。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来南宁,我可当面同你讲讲。又,首先要会判别平仄,倘你会南宁话,这事不难,若只会北方话,就难一些。我希望你不畏难,学下去。当然,也可写新诗。
那时,他创办了一个在省内乃至全国都有相当影响的刊物《语文园地》,每期都寄给我,我也在贵县语文界、文化界极力推广。为了让我学诗,他还寄赠了他的《两间居》诗集和《当代诗韵》等书给我。
老师的鼓励对我是极其珍贵的,对我这个在坎途上生活了半辈子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理解、关爱更值得珍重呢?以往的遭遇使我变得自我封闭,向来不大过问本职工作以外的事。恢复高考后,学校让我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把紧教学质量这一关,千方百计提高升学率;1981年又被推选为贵县第一届人民政协委员,分在文教委员会,这才扩大了我与社会的接触面,很自然地促使我必须写点东西。贵县政协文教委员中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诗人,如黄飞卿、梅竹公等。梅先生的旧体诗在广西都是一流的,要跟他酬唱应对,也必须得拿出几首登得大雅之堂的诗作,逼使自己下功夫学习。前有秦似老师的鼓励,后有跟着梅先生的实践,我的旧体诗写作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打下的基础。
可就在这年冬天,我的腰腿痛发展到双腿抽筋,不能行走。有一次,眼见晒在窗外的棉被被大雨淋湿,近在咫尺,却无法爬过去将它收回。许多好心的同志担心我生了“什么”,劝我早到医学院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我知道这“什么”就是“癌”的讳语,想到刚刚平反,正是为“四化”出力的时候,却得了这个病,难道我真的如此命苦?第二年夏天,我只好把两个尚小的孩子托付给工友照看,爱人陪我来到南宁。那时候广西医学院(今天的广西医科大)附属医院的床位十分紧张,住的多是危重病人,像我这种疑难病症只好每天排队看门诊,许多人即使得到留医通知,至少也还要等上半月甚至更久。我们人地两生,吃住都十分困难。开始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为了赶去挂号,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起床,胡乱在小摊上吃点东西,便去挤早班车。就这样,赶到门诊部,挂号的队伍早已排了几十米长。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然后又要排队候诊,排队交钱,排队拿药,排队打针……奔波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的病因没有查出,爱人也累得几乎要病倒了。我也曾想到在南宁的同学和熟人,可又觉得生着病到人家家去太麻烦,况且这么多年没有联系,突然上门,又是这种情况,人家乐不乐意接待呢?还是谁也不要打搅吧。
一天上午,爱人扶我搭公交车,由于行动不便,挤了几次都上不去,我们在马路上徘徊着,真觉得有点像叫花子。刚好那站牌旁有个交通亭,我突然想起借他们的电话打给秦似,试试看能否打得通。秦似当时是西大中文系主任,区政协、作协副主席,这种人物知道的人多,但一般不肯轻易接见客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请西大总机把电话打到他家,居然打通了。话筒里传来了老师那很重的口音,当他听说我来到了南宁,显得很关心,他耐心地听我讲了情况之后,便说:“我说呀,你能慢慢行走吗?你还是让你爱人陪你到我这里来,你来,我给你想想办法,或许能给你帮点忙。”接着,他把他的住处、走法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约我们午饭前到达。
我们找到他的住处,已经快晌午了。只见他穿件背心在楼前的花圃锄地,听到我的呼叫,他汗流浃背地迎了过来。老师老多了,而且行动也有些蹒跚。我说:“这么大太阳,您这么大年纪还锄地?”他说:“我活动活动筋骨,二来也等你们。你们看见我在这里,不是好找些么!”
老师把我们让进屋里,一一向家人介绍。他显得特别高兴和激动。师母陈翰新和保姆都在忙着做饭,他又把刚从北京回来的女儿王小莘叫来,吩咐她去把我读书时的年级主任也请来,自己一面又要蹬自行车去再买些菜来。刚好小莘在北大跟爷爷王力教授进修期满,回来时带了两只烧鸡,吃饭时秦老师不住地往我碗里夹,一边招呼着:“这是你家乡的烧鸡,你要多吃点。这么多年,回过老家吗?”我说:“烧鸡是我家乡的特产。记得小时候坐火车,一到漯河站,乘务员就要介绍。这烧鸡又便宜,味道又好,旅客们经过这儿,常要买上几只带回去送人或自家吃——不过,一九五八年以后就再没见了。”
“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的。要是前几年,你就是来了,我也拿不出你家乡的风味特产招待你!”他说着,显得很开心,一面又招呼我爱人:“小苏哇,你可是要下力气的哟,一定要吃饱。吃饱吃好了才好照顾病人。你们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千万不要拘束。”
饭后,他特意为我写了封信。那时他的弟弟——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王缉平教授出国援外去了,他便请他的弟媳——广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徐慧蓉医生帮助我。当他得知我病中还在读辛弃疾词时,又特地上楼,从书房找出《稼轩词编年笺注》,结合声律给我讲解我提出的问题。我见老师累得满头大汗,精神很疲倦,知道他有午睡的习惯,不好再让他讲下去,便告辞了。
这次会见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仿佛又看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热情、亲切、富于人情味的作家秦似。人世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碳难,秦似是“文革”后最早给我雪中送炭的一位长者!
检查出是长期劳损引起的痉挛,我和爱人都放下心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终于康复了,真是打心底感谢秦老师。1983年初我调到广西教育学院任教。家搬到南宁,离老师近多了,可又迫于新到一个教学环境,不得不特别下功夫,总觉得有许多想读的书来不及读,许多想做的事来不及做,时间特别紧,竟很少去专门看望老师。这年春,桂林市园林学会的张大林先生到南宁来开会,与我谈起桂林市的园林建设,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在各风景点增加石刻。他说:“广西有自己的人才,在各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应该留下他们的墨迹。像王力、秦似父子,在文学界、语言学界就很有影响,传为文坛佳话。趁他们都健在,请他们为桂林风景区写诗题词,刻下来,流传后世。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建树。历代都有自己的建树,风景区也要不断丰富新的内容,不能光看古人的。”应他的委托,我专门去找秦似老师,他很爽快地答应写一副对联并即刻与父亲王力联系。随后王力教授寄来了他为桂林风景区撰写的长联,这便是那副受到广泛赞誉的著名的为七星公园月牙山上的小广寒楼撰写的138字长联:
甲天下名不虚传,奇似黄山,幽如青岛,雅同赤壁,佳拟紫金,高若鹫峰,穆方牯岭,妙逾雁荡,古比虎丘,激动着倜傥豪情,志奋鲲籴,思存霄汉,目空培鹯,胸涤尘埃,心旷神怡消块垒;
冠寰球人皆向往,振衣独秀,探隐七星,寄傲伏波,放歌叠彩,泛舟象鼻,品茗月牙,赏雨花桥,赋诗芦笛,引起了联翩遐想,农甘陇亩,士乐缥缃,工展宏图,商操胜算,河清海宴庆升平。
张大林先生如获至宝,他是一位有眼光、重承诺、负责任的老文化人,经过他和桂林园林局的努力,王力、秦似父子的两副对联都由桂林园林局刻在风景区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二位老人会那么快就相继去世,他们的墨迹竟这么快成了遗迹!
秦老师笔耕很勤,他不喜欢懒惰的人。虽然他是一位成就蜚声中外的作家,但对学生坦率、热情,不拿名人的架子。秦似的古道热肠在我们同学中广为传颂,我的许多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学常求他赐稿、题词,无论报纸刊物的级别是高是低,甚至一份县报、校刊,只要是鼓励青年人上进的,他都有求必应。为此,也遭到一些非议,有人说,一个那么有名气的大作家,这样做有失身份。其实,这正是老师可贵的地方:坦诚、率真,有一颗不知势利为何物的赤子之心。
1986年3月,我到西大办事,顺便去看望他。他正忙着审阅稿件,精神还挺好的,只是吃饭的时候,师母专门给他煮一瓦煲黑米饭,说是玉林的特产,对糖尿病人有好处。此时,师母已从广西大学附中校长的岗位上退休,女儿小莘早已调华南师大,身边的小外孙也准备跟随父母去广州读高中,家中只剩一个十几岁的亲戚照料他们的生活。我担心两位老人会感到孤独寂寞,便安慰了几句。师母笑着说:“他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亲戚和学生们常来看他。只是他觉得年纪大了,怕要做的事做不完,会感到遗憾。”老师也说:“平常我没时间接待你们,星期天带孩子来玩吧。我不专门为你做吃的,我那侄儿侄女们也都要来。”
是啊,一个醉心于事业的人,是永远不会感到空虚和无聊的,这是他的幸福,也是他的悲哀,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不及常人的地方,我这样想。临走时,我说:“学生要出远门学习去了,不能常来看望您。十月吧,等您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南宁的同学来给您祝寿,到时候您给自己放一天假,我们好好地吵吵您!您不怕吵耳朵就行了。”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那么爽朗、开心。
可是,我万没料到这次拜见竟成了永诀。老师竟没有活到十月,没有过他的七十寿诞便匆匆地离去了。
在为老师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见师母和小莘都憔悴多了,唯一能劝慰她们的话就是节哀。
站在老师的遗像前,我想得很多很多。他依然是那样质朴、自然,那专注的神情似乎在品味着这宏深恣肆的人生,那抿着的双唇似乎又想开口说些什么。他还能说些什么呢?人去了,一切属于个人的恩怨是非也都结束了,千秋功过,任由后人评说。然而,他对人类的贡献,他在文化教育事业的成就、建树却是不会被岁月之河冲刷去的,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些。他不枉为人一世,他活得有价值。
我和我的老师、同学们在他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深鞠一躬。三十二年前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童声合唱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又回响在耳际: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三十多年间,我们都走过一段漫长曲折的道路,然而,对祖国的爱,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专注却是更执着了。我和老师曾经隔膜过,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融化了我们心中的冰垒,恢复了师生间的信任和往来。人啊,多么需要友爱和理解,坦率和真诚——没有性别年龄的界限,没有尊卑贵贱的鸿沟,没有权势对心灵的污染,也没有陈规陋俗的偏见……
老师去世后,叶圣陶、夏衍、林默涵、胡绳、吕叔湘、骆宾基、秦牧、陈残云、冯英子、周而复、公刘、端木蕻良、黄秋耘、舒芜、方纪等国内著名作家、学者,还有部分海外知名人士纷纷发来唁电或写悼念诗文,作了高度评价。这年冬天,广西师大和广西大学的校友们发起倡议,集资出版秦似纪念文集,这些早已实现。故乡博白的父老乡亲们还在王力的故居建了王力、秦似父子的纪念馆,老师写给我的那封信也被当作馆藏文物加以收藏。
老师生前出版的著作已达三十种之多,而且涉足领域广,形式多样,不愧为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艺术家、学者、教育家。
为了更全面地搜集整理老师的著作,不使九泉之下的亡夫有遗珠之憾,在老师去世后的一年多内,师母和他的助手到自治区图书馆查阅文献,每天一大早从广西大学乘公交车到区图书馆,到下午图书馆关闭才回去。那时区图书馆还在人民公园内,两处相距很远,其文献部收藏有大量的古籍和解放前的报纸杂志。师母和他的助手要从这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出老师发表的著作,无疑披沙淘金,那得要多大的精力和毅力啊!那时我正在撰写《中国历代奏议选》,也经常要到文献部查阅古籍,深为师母的精神感动。教育学院离人民公园较近,我想邀他们到我这里吃午饭、小憩,师母谢绝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宁可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米粉,填饱肚子,又继续工作。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此执着地去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我心中十分钦佩,也十分心疼,有时我也会煮点骨头汤什么的带去给她,略表寸心。在他们的努力下,老师尚未结集出版的五六百篇各类文章,包括杂文、散文、散文诗、新诗、小说、文学评论、学术论文、翻译作品等,以及数百首旧体诗词,得以保留,为后人研究秦似留下全豹,从而也可以看出秦似在文学创作及语言学、音韵学、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学等方面的建树。我为老师有这样一位忠贞的伴侣而欣慰。
老师晚年把自己的居舍叫“两间居”,他的一些著作也以此命名,如《两间居诗词》《两间居诗词丛话》。于是有人攻击他,说:秦似这个老头儿在用鲁迅笔法发牢骚,他嫌自己的房子小了,连书名都叫两间房子居。我觉得这种附会实在浅薄可笑。我理解“两间”就是天地之间,即人间。韩愈《原人》说得明明白白:“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鲁迅也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诗句。
有一次闲谈,我即以此意请教老师:“五柳先生诗云:‘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既然‘两间’就是人间,您为什么不干脆把自己的居舍叫人间居而叫两间居?也免得别人产生误解。好在现在已经不时兴深文罗织了,不然又会给您扣上一顶‘不满’的帽子。”
老师说:“你说的也不无道理,但你并没有完全弄明白我所说‘两间’的含义。‘两间’也不仅是天地之间,说开去,生死之间、成败之间、荣辱之间、是非曲直之间、进退之间、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取舍之间……人间万事,无一不可构成‘两间’。人生天地之间,随时都会面临‘两间’的选择,这是人生的一个大课题呀,做好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大是大非面前,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义面前,有关个人生死荣辱面前,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做出正确的抉择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有的人一念之差便沦为千夫所指,身败名裂,万劫不复,不能不慎重啊!”
到此时,我方明白老师“两间居”的深刻含义,这是他对自己的砥砺和鞭策,也是对我们每个后辈学人的砥砺和鞭策。
从老师的谈话中,我感到深深震撼的是两个字:气节!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应有的那股气节!浩浩然充塞于天地之间,书写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