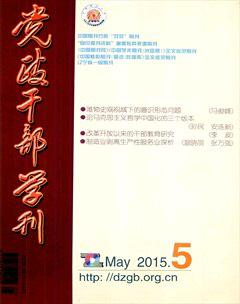优秀传统文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2015-10-21程晓峰
程晓峰 金 钊
(1.湖南大学,湖南 长沙 430012;2.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 沈阳 110004)
一、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1]13。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选择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自己的道路,建立文化自信,就必须重视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资源。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澳门大学时曾着重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文化自信之所以能够成为建立 “四个自信”的基础,建立文化自信之所以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深刻的经验积累和价值积淀,代表了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是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精神信仰和行为准则。概括起来讲,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竞争力。
要依托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就需要准确把握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具备长久生命力的历史根基。一方面,从先秦延续到明清,今天在中国还普遍存在的亲缘社会形态,是优秀传统文化扎根、生存并不断汲取营养的重要社会载体;另一方面,一代代的文化巨匠和思想巨人,以其卓越于常人的智慧编写的经典著述,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本载体;再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它既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需求相契合,又以清晰而准确的概念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认识世界、追求真理的成果。“两个载体、一个核心”,共同构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根基,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历史根基,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有源之水、有根之木,我们才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坚定自身的价值追求”[1]13。
二、传统亲缘社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载体
任何一种文化,从本质上讲,都是人们现实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反映。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从我们这个民族特殊的实践活动中来,并形成了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这种特殊性,从根本上归结于中国传统社会构成形态上的特殊性,也即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本维系因素的社会形态。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对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有过这样的论断,即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经历了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的转变,而社会形态的转变必然带来与之相应的文化的转变。恩格斯就曾以公共权力的出现,作为氏族血缘社会组织被破坏的标志,他关于社会发展的论断认为,国家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后,各种新的权力机关、新的公职都设置起来,尤其是一支维护新生国家的军事力量成为必须[2]。这些从属于政治的公共权力出现后,国家的构成及其治理,就可以超越一个血缘族群的范畴,在不同的地域实现。然而,正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史在世界史的总趋势之中,亦并非依样葫芦别无个性;相反地,它在一般的合规律的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合规律的运动路径,在思想领域里更有它的生成和变革的传习,有它自己创造的特别语言文字,以及有它的处理人生与变革现实的特殊方式”。[3]由此,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了解它的思想认识,并将其作为当今社会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的精神资源时,就必须把握好这种特殊性。张光直先生也强调,“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时,常有这样一条法则:在古代王国文明形成过程中,血缘关系渐被地缘关系所取代,政治的、地缘的团体占的成分比亲属占的成分越来越厉害和强烈,而亲属关系则日趋衰微。这是根据外国古代史所得的经验作出的结论,用它来看中国具体的史实似乎很合理,然而是错误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转变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是加强了,即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4]。
可以说,以亲缘为社会基本维系因素的传统社会形态,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在当今社会依旧普遍存在。著名社会学家郭于华十分关注亲缘关系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顽强存在,她曾指出,以中国的情形来讲,亲缘作为一种生物性并且是社会性的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形式或象征体系是无所不在的,它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地或潜在地发生作用,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模本。[5]50这种社会构成形态在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是:
从政治层面,也即宏观层面来讲,特别强调“大一统”观念,这种“大一统”既包括国家在管理制度和执政范围上的统一,也包括一个族群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精神信仰。在这个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最具有国家统一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亲缘社会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化认识和价值追求,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的。我们知道,传统社会基本是靠亲缘维系并形成了一个个的宗族组织,亲缘关系是超越个人和小家庭之上的,它使一个个单独的社会个体(个人和家庭)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保证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连续发展。而社会个体对亲缘社会的依赖,又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群体同聚意识”[5]50。 而传统政治社会建构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之上,并依托亲缘因素维系和管理社会,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泛血缘、泛亲缘的社会。[6]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使我们这个民族在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就以同根同祖的理念在幅员广大的地区内建构起社会管理组织[7]61。而在司马迁编纂《史记》的时期,同根同祖观念就以十分稳定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成为人们的既有认识。这种观念放置到政治社会,群体认同意识就顺理成章地转化并表现为国家认同、国家统一意识。在中国历史上,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为标志,很早就形成了对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并逐渐凝练为绵延至今的爱国主义精神。摒除“大一统”思想最早提出时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初衷不言,这种认识,首先强调要“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也即从通观的、整体的角度去把握整个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的各个有机构成视为一个统一体,当然包括将整个国家治理结构视为一个统一体。其次,选择契合这种整体认识并能强化这种整体认识的文化观念,作为全体社会的思想行为规范。贾谊在《治安策》中就说“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之所共闻也;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治安策》)。也就是说,只有选择了契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思想,才有可能指引整个社会积极向前发展。可以说,族群归属意识、文化认同观念、国家统一追求已经成为建构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我们在当今社会建立属于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自信,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尊重文化形态的多元性,使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从社会层面,也即微观层面来讲,特别强调伦理亲情观念。伦理观念,是自然存在于亲缘社会的普遍性观念,它以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体现为带有某种特定社会属性的称谓关系。以“父”为例,殷墟甲骨中的“”字,意为手持农具进行劳作的男子,《说文》则讲“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说明,“父”这一称谓,已经蕴含了其在某个亲缘群体中所具有的管理权力以及承担的社会职责,其他成员也以其德行为表率,尊重并遵从于家长的领导。也就是说,伦理观念,自然的包含了一个社会应该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提倡的纯粹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不主张绝对的人人平等和契约关系,而是在社会身份、权利义务的区分中带有一种属于中国文化的温情。
首先,它体现为基于血缘的尊重生命意识。如在我国古代司法领域长期存在的 “亲亲互隐”观念,其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亲情和伦常[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尊崇人性、注重人伦、珍视生命的认识。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亲缘、宗族是个体情感的依附和归宿,也是基本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如果法律过于强调应然状态的正义,则有可能因为对某种社会价值的追求而戕害传统社会运行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被写入国家法律,这不仅和现代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相契合,而且在我们国家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情感诉求。
其次,它体现为源自亲缘的社会稳定力量。传统社会建构在亲缘关系基础上,并顺着亲缘关系的脉络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一般社会职能在一个广义的亲缘关系网络内基本都可以实现。当然,社会职能的实现过程,依赖的是亲缘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费孝通先生就明确指出,中国是依靠社会发展所累积的经验,也即“传统”来运行的礼治社会。[9]传统中国社会,因此得以长期稳定地运行和发展,中华文明也成为不多的没有“断流”的古老文明。需要强调的是,亲缘社会所具有的稳定性力量发展到现代,并没有因为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冲击而趋于瓦解,而是和后者更加密切地交融在一起。郭于华在考察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时曾指出,这种 “既无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又无人员的整体性重组的独特的乡村工业化道路”,是一种“亲缘与业缘交织融混”的社会关系类型。[5]50可以说,传统亲缘关系在社会进程中并没有显得落后,反而为现代社会关系类型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选择。
再次,它体现为超越社会规则(包括法律)的情感粘合。因为对亲缘关系的重视,传统中国社会既不像成熟法治社会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对立”,也不可能像早期国家缺乏成型的社会规范而频繁爆发战争。它在遵循来自传统的经验和规范时,时刻带有来自亲缘的温情。虽然诸多法学家对中国的“人情社会”特性有颇多诟病,但不可否认,一个保有亲情温度的社会,才可能是人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理想环境。尤其在物质生活不断富足的今天,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将日益变得重要。以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的“居家养老”模式为例,某地区的相关法律不仅规定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更明确地对子女的赡养扶助义务作出了规定。诚然,“子女赡养义务”不仅应该成为法律义务,更应该成为“居家养老”制度中的重要环节。完善居家养老模式,不能只看我们在硬件上做的多么完备,更应该提倡子女尽孝。这种认识,不仅有着坚实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基础,而且它也将使现代社会的养老制度带有更加充分的家庭温情和人文关怀。
概言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建构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中国社会,是传统文化扎根的土壤、成长的载体,这一特性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进程中也没有被消磨,而且可能长期稳定地存在。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就要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找好社会载体,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和理念,与中国社会固有的生存模式、生活样式、思维方式相结合,这样建立起来的自信,才是接地气、有底气的自信。
三、中华文化经典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是我们先民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总结、生存智慧精粹。当今社会,“无论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抑或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都是要以文化为载体的。而经典文化作为其中的骨干部分,永远都是文明发展的根基、创新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10]。然而,要准确认识、接纳先民的智慧和经验,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的接轨,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就要求我们重视中华文化经典。
什么是经典?《文心雕龙》曾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也就是说,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强大的精神力量,含有不会磨灭的美、伟大的情感和信仰的高度,它们代表着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价值趋向”[11]。中华民族几千年,从先秦以至明清,历代哲人都不断的以时代先觉者的姿态,将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书之于简策,传之于后世,并将其视为一种使命,《左传》就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由此,中华文明的火种才得以绵延不熄,成燎原之势,经典成为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载体。可以说,没有了这些文本,即使我们先民的智慧再深邃、再精道,我们都无缘与闻,甚至整个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都有可能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经典之所以能够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源自经典本身所具有的特性。
1.中华文明经典著作在形成时,就提出并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本源性。任何一种观念,都产生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但是经典所承载的认识,并不严格受时代因素的局限,而是超越了时代,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一位西方学者就指出“经典著作乃是在每一个时代都具有当代性的书籍”。经典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性,从源头上取决于它所关注并回答的社会问题的根本性。中华文化经典,同样具有这样的特性。钱穆曾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一民族或一国家所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线相承’,‘传统不辍’”,而且很早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已经以“融凝为一”的观念,看待与思考“国家”和“民族”问题。[12]以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儒家经典《论语》《老子》为例子,它们都十分关注早期中国应该如何治理、华夏族群应该以什么作为基本社会规范的问题。《论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老子》则提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也就是说,在孔子和老子这些先哲看来,最适合中国社会的治理法则和社会规范是“道德”,是仁义礼智信等一整套伦理价值规范。他们这种认识,正是建立在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准确把握上,加之亲缘社会在中国稳定且长久的发展,《论语》《老子》所提出的国家和民族治理方案,就具有了跨越时代的意义,成为了属于和适合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即使在当今社会日益多元、构成要素日益复杂的情形下,我们依旧不能忽视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和观念的强大惯性,更何况这些观念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就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种启示和启发,正来自传统经典所承载的先哲智慧。
2.中华文明经典著作的阐释和发展,无不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也说明了经典的知识体系本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一种观念被记录并形成文本之后,它能否成为文化经典,就看它在阐释和发展过程中,能否对新的社会问题作出适合当时社会需要的解答。中华文明经典著作的形成,也经历了这一历程。以《春秋》的编纂为例,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春秋》一书,寄托着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挽救世风、维护周礼的强烈愿望。而在汉代武帝时期,面对汉初以来的社会发展累积的问题,董仲舒认为“《春秋》解释历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中解释出能运用于现实的,具有超时间性的价值理念,因此,凡是有助于昭示从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现实社会起着统帅与驱动作用的社会价值理念,如仁义礼智信等,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史料都可以选取”[13]。而在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则直接组织参与对 《周礼》一书的诠释,并从中“梳理出一套理财的理论以作为变法的根据,并作为回应反对派的思想武器”,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周礼》中所包含的制度和思想资源,能为后人的政治实践提供某种启示”[14]13-17。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清代,著名学者秦蕙田著《五礼通考》,钱穆评价他说“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15]。清末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则私淑秦蕙田,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儒家经典用于经邦济世,挽救清末社会发展的颓势。
可以说,经典形成的历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经典自身具有巨大的诠释空间,其知识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华文化经典,则在范围上涵盖了政治、哲学、文学、历史、宗教、道德、经济、教育、礼乐等等。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经典见仁见智,总能从其中寻求到解决时代问题的启示。加之,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并拥有诸多文化经典的民族,社会发展到今天,它们依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高度重视经典的历史价值,充分挖掘经典的时代价值,“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6]。
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经典关涉问题的本源性、诠释空间的巨大性、知识体系的包容性,以及经典诠释要紧跟时代步伐的要求,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对中华文化经典的文本进行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所谓“创新”改造。近年来出现的肆意歪曲经典、割裂经典、娱乐经典的文化现象,不仅说明我们当今社会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经典应有的尊重和怀有敬意的传承,更在根本上说明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华文化经典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方面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我们全社会应该形成一种正确认识经典、充分尊重经典、积极阅读经典的文化氛围。李克强总理已经明确指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学艺术……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我想,这里的“书香”,应该包括也必须包括中华文化经典的魅力和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中华文化经典的核心价值观念,紧紧围绕当前的文化发展情形进行创新,才可能建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四、传统价值观念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它不仅为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源源不断地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具体可行的办法,而且它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信仰,并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认识世界、认识自身、完善人的发展的价值观念。有学者就明确指出,中华文化在其开创时期,就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都是面对着现实的人生、社会的问题而传承;都是通过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探讨体验而加以传承”[17]407。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从其产生到发展,都是一代代人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具体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作观察、体验、思考、实践的活动。经过这一过程所沉淀下来的,就是最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最符合中华民族思维习惯、最符合中国人民心理诉求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这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就必须从根本上触及并接受传统价值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认识传统文化,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面,我们就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来了解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
个人层面,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提倡修身养德。也即,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十分注重个人的德性修养、身心修养的。这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华文化是属于“人”的文化,是关注“人”的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徐复观就曾指出,对人性的认识和探究,不仅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主干,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17]2。 对人的认识,实际上包含了几个方面,即人对世界的认识,人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人对自己如何更有意义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认识。先秦时期,《庄子》就讲“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超越自己日常生存的狭小地域,去认识和思考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以至于他们最后将这个超越个人、涵盖广袤的认识对象称之为“天”。“天”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提出,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形成了将人类自身、将生命个体放置在整体世界中去考察的思维习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先民充分认识到了生命的渺小和可贵,从而对人类的生存世界有一种敬畏。他们也认识到“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破坏了这一基础,就会损害人类本身”[18]45。从而,人们希望遵从而不是违背世界的运行规律,也即传统文化中的“道”,来实现自身的有序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中华文明将个人放置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去考察,这种对天道的遵从、对个人人格的提升才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 “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的自由和自觉。
由此,传统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清晰的轨迹:人们不断地认识“道”,不断地提升自身素养来符合“道”的要求,希望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北宋思想家程颐就讲“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 中正而诚,则圣矣”[19]191。 至于具体的修养功夫,则是“孝其所当孝,悌其所当悌,自是而推之,则圣人而已矣”[19]318。这就要求每个人在现实中能够积极遵从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体社会的发展中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实现人生价值。
社会层面,传统价值观念特别强调伦理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述及,传统亲缘社会,是以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得以产生的最早土壤,得以延续的基础载体。在长期的发展中,一种奠基于亲缘社会的伦理观念逐渐稳定下来,并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运行规则。一方面,亲缘关系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的重要纽带,它直接促生了以“孝乎唯孝,友于兄弟”(《论语·为政》)为代表的家族伦理价值观。以“孝”这一价值观念为例,传统社会之所以如此重视“孝”观念,就在于它能够维持宗族血缘关系的稳定,尤其在巩固 “父—子”关系这个宗族社会的核心关节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孝”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信仰,维系和团聚着一个个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家族——的稳定发展,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体系和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亲缘社会基础上的,因此,它必须将“礼”“义”“忠”“信”“和”等观念纳入到它的政治伦理价值追求中。以“忠”这一观念为例,“忠”是从一般意义的忠信、诚敬、尽心转化而来的,并非指忠于君主个人,而是忠于自己的职责、操守,为社会或公众利益考虑。比如,《论语》有“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是说臣下可以为了追求真理而犯颜君上,这就是忠;《左传·桓公二年》有“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二年》),是说在上位的人以给民众谋利为职责,这就是忠。可以说,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忠”才可能成为积极的儒家政治伦理价值观。另外,传统社会发展中,以礼治家体现的孝亲、友善,人文教化倡导的仁爱、和谐,经济活动必需的敬业、诚信,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有序发展,成为整个民族认同、接纳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念。
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它生发于社会的伦常观念、生活习俗,成为严格意义的法律之外,社会运行必须遵循的规范,也成为全体社会的精神追求。而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它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正因为此,“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观念与传统的道德观念也是血脉相通的”[7]14。 今天,我们探讨传统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并希望重新树立其重要地位,也必须认真思考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传统价值观,只有和现实中国社会,尤其是基层家庭社会做好合理对接,才能与积淀深厚的乡土情怀产生共鸣,才能找到其真正的生存土壤,焕发新的活力。
国家层面,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注重以德治国。“德治”思想,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在中华文化的基本认识中,天下,也即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18]47在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以德治国首先强调的就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孟子》中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的税赋、兵力以及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都来源于人民,都依靠人民。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群众推动和主宰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因此,唐太宗才会发出“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的感慨。其实这种认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依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第五次领导人会晤时就着重指出“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这已经成为我们当前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其次,以德治国的核心内容是“仁政”。所谓仁政,就是以伦理道德观念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纲领,行“爱人”、“爱民”的仁慈政治。《孟子》就讲“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这就要求国家的管理者要时刻保有一份爱民之心,以国家的发展和生民的福祉为职责,要有一种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仁爱精神。我们知道,当前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我们也依然要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建设,尤其在国家层面,我们要十分重视通过道德建设提高全体社会的公民素质,为法治社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将 “德治”作为“法治”的重要支撑。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论述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乃是一种人文道德教育”[14]13。这种人文道德教育,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将国家、社会、个人都纳入其中。国家作为社会的管理主体,它要担负起社会有序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责任,尤其是身处其中的管理者,要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担当意识。只有如此,生活其中的人民才有一种大家庭的归属感。个人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它要积极融入这个社会,遵从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引导,妥善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创造社会财富,实现人生价值。只有如此,我们的国家才可能更加有效地集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获得健康、有序的发展。
[1]刘茂杰、张明仓、林涵.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J].求是,2014,(12).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一)·中国学术研究所序[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7.
[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118.
[5]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社会学研究,1994,(6).
[6]巴新生.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泛血缘特征初探[J].史学集刊,2008,(2),3-11.
[7]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J].中国社会科学,1997,(3),96.
[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71.
[10]艾斐.如何丰富经典文化[N].人民日报,2008-7-17,(16).
[11]蔡毅.今天,我们怎样面对经典[N].人民日报,2015-01-15(24).
[1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1.
[13]钟振翔,张剑伟.简论董仲舒的历史认识论思想[J].湖北社会科学,2005,(2),96.
[14]王启发.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 》 的 具 体 实 践 [J].湖 南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2007,(2).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49-650.
[16]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1-1(1).
[1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8]姜广辉.儒家经学中的十二大价值观念———中国经典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解读[J].哲学研究,2009,(7),45.
[19](宋)程颢,程颐.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