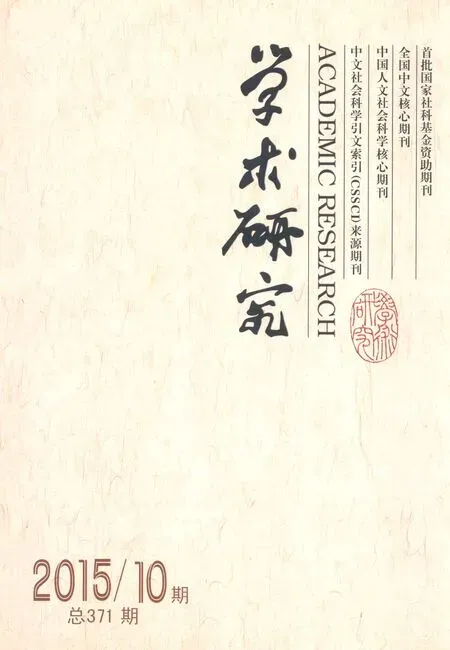传统管理思想的殊途与同归
——兼论中道思想对管理悖论的启示
2015-10-18刘刚雷云
刘刚 雷云
传统管理思想的殊途与同归
——兼论中道思想对管理悖论的启示
刘刚雷云
传统管理思想以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思想为代表,它们虽然视角不同,儒家体现为中庸视角,道家体现为阴阳视角,法家体现为法术势视角,兵家体现为奇正视角,但却具有很大的共通性,都强调适度、权变与和谐。我们将这种共通性总结为中道思想,它对企业管理,尤其是对战略与细节、稳定与变革、制度与人情、分权与集权等管理悖论具有深刻的启示。这些启示包括:以适度为原则,在矛盾双方中注重分寸感的拿捏,从而达到平衡;以权变为原则,根据具体环境而灵活应变,做到与时俱进;以和谐为原则,强调整个组织的利益及以人为本,实现长远发展。
传统管理思想中道思想管理悖论
诸子百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来源,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为最。总体来看,虽然它们视角不一,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在它们中间潜藏着巨大的共通性,对这种殊途与同归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传统管理思想的认识,提升管理水平。
一、殊途:不同学派的视角差异
由于视角差异,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这四大学派具有较大不同,并在历史上长期争鸣。儒家主要立足于中庸视角,强调管理中的伦理规范;道家主要立足于阴阳视角,强调管理中的顺势而为;法家主要立足于法术势视角,强调管理中制度、权术及权力的综合运用;兵家主要立足于奇正视角,强调管理中的随机应变。
(一)儒家的中庸视角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自孔子提出中庸,将其奉为最高标准之后,这一理念在后世被不断完善。中庸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胡适甚至评价“中庸的哲学,可说已成了一般中国人的宗教”。[1]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对于中庸,往往莫衷一是,有人将之视为老好人式的和稀泥,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那么,中庸究竟是什么呢?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四书章句集注》),由此可见,“中”指的是个体在面对矛盾时,注意对度的把握,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以适度为原则;“庸,平常也”(《四书章句集注》),“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二程集》),“庸”指的是恒常不变。因此,中庸的意义可以总结为:在处事过程中注意分寸感的拿捏,随时随地保持适度。围绕“度”的具体标准,儒家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比如“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恭而无礼则劳”(《论语·泰伯》),“知者不失人”(《论语·卫灵公》)等。
当然,儒家在强调伦理规范的同时,也注意到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因而提出“时中”,“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其含义为君子应善于权变,应时、应地、应事而采取最优策略。比如,孟子就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这种权变作为适度思想的补充,最终指向和谐。
(二)道家的阴阳视角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下》),如果说儒家的核心是中庸,那么道家的核心便是阴阳。在注意到阴阳对立关系的同时,道家也认识到阴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在特殊的情况下,阴阳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在对立、依存及转化的作用中,阴阳最终达到平衡。[2]
就阴阳相互依存来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二章)。在道家看来,有无、难易、长短等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以另一方为前提,因此不会出现一方消亡的情况。就阴阳相互转化来说,老子将其总结为“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淮南子·人间训》)。在阴阳双方的互动中,二者往往此消彼长,但这种消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一方太过强盛,那结果可能是盛极必衰。这就好比一个企业,如果形成了绝对的垄断,往往会因为失去活力而衰竭。
阴阳平衡则是道家的最高追求,它实质上是保持阴阳双方适度而达到的和谐。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在混沌初开之后,较轻的一部分逐渐上升为天,较重的一部分逐渐下沉为地。随着天地之间的阴阳交感,万物得以萌生,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由此可见,阴阳平衡是万物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这种思维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中国人的价值观结构也表现出阴阳平衡的特征。[3]而在相互竞争的两个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相互合作,竞争与合作间的阴阳平衡则有利于双方的长远发展。
(三)法家的法术势视角
在韩非子之前,按理论侧重的不同,法家分为法、术、势三个派别。其中,商鞅重法,强调明君治国“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具体来说,他对法的强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这体现的是法的公平性;其次,“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开塞》),这是提倡重罚;再次,“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在之”(《商君书·定分》),这是要求法的简单易懂;最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这是要求法的与时俱进。
申不害重术,其术治思想主要包括以下这些方面:首先,不可过分依赖某一个下属,“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申子·大体》);其次,强调君臣的分工及君主集权,“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再次,强调岗位责任制,“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申子·大体》);最后,秉承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倡导君逸臣劳,君主当“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
慎到的学说对法、术、势均有所涉及,但其核心主要集中在法与势上,尤其是后者。在法方面,他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慎子·逸文》)及“以道变法”(《慎子·逸文》);在术方面主张君逸臣劳;在势方面则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君主应运用法、术以护势,从而做到法、术、势的结合。
在法、术、势三个学派的基础上,韩非子综采各派之长,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高度评价商鞅、申不害及慎到,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不足在于缺乏融合,比如商鞅重法而不重术,导致君主不能识别奸臣;申不害重术而不重法,尤其是法令的不统一造成了混乱;慎到则太看重势,被韩非子批评“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韩非子·难势》)。由此可见,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倡导在法术势之间保持适度,最终实现国富民强。
(四)兵家的奇正视角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那什么是奇正?“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孙膑兵法·奇正》),由此可见,“正”指的常规的,可以预料得到的战法,而“奇”指的是非常规的,出人意料的战法。进一步推广,“正”是正面战,“奇”是游击战;“正”是基础,“奇”是运气;“正”是原则性,“奇”是灵活性。对于奇正的关系,兵家主要强调奇以正生、奇正互化、奇正结合这几个方面。
首先,奇正双方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在二者之间应保持适度,以正为主。“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孙膑兵法·奇正》),可以说,在动静等奇正概念中,没有奇,就无所谓正,反之亦然,因此奇正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种依赖关系中,正居于主导地位,“非正兵,安能致远”(《百战奇略·正战》),可以说,“正”是基本功,它决定了“奇”的发挥空间和成效,基本功越扎实,出奇制胜的效果就越好。比如,同样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项羽大破秦军,而马谡则失了街亭。
其次,奇正双方相互转化。“天地之理,至则反,盈则败,阴阳是也”(《孙膑兵法·奇正》),“至则反”与“盈则败”说的是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就会走向其反面,这实质上就是阴阳互化。在战争中,正与奇并不是泾渭分明,正可以为奇,奇也可以为正,“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唐李问对》),这便是奇正互化的灵活体现。
最后,在奇正的运用上应不拘一格,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制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以控御也”(《阵纪·卷二·奇正虚实》),这说的是:如果单纯依靠常规战略,杀伤力不够强,获胜比较困难,而如果完全依靠非常规战略,则缺乏后备支持,局势难以把控。因此,应实行奇正结合,至于什么时候用奇,什么时候用正,兵家则强调根据具体环境而保持权变。总之,在奇与正的相互作用中,通过奇正的相互依赖、相互转化,最终要达到的是奇正的灵活结合,“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兵法·势篇》)。

表1 中道思想在各派学说中的具体体现
二、同归:传统管理的中道思想
总体来说,儒家、道家、法家及兵家思想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通之处。首先,它们都认识到事物具有多个方面的矛盾,解决问题需要把握其中的“度”,既不能超过这个“度”,也不能不足,以适度为原则;其次,“度”体现为标准,在遵从标准的同时,个体应根据具体情势的不同而灵活调整,也就是说,在处理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到具体环境,坚持权变的准则;再次,无论是适度,还是权变,最终的目标是和谐,这包括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体性,体现为以人为本,另一方面强调视角的全面性,体现为大局为重。我们将这三个方面的共通性总结为中道思想,它的核心特征是尚中,内涵则在于适度、权变与和谐(详见表1)。
(一)适度
适度作为中道思想的重要内涵,它在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思想中均有深刻体现。
重义不轻利为先秦儒家所提倡,“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在先秦儒家看来,逐利是人的本性,应该得到尊重,但同时也应该进行限制,那就是在义的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责任。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并不是碌碌无为,而是将精力放在那些最值得有所作为的领域,对其他的领域,则敢于放弃或放权,从而在核心领域有所作为。可以说,道家的无为实质上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它强调的是在核心领域上的持续专注,追求的是“无不为”,也就是“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的最高境界。
就法和势来说,制度可以用来加强权力,所谓“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难势》),君主一方面要掌握制度,另一方面要保持威权;就法和术来说,二者具有相当强的互补性,“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制度与权术可谓一明一暗,一刚一柔;而在术与势的关系上,韩非子提出以术御势,“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详见图1)。

图1 法家法术势关系图
“非危不战”(《孙子兵法·火攻篇》),这表明了兵家对战争的谨慎态度。虽然兵家的学说均围绕战争展开,并将战争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但即使如此,兵家并不鼓励战争,“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而在反对战争的同时,仍要积极备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这种未雨绸缪正是为了让潜在的敌人知难而退。
(二)权变
在中国文化中,强调权变的成语非常多,比如随机应变、通达权变、机变如神等,这表明了权变思想的深厚底蕴。权变思想在传统管理思想中广泛存在,它们都强调个体在处事过程中保持灵活,基于具体环境而选择最优策略。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先秦儒家不赞同道家式的无政府主义,也不认可法家式的绝对控制,而是强调视情况而定。具体条件包括君主的以礼待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以及君主的仁德之心等,忠诚于不仁的君主等于助纣为虐,“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因此,作为臣子,对君主的态度应保持灵活。
“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八章),在道家看来,水具有许多的优良品质,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八章)。这说的是:水放在方形器皿里面就是方的,放在圆形器皿里面就是圆的,冬天的时候凝固,而到了春天则消融,总之,只要外界环境发生改变,水就会进行调整,这种权变思想正是道家阴阳思想的重要内容。
“法与时转则治”(《韩非子·心度》)。在法家看来,世界处于不停的发展中,既然周围环境变了,那治国方针就要做出相应改变,所谓“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在上古三代,人民淳朴,以仁义治国行得通,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不行了,国家制度应该随着时代变化,不能墨守成规。“法与时转”是法家在管理中的积极变通,是法家权变思想的体现,为法家学说赋予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孙子兵法·军争篇》),这说的是在战争中,主帅要善于综合分析各种形势,相机采取行动。“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篇》),“兵因敌而制胜”(《孙子兵法·虚实篇》),这种强调根据外界环境而灵活采取策略的权变思想,是兵家思想最为核心的部分。
(三)和谐
儒家、道家、法家和兵家虽然相互争鸣,但它们异曲同工地将和谐作为最终目标。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和”可以说是儒家的终极追求,为了达到“和”的境界,儒家强调修齐治平,修身的核心在于对个体伦理规范的要求,通过由内而外的方式实现天下大同,由此可见,儒家强调基于伦理规范而达到和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从效法自然的角度,道家提出了许多富有哲理的创见,比如上善若水、无为而治等。人需要做的是尊重自然,去掉人为的雕饰,虚心向自然学习,最终达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的和谐状态,由此可见,道家强调顺应自然规律而达到和谐。
“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法家以冷酷而著称,提倡重罚,似乎与“和”的理念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商鞅变法后,“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这种理想状态不正是“和”吗?只是在法家看来,人性本恶,在管理中必须使用强硬的手段,“以刑去刑”正是法家辩证和谐观的体现。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在兵家看来,战争是实现和平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兵家与法家一样,具有辩证的和谐观。当然,兵家的和谐观也反映在其他方面,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从而尽量避免战争,减小伤亡。
三、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应用原则
基于中道思想的内涵,中道思想的应用原则包括适度、权变与和谐这三个方面。其中,适度本质上是一种对标准的遵从,它划定了相应的操作范围,而这种标准往往基于科学分析及过往经验,是科学性的体现;权变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对标准的调整,反映了管理过程中的灵活性,因此是艺术性的体现,它表面上看起来与科学性相矛盾,但实质上则是对科学性的补充;如果说适度与权变是中道思想的方法论,那么和谐则是中道思想的价值观,它站在整个组织的角度,是中道思想系统性的体现,正如彼得·圣吉的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4]可以说,适度、权变与和谐这三者辩证统一于中道思想(详见图2)。

图2 中道思想应用原则关系图
在管理实践中,针对管理者面临的两难困境,适度原则可以较好解决这一问题。这又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两端均需兼顾的情况,比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利润与社会责任等问题,而另一种是两端均不可取的情况,比如冒险与保守。在这些问题上,企业均需要把握适度的原则,在综合考虑各种矛盾的情况下,注意分寸感的拿捏,最终达到平衡。
相比于具体环境,制度规范往往具有滞后性,比如计划赶不上变化,而且实际情况往往更加复杂。因此,在强调适度的同时,管理者也应保持权变,实现策略与环境的最优匹配。在领导方面,费德勒的权变理论表明:在领导过程中,没有一种领导风格是绝对有效的,具体领导风格取决于任务及下属等条件;在战略方面,稳健型战略则并不一定永远是首选,在环境较为乐观的情况下,企业更加强调的应是顺势而为,积极进取。
和谐原则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和谐原则体现为大局为重,它追求的是整个组织的和谐,这包括组织内部的和谐,即组织内成员之间的良好协作,也包括组织与外部环境间的和谐,即组织对外界环境的适应;从微观层面上来说,和谐原则体现为以人为本,在管理过程中,要注意以员工的需求、能力和情感作为出发点,最大程度地尊重员工,关爱员工,倡导员工之间竞争中有合作,和谐共处。当然,和谐原则也适用于企业与顾客、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处理。
四、中道思想对管理悖论的启示
在管理中,时常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具有非此即彼的逻辑,管理者无论选择任何一方,都会损害另一方,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这类问题便是管理悖论。[5]它在计划、组织、领导、控制领域内均广泛存在,比如计划领域的战略与细节、规划与应急,组织领域的稳定与变革,领导领域的制度与人情、个人利益与集体绩效,控制领域的分权与集权等。在这些悖论上,现有的西方理论往往强调局部而忽视整体,强调刚性而忽视柔性,而中道思想则具有独特的启示。以下本文将基于中道思想,对战略与细节、制度与人情、稳定与变革、分权与集权这四组悖论进行分析。
(一)战略与细节
战略与细节的关系很早就得到了关注,比如“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第六十三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后汉书·陈王列传》),但即使如此,二者之间的悖论仍然困扰着许多管理者。一方面,细节决定成败,海尔之所以成为国际知名企业,这与它数十年如一日的细节管理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战略决定成败,“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孙子兵法·计篇》),管理者的首要工作是“抽身谋大计”,避免战略方面的失误。
对管理者来说,太过重视战略而忽视细节,会有可能打造一个空中楼阁,或者重蹈因为一个马掌丁而输了一场战争的覆辙,因为战略一方面源于无数的细节,另外一方面也依靠细节而落地;太过重视细节而忽视战略,则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以正确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基于中道思想,在战略与细节之间,管理者应保持平衡,而平衡二者的关键在于战略性细节。[6]
针对多如牛毛的细节,管理者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便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如果一概置之不理,则可能造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韩非子·喻老》)。事实上,只有“蚁穴”这样可能影响全局的战略性细节才值得重视。战略性细节可谓战略与细节的中间枢纽,也是二者的平衡点,在对细节的管理上,管理者应实行分级管理,甄别战略性细节并见微知著。
(二)制度与人情
在制度与人情的问题上,许多管理者面临“挥泪斩马谡”的困境。对员工有错必罚,则容易给人留下严苛的形象,造成员工在情感上的疏离,正所谓“宽则得众”(《论语·阳货》);网开一面照顾了一时的人情,但有失公正,由此造成后患无穷。因此,在制度与人情的问题上,管理者需要做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制度体现刚性管理,而人情则体现柔性管理,卓越的管理讲求刚柔并济。基于中道思想,管理者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制度与人情的平衡工作。
首先,平衡制度与人情的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即在制度订立时,将人情因素纳入考量,尽量避免制度与人情相冲突的情形。并且,制度本身也应讲求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在追求面面俱到的同时,也应预留一定空间,便于执行者依据具体情况而进行裁量。
其次,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制度和人情不可等量齐观,而应以制度为主,适当兼顾人情。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应有法必依,毕竟无规矩不成方圆,而只有在少数特殊情况下,管理者才能审时度势,做出人情上的变通。在这个过程中,值得警惕的是,人情不可泛滥,例外绝不能成为常态。
再次,在正式场合,制度应居于主导,而在非正式场合,人情应居于主导。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制度好比一个容器,通过外力的方式限定了组织成员的活动范围,而人情则是黏合剂,是将组织成员聚合为一个团队的内在力量。二者内外结合,最终提高整个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稳定与变革
在稳定与变革的问题上,一方面,稳定是企业持续经营的保障,是企业发起变革的基础,具有必要性,也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环境往往是多变的,包括政策环境及技术环境等,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如果过于强调稳定,企业最终只能成为一潭死水,遭遇淘汰。
无论过去的成功是多么的辉煌,企业都不能固步自封,而必须对变革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柯林斯和波拉斯在《基业长青》中指出:“那些高瞻远瞩的公司根据兼容并蓄的精神,不断地寻求阴阳之间的平衡。”[7]其中,“阴”指的是企业的核心理念、企业文化等,“阳”指的是大胆创新,持续改进等,根据阴阳的内涵可以看到,“阴”更多关系到企业的稳定,而“阳”则关系到企业的变革。
总之,对于稳定与变革的关系,管理者应基于中道思想进行理解。二者看似对立,但实质上相互依赖,稳定有利于变革,变革则有利于更长远的稳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是保持适度和权变,强调适度的变革,其标准在于不能造成混乱,强调适度的稳定,其标准在于能够容忍和支持变革,而在具体变革过程中,究竟是小步快跑式的渐进式变革,还是一步到位式的颠覆性变革,则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抉择。
(四)分权与集权
由于领导者个人精力有限,以及需要提前对下属进行锻炼,分权势在必行。但在分权与集权的问题上,领导者往往左右为难:权力过于分散,企业的运作效率往往受损,甚至因为权力斗争而影响稳定,而且在下属能力跟不上权力的情况下,也可能造成关键性失误;权力太过集中,下属的创造性得不到发挥,领导者事必躬亲,而整个企业成为“一言堂”,缺乏活力。
因此,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归根结底是把握好“度”的问题,既不能过于分权,也不能过于集权,而应坚持适度原则,追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领导者权力按照重要性进行划分,对非核心权力大胆下放,针对部分核心权力,在不影响企业稳定的情况下,实行渐进式下放。至于分权与集权的平衡点如何把握,则应坚持权变的原则,视情况而灵活操作,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宏观环境、所属行业、组织特征及下属特性等。而无论是分权或者集权,它们都统一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整个组织的和谐,它体现为组织内部的人尽其才与相互协作,体现为整个组织的高效运营。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刘刚、吕文静、雷云:《现代企业管理中阴阳学说新述》,《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3]于广涛、富萍萍、刘军等:《阴阳调和: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观结构》,《南大商学评论》2007年第15期。
[4][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5]普华永道变革整合小组:《管理悖论:高绩效公司的管理革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
[6]刘刚:《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8-130页。
[7][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基业长青》,真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13-116页。
责任编辑:张超
F270
A
1000-7326(2015)10-0069-07
刘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供应链战略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雷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培训部,管理学博士(北京,1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