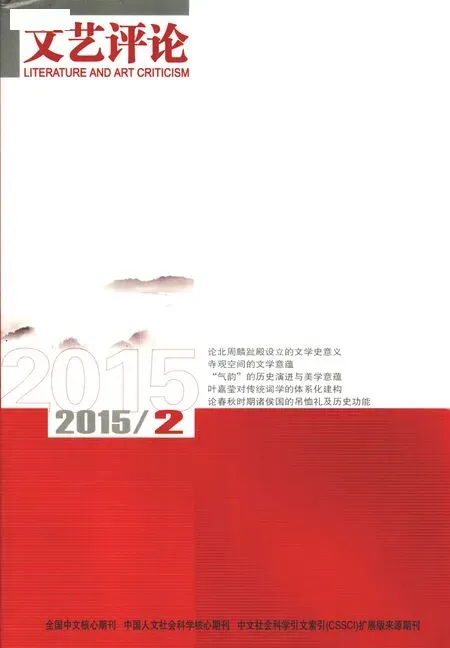宋代南渡时期诗学思想的一个转变
2015-09-29戎默
戎默
宋代南渡时期诗学思想的一个转变
戎默
魏庆之《诗人玉屑》“不可作意”条引《小园解后录》云: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此简斋之诗也。观末后两句,则诗之为诗,岂可以作意为之耶?①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是宋代南渡时期的诗人陈与义的绝句《春日》中的名句,常为诗论家们所引用,来说明作诗要自然流露,不可刻意的特点。《春日》诗正体现了陈与义的一种论诗观点:诗人所看到的外部美丽的景色本身就是一首好诗,诗人的主观表达,所谓“安排句法”,在诗歌创作中并不重要。《爱日斋丛钞》亦云:
陈去非云:“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静中置心,真与见闻无毫膜隔碍,始得此妙。②
更进一步抓住了陈与义诗歌中表现出的追求自然流露,摈弃刻意表达的诉求,认为陈诗所表达的观点乃是追求一种完全抛却表达技巧,“与见闻无毫膜隔碍”的诗学境界。
《春日》所体现的诗学观点并非孤例。相反,与这一观点相类似的例子在陈与义的诗集中比比皆是:
此中有佳句,吟断不相关。(《题许道宁画》)③
新诗满眼不能裁,鸟度云移落酒杯。(《对酒》)④
城中哪有此,触处皆新诗。(《赴陈留二首》)⑤
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题酒务壁》)⑥
可见诗人对这一观点应该十分认可。然而,这种观点与陈与义的前辈诗人的论述则完全不同。北宋中期的诗歌大家,后来被认为是宋诗典范的苏轼及黄庭坚关于这个问题就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朱弁《风月堂诗话》云:
参寥诗立成,有“禅心已似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⑦
苏轼对描写“柳絮入泥中”这一情景的态度是,诗人需要通过“收拾”,方能成诗。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外部风景需要诗人的意志与加工的观点。
黄庭坚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论述,《冷斋夜话》卷三载: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人以为山谷之言为确论。⑧
黄氏认为,美丽的景色无论贤者愚者都可以遇见,却又是专为“我辈”即诗人专设,只有诗人才能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加工,将景色记录下来,形成好诗。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强调的也是诗人的主观意志。显然,在景色与诗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苏黄二人的观点与陈与义诗的观点大相径庭。
二者观点的不同正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差异。苏轼《答谢民师书》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关于“辞达”的文学理论: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⑨
在这段话中,苏轼探讨了言、意、物三者的关系。所谓“了然于口与手”,正是提出言需尽意的要求。而所谓“了然于心”,即自身的主观意念可以准确反映外部的客观事物。做到“了然于口与手”、“了然于心”便可以达到创作的最高境界。显然,苏轼认为,影响创作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作家能否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和技巧。而其《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⑩则专论诗学,也更为直观地强调了诗人在描摹物态最主要还是需要依靠自身表达技巧的观点。
黄庭坚的文学观念,也是偏向注重诗人自身的表达技巧,如论苏轼词《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首则云: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⑪
这首词清空幽眇,正需要一定的心境与经历方能做出,黄氏却只认为这是东坡“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的缘故,可以看出他对作者内部的学力及表达十分重视。
可见,在苏轼、黄庭坚的诗学观念中,诗人内部的表达才是作诗成败的关键。只要诗人的表达到位,诗人之“意”与外界之“物”,都可以做到完美表达。实际上,这一诗学观念也并非苏、黄独创,他们的前辈,有变唐趋宋之功的宋代初期大诗人欧阳修与梅尧臣,已经有类似的观点。《六一诗话》中有一段常为研究者所引用的话,最可以说明梅尧臣的观点: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⑫
梅尧臣认为,通过诗家的“造语”,虽有“不尽之意”、“难写之景”,亦可使之“见于言外”、“如在目前”。可见诗人内在表达技巧在梅尧臣的观念中何其重要。而欧阳修在评价他人诗歌时,也往往认为其诗歌的美妙正在于能够写尽万物,如其《感二子》诗,评价苏舜钦、梅尧臣二人的诗歌时,道:
二子精思极搜抉,天地鬼神无遁情。及其放笔骋豪俊,笔下万物生光荣。古人谓此觑天巧,命短疑为天公憎。⑬
诗人精思搜抉,则天地鬼神皆可尽其物情,笔下万物皆生光辉,亦可见诗人内在表达在欧阳修观念中的重要性。
显然,陈与义的前辈诗人们,对诗人内部的表达技巧有着十分强烈的信心,认为只要诗人具有十分强大的语言表达能力,无论在表情达意,还是描摹物象上,都可以取得成功。关于这一点,李贵的《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一书中将其总结为“北宋的语言乐观主义”,并说:
无论是梅尧臣的“造语”还是苏轼的“辞达”,着眼点都在语言,说明在他们心目中,诗歌的根本问题是语言问题。⑭
那么,再回到苏、黄二论述景色与诗人创作关系这一点上,他们自然会偏向诗人自己的加工与意志,那些所谓“我辈”、“贤者”的诗人,具有超强的“造语”能力,一切景物在他们面前都能曲尽其情,熠熠生辉,这些“清景”便“专为之设”了。
如此,陈与义诗中所反映的,不只是景色与诗歌关系的问题,更是作者的外部体验与内部表达技巧哪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黄庭坚、苏轼等人显然认为后者更重要,陈与义则反之。即从《春日》诗中看,“好诗”的关键正是高树鸣禽,远林红绿的美景,而“句法”在倏忽即逝的美景面前则难以施展,显得何其笨拙与累赘。
陈与义认为,美好的景致,即作者外部的体验和感知才是做好诗的关键。和苏、黄正相反,他认为那些整日浸淫在美景之中的“野人”倘若做诗,会比他的前辈们所谓的“造语”能力极强的“我辈”诗人们要好很多。《将至杉木铺望野人居》如是说:
春风漠漠野人居,若使能诗我不如。数株苍桧遮官道,一树桃花映草庐。⑮
正是此意。甚至陈与义在诗中还表达了做诗不用工夫,随意而为的特点,其《秋试院将出书所寓窗》云:“百世窗明窗暗里,题诗不用著工夫。”⑯《墨戏》则云:“併入晴窗三昧手,不须辛苦读骚经。”⑰这些论调居然要求完全抛却内部技巧,更为直观地表达了陈与义对诗人外部体验的重视,则完完全全是对苏、黄诸人诗学观念的反拨。
陈与义主张做诗应当推开门,走向户外,“寻找诗歌”,而不是如他的前辈一般“造语”、“写物”。他有《寻诗绝句》云:
醒来推户寻诗去,乔木峥嵘明月中。⑱
苏轼的《僧清顺新作垂云亭》却说:
天工忽向背,诗眼巧增损。⑲
从“诗眼增损”与“推户寻诗”,陈与义对其前辈诗人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观点,可谓产生了不小的转变。苏、黄等人的诗学主张是诗人内部的表达和技巧是做成好诗的关键,而陈与义所谓“醒来推户寻诗去”,正是强调诗人应放眼广阔的外部世界,不应一味追求“造语”即自身表达的精巧。
苏、黄在北宋诗坛的影响力和典范作用毋庸讳言。尤其是黄庭坚,他被后来的追随者与崇拜者们奉为所谓“江西诗派”的“三宗”之首,称为江西初祖。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即云:
豫章稍后出,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袓,在禅学中比得达磨,不易之论也。⑳
不只体现了黄庭坚在宋代诗坛的地位,也道出了其做诗的特点,所谓“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即重视揣摩形式技巧,并从书本中汲取做诗的营养。显然,这一特点正是出于诗人对自身内部表达技巧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有时也会造成黄氏做诗过于追求诗法句律、片面追求学养文字的弊端。历来提到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诗歌与诗学理论,必然会提到其不重内容,只重形式的特点。刘大杰先生《黄庭坚的诗论》一文就认为:“(黄庭坚)其理论也主要偏重形式技巧方面”、“片面强调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正指出了这个特点。㉑而他这种片面重视诗人内部表达技巧的观点也为江西后学们所广泛接受和发展:陈师道之“闭门觅句”,重视工夫学养;韩驹讲求师法古人,借用禅宗语所谓的“遍参”之法等,都是继承了黄氏做诗重视诗人内部表达技巧的理论。
陈与义虽然被后人推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但其主张“推户寻诗”,重视诗人外部的体验与感知,则可以说是对黄氏诗论的一种修正和突破。这一观点,在与他身处同一时期的诗人里,也有一些其他的诗人提及。如唐庚《春日郊外》:“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吕本中《邵伯埭路中》:“忽见云天有新语,不知风雨对残书”、洪炎《四月二十三日晚同太冲表之公实野步》:“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等诗,都与陈与义诗所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
而与此同时,南渡时期的诗论家中,也出现了不少重视外部体验的感法,崇尚诗人自然流露,反对过分雕琢的论调。这些论调,似乎正是针对北宋诸家过于重视诗人内部技巧而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诗僧惠洪,他与陈与义时代相近,其所著《冷斋夜话》中论诗文,不乏崇尚自然之语。如卷三记李格非论文云:
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㉒
认为作文的关键乃在“肺腑流出,不见斧凿痕”。与贵“造语”,重视诗人内部表达的观点已有很大不同。而卷四记潘大临语,则是突出外部体验之景色对作诗的重要性:
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㉓
潘大临在论作诗时,并没有强调“造语”或是诗法句律一类的问题,却强调了外部景物对诗人的感发。
另一个有相似论调的诗人就是徐俯,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
(汪藻)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驰骤约束,触类而长,皆当如人意,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忘实之想也。㉔
汪藻向徐俯问做诗之道,徐俯的回答,正是让他从诗人的外部体验出发。而曾季貍《艇斋诗话》云:
东湖(徐俯)论作诗,喜对景能赋,必有是景,然后有是句,若无是景而作,即谓之“脱空诗”,不足贵也。㉕
提出“对景能赋”的理论,更明确得表示了诗人应该注重外部风景,有感而发的理论。正针对了前人过于重视内部表达技巧的流弊。
其他诗论家的观点,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云:
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㉖
可见,陈与义的观点产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当时论诗风气关系很大。可以说,与北宋诸家注重诗人内部表达不同,诗人应该兼重外部体验,强调诗歌是受外部条件感发的自然流露的诗学思想和论调,已经在南渡时期的诗人那里逐渐出现并发展起来。不过,即使一些诗论家要求“出于自然”、“对景能赋”,但南渡时期诗论家大多还是认为创作诗歌更需要仰仗诗人的表达技巧,也少有人如陈与义一般直接要求写诗不着工夫,认为“句法”乃累赘,“造语”不必要。因此,陈与义的诗学观点在对前人的改变上,无疑是更彻底的。
与陈与义更为相同的观点出现的要更晚一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兴时期的大诗人杨万里。其《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之二云:
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㉗
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正与陈与义“安排句法已难寻”、“醒来推户寻诗去”的诗学旨趣相同。他在《荆溪集序》中,说道:
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窹,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试令儿辈操笔,予口占数首,则浏浏焉无复前日之轧轧矣。自此,每过午,吏散庭空,即携一便面,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㉘
他认为,只有与外界环境多接触,方能诗兴滚滚而来,“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而前人的典范,都应“辞谢”和抛却。
黄宝华《杨万里“诚斋体”与杨万里诗学述评》一文,认为杨万里的“诗学思想以对江西诗学的修正标志着宋代诗学的转型”㉙。肯定了杨万里诗学思想在宋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转变之功。但实际上,杨万里诗学思想中的转型,陈与义已经道夫先路。
在大多数关于宋诗、宋代诗学的著作中,两宋之际的诗歌创作、诗学理念都秉承着北宋诗学,尤其是江西诗派的路子,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许总先生更是以“水阔风平”这四个字来概括徽、钦、高三朝的诗歌风貌,其《宋诗史》说道:“这时期的诗风显示出空前的大面积的一致与稳定。也就是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诗坛,虽然不再有宋诗艺术高峰期的苏、黄那样的一流大家,但是却涌现出众多的中小诗人,而这些诗人在创作风貌及理论主张方面正是上承苏、黄、陈(师道)诸家余绪。”㉚然而实际上,许先生的话也未必尽然,陈与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诗学观点在有些方面与他的前辈,被公认为一流大家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学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有些地方是对他们观点的反拨与修正。这些观点,又与两宋之际的一些诗人、诗论家的论调有着紧密的联系。可见,两宋之际的诗风、诗论,也并不如一般研究者所论,上承北宋大家的余绪,那么“水阔风平”,而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转变。而这些转变似乎也启发了南宋中兴诗人的一些观点,推动了宋代诗史另一个高峰的出现。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200241)】
①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②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守山阁丛书本。
③④⑤⑥⑮⑯⑰⑱陈与义《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189、192、207、378、325、172、512页。
⑦⑧㉒㉓㉕吴文治《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9、2439、2436、2442、页。
⑨⑩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18、2143页。
⑪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0页。
⑫㉖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420页。
⑬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⑭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⑲苏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1页。
⑳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78页。
㉑刘大杰《黄庭坚的诗论》,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㉔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㉕曾季貍《艇斋诗话》,清光绪《琳琅秘室》丛书本。
㉗㉘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6、3260页。
㉙黄宝华《杨万里“诚斋体”与杨万里诗学述评》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㉚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