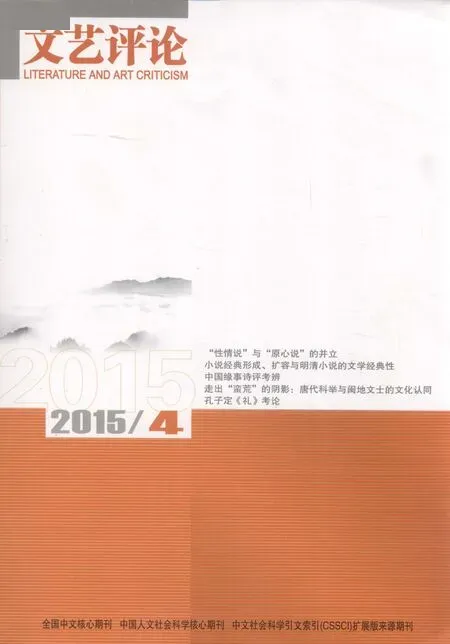从《世说新语》看玄学对晋人淡美趣尚之影响
2015-09-29梁愿
梁愿
从《世说新语》看玄学对晋人淡美趣尚之影响
梁愿
生命的动人之处,在魏晋时期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晋人风流之种种。或纵情山水,或口吐玄言;或风神潇洒,或放荡不羁;或肆意酒乐,或守朴抱素;或不甘沉寂,或志在安逸;或气度优雅,或情真率性。此之种种,都与玄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玄学影响下的晋人淡美趣尚
(一)对自然山水的品悟——“清风朗月”境界
个体意识、玄学思潮,使得晋人的自然观摆脱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山水比德思想,而呈现另一种姿态。徐复观这样阐述道:“……在魏晋以前,山水与人的情绪相融,不一定是出于以山水为美的对象,也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美的要求。但到魏晋时代,则主要是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美的要求。”①这种以山水为美的追寻,在东晋中期以后,更加发展为一种怡情悦性的士文化。《世说新语》记载了晋人追寻山水美的种种表现。兰亭集会、竹林之游,以及谢安与诸公的“泛海戏”等都是群体性的追寻;许掾的“好游山水”与孙统的“赏玩累日”不足,则是个体性的追寻;最后,这种追寻甚至成为一种移造山水的风尚,如宗炳卧室作画、康僧渊立精舍与世家大族造庄园等。以下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晋人发现的自然美。
晋人对自然山水的品悟,首先表现在对动态生命的发掘中。这以前的山水比德思想,实际上看重的是山水的静态特征,看山重深邃,看水重澄澈,绝非山的四季之貌与水的流动之态。晋人一改这种习识,开始“崇尚活泼生气”(宗白华语)。
其次,晋人对自然山水的品悟,凭借的是“天和”的审美心态。摆脱了比德思想后,晋人以情为出发点而完全用美的眼光来观照万物。“天和”的审美心态来自庄子,徐复观作如此解释:“惟有物化后的孤立的知觉,把自己与对象,都从时间与空间中切断了,自己与对象,自然会冥合而成为主客合一。……此即庄子之所谓‘和’,所谓‘游’。”②宗炳的“澄怀味像”与王羲之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正是抱着物化的态度来品悟自然,而自然之道的呈现恰是在这种满足且陶醉于斯美的观照当中。
最后,尽管晋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又受到追求清高、飘逸的人格美的影响,但这不是说玄学人格始终制约着自然美的认识,而是说自然美在人格美的促进作用下发展起来,形成了独自的境界,又在这最高境界上与人格美有汇通之处。这种独自的境界,从《世说新语》中描绘的情景来看,实则一种清明澄澈的“清风朗月”(《言语73》)境界,如“日月清朗”(《言语81》)、“云兴霞蔚”(《言语88》)、“天月明净”(《言语98》)等情景。
罗宗强认为:“现代治美学史者论晋人风流,往往视之若神仙,而其实入世之深、机心之重,亦莫过于晋人”③,“他们的审美感受,他们的心态,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们的山水审美意识,是在偏安的环境中,在偏安的心态中滋长起来的,如此而已。”④无可否认,晋人之走向山水,有经党宦之争后欲保存自身的心态,以及东晋偏安心态的影响。但晋人山水审美意识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从这一点出发后走到了一个有相当高度的独立境界。且抛开躲避政治、标榜自身等现实因素,单从晋人描绘的山水之美,以及融入其中的深挚爱恋之情来看,这里确确凿凿是一个“清风朗月”的境界。自然摆脱了比德思想的束缚,在晋人澄怀观道的心境中,显露了原本那种纯和流动的生命之美,它仅是生命的气息、生命的姿色、生命的律动。
(二)对自然性情的崇尚——“岩岩清峙”境界
汉魏之际儒学的式微,使得儒家的理想人格也宣告破灭。于是魏晋士人不得不寻求新的人格理想,从而建立一种玄学人格。此时既然无望于建立外在功名,唯有转向追求内在的个性与精神自由,因而这是一种崇尚自然性情、自然人生的人格理想。李泽厚对此提出“人格本体论”⑤,认为魏晋的人格本体不是为“仁”的儒家“圣人”,而是体“无”的道家“圣人”,它是一种富有情感而独立自足、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人格本体。值得一提的是,晋人对“自然”的理解是随着现实遭遇而有所改变的。嵇康、阮籍认为“自然”就是清高独立的人生追求,这一观点以嵇康被害告终;之后,向秀、郭象主张各安其分的人生观,“自然”在他们那里便偏指清静无为。
以自然喻性情和对自然物的癖好,是《世说新语》中表现晋人崇尚自然性情的两个非常直接明显的地方。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16》)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46》)
对自然山水的澄怀观照,必然把精神引向更高的自由境界。正是在这样的与自然冥合的自由境界中,最能体现玄学人格的理想境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四》)嵇康这首诗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山水与人格的内在联系。因而在人物品藻中以自然比喻某种美好的性情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恰如上文分析过的,晋人发现了自然的动态美,同样在用以比喻性情的过程中,取的仍是自然静中含动的一面,即在一种宁静谐和的状态中表现出生气来。如“谡谡如劲松下风”、“濯濯如春月柳”等。晋人这种生气并非在群体状态中表现出来的,相反地,它是个体独立状态的产物。“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这些描写指向一种独立状态。而且,他们对自然物的癖好,大多也仅仅与这种生气有关。羲之爱鹅,爱其“善鸣”;孤姥不懂,“烹以待之”,令“羲之叹惜弥日”⑥。
晋人对自然性情的崇尚,还表现为对真性情的追求和以一种寡淡姿态居高。这两种行为都非常注重个体自我独立的一面,也就是追求心性自如。钱穆说:“要之一任内心,不为外物屈抑,凡清谈家行径,均可以此意求之。”⑦
“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德行12》)
“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言语89》)
“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赏誉91》)
模仿名士风流,其实是这一时期十分常见的行为。然而张华却认为王朗之学华歆仅得到皮毛,反而失真。司马氏提倡以“孝”治天下,时年十余岁的孝武帝却说,哭是人悲痛到极点时感情的自然流露。可见,在魏晋名士看来真性情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甚至认为只要有真率,便胜过其他许许多多的优点。
“萧条方外,亮不如臣;从容廊庙,臣不如亮。”(《品藻22》)
“真独简贵,不减父祖,然旷澹处,故当不如尔。”(《品藻23》)
晋人是非常重人物品藻的,“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品藻25》)。而他们在对自己的评价当中却以一种寡淡姿态自居,可知这样一种性情在此时倍受推崇。他们选择纵身事外、清真寡欲,“若夫圣贤之礼法,家国之业务,固非晋人之所重也”⑧。再次证明,清静无为、清高独立就是晋人所崇尚的自然性情的涵义。
自然性情最终指向自然人生。魏晋名士的自然人生主要表现在“大人先生”的理想形象,以及醉酒的理想境界当中。“大人先生”是阮籍对“真人”理想人格的另一种描绘,是自然之性的体现者。“……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帏,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不以世之是非为是非,而能独立遨游于天地之外,真正做到适其情,得其性。这可以说是阮籍出于内心的苦闷与矛盾而设想出来的一个理想形象,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但它无疑代表着精神上的一种自由和超越。完全的自由和超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尤其在魏晋时期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因此晋人便让自己在另一种状态中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与超越,那就是醉酒。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21》)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任诞52》)
总之,以自然喻性情、对自然物的癖好,以及追求真性情与以寡淡姿态居高,还有对“大人先生”理想形象的设想与对醉酒理想境界的推崇这三方面,正是关于晋人对自然性情的崇尚的一个由表及里的阐述。纵观晋人自然性情、自然人生的种种表现,不难发现那其实就在追求一种清静无为、清高独立的境界,此一境界可用《世说新语》中的词形容为“岩岩清峙”(《赏誉37》)境界。
(三)关于自然之趣的艺术思想——“丝不如竹,竹不如肉”
晋人的艺术思想,可以说就是晋人淡美趣尚在艺术层面的表现,因此可看作晋人淡美趣尚的理论升华。《世说新语》中有一句话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晋人的艺术思想,那就是孟嘉所说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⑨。它表达的正是一种受玄学自然观影响的“渐近自然”⑩的艺术精神。这一时期的音乐、绘画、文学,都透露出以自然之真为美的艺术思想。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晋人重论乐、赏乐,以音乐为情感抒发的一大途径。阮籍、嵇康对音乐作过专门的论述。对于音乐自身的存在问题,两人都认为是“道”的自然呈现。“八音有本体,五音有自然。”⑪“夫天地含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无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秀味在于天地之间。”⑫即音乐之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的,它生而具有自然之性。而且,乐被赋予某种形式固定下来,也是顺自然而为的。“昔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⑬在这样一种乐本自然的艺术思想之下,晋人认为最能传达自然之性的不是管弦之乐,而是啸。
晋人的画,也造诣甚高。“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7》)从晋人对画的论述来看,重的是“神”而非“形”。顾长康的点睛之笔素来有名,而他之重点睛,完全出于眼睛最能传神的想法,“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巧艺13》)他认为“神”才是人之本性,才能表现人物之真。“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巧艺9》)“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巧艺12》)之所以“益三毛”、“置丘壑”,便是因为此二者关乎人物神明。重“神”、重“性”、重“真”,体现的也是“渐进自然”的艺术原则。
“渐进自然”,表现于文学,则是其中抒发的那种绝世存真的自然情感。受玄学影响,此时出现了大量游仙诗、玄言诗。虽言及游仙,其实表达的是晋人那种视世俗之情为矫情的心态。他们向往、珍视世外真情,以此种感情作为超越现实的理想栖身之所。“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奇灵岳,怡志养神。”(嵇康《兄秀才入军赠诗》)在这种淡泊、出世的情感当中,诗人才感受到人之为人的真性。而绝迹俗世,遨游天外是成全这种自然情感的唯一方式,“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嵇康《游仙诗》)。要之,晋人淡美趣尚是在玄学影响下对自然之性的追求。这种自然之性表现于晋人对山水的品悟、对自然性情的崇尚、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二、晋人淡美趣尚的思想渊源追溯
如上文所述,玄学对魏晋士人的影响至广至深。明代胡应麟说:“《世说》以玄韵为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世说新语》中上至帝王,下至一般士人都对清谈极为沉迷。⑭玄学思潮是在晋人清谈义理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对老庄哲学思想的辨析和改造。郭象的《庄子注》就在对《庄子》的阐释中衍生出了“自生、自是、独化、适性”的玄学新义,这些玄学新义又导向对适性、称情的追求。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还形成了晋人的山水审美意识。可以说,山水审美意识的形成,是必须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骆玉明认为,宗白华关于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⑮的表述,反过来说成“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自然被发现的精神过程”⑯。也就是说,山水审美意识的形成,才是晋人对于“风流”的追求中的最终收获,也最能代表晋人风流的高度。晋人的山水审美意识,实则如宗白华所说的“倾向简约玄澹,超然脱俗”⑰。而这种倾向,与玄学思潮对于老子“无味”之“味”说所指向的“淡”之境域的崇尚有关。
老子在论“道”的显现时曾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他认为“无为”、“无事”、“无味”是“道”的表征,所以他又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第三十五章)从老子对于“道”之“希声”、“无形”的论述可推及作为“道”的表征之一的“无味”,也是“希声”、“无形”的。而且,它还是至高无上的——“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老子》第三十一章)。把老子关于“道”之表征“无味”的思想加以拓展的,是庄子对于“淡”范畴的提出。庄子把“无味”直接界定为“淡”,明确指出“淡”为“道”之本。他反反复复地论道:“夫虚静恬淡,寂漠之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为天乐。”(《庄子·天道》)“游心于淡,合气于漠。”(《庄子·应帝王》)在庄子这里,“淡”被推为一种至境,它既是“道”的根本,也是通向“道”的唯一途径。那么,从老子到庄子,“淡”便从一种“道”的表征发展为一个既联系“道”又联系人的境域⑱。后来中国美学对“淡”之境域的追求,其契合点正在于此。
“逻辑地潜含着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⑲的庄子纯艺术精神,被魏晋的玄学思潮宣扬之后,它那种“审美意识就具体得到了体现和展开”⑳,表现在伴随山水审美意识形成而出现的真正审美意义上的山水诗、山水画上。以自然山水喻性情,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这是源于中国文化中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同构心理,即自然之“道”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直接指向人生。具体表现为晋人在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开始刻意追求某种人生理想,而恰恰在与自然山水的观照中发现了这种人生理想的最高境界。如宗白华所指出的,“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㉑;不仅如此,自然美与人格美此时还在最高境界上达到了统一。所以,中国美学所追求的“淡”之境域,不仅在山水诗与山水画之中作为一种最高意境存在,也同时出现在晋人对人格美的追求当中。刘劭在《人物志》中说:“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由此看来,刘劭认为“中和之质”是最好的一种性情,而对“中和之质”的追求其实就是对“道”之“淡”至境的追求。嵇康也说:“以恬淡为至味。”(嵇康《答难养生论》)可见,晋人追求“淡”之境域,实则出于对一种“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极致的追求。可以说,晋人就是在对以老子“无味”之“味”说为生成原点的“淡”之境域的追求中,展现了他们的无限风流!
三、晋人淡美趣尚的生成环境探究
晋人的淡美趣尚,是在魏晋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汉魏之际,党锢祸起,社会动荡不已。政治上,大汉时期那种积极奋进、建功立业的儒家理想,被现实的残酷斗争和无望局面严重动摇而渐渐消磨殆尽。生活中,战乱和杀戮所带来的朝不保夕、生命无常的焦虑感与恐惧感时常萦绕心头,以致导向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氛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但正如李泽厚所说:“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㉒面对儒家理想的落空,士人开始寻求另一种精神支撑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
道家思想追求清虚玄远、超脱恬淡的人生理想,这正契合魏晋士人远离祸患、保存自身的心理需求,于是结合老庄思想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为了他们试图寻求的另一种不同与汉儒的生活方式的理论指引。冯友兰曾说:“(魏晋)多数的玄学家都是企图达到……一种精神境界,当时称为‘玄远’。这种精神境界的内容就是后得的无分别的混沌,当时称为‘达’。有了这种境界的达人,当然能够‘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真正的名士。”㉓“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是竹林七贤最推崇的理想生活方式。
尽管晋人淡泊超脱的人生理想来源于道家,但其与道家理想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玄学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它对老庄思想的改造之处是准确理解晋人人生理想的关键。“小国寡民”是老子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的设想,他说:“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如果说老子的追求倾向独立自在的状态,那么庄子的理想生活方式则倾向个体自在的逍遥境界:“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庄子·天运》)就是说,庄子追求的是一种独立适意的“游”的浑然状态。后来嵇康“但愿守陋巷”的生活理想,就是对老庄所推崇的生活方式的另一番描述。但这种描述更侧重个人情感,更追求适意于自我,即人的个体意识非常强烈。老庄那种独立自在的玄远状态只是他的愿望得以达成的凭借,情真意淡才是他的愿望本身。换言之,老庄追求的是一种与本能、生命浑然一体的无欲的至情,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庄子·齐物论》),而嵇康追求的只是一种常情,它符合世俗的自然情感,因淡朴而显出诗意,如罗宗强所说,“只是一种心境的宁静,一种不受约束的淡泊生活。这种生活是悠闲自得的,应该有起码的物质条件,起码的生活必需,必要的亲情慰藉,是在这一切基础上的返归自然”㉔。罗宗强由此认为嵇康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晋人之淡,并非无情无欲,而是任情节欲。
追求悠游适意、自足怀抱的人生理想的价值取向,影响到审美情趣上相应地表现为一种淡美趣尚。阮籍在《清思赋》中写道:“夫清虚寥阔,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活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他所要达到的就是淡然玄远的精神境界。音乐在这一时期常被士人用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理想。阮籍的乐论明显带有玄学色彩,他认为自然之乐是无味无欲的,“无味则百物自乐”。而养生此时也可看成一门艺术,嵇康的养生论表现出鲜明的淡美趣尚,“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如同晋人之人生理想是对道家理想的改造一样,晋人的淡美趣尚与道家美学也表现出差异。《世说新语》中记述:“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言语98》)虽说司马道子后面以嘲讽的口吻反驳了谢景重的观点,但由此可见“微云点缀”这种朦胧的淡美此时已被注意。顾长康则明确把朦胧的淡美推到极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88》)这样一种淡美,较之庄子“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庄子·逍遥游》)的清澈明净、超然大气、偏向理性的审美理想,显然更隐约、微妙、感性。总之,从何晏、王弼抱有仕进之心的“贵无”之举,到嵇康、阮籍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遭遇祸害或陷于困境的悲剧,再到郭象、裴頠对名教与自然的调和,可以看出玄学要义的更新是随着生存方式的不断尝试而进行的。因此在玄学影响下出现的淡美趣尚,也在老庄淡美境界的无情无欲、超然大气的基础上变得更注重适意于自我,它是倾向个体的、倾向隐约的。
四、晋人之清淡与宋人之平淡
综上所述,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晋人淡美趣尚是受玄学影响的结果,而玄学在根源上又是对老庄思想的改造,因此玄学影响下的晋人淡美趣尚既继承又改造了老庄思想的“淡”。在晋人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当中,表现出更多个体性与主体性,“淡”从而成为指向清静无为、清高独立境界的“清”。徐复观说:“由庄学而来的魏晋玄学,可以说是‘清的人生’、‘清的哲学’。”㉕由庄学影响而来的玄学,把“淡”理解为“清”,其缘由在于老庄之“道”的境界在理想性、涵盖性方面比晋人的人生理想、审美理想所追求的境界深远得多,因而后一境界的特征,就从前一境界更为本质的、整体的“淡”的特征,落实为相对外在的、倾向个体表征的“清”。这是就哲理逻辑层面而言。从现实效用层面来说,前者关涉天道、人道,后者几乎仅关涉人道。按徐复观的观点,从老子到庄子,就是道家思想由“道”至“心”的落实。那么,可以说在晋人这里道家思想完全落实为人超越现实世界的途径。庄子的“淡”是就“德”的层面而言,它以自然为法,是一种泯灭了个体分别才达到的大美;而晋人的“清”并未到达“德”的层面,它只是现实环境中的一种审美选择,是试图泯灭是非、好恶来保存个体的努力。所以,尽管“清”的选择是为了超越现实,而实际上仍是切近人生的。阮籍《乐论》“无味则百物自乐”,以及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淡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中的“自”、“不足”,都表现一种在对“恬淡”的推崇中倾向个体适意的人生趣味。总之,晋人那种由于社会环境所迫而选择的淡美趣尚,同样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对“淡”的理解、期望都指向“清”。
玄学的影响,又使得晋人之清淡不同于宋人之平淡。晋人对自然山水的“清风朗月”境界之品悟,对自然性情的“岩岩清峙”之崇尚,以及其“自然之趣”的审美观,都在玄学的影响下呈现出一种清明空灵、清高独立的气象。而赵宋平淡美则因为儒道释三教合流而显得平和圆融、深沉透彻。“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颇似枯淡,久久有味”(陈善)、“外若枯槁,中实敷腴”(曾纮),这些描述要表达的,都是一种成熟美、老境美。比较而言,后者更加内在化、心灵化。
从审美心态与审美情怀、审美理想与审美境界等方面,可清楚看出清淡与平淡之差异所在。由于晋宋时期的主体风貌,魏晋士人的审美心态也呈现出“稚子之韵”的感性的一面。强烈的感情、张扬的思维,是其感性的最大特点。对于自然之美,魏晋士人抱的是一种“天和”心态。他们刚刚发现了自然之美,便以一种全新的感受投入进去。这份投入里面就有道家玄学影响下的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意味。如果说晋人这种“天和”心态是走进了山水,那么,宋人的“中和”审美心态则是走出了山水。赵宋时期的“老者风范”的主体风貌,决定了其审美心态的理性特点。宋人的内敛思维,使其走向内在、走向心灵。于是,晋人那种与山水合一的适意与满足已经无法寄托宋人的深沉心灵,他们需要的是走出山水之后仍感觉到人与天地同在的圆融境界。这是一种在儒道释共同作用下的相当平和、成熟的审美心态。晋人与宋人的不同审美心态,又通过两种不同的审美情怀表现出来,那就是山水情怀与田园情怀。晋人之名士理想追求清高人格,注重人与俗世之间的距离。所以,山水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之所。他们在山水中遨游自适、潇洒风流,追求山水的清新自然、清明空灵之美。而宋人之居士理想不以一味出世为高,它追求的是入世又超世的人生。更能慰藉他们的心灵的,是一种恬淡平静、和谐自然之美,即宋人的审美情怀倾向陶渊明式的田园情怀。“天和”与“中和”的审美心态,以及山水情怀与田园情怀,都源于晋人与宋人的不同审美理想。前者追求“天地大美”,后者追求“中和之美”。“天地大美”是道家的理想,晋人崇尚其开阔之境与物我合一之境,如嵇康就曾有游心太玄的理想。晋人的强烈情感与张扬思维,使得这种审美理想带上了浓郁的生命之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这些对于自然之美的描写,似乎表明美就在于生命之气,而且生命之美是铺天盖地的。“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主要来源于儒家,还融合了道家的淡泊飘逸与释家的清静无为。事实上,宋人追求的就是一种动中含静、动静结合的理想。“外枯中膏”、“绚极而淡”,都指向一种不张扬、不过分、和谐自然的美。由此,清淡与平淡之审美境界,也分别表现为清水芙蓉之境与炉火纯青之境。清水芙蓉之境,呈现出的是“稚子之韵”,它指向生命之美,偏重自然清新;炉火纯青之境,却指向由对生命之气的内敛而来的含蓄从容、冲淡平和。若以一年四季之景来比喻,则前者为春荣夏盛之景,后者为秋冬之清明澄澈之景。总之,玄学是造成感性、富于生命朝气之清淡区别于理性、圆融、透彻之平淡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516000)】
①②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58页。
③④㉔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250、87页。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⑥《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93页。
⑦⑧钱穆《国学概论?魏晋清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1、141页。
⑨⑩刘强会评辑校《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6页。
⑪⑬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77页。
⑫嵇康《嵇康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⑭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他认为“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深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美学的自觉,就是在魏晋玄学的启示下发生的。”
⑮⑰㉑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209、219页。
⑯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⑱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30页,他认为“庄子思想重心不在‘道’的本体,而在对人间苦难(死当然是最大的苦难)的超越”。
⑲⑳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9、49页。
㉒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重印版,第151页。
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7页。
㉕徐复观《董其昌的艺术精神》,见《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