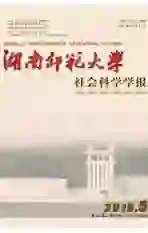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研究
2015-09-25富童
富童
摘 要:在中国法律体系近代化的过程中,监狱法的近代化始终占据着一个较为特殊的地位。自沈家本起,立法者通过一系列监狱立法,试图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在保障犯罪人人权的基础上,实现惩罚犯罪和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目的。设置监犯申诉权便是其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之一。申诉权通过允许监犯对监狱官吏违法处分监犯的行为进行申诉,成为监犯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最主要救济手段。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权利主体、申诉程序申诉对象上均逐渐科学化,尽管该法受时代所限仍有缺陷,但立法者也以该立法为导向尽可能地实现了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
关键词:监犯申诉权;大清监狱律草案;监狱规则;监狱行刑法
作者简介:富 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
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监狱改革始终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出自收回治外法权之需,监狱的文明程度亦被视为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清末变法中,监狱改革甚至被提到辅助宪政之根基的高度{1}。宪政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人权,因此,以法律的形式保障监犯在押期间的基本权利,就成了清末乃至民国监狱立法的核心目的之一,受到了统治者和立法者的广泛重视。然而,正如那句古老的法谚所说:“没有救济则没有权利”,为了实现保障监犯权利的目的,申诉权作为最主要的救济手段,必然成为近代监狱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监犯申诉权的概念
近代监狱改革立法中的监犯申诉权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犯罪人申诉权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二者均属于权利的范畴,具有权利的结构。杨春福博士在其《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一文中认为,权利的结构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权利的主体,指权利的所有者或者具有某项权利的人或组织;二、权利的内容,即权利人的权利所涉及的作为或不作为;三、权利客体,是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四、相对义务人,权利是一个关系范畴,它与义务相对,与权利人相对的是义务人{2}。下文就从这四个方面对监犯申诉权和犯罪人申诉权进行比较分析。
1. 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犯罪人申诉权的概念
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申诉的概念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不服所提出意见和要求的行为,根据案件性质可以分为对民事判决的申诉、对刑事判决的申诉和对行政判决的申诉。对于刑事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3}说明刑事案件的申诉权并非是由犯罪人独占的权利,而是由犯罪人、受害人及其二者近亲属,四方共同享有的权利。犯罪人的申诉权只是刑事申诉权的一种。也就是说,现代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罪犯的申诉权是指罪犯“在执行刑罚过程中,认为原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或者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导致量刑失当,从而提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罚的意见和要求”{4}的权利。
在明确了犯罪人的申诉权的概念的前提下,分析该权利的权利结构。
(1)权利主体
鉴于申诉权是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提出抗议的权利,犯罪人的申诉权是在犯罪嫌疑人在被已生效的判决认定为罪犯的情况下开始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只有已决犯才享有这种权利,犯罪嫌疑人并没有申诉权。犯罪人的申诉权的权利主体是已决犯,当然,其申诉权也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来行使。
(2)权利内容
犯罪人的申诉权要求犯罪人向一定机关进行申诉行为,所以它的权利内容是一种积极的作为。它的实质是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权利——辩护权在刑事判决生效后的继续和延伸{5}。
(3)权利客体
犯罪人的申诉必须是针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提起的,因而,其权利客体是已经生效的法院的刑事判决。
(4)相对义务人
尽管监狱可以且应当接收犯罪人的申诉材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说明监狱只是对罪犯的申诉材料进行转交的一个中间环节,并不具备接受、处理申诉的权力。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人应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因此,犯罪人申诉权的相对义务人是相应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2. 近代监狱立法中监犯申诉权的概念
对于近代监狱立法中的监犯的申诉权,则完全不同。它是指在监人员对监狱处分不服,向监狱监督机构和巡查官吏提出申诉的权利。
(1)权利主体
监犯申诉权的权利主体是在监人员,而在监人员,并非一定是犯罪人,也包含犯罪嫌疑人。如《大清监狱律草案》规定监狱分为三类:徒刑监、拘役场、留置所{6}。其中留置所拘禁刑事被告人。因此,刑事被告人也是在监人员。但是随着近代监狱立法在我国的发展,监狱法规定监狱不再设有留置所(看守所),在监人员的范围才缩小为已决犯。但这并非绝对,按照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第三条规定:“监狱内得附设看守所羁押刑事被告人及受禁闭处分者。”{7}在监人员也并不限于已决犯。另外根据民国三十五年《羁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申诉权的规定也可看出立法者有意将犯罪嫌疑人纳入监犯范畴。
(2)权利内容
在权利内容方面,监犯申诉权与犯罪人申诉权相同,都是积极的作为。但它是在刑事判决执行开始时产生的权利,是犯罪人对自己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行为的辩护权,而非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的延伸。
(3)权利客体
监犯申诉权的权利客体是监狱对监犯的处分。这种处分行为的对象是监犯违反监狱纪律的行为,而不是导致监犯入监的犯罪行为。做出这种处分的主体也非人民法院,而是由监狱内部,或典狱,或监狱委员会做出。处分的内容也不是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监狱法规定的处分措施。
(4)相对义务人
对于相对义务人的规定,由于政治因素,作为监犯申诉权相对义务人的具体机构有所变动。但可以确定的是监犯申诉权的相对义务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监狱监督机构和巡查官吏。法官与检察官并不以其本身身份,而或以监督机构工作人员,或以巡查官吏身份出现于监犯申诉权中。且监犯申诉权的义务主体通常也会包括一定的行政机构,如民国时期的司法部。
二、设置监犯申诉权的必要性和意义
现代法律体系中犯罪人的申诉权与近代监狱立法中的监犯申诉权在权利客体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权利主体与相对义务人的范围也仅有部分重叠,且其权利的来源并不相同,犯罪人申诉权来源于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人的诉权的一部分。而监犯申诉权来源于监狱法,且其行使也不涉及诉讼。另外,二权利在设置目的上也不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人的申诉权可以看出,该权利的设定,是为了避免错误或不适当的裁判进而避免错误、不适当地剥夺公民的自由权乃至生命权,最终实现保障所有公民人权的最终目的。监犯申诉权的设置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特定人群的人权,即监犯的人权。基于以上理由,其二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权利,同时设置二权并不冲突。
在这种不冲突之上,设置监犯申诉权也有其必要性。一方面,监犯作为特殊的公民,为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剥夺了其相当部分的公民权。这种权利的不完整在客观上使其成为弱势群体,法律又应当予以特殊保护。另一方面,在实践上,由于犯罪行为导致其难免受到歧视,且处于监狱或看守所这一封闭环境,其权利更容易遭受侵害,而其遭受侵害后更难得到救济。基于此,法律应设置监犯申诉权。
设置监犯申诉权对于保障监犯人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在罚的层面上。按照监狱法的规定,监犯在监期间享有通信权、接受劳动报酬的权利、按时按量得到给养的权利等,监犯因违反监狱管理规定所受到的处分就是对以上这些权利的部分剥夺以及其他一些非刑罚的处罚措施。通过设定监犯申诉权,可以使监犯对于剥夺行为或处罚行为进行抗辩,保证该剥夺或处罚行为的正当与合理。第二,在赏的层面。这一点主要针对的是实行监犯分级管理方式的监狱关押的已决犯。在该管理方式下,已决犯的各项指标均可对应相应加减分数,其所受处分,必然导致减分的后果,从而直接影响其晋级,进而影响已决犯在监狱中所享有的各项人身、财产权利,甚至影响其的刑期。因此允许已决犯对监狱处分进行申诉,可以保障其按时晋级,保障其相应权利的增加和实现。
综上,设置犯罪人的申诉权,可以有效保证犯罪人对于其犯罪行为承担正确、合理的责任,并对其改过自新之努力予以鼓励,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事实上在清末变法中,监犯申诉权与犯罪人的申诉权也始终并存。
三、近代监狱立法对监犯申诉权的引入及变革
中国近代对监犯申诉权之引入虽始于清末变法,但对于该权利之注意则早于此。清末清政府派遣各国外交官在出使中已对西方之监狱制度多有观察瞩目,并将其所见所闻介绍至国内,而这种对西方监狱制度的介绍已经超越了对监狱设置以及囚犯管理等方面的直观描述,涉及了对监狱运作较全面的考察和思考,其中即包含对监犯申诉权的描述。宋育仁所著《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观英狱政益知中国狱政之弊》一篇篇幅短小,但却详记到:“有按察巡狱坐厅一所,律师治事房数所。狱官如有苛待罪犯、克减饮食节,狱囚得赴律师,书所欲告达于按察。按察司临狱,问之事实,狱官必咎。”并感叹:“中国之政弊,莫狱为甚。”{8}而将监犯申诉权之概念正式引入中国的应为小河滋次郎。1906年9月,应修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奏请,清政府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1907年清政府聘请小河滋次郎在此主讲监狱学,在授课中,其对监犯申诉权进行了详解。他将该权称为“情诉”,是一种特殊的“诉愿”——人民不服下级行政官吏之处分,而诉于上级行政官吏之谓,为在监者独有。即监犯申诉权是由监犯独享的行政申诉权。同时他还独创性提出设置提法司一职,作为监狱监督官署接受监犯申诉{9}。而后,小河氏受聘起草《大清监狱律草案》,正式将监犯申诉权列于其中。以此为起点,随着中国近代监狱立法的发展起伏,监犯申诉权也经历了多次修改,体现出以下的发展特点。
1. 权利主体由混同转向分化
中国近代监狱立法按照其立法的密集程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共四个时期。第一阶段为清末,以1908年至1910年起草《大清监狱律草案》为代表,该草案虽因清政府的覆灭而未生效,但其架构和内容多为后来民国政府监狱法所继承,民国二年及民国十七年的两部《监狱规则》可以说是其翻版{10}。第二阶段为民国,又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以民国二年公布的《监狱规则》为代表,同时也制定了一系列监狱法规,如《在监人遵守事项》、《监狱看守点检规则》、《视察监狱规则》等。第二时期为民国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三年,以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为代表,另外还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监狱作业规则》等。第三时期自民国三十五年始,以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为代表,此法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被台湾地区所沿用{11}。监犯申诉权之变革也大致随之变化。
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大清监狱律草案》第12条规定:在监人有不服监狱处分者,得申诉于监督官署或巡查官吏{12}。也就是说申诉权的权利主体为在监人。而按照《大清监狱律草案》第1条的规定,在监人包含在押已决犯和犯罪嫌疑人。虽然本草案第37条规定了刑事被告应独居拘禁,但通观本法,刑事被告人在适用监狱规则时并不能与已决犯完全分离。待到第二阶段,民国二年《监狱规则》第2条即改为:“监狱为监禁被处徒刑及拘役者之所。”{13}监犯申诉权的主体成为单一的在押已决犯,虽然申诉权覆盖面有所收窄,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对于二者申诉权进行区分的倾向。此后各法基本都持监犯申诉权为已决犯独享之态度。而民国三十五年公布的《羁押法》规定:“刑事被告对于看守所之处遇有不当者,得申诉于推事检察官或视察员。推事检察官或视察员接受前项申诉,应即报告法院院长或首席检察官。”{14}首次独立明确了刑事被告的申诉权。这种权利主体由混同转向单一而后又转向区分的变化,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和对监犯申诉权的全面保障。
2. 申诉程序的变化
(1)申诉渠道的拓宽
按照《大清监狱律草案》第12条规定:“监犯可向监督官署或巡查官吏申诉。”{15}第13条则规定申诉可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第14条、第15条规定典狱有审查并及时呈递申诉书之义务,而在听口述申诉之际,除有必要外不可令监狱官吏在场。也就是说,审查申诉的主体应为监督官署或巡查官吏。对于监督官署,本草案并无说明,巡查官吏则为推事检察官或司法部派出官吏。从表面看,草案意图将作出处分的主体——监狱屏蔽在申诉的程序之外,但仔细分析条文可以发现,实际上监犯的申诉渠道并不畅通。一方面对于典狱长是否接受口头申诉以及口头申诉的报告程序并无说明,因此监犯口头申诉权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即使不谈监犯的受教育水平是否足以承担书写申诉书的任务,典狱有拆阅审查申诉书之权利,且可认定该申诉书是否有关监狱处分事项,如典狱认为无关,则不承担呈递之义务。书面申诉的途径也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民国二年《监狱规则》仍规定监督官厅或视察官吏为审查监犯申诉的主体,但取消了有关书面申诉的规定,使得监狱长官不再具有对申诉的审查权。另外同年颁布的《监狱处务规则》规定:“凡公文书之有关于在监人权利义务者,当迅速办理。”{16}虽然较为笼统,但较之《大清监狱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速对监犯申诉案件的处置。民国十七年公布的《监狱规则》则更进一步,其第6条规定:“检察官得巡视监狱。”{17}相比较民国二年《监狱规则》所规定的司法部所派巡视员可由检察官充任,可以看出检察官的巡视权与司法部的巡视权在此得以分离。在随后的民国二十一年《视察监狱规定》则首次明确了视察员遇有监犯申诉事项有立即处理的义务。同年《司法行政部处务规程》第九条“监狱司掌理事务”规定监狱司第四科掌管视察监狱所有事务,包括视察时人犯申诉事项{18}。同时司法部又以部训的形式规定视察监所人员必须轮换,以防流弊{19}。都表明了监犯的申诉渠道得到一定拓宽和保障。另外,民国二十四年《监狱待遇犯人最低限度标准准则》也不应忽视,其虽非法律,但其对监狱立法的改革方向和标准进行了说明,该准则在绪言中提到:“此种规则并非包罗一切待遇犯人之规模,乃根据人道及社会观点而指出监狱待遇犯人所应注意之最低限度条件。”准则中有关监犯申诉权的内容对之后的监狱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将“各犯人每日要有机会向典狱长或长官代表申诉或请求。”“各犯人须有机会依照程序向监外之高级长官申诉。”规定为监犯申诉权的最低标准{20}。为进一步拓宽监犯的申诉渠道指明了方向。
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对监犯申诉权的申诉渠道规定的较为完备。首先,在规定了申诉的审查机关为监督机关和视察人员之外,明确规定了典狱长对监犯申诉的呈交义务,且典狱长在接受申诉时,应即时转报。同时亦明确监犯申诉“得于视察人员莅临监狱时,径向其提出。”{21}其次,巡查监狱的频率也有所提高,由过去的司法行政部至少两年一次巡视监狱改为司法行政部每两年至少一次,高等法院每年至少一次,而检察官则可随时考察监狱。
综上,监犯申诉渠道之拓宽具有全面性,不仅申诉所提交对象有所增加,申诉机会予以增多,申诉效率也有所提高。
(2)申诉限制的减少
第一,对于申诉形式的限制的减少。《大清监狱律草案》第13条规定:“申诉用书状或口述皆可,但典狱认为必须用文书的,则不在此限。”{22}虽然小河氏对此规定有自己的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该条必定是对监犯申诉权的一种不合理的限制。在此后民国时期的监狱立法中,申诉的提出形式均未再加以规定,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第二,对于申诉的时限的限制及其他限制的减少。《大清监狱律草案》对监犯申诉权的限制相对较多,除前文提到内容外,其第17条还规定:“申诉须在事故发生后十日以内为之,或为豫告。不许数人连名申诉亦不许对已经裁决事件重新申诉。”不仅规定了申诉的时效,还禁止联名申诉。同时亦规定:“在监人滥用第十二条之申诉者,受其申诉之监督官署或巡查官吏得处以惩罚。”{23}监犯对于监狱处分不服的申诉不仅要经典狱长之审查,即使有机会申诉,还要面临超期或滥用申诉权的处罚,申诉之难可见一斑。民国二年、民国十七年《监狱规则》虽亦规定十日之限,但已不再禁止联名申诉,也取消滥用申诉权的惩罚。至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申诉的时限限制亦被取消。
3. 申诉对象——处分的变化
作为申诉的对象,即监犯所受处分的变化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处分内容的变化,一类为处分作出方式的变化。
(1)处分内容及其强度的反复
沈家本在为《监狱访问录》作序时提到“古人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自此义不明,而吏之武健严酷者……由是感化之地,变为苦辱之地。”而现今西方监狱之宗旨亦是感化人。因而中国监狱改革,应废除苦人、辱人之法,回归感化之宗旨{24}。废除苦人、辱人之法并不仅仅是刑制的变化,监狱处分之法也应相应变化。因而在制定《大清监狱律草案》时,立法者参考西方监狱处分手段,规定了十四种处分方式,分别是一、斥责;二、三月内停止赏遇;三、废止赏遇;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五、三次以内禁止发收书信;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八、一月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九、一月内停止自备粮食;十、七日内停止运动;十一、减削作业赏与金之一部或全部;十二、七日内之减食;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十四、七月以内之屏禁{25}。其中除十二、十三、十四真正涉及对监犯身体直接采取某种手段外,其余或为财产处罚,或为停止监犯部分在监权利。对于涉及身体处罚之减食,也规定了减少的最大份额,以及不得连日执行。相较于清前期之监狱,对于在监处绞斩重刑犯狱内赌博即用杖一百之刑,且还要待秋审再加处置相比较,已有极大改观{26}。
待民国二年的《监狱规则》,又大大缩减了可适用的处分方式,仅保留了六条,可并科之。在财产处分方面,除酌减赏与金仍保留外,其余均得取消。对于身体处分保留了减食,但其减少分量有一定缩小,同时以暗室监禁代替独慎、屏禁,且日期大大缩短,更进一步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但遗憾的是,在民国三年,掌责这带有侮辱性质的身体处分方式以核准呈文的形式回归部分监狱的处分之中,且未规定掌责之数的上限{27}。
民国十七年的《监狱规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监狱处分的种类又有所增加,慎独再次列于其中,且暗室监禁的上限由三日增加到五日,唯减食不再列于处分方式之中。至于民国十九年的《军人监狱规则》,掌责明确列于处分方式之中。
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在监狱处分方面较前一时期有较大转变,虽然处分方式仍为八条,但处分强度明显减轻,尤其是慎独由过去的两个月减少至十日以下,且“病弱者、衰老者、妇女之携带子女者、及怀胎五月以上或生产后未满二月者,不得施以慎独。”这也是法律第一次将除未成年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监犯单列为限制处罚的对象。即使是其他可施以慎独的“在执行中应令医师随时诊察其健康。”{28}另外,暗室监禁不再列于处分之列。同时由于受监狱矫正理论的影响,强制劳动出现在了处分方式之列。
(2)处分做出方式的慎重化
处分做出方式的慎重程度直接影响了所作出处分的正确率以及适当程度,因此也必然会影响监犯对处分的申诉。《大清监狱律草案》并未对处分的做出主体进行明确的规定,但典狱无疑对其有重大影响。民国二年《监狱规则》虽规定赏罚由监狱长官行之,但在同年公布的《监狱处务规则》中规定典狱须于预订时间每周两次以上招集看守长、医师、教诲师会议监狱一切事务,会议内容即包括在监者的赏罚事项,对典狱的赏罚决定权有相当的制约。此后立法基本延续了这个思路。至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于第79条规定:“减少赏与金超过二十元及慎独监禁超过三日者,应经狱务委员会决议。”{29}将重大处分的决定权交予了狱务委员会,体现了对处分决断的慎之又慎。
纵观整个近代,虽然有所起伏,但从总体上来讲,监狱所采用的处分方式在逐渐减少,尤其是在涉及身体处分的方面,较之中国古代,可以说有了彻底的改观,而在处分强度方面也处于逐渐减轻的趋势。另外对于处分作出的慎重程度则日益加强。在处分的具体执行层面上,从民国二十八年司法行政部第二○五五号训令也可看出其是十分严格的。任何监犯的处分都应造表以存,表内登记也十分详细。除监犯基本信息外,还应将处分原因、处分建议、处分决定、执行日期,执行前后身体状况以及停止、免除执行的情况列入其中,且各项均有负责人签章{30}。这种步步到人的处分执行管理方式也能够保证监犯申诉成功后如有对责任人进行处分的情况,能将该处分确实落实到位。但遗憾的是,在立法中并未对责任追究进行详细规定。
四、评 价
从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的变革来看,虽然具有一定的曲折性,甚至在特定的时期出现了相当的倒退,但其总体趋势是逐渐科学化、完善化的,虽然其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时代的缺陷性,但立法者仍能因时制宜,有所取舍。
1. 受时代所限立法具有一定的缺陷性
美国学者布利德(Allen·F.Breed,1986)曾强调对监狱内受刑人申诉权的规定应具备以下六项原则:一是不论任何的决议,都必须予以正式记录并以书面答复,以显示过程的公正性;二是所有的申诉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回答;三是任何一项有效的申诉程序,必须有外界独立裁判的公正人士参与;四是受刑人及监狱官员必须共同参与设计以及共同行使这项申诉程序;五是所有受刑人都必须能够运用这套申诉制度,而不受到监狱官员报复;六是申诉制度必须能运用到非常广泛的各种事件上,并且有一套明确方法能够决定申诉事件的范围。{31}如果以此来衡量近代监犯申诉权的立法,显然标准过高了,尤其是原则四,即使在今天也未必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原则二与原则六的内容确实应当作为衡量监犯申诉权立法的标准,而未能实现此二点也是中国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的最大败笔。
对于原则二,申诉应当在一定期限内答复。申诉的目的之一应当是实现正义。然而迟到的正义非正义,鉴于申诉权的主体监犯的特殊性,其大多数在监时间是有限的,也鉴于其申诉所指向的对象——处分通常所持续的时间也是极其短暂的,最长也不过两个月,且在申诉中并不停止处分的执行,那么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申诉结果,监犯的申诉就失去了其价值。显然近代监狱立法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均未规定申诉的答复期限。由此又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后申诉成立,如何弥补监犯因错误处分而造成的损失?这一点也未有法律规定。由此可见,未规定答复期限确实是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的一大败笔。
对于原则六,申诉必须能够运用到非常广泛的各种事件上,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也并未做到这一点。监犯申诉所指向的对象只能是监犯因违背监狱管理规定而引发的单纯的处分行为,而不能针对赏遇。且不说判断标准带有主观性的赏遇,在赏遇条件有明确的客观规定的情况下,如民国十七年《监狱规则》规定救护人命或捕获逃走中之在监者得赏给二十元以下之金钱{32}。如若监犯达成条件而未能得到该赏遇,而监犯对此没有申诉权得不到救济,该法条在实践中的效力也就成了问题。同时,根据民国时期实行的行刑累进处遇制度,监狱将对犯罪人的日常改造进行考核,监犯的赏与罚均影响监犯的分数与定级,进而影响监犯在监期间的权利,甚至影响监犯的刑期。如果不当赏、罚不能得到全面、有效救济,必然会导致监犯权利受损的结果。在假释问题上亦如是,民国十八年《假释管束规则》规定假释者违背相关规定,司法行政部可撤销假释。这种撤销行为其实是对假释者的处分,但其也不可申诉。假释犯虽已出监,但其刑罚并未执行完毕,因此在广义上也可划入监犯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近代监犯申诉权确实在范围上过于局限。
当然在此之外,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也还存在其他问题,但以上两点确为最大败笔。虽然导致这些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立法技术的不成熟等,但我认为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即近代以来中国“旧有道德趋于崩溃,西洋法制精神尚未建立,兼之内乱外患,天灾人祸,相洊而至,犯罪有增无已,致各监所,咸有人满之患。”{33}犯罪人众多必然导致申诉数量庞大,而监犯申诉的处置主要依赖司法官吏,中国法制近代化时日尚短,培养司法官吏之数量整体处于不足状态,而相较于审判等司法需求,监犯申诉的审理之需求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所能分得资源更加有限,两相矛盾之下,申诉案件之堆积拖延已成必然,在明知无法完成之下规定申诉答复时限也就没有意义。同样基于监犯人数与司法官吏数量上的矛盾,相对于不当惩罚带来的直接损害监犯权利的后果,不当赏遇的损害则相对曲折,法律也不得不基于轻重缓急有所取舍。但是,立法者也并非坐以待毙,随着立法技术的成熟,对监犯权利的保护也转向多样化。
2. 以目的为导向从全局角度对立法进行调整
自《大清监狱律草案》第16规定“有不服监狱官署或巡查官吏对于申诉之裁决者,许其抗告于司法部,但司法部之裁决则均有最终效力”{34}后,民国二年、民国十七年《监狱规则》均对此予以继承,对于监犯不服申诉裁定的,均许其再诉于司法部,而不服军人监狱处分的申诉的裁定准诉于军政部。在此阶段,对于监犯在监权利受到侵害最重要的救济方式就是申诉,因而立法者对监犯申诉权予以重视,允许监犯对申诉结果予以上诉。实际上就形成了监犯对于监狱处分不服的二级救济体制。这样的立法对于监犯申诉权来讲无疑是有利的,给予监犯二次申诉的机会,更利于保障申诉结果的正当性,进而保障了监犯的人权。
但依据民国二十四年《监狱待遇犯人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5条之要求:“执行惩戒之前对于人犯应有精密之审查,并使犯人有辩护之机会。”{35}民国三十五年《监狱行刑法》虽仍采用了监犯对监狱处分不服的二级救济体制,但取消了监犯向司法部再次申诉的权利,而改为在向监犯告之惩罚后允许其解辩。虽然单从监犯申诉权立法上看,申诉机会从二次变为一次是对申诉权本身的削弱,可以说是申诉权立法的倒退,但由于之前监狱立法均规定在监犯申诉期间处分不停止执行,因此无论申诉是否成功,在其申诉结果得出前监犯实际上已经开始承受监狱处分,并且鉴于监狱处分期通常并不长,很有可能处分已经执行完毕。而按照《监狱行刑法》的规定,监犯在解辩前并不执行处分,而视其解辩确定是否具有免于执行或缓于执行的情节而确定处分是否执行,这就将对监犯的救济变为处分前、处分后各一次,一方面减少了监犯承受错误处分的机率,另一方面,通过将对监犯情况更为了解的监狱纳入对监犯施以救济的主体范围,在并未减少监犯得到救济机会的前提下,减轻了单一申诉对司法资源的消耗,以便为更多监犯提供救济。这样的立法修改,通过对监犯申诉权这一单一制度完善度的适度牺牲,换取了在总体立法层面的合理性的提升,并提高了司法效率以应对司法官吏不足与监犯超员的矛盾,无疑是更为合理的,体现了立法者的智慧与全局观。
虽然近代监狱法多有修改,同时监狱相关立法层出不穷,监犯申诉权却始终存在于作为监狱相关立法的基本法的监狱法之中,并且始终居于总则之地位,确实表明了统治者对监犯人权的重视和改革传统监狱的决心;虽然在清末及民国的监狱中存在与法律大量相左的情况,但制度的完善是现实状况改进的前提,毕竟只有在可以得到可靠救济的情况下,权利的行使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法律也才不是一纸空文。在立法应时而变的基础上,做到立法先行,是近代监犯申诉权立法应当为当今中国所借鉴之处。同时更为当今所欠缺,更应当为当今所学习的是,在总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任何立法与法律修改都不以一单一制度之完善为目的,而应明确立法目的,从大局出发,以立法为导向,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近代立法者的法律理念。
注 释:
{1}肖士杰:《清末监狱改良》,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页。
{2}杨春福:《权利法哲学研究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6-101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http://www.gov.cn/flfg/2012-03/17/content_2094354.htm.
{4}肖胜喜:《略论我国罪犯申诉制度的完善》,《政法论坛》1990年第2期。
{5}李银波、李志民:《〈监狱法〉与现代化文明监狱对人权的保障——关于罪犯申诉权保障的法律思考》,《政法论坛》1995年第6期。
{6}{12}{15}{22}{23}{25}{3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大清监狱律草案》,《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上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08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09、228页,第227页,第209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军人监狱规则》(民国十九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8}郭嵩焘、刘锡鸿:《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王立诚遍校,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33-334页。
{9}(日)小河滋次郎口述,熊元翰编:《监狱学》,易花萍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6-287页。
{10}薛梅卿、叶峰:《试谈〈大清监狱律草案〉的立法意义》,《政法论坛》1987年第1期。
{11}{31}王效:《台湾地区“监狱行刑法”评述》,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页,第12页。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监狱规则》(民国二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1页。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羁押法》(民国三十五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监狱处务规则》(民国二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164页。
{17}{32}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监狱规则》(民国十七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11页,第18页。
{18}{19}{30}河南省劳改局编:《民国监狱资料选》(下),开封市:河南省开封市新新造纸印刷厂,1987年,第4页,第319页,第385页。
{20}{35}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监狱待遇犯人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民国二十四年),《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95-102页,第101页。
{21}{28}{29}《监狱行刑法》(民国三十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编:《中国监狱史料汇编》(下册),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年,第33页,第43页,第43页。
{24}{27}薛梅卿、杨殿升等编:《清末民初改良监狱专辑》,北京:中国监狱学会,1997年,第449-450页,第207-209页。
{26}张秀夫:《提牢备考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33}孙雄:《监狱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页。
The Legislative Research about the the Prisoners Right of Appeal in Modern Times
FU Tong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prison law holds a special position. From SHEN Jia-ben,the legislators made a series of prison law,trying to build the modern prison law system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unishing and educating crimmers based on the reinspec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establishing the prisoners right of appea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safeguard human rights. The right of appeal allows the prisoners to complain about the illegal punishments that the prison officers did,and it is the main remedy way for the prisoners human right.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risoners right of appeal has gone through a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It was more reasonable in many respects,such as the subject of the right,the procedure of appeal. And oriented by the legislation,the judicial resources were allocated effectively.
Key words:the prisoners right of appeal;The Prison Law of the Qing Dynasty(rogation);the rule of the prison;the prison execution law
(责任编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