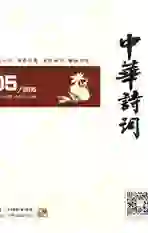诗的对话
2015-09-15刘征李树喜
刘征 李树喜
小引
刘征:李树喜君同我相交已近四十年。先是文字往来,后来相识,交往更多。笔口所及,总离不开诗。
不过,谈一时之感,尽一时之兴,信马由缰,口无遮拦,相视而笑,过则忘之。李君是有心人,把我们的谈话,摘录或记录下来,集腋成裘,至今竟有两万字之多。拟以付梓,李君要我写几句话。
东坡题画诗道:“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这堆文字中,虽然没有什么真知卓见,却保留着诗人的“无人之态”。读者游目之余,如能引出一二关于诗的思考。我们会感到望外之喜。
2014年夏刘征书于潮白河畔时年八十有八
何为诗
树喜:有一天深夜,敢峰(著名教育家、哲学家)老先生发短信给我,只有三个字:“何为诗?”深更半夜,可见其思也深。我抛开字典定义,率意答之日:人间万象,胸中块垒,兴观群怨,感之为情,发之为诗。赞之为歌,悲之为哭。皆本性之释放、心灵之呐喊也!还附小诗一首:“友人问我何为诗,身在其中心自痴。百感茫茫连广宇,为民歌哭是男儿。”当然,这是我一己之见。
刘征:抛开定义,每个人体验和表达不同。我换一个角度说,诗是心的音乐。心是什么?是主观对客观的真实感受。这感受中最激动或最宁静,最深邃或最清亮,最雄浑或最飘逸,如管如弦如钟如鼓的一部分,若是得到艺术的体现,那就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是诗。
取法乎大家熟读多做
树喜:做诗有什么诀窍,讲究什么章法?
刘征:我少年时的启蒙老师贺孔才先生说,“学诗之道无他,取法乎大家,熟读多做而已”。取法大家很重要,有起点和视野的问题。他让我从杜诗学起。
要我谈诗的章法,实在谈不来。一定要说几句,那么,大约也只是“熟读多写”四字而已。多读些好诗,用心体会;多写些东西,自己总结经验。而文艺学、文章作法之类,实在没有什么用处。大体说来,积语于胸,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就好些;本无想说的话,或略有几句,却极力铺写,敷衍成文,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淡而无味。如是而已。
诗律非铁律
刘征:视诗律为铁律,乃唐以后特别是明清科举影响所致。某些“冬烘先生”借以吓人。出格在唐诗中并非罕见,这固然与当时“近体诗”格律在形成的初期尚未完全凝固有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诗人吟诗以充分表情达意、创造意境为主,不斤斤于格律,绝不以词害义。唐诗中有大量合于格律的好诗,也有不少不尽合格律的好诗。此类诗并不因其失律而减色。由此可见唐大家对待格律“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气度。当非常佩服《唐诗三百首》的选家,在清朝中期,诗律已被科举弄得不得丝毫松动的铁律时代,竟然有如此法眼。
爱国与忧民
刘征:诗的现实主义,就是关注社会和民生。很多社会或国家的大事件、大变化,我这里都有诗,比如抗洪、抗震、非典(非典我写了好多诗),还有每一次评选感动中国人物或者最美人物的时候,我都激动不已!这种“感动人物”我作诗起码有十多位。有一次我写了这么一组诗,孙轶青先生看到之后就非常赞赏,就要在《中华诗词》发表,还写了《编者按》。我们这些人——孙轶青、侯一民同志是同龄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好像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已经变成自己的血肉。国计民生大事,岂可袖手旁观!
拒绝陈套
刘征:《人间词话》说:“四言弊而有楚辞,楚辞弊而有五言,五言弊而有七言。古诗弊而有律绝,律绝弊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日多,自成陈套……”兴弊之说尚须商榷,不在本题之内。而陈套之说极当引起重视。
诗词有几千年历史,作者如林,作品如山,讲究日多,格律也日繁琐。从事当代诗词创作首先遇到这个难题。怎办办?深入其中,掉臂而出,法古不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入虎穴是为了得虎子,不是为将虎穴中的垃圾一起接受。古人留下的种种规矩,有的本来就繁琐,有的已过时,如果一一奉为金科玉律,那就真的自缚手足,诗花也就枯萎了。《红楼梦》里,凤姐具体讲述了“茄”的做法,刘姥姥大为惊异。俞平伯先生按照凤丫头的叙述烹制了一番,结论是根本做不出来——茄子在烹制过程中早已经烂得没形了。
不理时尚
刘征:不论作诗还是从事书画,我一向不大理会潮流和时尚,多是我行我素。老了,一支秃笔越加没个遮拦。在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的东西,自然很少流行色。您展卷之时,或者点头微笑,或者摇头皱眉。那使您高兴或者惹您生气的是什么?那是真实的,我的本色。点题或应景之作,我做不来。往往婉拒。
本色是诗人
刘征:总体来说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我自己说不出。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平民百姓也不需要去归纳他是怎样的人。但是就是一条,我觉得我算不算是诗人呢?陆游过剑门关的时候还有两首诗,其中两旬是:“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国家偏安江南,社稷风雨飘摇,本该建功立业,到前线去作战,他老有这个激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觉得是应该这样。但是想不到怎么就做诗人了?他是为自己的遭遇不平。古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与立言”,立言,就是不得已的一种做法。元好问死后,自己给自己立了一块碑,上写着:“诗人元好问之墓”。我到他的墓前去拜谒过。他的坟前立着两块这样的石碑,怎么回事呢?元好问是金朝的大诗人。他自己写的那块碑后来丢了。好事者后来给他写了一块碑,依然写着:“诗人元好问之墓”。后来农民在耕地的时候发现一块碑,就是他的原碑,也立在他的墓前了。他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是有亡国之痛啊,不想写别的。就像陶渊明,晋朝亡了以后,他记时间仅书甲子,不写年号了,这都一样。
诗是今生未了缘
刘征:老了,许多东西都放下、割舍了。但诗心未了,即使手不能写的时候,还能想,还能吟咏。这是我最重要的精神寄托。因为我是诗人。我可以什么都不是,但我是诗人。有这么一个头衔就满足了。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诗人是很崇高的称号,据我所读到的古代大诗人如元好问等,都可以证明他们人格是很高尚的。其诗其人都在九霄之上。最后,我能不能算个诗人呢?这个问题就放在这儿吧。好在我还在往前跑,还要写诗,诗是今生未了缘。今天还不是做总结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