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迦南之地,发现没有“应许”
2015-09-13少远
文/少远
不管是“羁鸟恋旧林”还是“近乡情更怯”,前提都是存在一个家乡,但是读罢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我陷入一种对犹太民族异常体恤的伤感中——作家所书,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除了在茫茫的历史之河中流徙、漂泊,遭受其他文明的屠戮和戕害,还有一重更为深重的“找不到家”的孤独。
这本书描绘了二十世纪在以色列生活的犹太人的复杂面相,他们包括从纳粹的屠刀下逃脱的二战难民,为建设新以色列的理想所鼓动的复国主义者和其他无数普通而有着真实爱憎的凡人。相比呈现在其他文艺作品中被屠杀被迫害的悲苦形象,《爱与黑暗的故事》里的犹太人底色驳杂,他们抱着不同的思想和立场生活在同一片新的土地上,互生龃龉,各自背靠不同的历史,却抓不住同一个未来。
在20世纪前半叶,无数移民乘坐火车、邮轮来到以色列,他们踏上新世界的口岸,以为可以迎来新世界的曙光。奥兹描写他的阿姨踏上这块新的土地时的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欧洲国家,他们被认作暴民,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帮派、气势汹汹的波兰群众,或是一些立陶宛人,都在黑暗中磨刀霍霍,意图杀戮这个族群。
相比复国的愿望,他们更像是被驱赶至这块土地上。奥兹写他身边的犹太知识分子,尊欧洲文化为大,却对这块贫瘠的亚洲土地诸多指责。这个新国家是这样的构成:教授比学生还多,许多在西方文明浸染中长大的犹太人,来到这里,举目四望,却发现没有用武之地,其中也包括作者满腹学识的父亲。奥兹的奶奶,成天对家里的用具进行消毒,因为她认为亚洲的土地满是细菌。奥兹的母亲,最终选择自杀,其间成因,不能脱开她所受到的波兰——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影响,她实在敏感而耽于幻想,不能抵御新国家的粗砺生活。
来到迦南之地的犹太人,不能脱掉他们曾经生长于兹的欧洲的文化印迹,“有一些是厨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托尔斯泰式人物:饱受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备受压抑,对理念着迷。但是所有的人,无论托尔斯泰式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凯里姆亚拉罕,为契诃夫工作”。作家笔下,尽是因为徙居而生的失落感,来到迦南之地的人们发现,随着曙光而来的,是密密麻麻的生活的乌云。而对于在新以色列出身的孩子,父母让他们困惑,因为“几乎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其父母是哪里人,为何来到此地,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
由此,以色列的犹太人对欧洲产生了一种复杂暧昧的态度,他们崇尚欧洲文明的光辉,却又在现实的失落中禁止他们的后代靠近欧洲,奥兹写他的父母禁止他学习欧洲语言,仿佛欧洲是一座极具诱惑力的魔山,如果他“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欧洲”,会“在那里遭到欧洲人的杀害”。在绵延的迁徙的历史中,犹太人对自己的文化母体渐渐迷失,来到新国的人们,找不到应该有的民族认同。
犹太人群内部还呈现了一种“不相容”。奥兹写人群对二战幸存者的想法,“我们对待他们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生发这种情绪是因为“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他们选择坐以待毙等候希特勒而不愿在时间允许之际来到此地,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他们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要是他们不再向我们讲述那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为那边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什么荣耀之事。”这其中是一种对受难者苛责的刻薄,和强行割裂过去的残忍。战争的受难者,从战火和毒气中逃生,却得不到同胞耐心和宽容的体恤,对于他们,这里也没有应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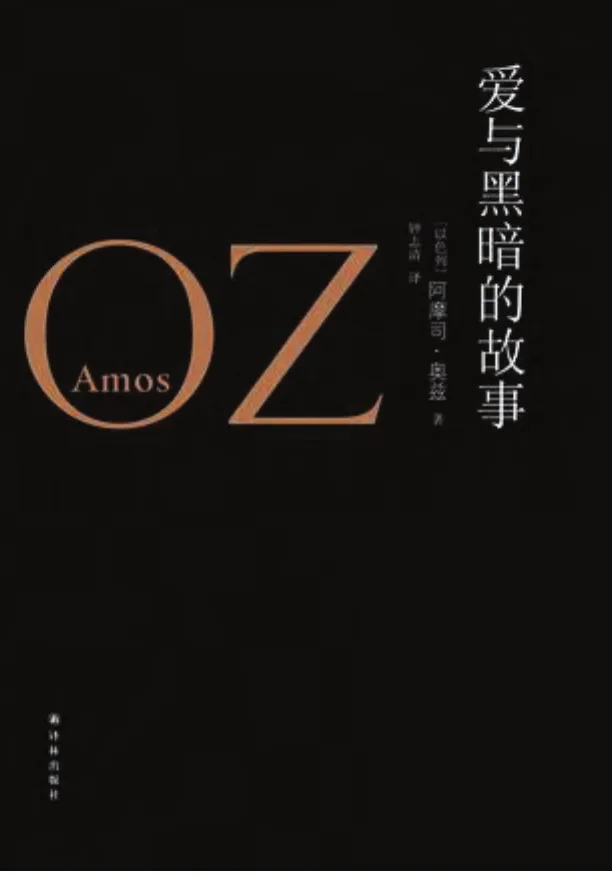
《爱与黑暗的故事》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钟志清 译
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奥兹写他们希望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因为他们的过去是绵延的漂泊和无尽的苦难。但是对于这份“未来”,犹太人内部也并未达成共识。《爱与黑暗的故事》所呈现的,就是这许多种“找不到家”的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