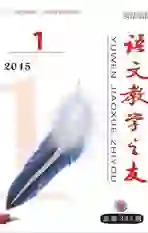初语传统选文阅读教学的陌生化策略
2015-09-10张晓毓
张晓毓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虽历经多次版本和课标的修订,一直是教材选文的中流砥柱。作为文学文化的经典,这些文本肩负着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重任。而在教学过程中,这些文本经过多次咀嚼,教师的教学思维渐渐僵化固定——从作家作品、生字生词,到分层概括、语句赏析和写法总结,模式化的教学不仅难以传达出经典文本的魅力,更会让学生感到单调乏味、渐生厌烦。
俄国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1]对于每一位语文教师来说,从惯常的思维定势中跳出来,寻找新的切入点以实现课堂教学陌生化的效应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将有助于实现深入、持久、高效的阅读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感知兴趣和审美体验,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本文结合教学实践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探究疑点空白,品味语言间隙中的真精神
空白是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文本语言之间的未定性激发我们根据文本提供的线索去进行补充,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语言之间的间隙,探究文本未能尽言的内涵,从而将学生引向思维的深处。
《背影》是一篇典型的传统选文,多年来的教学大都围绕赏析父亲背影的白描语段和“我”的数次流泪展开,以“父爱如山”的结论结课。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过,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应该把眼光放远,“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2]
由于公认文章主要表达了厚重温馨的父爱亲情,我对学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既然大家认为本文渲染父子深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文中呈现了良好的父子关系?从文章最后一段的字里行间,“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学生得出了否定的答案。继而,我提示学生仔细阅读咀嚼在父亲送“我”并买橘子时,关于“我”的心理描写的句子,“我再三劝他不必去”;“我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学生对文本语言缝隙间暗含的父子之间难以修复的矛盾有了更深的感知,这些平淡的语言告诉了我们这是一对爱子情深却不容忤逆的旧式家长和试图反抗父亲权威的儿子。对无法面对面交流的父亲,朱自清只能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只能通过写《背影》这种间接的方式向“大去之期不远矣”的旧式父亲隐晦地传达内心难以言明的情绪——对父亲夹杂着几分怨、些许悔和深沉爱的复杂心绪。
二、材料补充互证,文本间性拓展深广境界
有些传统的重点篇目因其本身理解的难度让不少学生望而却步,我们可以对课堂上学生不易理解、教师难以简单阐释清楚的问题,通过补充教材之外的材料,与课文形成互证,拓展学生认识的空间和课堂教学的有限视界,也可以使平淡的课堂生出思想的涟漪。
《风筝》篇幅虽短,但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初一的学生因阅历尚浅,如果仅限于文本涉及的这些内容,他们很难理解鲁迅先生因小兄弟的遗忘而感到的悲伤、自责和自我反省。
在设计《风筝》这段关于自省情感的阅读教学时,我给学生补充了鲁迅作于1919年的《我的兄弟》。引导学生比较对同一往事的描写。由于前面已经有了关于愧疚心情的铺垫,对比写作时间,学生就能理解鲁迅重写风筝事件的原因——先生对记述当年往事的那篇小短文并不满意,写法上的差异告诉我们,他的心一直没有平静,所以时隔六年,他又一次撕开当年的疮疤。为了将课堂的情感共鸣升华到高潮,我又补充了一个细节,课文下面的时间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1925年的农历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样一个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节日里,鲁迅先生在书桌旁孤灯下将萦绕心头多年的、六年前未能尽言的不安内疚再次书写了出来。至此,学生已经能够清晰地把握文中自省的人生态度。
从小处着眼,学生很容易理解“我”的自省其实是一种兄弟情,从大处来看,因为“我”的深刻自省与小兄弟的遗忘、惊异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差距,在“四面又明明是严冬”的环境里,“我”感到了“无可把握的”“悲哀”,这显然不只是为小兄弟一人的忘却而有所感,学生联系起当时的社会环境,就能体会到鲁迅是为全体被精神虐杀而不自知的国民而心情沉重,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说,这种情感就是一种大爱。
通过整合教材之外的材料,文本间的互证互释将文意梳理清晰,既能为学生搭建了合适的理解台阶,课堂阅读也进入到一个更为深广的理解境界。
三、深入品读诗歌,领悟语体风格暗示的形象
诗歌教学重在让学生充分诵读,诵读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准确地理解诗意。以《木兰诗》为例,比较传统且长期在语文教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观点是将木兰视为经受了悲苦考验的、孝顺的女英雄。大量诵读并深入咀嚼后,我们不难发现诗歌不是强调木兰作为高居神坛的英雄这一面,而在刻意渲染她的平民姿态。诗歌开篇就用了这样冗长拖沓的诗句:“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不厌其烦地铺陈木兰想家:“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使用互文修辞写木兰四处买东西:“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以及回家后亲人出门相迎的场景“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此类的诗句占了全诗的大量篇幅,学生通过反复诵读在体会诗句朗朗上口之余,仔细品味其语言风格,不难体会到诗歌颇具生活中女性口语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特点,而迥异于男性语言的简洁明快以及书面语的严谨理性,语言风格本身也凸显了人物的性格。
木兰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她是巾帼英雄,而文本的悖论就在于成就了木兰英雄地位的战争场面却没有成为全诗的重心,而只用了一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轻轻诠释了战争结果,如果我们只是分析内容与结构,那么课堂仍然是以讲为主,诗歌教学诵读的目标就没有落实。通过诵读体会诗歌语言风格,将有助于学生理解取得功名利禄的木兰不以此为荣,反而以回归家园和女人本色为价值追寻的终点。这首诗歌既在内容层面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去中心化和边缘性特点,也在叙述上实现了对男权中心宏大叙事的消解。
四、重置教学情境,探索启发自主求知的新路
创造性地开展活动、重置教学情境是一种既能有效实现教学目标,又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以蒲松龄的《狼》为例,常规文言文教学的做法是先字句对应翻译,然后分析文章内容,文与言分家的教学方式虽有助于夯实学生掌握文言现象,但繁冗的解词翻译让学生望而却步,难以体会到学习古文的乐趣。创设有趣有效的教学情境,可以另辟蹊径地鼓励学生自主感知古文的精妙。
我为《狼》的课堂阅读教学设置一个故事型的情境:狼族声称有两狼被杀,请求惩办杀狼凶手,假设你就是侦破人员,通过分析蒲松龄所写的案发经过,判断一下两狼之死是死有余辜还是含冤身亡。这样的设计立即就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们通过“止有剩骨”得出这是一个勤劳的屠户,通过抓住“缀行甚远”理解到狼与屠户的“途中”相遇绝非偶然,两狼跟随屠户意图昭然,它们挑起了事端;通过“一狼仍从”,“后狼止而前狼又至”和“并驱如故”,学生认识到两狼贪婪的本性;分析“犬坐于前”、“目似瞑,意暇甚”、“一狼洞其中”这些句子,狼狡诈的特点就呼之欲出了;再分析屠户的杀狼行动,屠户为了扭转被两狼追踪的局面,开始他惧怕并妥协,即“屠惧,投以骨”,在“恐前后受其敌”的情况下,才“弛担持刀”。在这个辨析故事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学生对词语活用等文言现象的理解。
综上所述,传统选文作为语文教学的重头戏,我们的课堂阅读教学必然也必须重视对文本的研读,挖掘文本的“言”外之意和“文”外之旨,增加学生感受文本魅力的难度和时长,这是从教学内容上实现课堂阅读的陌生化;在教法上寻求突破是另一种重要的思路,詹姆斯·斯夸尔指出:“研究文学不仅仅应该考虑到文学作品本身,还应该考虑到学生对文学作品是如何反应的”,[3]品读诗歌风格、创设合理情境等方式可以打破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等刻板教条的做法,使我们的课堂更加贴近学生的学习状态,更好地激发学生理解文本的主观能动性。
————
注释:
[1]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辞典》,第2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2]《季羡林说朱自清散文<背影>》,《名作欣赏》,第2页,2003年第3期。
[3]《青少年在阅读4篇短篇小说时的反应》,(美)汤普金斯等,《读者反应批评》,第2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本论文为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新课改语境下中学教师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培养研究》课题批准号DBG125116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