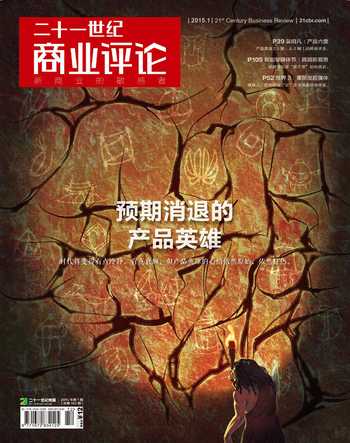高铁浪潮的真正遗产
2015-09-10余健
余健
几乎是在2014年的最后一刻,缄默已久的南北两车同时发布公告——分治结束,“中车”回归。戏剧里的轮回情节上演产业现实版,笼罩着前世今生的朦胧光晕,铁路装备产业的命运已然不由企业控制。
时光回到1996年,原为工业局的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获得铁道部授权成为控股企业,首次体会到政企分开的感觉。彼时“中车”年产值不过200亿元,出口成交额仅1亿美元,它随后被一拆为二,为的是创造竞争。十四年后的今天,南北两车合计收入近2000亿元,海外订单储备达40亿美元,在这高光时刻,生龙活虎的两车又被合二为一,理由是避免过度竞争。反复权衡中,那只“看得见的手”内心似乎并不淡定。
世纪之交,中央政府对企业“断奶”的直接原因,是国库已不堪重负。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并独立脱困,当局则松了一口气。以原中车为例,其收入的95%以上来自于铁道部,而如今南北两车的依赖度已大幅降至50%,原铁道部从“上级机关”转变成“客户1”(两车年报用语)。
尽管刘志军时代的铁道部常遭非议,但“竞争”正是在那个时期烙在了南北两车的骨子里。如根据谈判结果,南车四方厂负责日本川崎E2原型车的国产化,北车长客厂拿到手的则是法国阿尔斯通的SM3。由于SM3结构更为复杂,致使北车在200公里/时级别平台上的进度一度落后于南车。原铁道部自然乐见双方较劲,长客厂只得在较短时间内啃下该车型,如此效率恰恰是竞争的结果。
南车株洲所在电气领域积累颇深,故北车在IGBT变流元器件、网络控制系统等核心部件方面表现出强烈进取心,其目的不外乎是争夺整车成本优势;同样,南车积极重组长江集团也是为了应对北车的货车优势。所以当中铝还在为与魏桥铝业400元/吨的成本差距长吁短叹之时,南北两车已有能力与民营企业贴身搏杀。
过去十年,是铁路装备企业受惠于政府产业政策最大、也是摆脱政府直接干预最迫切的时期。时间将证明,高铁浪潮的最宝贵遗产绝非380公里/时的列车,而是狼性初显的企业群落。具有政策制定者和采购者双重角色的原铁道部,一只手借力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产业需求,另一只手利用采购权优势提高产业竞争,其寻租行为固然令人不齿,但它促进市场竞争的意识与手段仍然值得其他产业政策制定者借鉴。
国内市场尚有“指导价”,当战火蔓延到自由搏击的国外市场,两车争斗升级,显然突破了某些人对“竞争”的心理承受力。垄断地位须通过检验产业集中度和价格控制度来确认,那么“恶性竞争”存在与否又该如何认定?就因为南北两车化身价格屠夫么?华为向中兴与思科都曾祭出价格战,惨烈血拼最终成就了一个让国外对手胆寒的华为。若华为和中兴也是央企,恐怕也早“被”合并了吧。
即便是在美国,前三家机车制造商Alco、EMD、GE经过多年自由竞争才形成目前Alco退出、EMD专注于内燃机车、GE占据全面业务的局面。就目前而言,该国政府尚无意敦促EMD并入GE。
此番南北两车合并,国内竞争的红利损失自不必说,最令人担忧的是公告中强调的“对等合并”。实际上,“对等合并”在世界并购史上可谓声名狼藉: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戴姆勒和克莱斯勒、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阿尔卡特和朗讯等等,无一不以反目告终。相似的实力使得任何一方的头目都难以顺利贯彻其经营意图,甚至会像《操纵交易》一书描述的那样,“高效地变成无领导的庞然大物”。
比如,尽管新中车在国际市场不再会看到其它中国面孔,但它在国内则须在南北两车分别掌握的技术平台之间做出抉择——倘若竞标东南亚高铁项目,CRH380A和CRH380B哪个应该写在标书里?考虑到日系技术与德系技术几无可能融合,新中车领导的拍板很难说比国际客户的选择更为合理。
就像寄希望于国家环保局升格为环保部就能杜绝环境污染,强行合并南北车同样是在用政治思维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市场终会挑出应该留下的企业。如果还有下次,借用一句台词,让市场竞争的子弹再多飞一会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