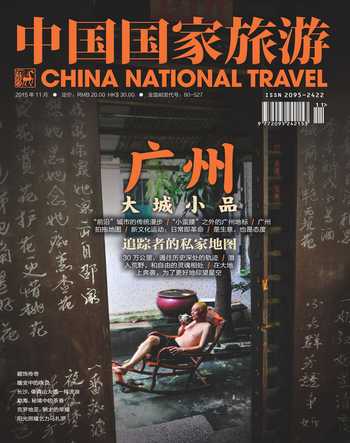藏饰传奇
2015-09-10刘杰文
刘杰文
藏族人爱美,不分男女,无论贫富,身上总有几件珍贵的物件。那些藏族汉子,戴头饰,挂狼牙,腰间一把藏刀,一抬手,腕上很粗的一串包金象牙。女人的装饰就更多了,除了耳环、戒指、手镯,还有头饰、佛珠、腰佩……这些年,大量游客涌入藏地,藏传佛教传播四方,藏饰也随之水涨船高,一颗真的包银狼牙,至少也要两三千元,好的天珠卖到上千万。我的兴趣却并不在此,因为在藏区收山货,天天跟藏族人相处,被藏饰晃着眼,我很想知道,这些藏饰是怎么得来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而我的藏族朋友们,是怎样在极恶劣的环境里,将一片色彩,一块骨头,一串佛珠,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

每当我提起狼牙,藏族朋友们总是冲我摆手,不要买不要买!
他们说,你买的狼牙,十个有九个是假的!狼和狗是本家,牙也差不多,尤其是大狼狗,牙形和狼都是一样的,很难分辨出来。
我问,那你们的呢?
真的!异口同声。
狼牙包银,可以辟邪,是传统藏饰之一,但是就连银店老板都不敢买裸牙。来自鹤庆的杨老板,在藏区经营银店26年,他和同行都是只买狼头,然后亲手把牙敲下来。总有山民走进店里,从怀里掏出一颗狼牙,神神秘秘地做手势:七百。
不买,杨老板说,我不买,管他多神秘。
杨老板只负责给狼牙包银,根据花色、款式和重量,费用从二百到一千不等,包好了再交给山民。至于牙是真是假,只有山民自己知道。
杨老板是鹤庆白族人,他自己也不清楚,祖上是什么时候开始制作并经营藏饰的,至少有好几百年了。他说,老弟你信不信,藏饰包金包银,都是我们做的,从青海到尼泊尔,从昌都到阿里,开这店子的,都是我们白族人!
这手艺,传到杨老板,已经是第四代了。他是地地道道的“老藏区”,穿着极随便,整天灰头土脸的,因为常年拿火枪喷银子,头发喷得枯黄。他总是一边叼着烟,一边打磨。

我散根烟给他:“大哥,我去找牙,你帮我包一下?”
“你?”他抬眼说,“你去哪里找?”
杨老板不知道,包银我不会,爬山我可在行。我走到猎人营地,已经是第四天的下午。这里是梅里雪山腹地,在神山卡瓦格博脚下。迎着雪光往下走,我越走越亢奋。在这里我曾见过好多皮子。有皮,还会没牙么?
走进猎人家,我累得双脚发麻。老朋友了,我喊了声“扎西德勒”,就躺倒在他家的熊皮上。醒来已是傍晚,正值火烧云,烧得雪山上下一片通红。我爬上明晃晃的阁楼,发现前几年的皮子都没了。我问:“大哥,你的皮子呢?”他说:“卖掉了嘎。”
我张开嘴,指着自己的大牙问:“呜呜的那种牙呢?”
他吃惊地看着我——认识了几年,我从来没问过。他说:“要嘎?”
我解释说,想知道那些牙是怎么来的,卖到哪里去了。他最后吐露,“单位上的”收走了——当地人把外面来的人都叫做“单位上的”,一般打到狼或熊,“单位上的”会专程来收,整头运走,但冬天除外,冬天大雪封山,他们才自己收拾。
打狼,要比狼还有耐心。大雪过后,用小羊做诱饵,人趴在雪地的灌木中,一等就是一整天,手脚冻得发木,就翻过身躺一会儿,烤烤太阳,活活血脉。但我等不到冬天,问猎人:“都没了啊?”

刚剥出的饱满狼牙。
“打去,”他说,“今年狼多,咬死好多小羊。”
附近有个草原,被冰川融水滋润着,周围全是原始森林,里面散养着牦牛和羊群,总有狼群伏击它们,先是驱赶,然后围剿,咬死掉队的。可我发现,猎人有些心不在焉,背着鞭炮在草原上闲逛,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不时放几声炮吓吓狼。之前跟他打猎,我只是拍照,这次想看狼牙,就有些心急,不停地望狼兴叹:这可怎么打啊!后来把猎人惹烦了,说我:“只要牙只要牙,坏的嘎!”在猎人看来,打猎只取某个部位,是特别卑劣的做法。他们闲逛只是想保护小羊,而不是存心打狼。
逛到傍晚,云层盖下来,高山牧场,7月飘雪,看样子打猎是没戏了。回去的路上,猎人带我绕道,走向高山营地—— 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他拔掉锁,走进去,拿出两颗牙,抛在木桩上,说:“给你”。
我捡起来一看,是空心的,牙根还有血迹,已经发臭了。
“三岁,”他说,“这狼三岁。”他从牙根扯出牙髓,臭味更重了。
我忍着臭味,擦了又擦,问他,这个,跟狗牙有什么区别?他说,一看就知道。可我怎么看都差不多。我如获至宝,把牙托在掌心,用卫生纸包起来。猎人却不太在意,拍拍我的肩头,笑着说:“走嘎。”
翻过木屋,猎人带我一直爬往冰川。不多久,我们脚下出现一条条蓝色的冰带,藏在乱石之间。他蹲在一块巨石上,指着一个方向:那里!我望过去,有好多个蓝宝石般的小冰湖,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猎人兴奋起来,大踏步跨过去,跳在乱石上,像猿猴跳在树林之间。他趴在一面很脏的冰墙下,拽出一个熊头。
那是一头大黑熊,龇牙咧嘴,像是突然被什么东西压扁了,牙从嘴里爆了出来。
据说,当年这只黑熊下山时不知怎地受到惊吓,伤了人,才被打死。猎人在冰墙下凿出一个冰洞,用铁杆做闸门,一方面可以存储熊头,另一方面也是设一个陷阱,吸引别的动物。这种天然冰箱的保温效果并不好,没放几天就臭味扑鼻。
走到山下的木屋,猎人取来工具,开始敲熊牙。这其实是个技术活,先要用到刀和斧头,最后用铁锥子沿着牙缝小心翼翼往里敲,不能把牙刮破,又要敲掉连带的骨和肉。猎人弄了好久,终于剥出两颗饱满的熊牙。
无论狼牙,还是熊牙,最珍贵的是上牙堂的那两颗獠牙。獠牙很长,牙根很粗,那是它们在野外生存、捕猎的工具。
我拿着熊牙,想着它们生前如何笑傲山林,如今却被我托在掌心,不由生出几分感慨。猎人见我怜惜,笑着说,还有更好的。他从脖子下面摸出一颗更粗大的老熊牙,接近实心,沉甸甸的。他说当时一共有两颗牙,托工匠用红珊瑚、绿松石给这颗包了银,另外一颗给了工匠当工钱。他打猎二三十年,仅遇到这么两颗牙,视如珍宝。
拿兽牙当饰品,是自古的风俗,不只是狼牙、熊牙,獐子牙、麂子牙,以及羚羊头、野牛头等都可以串起来,挂在身上或家里辟邪。有这样一个说法,野兽再凶猛,看到自己同类的牙,也会有几分害怕,不敢轻易冒犯。说得文艺一点,獠牙闪着寒光,几分孤独,几分苍凉,是男人勇气和坚韧的象征。
我们坐在火堆边,谈起兽牙的历史,猎人有几分心酸。过去藏家自己用,也用不了多少,都是就近取材,谈不上买卖,顶多是以物换物,各取所需。现在交通便利了,就有人从外面专程来买。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这里变得非常具体。禁猎、禁枪、保护野生动物,按理都是好事,但如果完全禁止,又不指出一条道路,反而破坏了当地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生态要平衡,猎人也是平衡里的一部分,分寸确实不好掌握。
从山上下来,我走进杨老板店里,像山民一样,掏出两颗狼牙:看看,是真的么?
他看了看,说,真的。我反问,你怎么知道?他指给我看,狼牙又弯又长,牙根粗,正面有V字突起,翻过来有三条血槽,侧面看还有裂纹,有黄色的斑状细纹……
我说:“你很懂嘛!”
“唉,”他腼腆起来,“瞎说,我这是瞎说。”
我叫他给牙包银,他摇头说,你不懂,不能包,要先浸油,最好是橄榄油或护发油,仔细擦一遍,用卫生纸包着,放上两个月,这样才能保证常年佩戴不开裂。
猎人负责取原料,要将原料变成饰品,就要靠杨老板这样的人。拿兽牙当饰品,不是藏族独有,不同的民族要做出不同风格。我叫杨老板用藏银包,“这样才地道嘛。”
“藏银啊,”他笑着说,“你又不懂了。”
杨老板说,藏地产银,但藏银的质地不好。他拿出一块,你看啊,灰色的。他咬了咬,还递给我咬,果然“硬硬的,含银量不高”。
“这个东西,”他说,“好‘蠢’。粗粗的,弯来弯去容易断,做不出细活来。”
很久之前,藏地就有自己的冶炼作坊,但冶炼技术不佳,烧出来是黑乎乎的一块。后来,藏汉交流越发便利,大量含银量高的雪花银涌入藏地,藏族民众也喜欢白花花的真银,藏银由于工艺落后、含银量不高,被迫停产。如今老的藏银很难找到,反而又开始升值了。
我说我不认识老藏银。杨老板说:“很简单,老藏银发黑,由于材料太‘蠢’,做不出太细的花式,你看藏族老奶奶的镯子,几根银丝缠绕在一起,用银块封口,串起来就戴上了。即便有那种老的花式,也都非常简单,几根线条,几朵花瓣,篆刻经文就很难。告诉你,大理丽江卖的老镯子,看起来精美,几乎全是做旧的!”

经杨老板启发,再进山的时候,我开始留意藏族老奶奶们的饰品。看起来确实粗重,常年被汗水浸泡,加上她们不常洗澡,上面总有一层污垢。
一般来说,交流过程是这样的:我竖起大拇指,夸老奶奶的首饰好看,她像小姑娘似的,笑着捂住脸,然后放下手,递给我看,有的还问我要不要,我告诉她,这个升值了,不要卖,可她们还是比划着,问我愿意出多少钱。
藏族女人是真辛苦。经常远远的,看到一大堆柴火在山上移动,走近了才发现,那是背着的干柴淹没了下面女人的头顶。她们老了,还是忙个不停,坐在山路上歇息,仍不忘念经念佛,手中的转经筒和手腕上的镯子,陪伴她们度过了几十年的山中岁月。
城里人的首饰,是为了显示某种地位;她们的首饰,虽然已经发黑了,却仍顽强地戴着,好像只是在表明,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爱美的女人。岁月磨人,不经意的渗透,不经意的点滴,落在镯子上,成了斑驳的记忆。东西旧了,但更有味道,带着备受磨难的时光。
今年是羊年,梅里的转山年,我有幸见到好多来转山的喇嘛。
他们身无长物,只有一串佛珠、一个转经筒,边走路边念经。转一圈会掉几斤肉的山路,他们走了一圈又一圈。我认识一个老喇嘛,已经转了二十多圈(每圈7天),鞋子走烂了,就赤脚而行,他曾踏过无数高山雪峰,眼窝深陷下去,目光却清澈而坚定。
老喇嘛来自川西德格,六十岁了,很瘦,轮廓分明,一看就是那种禅定功夫很深的修行人,只要一靠近他,就觉得安详、庄严。他手持佛珠,走一步,盘一颗,念念有词。问他念什么,他微笑着说,为众生祈福。
我跟着老喇嘛,破晓上路,天黑住下,扎营在大峡谷的溪水边,倾听潺潺的流水声。我们坐在帐篷里,围着火堆,听着头顶雨点拍打篷顶。老喇嘛身无长物,却非常博学,一路上为我开示,讲故事,并告诉我一些修行的法门。
火苗的影子在帐篷上晃动,他手里的佛珠发出幽幽的亮光,我问他,为什么要数珠子?
他微笑着说,这也是一个法门,数珠子可以平静心绪,把意念集中在手中,有利于诵经。佛珠是个法器,大都是由菩提子、琥珀、珊瑚、水晶或人头骨制成,都有说法的。

人头骨?
是的,他淡淡一笑,把那串佛珠递给我:这是什么,认得么?
我拿过来,借着火光,手上的佛珠油光发亮,数了数,共108颗,每一颗上面都有一个小眼睛。我说,知道,这叫凤眼菩提。
呵呵,他说,不是人头的吧。他继而解释,修不同的法,盘不同材质的佛珠,修观音法用菩提子珠,修金刚法用金刚子珠,修息法的用水晶珠,修诛法的才用人头骨珠,但是,修一切法都可以用这种凤眼菩提。
我问他,什么叫诛法,你为什么不修?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想到什么,长叹一声,说:“这个不能修啊,诛法是降魔的,杀气太重了,修了诛法,一言一行都必须谨慎,不能发脾气,对人一发脾气,那人马上遭殃,罪孽啊。我有一个师兄……算了,不说他了,总之不能修。你若见到人头骨的佛珠,尽快避开就是。”
我曾在藏北草原见过有人用人头骨的佛珠,原来那人修的是诛法,听大师这么一说,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拿着佛珠,问他,那您的这个是怎么来的?
他说起一段往事。他的上师,是一个活佛,和蔼可亲,慈悲为怀,待他如慈父。“文革”时期禁止念佛,上师过得十分艰苦,乞讨回来一点食物,自己舍不得吃,喂给他吃,并偷偷教他念经。有一次,上师的朋友去世,上师偷偷为故友诵经,被人发现了,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深夜咳醒了,咳出血来,弟子们看得眼泪汪汪。但上师不仅原谅打他的人,还要为他们祈福,消除罪孽。上师说,我是不会死的,你们也不要哭,这不正是最好的修行时机么?
“文革”结束后,上师传播佛法,成为川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之一,他把所有供奉都用于修建寺庙、学校和道路,自己仍然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过着极清苦的修行生活。一天下午,上师忽然叫弟子打水过来,他要洗个澡。弟子们很吃惊,上师一般是不洗澡的,是要出远门?上师换上干净的衣服,平静地说,你们都过来,我要走了。他画了一个圈,说,这屋子里的,都送给你们吧。弟子们这才明白,上师就要离他们而去,突然失去指引,个个泣不成声。上师竟然咯咯笑了起来,说,不就是在等这一天么,你们用不着替我难过。他这一世,只有经书、佛珠、唐卡、转经筒、僧衣和一些简单的用具。他一件件地交给不同的弟子,嘱咐他们各自好好修行。原来他早就算好了,根据每个人的修行法门,赐予不同的法器。明白了上师的良苦用心,弟子们更加悲伤,同时又充满了信心,因为上师是这样的来去自如。上师当晚入定,就这样走了。
诉说这些往事,老喇嘛双眼含光,不是悲伤,也不是感慨,而有一股平静的力量,河水般缓缓流动。这串佛珠,传承了好多代,浓缩了历代上师听到、看到、经历过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佛珠,让弟子觉得上师与他同在,就在他的心中,没有一刻离开过,指引他走向更高的境界。
老喇嘛告诉我,藏族人向死而生,直面死亡,研究死亡,活着就是为死亡做准备,为来生做准备。生活即修行。所以,很多藏饰,伴随人们生活,其实都是法器。天珠、菩提、蜜蜡、珊瑚、绿松石……无论价格多高,都只是在提醒每一个人,人身难得,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只有你心中有佛,它们才有独特的加持力。
布达拉宫
看藏族珍宝,最好的去处当然是布达拉宫。浩若烟海的珠宝中,不要错过那些用珠宝堆砌、但比珠宝还贵重的文物,比如8座用纯金包裹的灵塔。灵塔是历世达赖埋骨之地,塔内、塔外布满奇珍异宝。五世达赖灵塔塔高14米有余,耗黄金3700公斤,镶嵌各类钻石珠宝约两万颗,藏族人称它“赞木林耶夏”,意思是价值抵得上半个世界。此外这里还藏有释迦牟尼舍利子、用8种珠宝所做的颜料写成的七彩《丹珠尔》经书等珍贵藏品。
帕拉庄园
过去西藏五大第本家族之一帕拉家族的主庄园,位于江孜县城西南约4公里的班觉伦布村。第本家族是仅次于达赖喇嘛世家的贵族,地位很高。帕拉庄园中留存有贵族男女佩戴的各色饰物,珊瑚、绿松石、珍珠、金银器等不一而足,并保留有经堂、会客厅、卧室等生活场所,可以立体地感受旧时西藏贵族的生活。
特别提示
在藏区旅行,遇到心仪的藏饰,要特别注意:
1.不可指指点点。可以先竖起大拇指,夸赞一番,经过对方允许,再拿来观看或拍照。
2.藏族朋友喜欢交换,如果互相有看中的物件,交换之后有情谊,最好不要直接购买。
3.在藏族朋友手中购买佛珠,最好自己也佩戴一串,这样对方会认为你也信佛,佛珠卖给你也是一件好事。
编辑 陈曼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