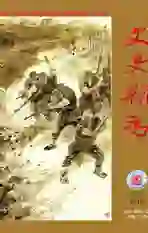屈原为什么要自沉汨罗江
2015-09-10肖燕
肖燕
战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在今湖南省的汨罗江自沉身亡,时年六十有二。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实是由探讨角度的分歧所致,如思想道德的角度、心理倾向的角度、政治人格的角度等等。总括起来,主要有五说:
一、洁身说
此说以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为代表。姜亮夫说:
屈原的个性是痛痛快快,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隐讳,虽然含糊隐讳,到最后也含糊隐讳不下去了,便跳水自杀。屈原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这个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阳,我是楚国的宗族。我又有这样的修养,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我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个人是光明磊落的,没有一点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这是屈原最高的理想。
潘啸龙在《从汉人的记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也指出:
屈原痛君不明,不忍见到楚国的前途败送在“倒上以为下”,“变白以为黑”的旧贵族党人手中;加之长期放逐,身心交瘁,再无重返朝廷、实施理想“美政”的一线希望。为了保持清白峻洁的操守,捍卫自己所毕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庄严宣告:“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终于带着不尽的遗恨,怀石自投于汨罗江中——这就是诗人在绝命词《怀沙》中,对于自己为何沉江所作的愤懑自白。熟悉屈原诗作的人们,耳边不还至今震响着这位爱国诗人的铮铮遗言?
在该文里,潘啸龙还强调说,至于屈原最终的自沉汨罗,虽然不是因为白起破郢而“殉国难”,但他是愤激于壅君佞臣的不识忠良,祸害国家,不忍心看到自己热爱的祖国将再次遭遇比怀王失国还要危险的祸难,才愤然投江的。这样的死,当然不是怯懦或逃避对祖国的责任。他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拼将一死,以期用“忿对沉江”的激烈举动,震醒壅君的昏聩,震撼人心离散的楚人;同时表达对于党人群小误国殃民、迫害忠良的抗议。这样的死,乃是出于对楚国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担忧,出于对宗土、百姓的热爱。当然,他的自沉之举,也表明诗人在理想破灭后的无奈与绝望。
二、殉道说
此说以曲沐为代表。他在《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载《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里说:屈原是第一位自觉的也是自杀的诗人。曲沐又引李泽厚“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采绝艳’的头号主题”为证,接着曲沐写道:
屈原的自杀无非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刚直,是生命在与现实的撞击中而毁灭。林黛玉的自戕何尝不是如此。屈原是出身于华族贵胄的政治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复存在。当着怀王、顷襄王这样的昏君、庸主,其怀抱与志向无法实现,加之群小的谗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言而齐怒”,因之愤懑不平,牢骚罹忧。……班固还批评他“愤怼忘身”,这说明屈原具有忘我的殉道精神。
胡学常在《“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理论与现代化》1992年第2期)里转述该学术讨论会部分学者的观点说,屈原的政治人格意义的影响决不亚于文学等方面,崇圣与忠君的冲突表现出了屈原的政治人格,他所孜孜追求的正是这种政治人格的完美和一贯。屈原的政治人格的伟大不在于功业与政治认识的超人,而在于他的行为逻辑的统一。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治人格酿成了他自杀的悲剧。屈原的死是他政治人格的升华,是追求理想决心的自我证明,是自我主体意识的壮烈表现。屈原是战国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位别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坚守“人道自任”的传统信奉而对自身“内美”“修能”的不可动摇的认知,义无反顾地坚持理想(“志于道”)并重实践的献身精神以及视利禄功名如粪土,只求楚国强盛继而统一天下的大志。
三、回归说
前述胡学常《综述》介绍了某些屈原研究者对屈原的心理顷向的研究,认为屈原的狂态表现在幻觉、幻视、幻听、孤独症和易装癖等五个方面,还分析了屈原充满悲剧性的双极血缘人格,并指出,屈原的人格精神促使他必然发狂,必然走向悲剧,他的自杀实现了他返本回归血缘的愿望。有的学者还采用西方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屈原自恋的心理倾向,认为屈原总是将自我理想化而自赞自誉自我夸大,这使得他在现实生活中举步维艰,最终导致失败;屈原的求女也是他自大狂心理的体现,其潜在目的仍然在于自恋的满足,而没有多少真正追求异性的诚意;屈原以美人香花芳草而誉自我之高洁,毁世人异性恋之淫逸;屈原出国与留国的心灵冲突在于他去国的瞬间再现了“初度”时与母体分离的焦虑;屈原的投水自沉,实现了他回归母体的愿望,意味着自我的再生。
四、尸谏说
此说以王之江《屈原之死刍论》(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为代表。在该文里,王之江认为,楚国“党人”横行,摇摇欲坠。屈原被流放,不能生谏楚王。但他忠心未泯灭,没有办法使楚王觉悟,只好采取尸谏,投水而死。
杨剑宇也在《千古之谜》(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里转述学术界的“尸谏说”观点,称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而当时的顷襄王已经忘却了疆土被蹂躏、父王被骗拘死于秦地的国耻父仇,反认秦为友,又“专淫逸侈靡”,“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国内奸佞弄权,城池不修,百姓离心,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国已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拯民之志的诗人却受谗言而身遭黜逐,报国无门。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启用的希望已经绝灭。身心交瘁的诗人不忍心眼见祖国和人民蒙难,也不愿在衰志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怀沙》中斥责了楚王的昏聩,在《惜往日》中写下了“宁溘死以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的诗句,决心以死谏来震醒昏聩无能的庸君,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两次长时间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绝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蒋建平亦在《千古之谜》中转述了类似观点,但稍有不同是增加了屈原效法彭咸一说。此说因屈原《离骚》中有“愿依彭咸之遗则”而生发,并引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彭咸,殷贤士大夫也,其谏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为证。此说认为屈原依彭咸的遗则,是指彭咸投江,屈原最后也选择了投江的道路。《离骚》篇末,屈原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对此,王逸特注:“我将自沉汨渊,从彭咸而居处也。”所以,此说指出,屈原之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
五、殉国说
此说在早以清初王夫之为代表。他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见国亡而殉国难之举。
此说在现代则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里如是写道:
屈原既活到了六十多岁,他的流窜生活已经经过了很长久,然而他终竟自杀了。自杀的动机,单纯用失意来说明,是无法说通的。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强的人,而又热爱祖国,从这些来推测,他的自杀必然有更严肃的动机。顷襄王二十一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那时,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顷襄王君臣朝东北逃难,在陈城勉强维持了下来。故在当年,楚国几乎遭了灭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
郭沫若还在《屈原考》中进一步发挥说:“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流离颠沛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他认定:“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王夫之,郭沫若的“殉国说”,可谓深入人心,并特别为一般群众所理解与接受。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