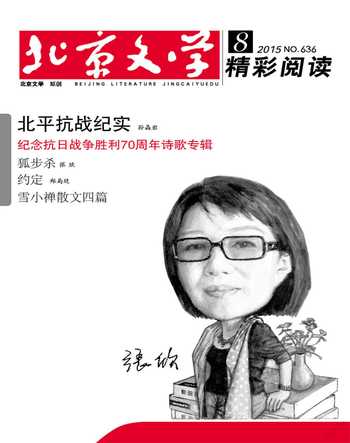在红尘中安妥灵魂
2015-09-10钟晓毅
钟晓毅
在万丈红尘中安妥好灵魂,这看似艰难而吊诡的命题作文,张欣孜孜不倦地做了足足30年,她所有的都市言情,都是想在万丈红尖的喧哗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如今,凭着她一点点水滴石穿的坚持,她成全了她的读者,也成就了她自己。
在当下,我们已无可置疑地处在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曾经拥有的已然丢失,不曾想到的却一下子就在面前。在快速变化的都市中,似乎每个人都惶惶不安。
“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的情怀已少见;“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风景也难再现。
每一个人都在匆匆忙忙地走着,梦想难以梦想的,追逐难以追逐的,永远在路上。
我们的小说家便也一下子陷入了是融入还是逃离的困惑中。
在一种急遽的变动不安中,要继续写作,小说家必须给自己一个明晰的命题,并且看自己的意向是放在大众接受的层面,还是只是私语性的放纵上。并不是别无选择,但每个人都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中寻找自己的选择,个人的真正成功只有选择那种超越个体感性的价值理想,让人类生活依其内在固有的辩证逻辑向前推进,生命才会灿若春光。张欣努力的结果完全可以对应那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跟张欣交往了多年,每次见面,都会谈到文学,但又从来不感到矫情,因为彼此都很真诚,并且是真的很知足于在年轻的时候就跟文学相遇,并缠绵到如今。最近的一次约会是在仲春的二沙岛御珍轩品茗,还是离不开这个永恒的话题。窗外的二沙岛是广州一个最美的小岛,它就在市中心,一样的人车喧哗,红尘处处。但这里那里,或者说是骨子深处,总还存留着许多优雅、安静的所在,星海音乐厅、广东美术馆的音乐声声和流光溢彩,留住了时间的脚步,也留下了生命的活泼和灵动。相信这里是张欣最喜欢的流连之处,一步出去就可以红尘万丈,笙歌处处,而往花木深处一藏,又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在这样的进退自如中,她将触角伸向了社会与时代,渴望为现代人无所依附的心灵找到一处安稳的归宿。
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借助天时、地利、人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张欣,一路走来,她那闪烁着亮色的作品都延续了广东文学积极向上、格调明朗的传统,但她又是一个“正面强攻型”的作家。作品的触角一直抵及时代的尖端之处,在小说领域里对现实作直截了当的发言。她是都市故事最好的叙述者,她从流行的爱情小说模式嵌进了广阔的社会写实小说的时尚潮流中,视域开阔而有纵深感,叙述清新质朴而又富于变幻,题材广阔,文笔洗练,情感饱满,细节生动,人物如画,煞是好看。虽然至今仍然有人对她的都市小说低估得厉害,这其实亦更证明了她的超前性和独到性——她就是那么一个曾经在都市文学创作的认知上领先了至少一个身位的广东作家。
最喜欢她的坦率。她从来不作,她会很老实地承认:
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当然我也对沦落街头的人深表同情,对失学儿童捐款热心,痛惜妙龄女郎因物欲所惑委身大款,总之我活得至情至性。而文学是离不开生活的,我也只能用我的眼光和角度去取材生活,尽量做成一盘好菜。
她还说过:
广州实在是一个不严肃的都市,它更多地化解了我的沉重和一本正经。
但其实,正是张欣熟知市场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都市生活的物质性、包装性、流动性与幻想性的万千变化,她近期的作品,重组了一个都市的独特星空。她不仅看到了都市生活张狂、激烈、焦虑、迷失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都市旺盛、充满活力的发展,并从其乐观积极的发展中展现繁荣的景象。所以,她的写作,并不是想对都市人进行气宇轩昂的教育,而只是“能为他们开一扇小小的天窗透透气”。她看到了物欲横流的丑恶,然而并不认为已发展到需要大家伙去壮烈献身的程度。她发现大家其实都在红尘中奋斗,与其冷眼看人生,不如换一副心肠去理解红尘中的悲欢。她觉得文学当然不能无病呻吟,但也不能把它们拔高到都是“精神圣地”。她是以一种轻松好看的笔调,在叙述中暗藏反讽机锋和对流行时尚与术语的应用自如而又随时嘲弄的行文风格,赢得当下读者的好感。
是的,在还没有多少作家去观照都市生活的正面价值时,张欣已用她的写作实践在思考如何把现实发展中的都市,与文学经验中的都市表现出的正反两面——乐观积极与悲观彷徨的两种矛盾特质,较好地融汇在一起,创造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当代都市形象。这确实难得。虽然在西方的文学经验中,有“文字的都市”与“真实的都市”这两个辩证的概念的划分,认为“文字的都市”往往表达一些作家无法对读者直接表达的概念,也就是一些隐藏的概念,因此,“真实的都市”和“文字的都市”之间的联想,是有些迂回、复杂的,作家必须从他们所欲表达的真实都市中的某些经验或理念里,去设定文学符码,或者经由对城市景观的转化与隐喻性过程,以传达作家所要表达的城市意象。这种重新书写的城市意象,展现了“真实城市”与“文字城市”之间的张力,同时也可能彰显另一个“看不见的城市”之情景含义。这些理论主张,若落脚到了中国的新时期都市文学创作实践中,我以为张欣是有前行者的贡献与担当的。
张欣写都市,有着对这一种人类自己创造的生存环境非常独特的感受,并把这种感受有效地转化为小说语言,在文字与节奏上的特殊处理,让人在一种绵密的行文中感受到文本所想控制达到的那种空间效果。她尤其擅长在对都市的困惑与迷惘中,站在“人”的立场上,弘扬“人”的精神,确立“人”的价值。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但人还需要进化,文学应当成为“人往高处走”的一种精神助力,成为人上进的精神灯火。更主要的是,她对“人”有信心,对于人走向美好实现人创造美好价值的努力有信心。人往往是处在一个“坡”度上的,如果不能说不进则退,那么,起码可以说不努力上进便会止步不前。人的心灵中也有一盏灯,点亮它,人的心灵空间就极为广阔,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就会明朗,人就会走向高尚和美好;熄灭它,人则会在难以自拔的狭隘中,在阴晦不明的黑暗中迷失。由是,精神是人的灵魂,精神的健康才能使人对“人”充满信心,使人对于真善美充满热情。在某种意义上说,张欣可作这样的“点灯人”。
一直以来也不乏议论之声,张欣应该也常常遇到浮士德所说的那种情形:
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一个正想同另一个分离/一个沉浮在迷离的爱欲之中/执着固守着这个尘世/另一个要猛烈地离去凡尘/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
但张欣有她的坚持,岭南30多年来醍醐灌顶的骤变与风雨历程,改革开放的多种实验,切实生动,使她避免了对某种写作态度的单纯依赖和执迷不悟,什么样的尝试不可能呢?写作又不是偷尝人类智慧的禁果,那么,写作只是为热爱它们的人们的存在打开方便之门罢了。什么样的血液里流淌着什么样的文字,重要的是对人生、对人、对社会以及大化沧桑的独特体验和领悟罢了。就作家而言,写这样固守着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固守着自然状态的人道民生而自得其乐,无非是以这种方式痛痛快快地舒一口气,放松甚或放纵一下自己的精神。就读者来说,读这样的作品,也无非在山林中突闻一阵清气,在片刻间消尽了鄙吝之心。
张欣的故事编得跟她的人一样,实在好看,“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她尽心于用纤弱的手掌抚遍都市男女的千姿百态,用敏感的心灵体悟人生的岁岁年年,让人不会错过每个微小的细节,也难以放过那些尖锐而睿智的叙述性文字。她的作品里永远流淌着蜿蜒的生活河流,演绎着纷繁的男女情事。但她就安于一旁,在心中留有一片理想的天空,来容下自己安然的起居和转身。
也正因为她始终持有着一个理想主义者该有的度衡,那么的“爱惜羽毛”,她的作品是不够“狗血”的。有例为证:她的几乎每一部中长篇小说,一出来甚或尚未出版,都会被影视老板们盯上,并在第一时间买断版权,但迄今为止,却只有10多部被改编成影视剧,真正的“出街”了。要领略她更丰盈、更饱满、更富人性含量和审美意蕴的作品,还得钻进她的纸质世界里寻味,这无论是对她还是对大众读者,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相信这些小小的不如意怎么样都不会影响到今天的张欣了,她已把自己修炼得“玻璃心肝,水晶肚肠”,成了一个大大的明白人。做人做事也如作文,看似高冷,实则是有一副助人的热心肠,大大小小的事到了她的手上,总是像她编的故事一样,编出别人惊喜,自己也满意的一份圆满来,颇有铿锵玫瑰的风致,透彻地了解了为什么而活,参透因何,迎接任何。于是,无论人和文,都已朝着“极致的风景”走去。
以此祝福张欣。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