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媒体报道过的仇和
2015-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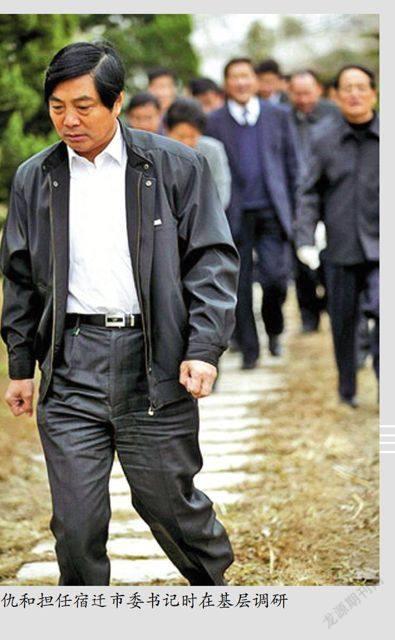
仕途近20年中,他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1996年—2005年 宿迁改革
官场中的“恶人” 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在县城的家里,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萬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以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2003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2000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2006年—2007年 江苏治污
人大代表的印象 尽管2006年1月,仇和即担任江苏省副省长,但直到当年4月,才卸任宿迁市委书记。
在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
在仇和当选副省长的省人大会议上,常州代表团的戎林海等10位代表联名提交了“关注民生,加强水源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确保生活饮用水源的安全”的议案。
南京代表团的阚延静等10位代表同时提出“关于加强我省沿江城市水源水的管理建议”的议案。
这两个议案提出的背景正是2005年11月、12月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广东北江污染事件。
会议结束之后,当时负责省人大常务工作的副主任王武龙,将戎林海等人的议案列为亲自督办,该议案也成为当年的第0001号议案。
这两件议案被移交给省政府办理,并限定在6个月内将办理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出报告。其后不到3个月,戎林海等人被请到南京,参加由省人大召集的议案督办会。
戎林海记得,那次仇和亲自到会,向代表们介绍全省水资源保护的情况,与代表们一道研究目前饮用水源保护的对策及方法。
尽管仇和是按照讲稿发言,但戎林海发现,他还是经过了认真的调研和准备,说话十分实在,态度十分诚恳。此后,江苏环保领域不断出现新动向。
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曾提出,到2008年底前,江苏将关闭淘汰2150家小化工企业,而截至2007年10月31日,仇和调任昆明前不到两个月,全省已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在江苏,化工是重要产业之一,关闭化工厂一直遭到各方抵制。
2006年12月,在省委书记李源潮的支持下,江苏举办了第一期市县领导干部环境保护专题研讨班,在开班仪式上,仇和说,“环保,现在再也不是光喊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的层面了,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定量学习,一招不让地严格执行!”
而2007年5、6月间发生的太湖蓝藻危机,则给仇和提供了一次施展拳脚的机遇。
其后,仇和在治理太湖污染方面的举措不断推出。他提出,在环保上,要从重微观达标转到重总量控制;在市政建设上,工作重点要从保障用水供给转向保障供水安全;在产业发展上,要由重货币化成本转向更重环境和资源代价。
7月7日下午,在三百多位省、市、縣、乡四级主要负责同志的见证下,苏、锡、常、镇、宁五市的市长与仇和分别签订了《“十一五”太湖水污染治理目标责任书》。
仇和的“强” 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期间,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仇和展示出的执行力,在担任副省长期间,更多的人看到了决策过程中的仇和。
仇和依然对数字如数家珍,有人清楚记得,在谈及全省花两到三年时间关闭小化工厂时,仇和放下讲稿,要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四市提前完成关闭任务,他当场将各市化工企业的总数、计划关闭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总数的比重等数据一一背出,并且其间毫无停顿,令听者面面相觑。
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仇和给官员们算过一笔账。
“江苏的土地面积占全国1.6%,耕地面积占全国的3.8%,2005年的粮食产量占全国5.86%,棉花产量占全国5.66%,油料产量占全国的7.02%,为什么我们的总产能够高于我们耕地面积的一倍?是江苏这个地特别肥吗?肯定是肥的,但更多地是靠化肥,靠复合肥,靠激素,靠农药,靠除草剂。否则怎么可能呢?这就表示我们的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乏力。”
在担任副省长之后,仇和的各种思考所得必须通过向上提建议的方式,才能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决策。在这2年间,仇和似乎不仅提出了很多建议,而且屡被采纳,当地政情人士认为,仇和的“说服能力”亦不输别人。
在节能减排方面,2007年11月,仇和担任副组长的江苏省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制订了《江苏省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节能目标评价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市政府,予以通报批评,领导干部不得参加年度评奖等……对未完成等级的企业,对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这些举措尽管是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出台,但都无一例外带有“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影子。
仇和的“和” 早在仇和当选江苏省副省长之初,就有人提出,宿迁市委书记和副省长角色不同,后者更看重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在太湖蓝藻危机爆发期间,仇和展示了他“求和”的一面。
2007年6月初的太湖治污现场会上,仇和本来是最高级官员,但出席会议的省水利厅一位官员却发表不同意见:2007年的太湖水位根本不是50年最低水位,最近5年的太湖水位全部低于2007年,因此不能将水位低作为蓝藻爆发的原因,因而也不能指望引江济太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這和高层的观点不和。当时,太湖出现历史较低水位、气温偏高被认为是导致蓝藻爆发的重要原因,因而从长江引水入太,提高湖水流动性被寄予很大期望。
这位副厅长摆出的诸多困难并非无中生有。从长江向太湖引水的常州枢纽设计时以向长江排太湖水为主,而现在整个枢纽完全是反方向运行,有很大风险。
此外,按国家防总调度原则,从4月1日到6月15日,太湖水位应控制在3米以下,但由于蓝藻爆发之后的调水,从4月1日开始,太湖水位一直超过3米,已突破防总太湖防汛标准。
为保太湖调水,苏州、常州两地的长江引水管道都被关闭,太湖向上海供水的闸门也被关到最小,如持续太久,苏州、常州和上海的用水将受很大影响。
水利并不在仇和分管范围之内,当时一些与会人员开始窃窃私语,但仇和似乎很能接受水利厅的观点,在总结发言时,仇和改变了之前的口径,他说,蓝藻爆发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水不流通,不是水位低了”。
仇和的改变还体现在他对下属的态度上,无论是对省环保厅、建设厅的主官,还是对不在自己分管领域的部门官员,仇和总不忘先强调,“你们才是这方面的专家”,言必称“请教”。
看到这一点,更多的人相信这样的说法:“仇和在改革上看似特立独行,但始终很好地遵守着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比如,他对事很严肃,对人则极具亲和力,跟省里职能部门都保持着充分的沟通。’”
2008年 云南拆城
治滇,先治官 “连昆明天上都没飞过”的仇和,2010年把“仇旋风”从平原宿迁刮到了高原昆明。
滇池污染恐怕是昆明城市建设史上最尴尬的一笔,至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滇池已成一湖污水。
2008年元旦,在昆明市环保局调研时,仇和抛出“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之言,语惊四座。
宿迁之后,仇和曾任江苏省分管环境的副省长,经历过太湖蓝藻爆发,后来亲任太湖湖长。沿用这一经验,昆明35条滇池进出河流都有了河长,书记仇和当河长的标示牌就竖立在盘龙江边,以告世人。
河长也好,湖长也罢,最根本的就是责任倒逼,任何人都难置身事外,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记得,仇和第一次到市文联调研,却指着不远处的滇池说,治理滇池不能慢吞吞的,话音甫落,文联也有了治滇任务。
仇和很急,“在2009年底前,入滇的35条河道河水变清。一年内让盘龙江水变清。”他规定,所有河长每半月要巡河一次,现场解决河道整治中的问题。直到现在,身兼东大河河长的汪叶菊从未感觉轻松,因为仇和已把生态环境指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坚决实行一票制。受此刺激,各河长纷纷想着法子,组织队伍拆除河两岸的违建,搬走水域附近畜牧养殖,设法把污水引入市政污水管线。
两年后,《昆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龚庆萍发现盘龙江水真的变清了。而所谓的投入资金,依旧难敷缺口,很多官员不得不佩服,“仇和书记真不一样!”
然而,还是有人不认同,滇池卫士、2009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张正祥就质疑,“35条河流进滇池的清水,就如矿泉水倒进了大染缸,还是一片黑。”他指责,仇和采取的环湖截污其实是把污水全部转移到金沙江,流入长江了。
截止到2009年,投入滇池治理的经费已达66.5亿元,但水质全年仍是劣五类。
拆字当头的争议 仇和在昆明上任后,没有按前任计划把行政中心立即搬到呈贡新城,而是扭过头向336个城中村动起了刀子。
用他的话说,城中村是顽疾,只要“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足见其铁腕决心。
尽管有人质疑城中村改造背后若隐若现土地财政的影子,但拆字还是转瞬贴满昆明的大街小巷。
仇和还要求城市开发一定要连片、成面地开发,以免新项目只是城中村的“遮羞布”。这多少成了改造扩大化的催化剂。
人民西路94号大院龙斯猷老人曾气愤地指责,云南省广电局生活小区使用不到三十年,就被当做城中村项目要求限期拆迁。2008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竟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被指为拆迁搭车。
一时非议如潮,据了解,2010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位当地官员还记得,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也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打工子弟。
被勒令拆除的还有居民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不少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
为了市容,仇和顾不了那么多。但一纸行政指令仍难抵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不得不节节败退。从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仇和难得遭遇事实上的挫折,一次会议上,他也难掩无奈,“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他自认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比如,他相信,城中村的农民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因为补偿标准高,拆一次,富一截。
昆明市政府有关人士也坦言,书记的想法是好的,也是大家赞成的,不过有些在具体操办中被改走了样,所以他对此也深恶痛绝,多次要求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