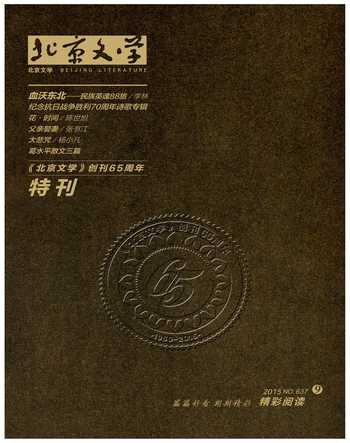头顶一道亮光
2015-09-10赵钧海
闫华内退了。那段时间他忽然对身边的复杂人际关系感到恐惧。正巧要改革——人满为患,人浮于事,轻装上阵,与国际接轨,还要在纳斯达克上市,必须脱去臃肿的外衣。闫华遂心绪有点烦乱。内退是对人生的一次挑战,不少人都焦灼不安,举止反常。我妻子就是例证,那段时间,她天天不睡觉,不做饭,不正眼看我。她手捏一张表格,填完后,一会儿打电话与闺蜜嘀嘀咕咕,表情严肃;一会儿又把表格撕了,哭得伤心欲绝。我和女儿都束手无策,大气也不敢出。闫华也一样,悲戚、伤感、无所适从。试想,在企业干了二十几年,十几岁进厂,刚迈进矫健的人生中年,却突然要退休,你会是什么感觉?
内心波澜起伏。闫华跌宕起伏一阵后,释然了,也随大流,学着同学、朋友的样子办理了内部退养。趁年轻下来再打一份工,或干脆自主创业,说不定也能有豁然洞开的收效。闫华想。他有一中学同学,因对女工耍流氓,闹出乱子,劳改出来后做生意,却摇身一变为闻名遐迩的企业家,常常挥金如土请官员吃饭,有时还让闫华陪酒,很有阔佬的金气。当年那同学极不起眼,时常会跟在闫华后面悄无声息地走路。
工资虽只拿百分之八十,但也有一千多元,比较惬意。不上班有这么多工资,不用看别人脸子,不用想复杂的内部纠葛,生活还随心所欲,闫华心气渐渐笃定。40岁,正值风华正茂的好年华,闫华忍不住偷偷笑过。
年轻时,我与闫华在一个科室,还同宿舍多年,有骨髓深处的透彻了解。闫华搞机务,我搞美术宣传。在一个旧洗澡堂改造的办公室,他在里间,我在外间。机务就是拾掇高音喇叭、小喇叭,维修线路,保养扩音设备,捣鼓录音机、电唱机、播放机等等,有时也帮别人修修半导体收音机,偶尔还会有人扛来老式电子管收音机——红灯牌的。闫华聪敏,执着,还有点小幽默。闫华手拿小焊枪,摆弄着焊丝,歪着脑袋,嘴里叼一支莫合烟,颇像那么回事。那时闫华桌子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小零件和五花八门的小工具,很是引诱招惹女孩子好感,桌边总是缠绕着色彩斑斓的女职工。他一边眯着眼睛抽烟,一边与女孩调侃。闫华调侃比较干净,不低俗,时有意趣与狡黠闪烁,搞得里间笑声一片。外间我和晋新就乜斜着目光看他,他一本正经,装作没看见。闫华好给女孩起外号,诸如稍胖的叫“胖胖”,稍瘦的叫“瘦瘦”,还有“彩彩”“云云”“瓶瓶”“花花”之类,女孩看似挺生气,其实喜欢得要命。他的大烟灰缸就成了女孩们的笑料。一个大罐头瓶,吃完瓶中的糖水黄桃后,就被他当作烟灰缸。闫华烟瘾大,一根接一根抽莫合烟,而且只用旧报纸。先撕下没有文字的白报纸边,待白报纸边撕完了,才用印有文字的油墨地方。他说:油墨吸入肺部有害健康,但烟丝里一点油墨也没有,就像菜里没有放盐,没意思。闫华歪着脑袋卷莫合烟,舌头伸得很长,脸上布满皱纹,其实那年他才24岁。他时常到我桌子上撕报纸,把我的报纸整得狗啃一般。我很无奈。我有剪报和抄写文字的习惯,如贾平凹的《满月儿》、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王蒙的《夜的眼》等等,都剪入我的收藏本。闫华不管,只管抽他的莫合烟。他烟灰缸里于是就黑乎乎的,一层厚厚的烟泥,黑黄发亮,烟头堆积如小山,一直堆到瓶口,实在挤不下时,才倒掉。
女孩们笑着,娇嗔地说,你的烟灰缸太恶心了!闫华就说,味道好啊,打瞌睡时,把它往鼻子这儿一放,马上睡意全无。不信,你闻闻。闫华拿起烟灰缸,追着女孩往鼻子底下放,女孩就哎哎呀呀在办公室乱跑,半高跟鞋敲击得水泥地嘎嘎直叫,弄得旧洗澡堂里浪笑一片。女孩从里间跑到我们外间,又风摆杨柳一样钻进里间,搞得雪花膏气味满天飞。闫华没结婚,围着他忸怩撒娇的女孩真不少。
闫华抽烟让我受了不少罪。他一边抽一边卷下一根,最少一次抽两根。睡觉之前两根,半夜醒来两根,早晨没穿衣服再两根。尤其是半夜,他赤裸上身坐在床上抽烟,黑咕隆咚,一点暗红明明灭灭,鬼火一样,我忽然被惊醒,懵懂中被晃动的暗红吓住,几次都喊出怪异的声音。我再也无法入睡,闫华抽完烟就呼呼大睡了。睁着双眼,闻着烟味,我烙饼似的在床上翻腾,直至天亮。
那时闫华学会了骑摩托车。顶头上司弄来一辆幸福250摩托车。上司酷爱摆弄摩托车。蹲在摩托车旁边,上司摸摸这,动动那,捣鼓很久,然后加上汽油,发动起来预热,嘣嘣嘣吼声响亮。这时,上司才进洗澡堂给我们几个小青年布置具体任务,然后屁股冒烟地上市里游荡了。我们小青年就撅着屁股在家里干活。我们五人,除了上司,其余四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小青年。闫华胆大,就乘上司出远差时,偷偷推出摩托车去骑,不久他就练熟了。有几次,还偷骑到市里兜风,被上司发现,好一顿训斥,骂得他狗血喷头。闫华假装虔诚地聆听,也不生气。没几天,他又偷偷骑摩托车上路了。
后来闫华就有了自己的摩托车,那是在他调入市区之后。早些年,时兴雅马哈,他下决心买了,时髦地在马路上飞驰,像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闫华当然不是小混混,他是离不开摩托车。
那些天,由于无事可做,闫华就被另一些内退的人喊去垂钓,说养身养神养心,还能吃自己钓的鱼。吃自己钓的鱼与吃市场买的鱼不一样,口感不同。闫华起先闪念过做化妆品或倒小孩玩具之类的生意,但总也没考虑成熟,就想先放松一下筋骨,歇息歇息,钓钓鱼也挺好。可一到鱼塘才发现,早有大批垂钓者长期在水边蛰伏着,迷恋很深,快慰已不能自拔。尤其不能谈钓鱼,一张嘴就唾沫星子四溅,滔滔不绝,如入无人之境——水肥水瘦,竿长竿短,钩大钩小,线粗线细,食浓食淡,坠活坠死,立漂碎漂,春钓秋钓等等,搞得初学者云里雾里,自愧弗如。
我也曾被朋友忽悠到鱼塘,撂给一根渔竿,配好钓组,一上鱼就被勾走了魂魄,喜欢得一塌糊涂。男子汉最希望有的搏击与拼拉夺抢,都藏匿在与鱼格斗之中,奇妙、惊悸。但我毕竟上着班,只能休假偶尔为之。
垂钓需要对水情、鱼情、季节、天气、时间、温度、钓具、线组、钓法、钓饵等等有精细研究,才能跻身融入。这些必须在摸爬滚打中自我探索。圈内,常有人说,那小子是身经百战的高手。身经百战,就和打仗一样,要搏击百场战役。战斗中磨砺,战斗中摔跤,战斗中觉悟。
与鱼斗智斗勇,与鱼拉抢拼搏。斗着斗着就恍然大悟了,就明白了,原来你是在与自己斗,斗技巧,斗心眼,斗智慧。鱼不会说话,你其实是在一次次打败自己的过程中,剥掉愚钝,攀登险峰,俯瞰大地。你发现你的收获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鲤鱼,草鱼,鲫鱼,鲢鱼,鲶鱼,黑鱼,鳊花,罗非鱼,黄辣丁,五道黑,小白条,等等,只要一下竿,浮漂一动,你就知道是什么鱼,有多大,该怎么应对。再后来,你就开始向往大自然水域,对家养鱼塘不屑一顾。只有大自然水域的鱼儿凶猛、彪悍,角逐正宗,是博弈的主战场。而且大自然能感受山川、大地、阳光、芦荡、草滩、风浪带来的惬意——你成了搏击专家。水色,水温,水面,气泡,气味,气息,以及钓位钓点,钓组结构,浮漂长短,手竿软硬,海竿粗细,鱼饵搭配,香、酸、甜、腥食,还有桂皮、丁香、蜂蜜、香油,等等。
闫华机敏、执拗,肯动脑筋,入道很快,痴迷程度让人惊讶。最能证明他痴迷状态的,是他天天泡鱼塘。天没亮,背着竿包,骑摩托车突突地去鱼塘占好钓位,龟缩着,聚精会神,直至天黑也不收竿,多数时候还摸黑夜战,用夜光漂和手电筒,黑魆魆地晃动,如夜鬼一般。曾经,闫华连续在水库待了一个星期——七天七夜,饭食就是干馕和咸菜。他老婆梁飞飞气得直跺脚,不再管他。梁飞飞在上班,也管不了那么周密。
风吹日晒,闫华变得黑不溜秋的,又干又瘦,如非洲难民,我都不敢辨认。一笑,闫华黑脸露出一口奶白的牙齿,皱褶密布。闫华说,比与人打交道松弛多了。
我曾目睹闫华用手竿钓过大鱼。那天满鱼塘只有他一人钓到了大鱼,着实炫耀风光了一把。前一天对我说,明天周六,咱们去九公里砖厂野塘垂钓吧,那里有大鱼。
深秋,天气冷飕飕的,太阳有气无力,北风一吹,如小刀刮脸。我说,这种天哪里还有鱼咬钩?闫华说,你跟我来,保证让你钓到。我将信将疑。那是一个过去烧砖取土挖的大坑,聚集了洪水,排放了一些废水,很深,好几年也没有干涸。我最早去过两次,都是小鲫鱼、小白条、小麦穗之类,偶尔会上一条野鲤,金黄的尾巴野性十足,但那要碰运气。曾经郁郁葱葱的苇塘,已经凋零,黄枯的芦苇叶被风吹得哗哗啦啦撕裂一般揪心,早已没了盛夏时的静谧、馥郁与幽美。下竿后,很久没有咬钩迹象,只有小杂鱼嬉闹,提竿也不见鱼的踪影。我知道,这种天气,大鲤鱼、大草鱼已不再吃钩。野塘周围石头一样蹲伏着许多垂钓者,没有一个人上鱼。我想,权当来水边消遣清逸了。
闫华另类,他抽着烟,慢悠悠在池塘边转,踱步过来又踱步过去,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在一片浅水处,放折叠椅,坐下。那水域几乎能看见池底,清澈透明。我有点不屑。
太阳渐渐温润起来,暖融融如贴在脸上的热膜。
静寂中,野塘里突然发出哗哗啦啦的鱼闹声,水声极大,如撕破寂寥的利剑。我转身望去,见闫华渔竿拉得弯弯的,吃劲很大,是上了大鱼了。他沉稳地起身,双手把渔竿抬过头顶,不慌不忙地遛鱼,老远,还能听见渔线嗡嗡直响。我一阵悸动。
不少垂钓者放下渔竿向闫华跑去。他们是去看热闹。钓鱼人自己钓不到鱼时,就去看别人,心绪纠结、好奇,有偷偷寻觅嫌疑。我终于按捺不住,也跑了过去。我想,我边看还可以边帮闫华抄鱼。闫华一本正经地与大鱼搏斗,须臾,又左手举竿,右手拿抄网,导引大鱼在水中绕八字,哗哗啦啦,噼噼啪啪,几个回合下来,大鱼翻出了白肚皮,一动不动,如一艘潜水艇被平缓地拉到水边,入了抄网。用毛巾压鱼、摘钩、托举,闫华敏捷而熟练。哈哈,闫华笑了,他向众人展示着大鱼,但不说话,很快又一本正经地端坐在折叠椅上。我知道,这是闫华最开心的时刻,往往这时他就会偷着乐。偷着乐时,就一本正经,目中再无别人。
闫华钓到的是大鲢鱼,足有五六公斤重。那样冷郁的天气,闫华居然会钓到大鲢鱼,人们目瞪口呆。炎热的夏季,鲢鱼也不好钓到,那是一个专项技术活。闫华那天一口气钓到三条大鲢鱼,让围观者唏嘘又大开眼界。有人反复看他的饵料,扒他的钓钩抚摸半天,还有人干脆就挤在他旁边下钩。可所有人都无功而返。闫华把第三条大鱼拉上岸,就收竿了,表情依然是一本正经。
后来他就承包了一个鱼塘。一边养鱼,一边开放垂钓,招来不少垂钓爱好者。有慕名学钓技的,有凑热闹娱乐的,也有狐朋狗友混钓不交钱的。闫华结交了一批钓鱼人,圈内声誉不低。闫华拍着胸脯说,来我鱼塘钓鱼。于是,垂钓者蜂拥而至,哗哗啦啦钓满一鱼篓,龇牙咧嘴提出水面,肩膀歪得很厉害,但交钱时就疙里疙瘩,说下次一块儿交。闫华只好憨笑一下,露出一口白牙。
承包鱼塘要给资产单位交承包费,要给供水、供电公司交水、电费,要购买成鱼放入鱼塘,以及买鱼饲料等等。闫华做成鱼让人钓走的生意,被钓走的越多越好,他只挣个批发到零售的差价,价位也不可定得太高。高了,垂钓者就不干了,会说他是“黑心老板”。闫华的价位与市场零售价差不多。闫华还往鱼塘大量投放饲料,让鱼增肥,怕几天下来鱼就瘦骨嶙峋,头大身子小,钓者更是指桑骂槐。
闫华就住在鱼塘,吃在鱼塘。一间小土屋内,拥挤着锅、碗、瓢、勺,渔网、渔竿、渔线(他还兼做钓具出租),台秤,杆秤,弹簧秤,大量饲料,一摞塑料盆,一摞塑料桶,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四腿桌。闫华在小土屋扎了根。他还时常穿胶皮水裤,在鱼塘清理矿泉水瓶、塑料袋和杂物。没几天又买了一条玻璃钢船,下水工作,还防止有人掉水。安全第一,闫华警惕性蛮高。实实在在又过起了30年前农场再教育的生活,条件比那时还差,因为要自己做饭。闫华不怕吃苦,过几天骑摩托车到市里,驮两袋饲料,带一些干粮、蔬菜和必需品。
闫华向我发出邀请,我推诿着,一直不好意思去。闫华说,到我这儿只管放开钓。我当然更不能去了。一天,闫华突然来接我,黑黑的脸,白白的牙。闫华笑出一脸皱纹,说,不亲自请还不来。我无言以对。闫华带我到喂食处,用脚踩探一下坚硬程度,然后说:就在这儿下竿,专门给你留的钓位。一会儿,我还要为你做鱼宴,尝尝我的手艺,味道极佳。我心里咯噔一下,忙回答:吃什么饭啊,我带了馕和鸡蛋,还有纯牛奶,我要钓鱼。
又来了一群钓友,很熟的样子,花花绿绿,全副武装。大包,小包,钓箱,大阳伞,钓鱼眼镜,活动小桌椅,支架和蒜皮色钓鱼背心。闫华过去寒暄。
我心情内疚地下竿。鱼吃钩狠,浮漂进水立刻有动静,信号明显。我兴奋了,频频起竿。鱼一条接一条上钩,而且个头不小,条条都在一公斤以上,不一会儿,就钓了六七条。那鱼拉力猛,遛起来过瘾,钓线嗖嗖直叫,还拉断了两次,险些拉坏我的钓竿。我手软了。这样钓下去,一两个小时,鱼篓就会钓满。于是我有意放慢了速度,在钓具上做了手脚——增加钓坠重量,调换更粗的钓线——为了不让自己上鱼。果然,很快不上鱼了。我悠闲地拿出一本书翻看。
闫华招呼完钓友过来,见我没上几条鱼,便说:什么钓鱼高手,半天不上鱼,还有雅兴看书。闫华拿起我的钓竿看看,一阵讥笑:就你这臭水平,还能钓到鱼吗?我说:去去,你别管。就把闫华推走了。闫华说,多钓啊,别心疼我的鱼。
后来,我谎称上面来人检查,要去接待,就收竿称鱼。闫华生气地说:打我脸,我能收你的钱吗?闫华脸色很难看,就如同从煤场出来一般。
我隐隐觉得,这样下去,闫华肯定做不长。他的鱼会被朋友、同学、管理者、关系户、钓友、酒友统统钓走,而且不给钱。
年底,闫华交完承包费,再核算其他费用,借款、水电、人工、租车、拉鱼、买饲料、买吹氧机、投食机等等,果然亏损三万多元。辛辛苦苦一年,只弄得两手空空。
梁飞飞不愿意了。态度煞是强硬,说:明年再承包鱼塘,我们就离婚。梁飞飞是个温顺又柔情似水的女人,但这次硬成了石头疙瘩。
忍痛放弃了鱼塘。
闫华又一次悲悯起来,伤感、悲戚、无所适从。闫华消沉了,就如同霜打后的蔫茄子,很沮丧,总也提不起精神。聚会时闫华闷闷不乐,自顾自地喝酒,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对闫华调侃说:一切都会好的,牛奶和面包都会有的。闫华皮笑肉不笑,强装欢颜。
春暖花开,闫华终于恢复了生机。他又骑摩托车在荒野、戈壁、山川、湖泊、水库、河流游荡——野钓。闫华说。到大自然领略闲逸之美,清新之美,到大水域与大鱼较量,施展男人的搏击。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闫华哈哈大笑,又呈现出早先的机敏和幽默。
骑摩托车滚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大小湖泊、大小河流,甚至去六七百公里外的喀纳斯湖钓冷水鱼——哲罗鲑,但因为那是国家二级保护鱼种,闫华悻悻无功而返。
后来,闫华又声名大噪起来,钓纪丰硕如雷贯耳。十几公斤,甚至20公斤的大鱼,他都钓到过。舞剑深潭,鏖战浅滩,脚踏峭崖,臂展涌浪。钓明,钓暗,钓风,钓雨,钓洞穴,钓石缝,钓草窝,钓急,钓缓,钓浮,钓深,钓素,钓荤,钓顺水,钓逆流。时而爆发,时而回转,时而强硬,时而舒缓。抛竿,走线,造声,引诱。静观,猛拉,轻摇,慢遛。大鲤,大草,大乌棒,大胡子鲶,哈哈。闫华终于与他钓到的一条大鲤鱼一同登上《钓鱼》杂志。闫华一本正经的,没有笑,但钓鱼背心上有一些淤泥。闫华说,那条鱼就像一头小猪。
梁飞飞不再阻止他。梁飞飞笑嘻嘻地说,想想一个退休的男人,不偷不抢,不赌不嫖,挺快活,还常常带来惊喜,就随他去吧。
但是,出事了。
那天,天还漆黑闫华就上路了。他的目的地是200公里外的黄沟水库。前次他去看到有人钓起一条30多公斤的大草鱼。闫华愕然了,帮那人照了相,又翻看了那人的钓具与钓饵。闫华眼神直勾勾的。
回家捣鼓筹备了好几天,闫华也不说话,盯着钓具琢磨、发呆。
闫华真想钓到一条更大的鱼,一个更为奇崛的目标。闫华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搏击过程——铃响,抢拉,松曳力,肌肉绷紧,双手抖动,屏住呼吸,缓拉,再松曳力,再缓拉,溜鱼……一个惊心动魄又热血沸腾的过程。闫华觉得自己有能力、有运气触摸到那个仰天长啸的壮丽时刻。
万籁俱寂,闫华像一个幽灵。闫华在行驶了100多公里后,路面上的一个小坑,让闫华的大鱼梦功亏一篑。摩托车失控了,被那小坑颠簸得偏离了方向,而这时迎面冲来一辆大货车,闫华无路可退,狠狠向右拐了一下,摩托车顺势翻下了3米多深的路基。
另一辆大卡车司机看到了那个惨烈的瞬间。好心司机停下车,跑过去大喊了几声,见没有反应,就探探鼻孔,见还有气,就速打120急救电话。那司机懂得,一个人也弄不动他。
闫华昏迷六天不醒。
从外表看,闫华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其实头部严重震荡,大脑某根血管破裂,头颅里一点一点渗出血液,堆积,凝固,缺氧。如若那天闫华没有戴头盔,早就一命呜呼了。还有,他的左腿股骨严重骨折,还是粉碎性的。
好在抢救及时,闫华保住了命。
闫华脑袋被切开头皮,敲开颅骨,先后做了两次大手术。第一次手术后,他的头盖骨右侧头皮变成了软的,能看见头皮上下有节奏地轻轻蠕动,谁看了都不寒而栗。第二次手术后,这块柔软的头盖骨变硬了,但闪着明晃晃的幽光——医生给他装上了金属脑盖,那依然让人发憷。大腿也动了大手术,接骨、打石膏、固定钢板、钻铁钉、缠绷带……闫华成了真正的钢头铁腿。在毫不知情中,闫华被护士扒光了身子,抬到手术台上,叮叮咚咚的彻底修理了。
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闫华苏醒时,懵懵懂懂的,甚至连疼痛的知觉都没有。呆若木鸡,数天后才能嗫嚅着嘴唇,半天挤出一个字,混混沌沌,如蚊子的低吟,谁也听不清,也听不明白。
一年后,闫华拄双拐下地。一颠一簸走在林荫道上,梁飞飞扶着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艳阳高照,太阳暖融融的,闫华头顶呈现有一道亮光,闪闪烁烁晃动,招惹不少路人愕叹。梁飞飞见偷睨者太多,就大声说:别着凉,把帽子戴上。就给闫华戴上一顶银灰色的运动帽,那运动帽的帽檐很大,阴影中,闫华的眼睛能看得很远。后来,梁飞飞干脆在室内也给闫华戴运动帽。
又一年后,闫华稍稍胖了起来,脸上肉也多了,皮肤白里透红,比先前还年轻许多。我们聚餐时,我给闫华夹菜,他笑眯眯说:我行,你、不用管、我。闫华变结巴了,但温和而客气,彻底换了一个人。晋新问:以后还钓鱼吗?闫华慢悠悠地回答:钓,钓啊。温柔中还能分辨出铿锵有力的内蕴。梁飞飞乜斜着眼睛剜了他一下,闫华像没有看见一样。
作者简介
赵钧海,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 。在《中国作家》《作家》《文艺报》《人民日报》《散文》《美文》《山花》《散文选刊》《上海文学》《芳草》《黄河文学》《文学界》等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小说200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准噶尔之书》《永久的错觉》《隐现的疤痕》《发现翼龙》《在路上,低语》,小说集《赵钧海小说选 》等,入选《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散文2013精选集》《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3》等多种选本,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中华铁人文学奖、首届西部文学奖等。现任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克拉玛依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新疆石油文学》主编。
责任编辑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