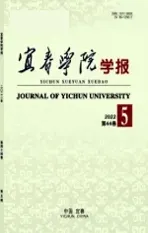从语言哲学观上看客家籍学生二语习得
2015-08-15汪莉
汪 莉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东 河源 517000)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二语习得的研究一直都很热衷。它的研究角度和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涉及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诸多方面。然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进行二语习得的思考不多。笔者结合粤东北区客家籍的英语学习者的特征,用语言哲学的方法,在客家方言的背景下,对二语习得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一、语言哲学与二语习得
在20世纪,哲学家研究哲学时已经意识到哲学的研究终究脱离不了语言。于是研究的方向自然就转向了语言研究。语言哲学研究语言是什么,语言与行为有什么关系,语言与现实有什么关系,语词的概念和意义等核心内容。语言本身极其复杂,语言哲学家们的研究角度也五花八门。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从逻辑学角度来研究逻辑和语言。其后的维也纳学派也是走逻辑实证主义的路线。二战以后,研究方向以日常语言分析为主。代表的人物有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莱尔,奥斯丁,威斯顿,威尔曼等为主。60年代后期,欧洲的逻辑实证语言哲学思想在美国被融入了实用主义。这种逻辑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蒯因和古德曼等。
二语习得简单来讲是除母语外的其他语言的学习。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对于它的研究兴起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语言哲学研究对二语习得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维特根斯坦早期对语言与世界的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图像说。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的反映。语言中的每一个字词都是对应着现实中的客体。语词和句子的意义和关系由现实中的客体或对象之间的关系来决定。试图将语词概念分解成原子命题是注定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的语言行为。这种语言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二语习得者在学习方法上会偏离语言学习的本质。枯燥乏味地背诵二语对应的母语含义;生搬硬套地理解语词和语篇,而不考虑实际的语境;按部就班地学习分析语法和规则,将语法与规则视为语言学习的目的。久而久之,语言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就渐渐丧失了。
中期的维也纳学派提出了意义实证论。对无法存在或实现的事物也只能做到原则上的可实证。这是将哲学引往实证科学之路,这种做法显然对于语言来说是行不通的。后期日常语言学派在研究语言哲学时对语言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如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更多关注了语言是怎样运用的。从使用的角度而非探究一般意义的角度来研究或者说他研究的语言的意义实则是使用。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P31)。他的语言游戏说,生活形式观和家族相似性等理论都是基于意义即使用的理论发展开来的。他认为语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我们在场景中学会说话,在场景中理解语句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语句逐步脱离特定的场景,话语套着话语,一个词的意义由另一个词或者一串词来解释。若把语言视作一个大领域,有一个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边缘地带,这个边缘地带就是语言游戏[2](P184)。语言游戏是将语言交织于现实情境中,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带有乐趣,富有变化。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观中,他认为语词的意义不在于把语词和所指连起来。语词坐落在环境中,坐落在生活形式中。语言是生活的一部分,语言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3](P9)。这种将语言扎根与日常生活中,并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的观念体现了语言的本质性,科学性和真实性。家族相似性的概念是在传统范畴理论的基础上完善出来的。一个概念之下的各种现象之间虽然没有完全一样的性质,但它们的子类所含的现象却可能享有共性的东西。家族相似性概念在语言研究的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语音、词语、句法、修辞等等。无论是生活形式观,语言游戏说还是家族相似性概念,维特根斯坦的这些围绕意义即使用的思想在二语习得的方法和策略上有很积极的启示。他的哲学思想鼓励了二语习得者在实践中学习语言,通过用法来代替意义,通过语言游戏和情境体验来感知语言,通过熟悉游戏规则,利用家族相似性的特征来提升对二语学习的认知。在语言与现实的错综复杂的交织中,一个概念的内涵可以通过比较和描述实现。语言就是个工具,使用工具的过程就是揭示语言本质的过程。
在众多的语言哲学家中,乔姆斯基或许只能算作纯粹的语言学家。哲学家研究的语法归根结底是从语言和概念层面上探索语法,试图理解语言如何反应现实世界,而乔姆斯基是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将语法当作一种机制来研究,从而了解各种语言现象。然而乔姆斯基在研究语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普遍语法的假说似乎可以在某些方面对二语习得起到推动作用。
二、客家方言与二语习得
客家籍学生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客家方言的影响。语言哲学观指导下的二语习得又能怎样充分利用客家方言和客家人文风情的潜移默化来促进二语的习得呢?下面笔者将具体谈谈客家籍学生二语习得的问题。
(一)客家话的发音特征——语音习得
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并不赞成传统哲学家对于普遍性的追求。他认为世间万物没有纯粹的普遍性特征。他说:“我没有指出所有被我们称为语言的那种共同点,我要说的是,这些现象没有一种共同点使我们能把同样的词使用于这一切现象,不过它们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着。正是由于这种联系或这些联系,我们才把它们都称为‘语言’。”[3](P33)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语言活动或语言游戏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家族相似性”。这种家族相似性是一种否认普遍共性的存在。不仅语言的内部概念是如此,各语言之间亦是如此。汉语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之间或许都可以找到语音,句法规则等某一方面或众多方面的家族相似性。在二语习得中表现为不同生活形式的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比相似性或相异性来归纳语言活动规则和掌握语言。
客家方言的发音特征与英语的语音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他们之间既有不同的发音规则也有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语音习得上就形成了语音正负迁移的现象。学习者可以利用这些特征纠正和提升英语的语音。
在客家方言的语音对比研究中,国内的学者也做了不少的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音素方面。元音上,无论是单元音还是双元音,客家方言的发音特征都对英语语音的习得产生负迁移的影响。客家方言发音紧凑短促,断音干脆。这使得客家地区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长元音和短元音时往往会将单词中本应该发的长元音直接发成短元音,忽略两者的发音口型差异和长短差异,造成发音错误和听力障碍;客家方言的发音部位主要依靠前口腔、舌尖及唇腭,很少使用舌根、软腭部位,因此没有普通话中的后鼻音。这一发音习惯很容易使客家学生在朗读具有后鼻音英语单词时出现偏误,难以区分前后鼻音[4];客家方言的发音中没有明显的口型变化和滑音现象。表现在英语双元音中往往只发前一半的音或者发不完整。在辅音发音方面,主要由于客家方言没有翘舌音和撮口呼,在/r/,/∫/,/t∫/等英语发音上出现偏差。
2.超音素方面。客家方言的音调变化少,而英语非常注重句子的语调和节奏。句式的语调不同,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即使是相同的句式,语调的变化也会对句子的含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音韵和节奏方面的区别就不仅仅表现在客家方言中,这是汉语和英语的语音系统差异导致的。汉语是以音节为节拍,英语是以重音为节拍。这些问题表现在非重音时不注意弱化,发重音时过于拖沓。这是客家学习者需要注意的方面。
研究者如廖珺,朱金华[5]认为,客家方言中没有轻声的现象,语言表达以降调居多,所以客家方言地区的学习者习惯性地重读这类复合名词(如:post office,birthday card,…)的第二个单词,以示朗读段落的结束。有趣的是客家方言地区的学习者在复合专有名词 (如:New York)的朗读上准确率较高,因为其读音规则正好符合了方言的特点,所以就带来了正迁移的效果。当然,除了重音问题,客家学习者在爆破,连读等方面与英语也有差异性,需要对比学习。
(二)客家方言的词汇特征——词汇习得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的基本思想是英语,汉语等特殊语言背后有一些一般的语法原则,这些原则是一种先天构造,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对已知人类是共同的[2](P300)。
乔姆斯基这种对语言普遍适用的共性原则的寻求似乎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尊重语言个性化,注重语言游戏间的紧密联系和家族相似性特征的思路相违背。但这里无需讨论孰对孰错,孰优孰劣。一种理论的存在即体现它自身的价值。不可否认,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语习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普遍语法观点下,每种语言都有动词名词之分,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则,按线性排列方式呈现,语词的范围和类别有上下范畴和等级划分。客家方言有其独特性。其词汇表现之一为词缀丰富。后缀如“呃”放在形容词或动词后面都可以构成名词像丑呃 (小丑),刷呃 (刷子)等; “牯、公、婆”等后缀放在表示雄、雌性动物后如狗牯,鸡公,猪婆等。英语当中同样有很多表示名词化的后缀如“-ness/-ment/-th/-tion”等,也有带有性别区分的后缀如“-er/-or”和“-ess”。前缀如“老”“阿”用在称谓前构成称谓名词像老公(丈夫),阿妹 (妹妹)等;英语中有表示辈分和关系的称谓前缀如“grand-”和“ex-”等。这些词缀现象在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蕴含内总能找到极为相似或相同的意义表达。在二语习得中找到这些普遍规则能让学习者事半功倍地学习。
(三)客家歌谣中的隐语特征——语义习得
后维的“意义即使用”的语言哲学思想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在他看来,工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有不同的用途,语言也同工具一样,在不同的场合使用 就有不同的意义[6](P110)。换个角度来讲,语言的意义囊括词汇,语法,句子,概念,文化,语体等等多维度的意义。只有在使用中,具体的语境下,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语义。
客家歌谣中蕴含着丰富的客家文化,反映了客家人对婚恋,自然和道德理念等文化精神。客家歌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充满了各类隐语。通过隐语,以物寓意,以情说理,将丰富多彩的客家人内心世界展露无遗。这些隐语主要表现为谐音和意隐两种类型。
利用谐音来达到语义双关效果的如“莫怕中间人阻隔,水流灯草放芯来”中以“放芯来”谐“放心来”,“饭甑里头放灯草,日后才知郎蒸心”中以“蒸心”谐“真心”等等[7](P21)通过隐喻来表达喜怒哀怨的更多。如“恋了一侪又一侪,莫再心向别人家。要学凤凰成双对,莫学黄蜂乱采花”这首歌谣用来规劝放荡的青年。又如“一支秤杆配一砣,一个锅盖配一锅,一针只有配一线,一针两线结头多”此歌谣用来表达客家妇女对丈夫忠贞不二的爱情观。这两首歌谣中出现的“凤凰”,“黄蜂”,“秤杆”,“砣”,“锅盖”,“锅”都是通过比喻的说法,将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东西来比喻爱情中人物角色的立场和观念,浅显易懂,非常朴实,又不失韵味。
英语中的隐语更是层出不穷。如利用明喻,暗喻或其他修辞格进行语义转换的隐语“break the ice”(打破僵局),baby(用来形容股票公司新发型的股票)等。利用谐音表达语义双关效果的隐语如谜语Which four letters are the thief afraid of?Key:O,I,C,U(oh,I see you)再比如Who is closer to you——your mom or your dad?——Mom is closer,because dad is farther.中英文的隐语带有很多的幽默性和趣味性,语义的解读常常出人意料又回味无穷。学生在这种双语文化的对比学习中,能体会到语言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同时增添了二语学习的乐趣和动力。
(四)客家文化与思维特征——语用能力
后维在他的生活形式观中强调语言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他说“我们是否对一个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的某个词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翻译,这取决于我们是否理解那个词在这个部落的全部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说,取决于它被使用的时机,取决于在通常情况下与这个词相伴出现的那种情绪表达,取决于这个词所引发的印象,如此等等。”[3](P34)生活形式的差异会造成背景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语境理解上出现偏差,从而构成语用失误。
由此可见,二语语用能力的提升是与对语篇中语境的掌控,目标语的生活形式,文化风俗,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等方面的把握有密切关联的。客家文化与思维在某些方面是与英美国家的文化与思维不相同的。客家人崇尚祖先,注重教育,族群意识强,传统保守但又具有开拓精神,勤劳刻苦,尊重妇德。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倾向集体主义,弱化自我意识和观念。表现在二语习得中就容易出现文化冲突和理解偏差,在写作和口语表述中个人观点不明确,语篇结构的中式化,以及句法错乱等诸多问题。因此,客家籍二语学习者除了对该语言所依赖的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要熟悉之外,还要避免将客家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负迁移到二语习得中。
结语
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为二语习得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语言哲学中的各种观念都可以为二语习得的方法提供一种角度。普遍语法的假说,语言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说及生活形式观等哲学假说和思想将二语习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客家籍的英语学习者来说,将客家方言与英语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主动性地将对二语习得中的负迁移的关注转移到正迁移上,提醒自己尽量避免语言的负迁移,将语言间相似的或共性的内容发扬光大,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在平时的点滴积累中,挖掘客家语的潜在特征并将这些特征与英语学习相结合,进行哲学思考,有效发挥语际之间的联系,改善和提高学生的二语学习兴趣,逐渐缓解对二语学习的情感障碍。外语教师们通过将哲学思考与二语习得相结合,将给二语的教与学带来新的启发。
[1][奥]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著.李步楼 译.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陈清润.粤北客家方言对大学英语语音学习的影响及对策[J]. 课程教育研究,2014,(28):89.
[5]廖珺,朱金华.客家方言在英语重音习得中的负迁移现象探究[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10):92-97.
[6]夏立新.论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核心概念的内涵[J].求索,2009,(1):110.
[7]卢华东.谈客家民间歌谣[J].语文学刊,2009,(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