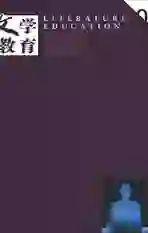扎米亚金《我们》中的性与政治
2015-08-12蒋娇
蒋娇
内容摘要:扎米亚金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联众国”的管理处处体现了阿伦特所界定的“极权国家”要素,学界也一直着力于对小说的极权要素进行分析,但却鲜有人从性这个层面进行切入。笔者认为,联众国之所以能完美地统治“号码”们,就在于其对性的控制和管理,而完美统治的动摇,也正在于性作为一种革命动力的反抗。本文首先将对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梳理,其次再从文本入手分析极权统治下性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扎米亚金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怀。
关键词:《我们》 极权主义 性压抑 性反抗
性不仅仅是作为官方统治的工具出现,它同样是一种有利的反抗手段。现代西方的女权运动、同性恋争取合法权利等都是将性作为反抗手段的成功案例。在扎米亚金的《我们》中,性一方面是作为极权统治的工具出现,一方面也是个人突破极权统治的出口。
一.性作为统治工具——性与爱的分离
在《我们》中,性作为统治工具并不是体现在直接的性压抑中,相反,它是体现在过度的性自由中。
联众国的《性法》宣告:“一个号码可以获得将任何的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许可证”。性的享用相比咱们“古代人”自由几万倍,人人可以享受平等的性爱,不用受道德、情感的钳制。但是,在这表面的自由之下,却是令人恐惧的统治深渊。福柯就曾敏锐地看到这种性自由下的性压制,“压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不是禁止说、限制做这一形式,它还有鼓励言性这样一种形式。在人们被鼓励言性,并且以为自己已经因此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的控制起来,受到了更深的压抑。它的严重后果是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引入歧途——人们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反而以为自己已经活在自由和解放之中。”人欲望的解除,根本目的是为了麻木地统治顺民,人不再有任何情感、欲望的需要,统治者以满足欲望从而达到了消除欲望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消解了人们反抗的动力和意义。联众国就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性自由完成了对个人的全面统治。
但事实是,这种表面的性自由其实是一种更为隐秘的性压抑。我们可以把联众国的性规则简单明了的概括为:性行为可以无关性对象,但却不能对性对象产生感情,不能结成家庭。在这里性和爱必须是分离的,但这种性和爱的分离是完全违背人性的,人的性与爱是相连的而不是分离的,性行为的后果之一便是你有可能爱上你的性对象。联众国的性规则很明显是漏洞百出的,O-90对D-503的爱,D503对I-330的爱,U对D-503的爱,都是这种性规则下的“漏网之鱼”,这种看似严谨的规则实际上是百密一疏,它忽视了人类最伟大的能力——爱的能力。同时,这一性规则还要求性行为不能生育下一代。我们知道,性行为的目的一般有三种:一是为了生育繁衍;二是为了性快乐;三是为了建立维持某种人际关系,如爱情关系、婚姻关系。但是联众国的性规则直接消除了性目的的第一第三种目的,只把性行为局限于获得性快感,取消了人为建立稳定人际关系的愿望,剥夺了人生育下一代的可能。所以,这种看似自由的性规定,实际却是变态地压抑了人的本能需求:获得爱与家庭的需求。
那联众国为什么要剥夺人的这种需求呢?阿伦特在其《论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就对极权统治的方式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她认为极权统治的基础是分子化的孤独的个人,极权政府要想达到全面统治,必须消灭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而家庭正是我们建立独特个性的场地,是我们形成稳定亲密的社会关系的场地,是我们面对浩瀚宇宙避免孤独的场地。现代家庭的基础就是性关系的稳固与排他。联众国为了使每个个体保持一种绝对的孤独状态,避免了性关系的稳定性与排他性,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人就会永远处与孤立无援的分子化状态,这样反抗便缺乏有力的同盟,自然极权统治也就变得坚不可摧。
综上所述,联众国的性规定是与其统治需要紧密相关的。但是,这种规定却是严重反人性的,它忽视了人获得爱和生育下一代的本能需求,这种忽视也最终导致了“完美统治”的破产。
二.性作为反抗手段——性与爱的弥合
联众国反人性的性规定不可能安然无事,“号码们”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撼动了联众国的统治。性在这里不再是沉默的统治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革命动力,对极权统治发起了攻击。
(一)D的反抗
联众国的号码们虽然享受着性行为的自由,但是却不知爱为何物。萌动的爱的渴望使得他们开始对性规定产生质疑,从而对联众国的统治产生反抗之心。
以性作为反抗手段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D-503,他也是文本的叙述者。文本开始时,他作为“积分号”的建造者对联众国充满忠诚,然而这种绝对忠诚却在一夕之间倒塌,原因就在于,他爱上了一个人——I-330。为了得到I-330,为了取悦她,D不惜时时触犯联众国的法规。他明知I有许多违背规定的喜好、行为,却因为爱情一再找借口没去揭发她,最后甚至被她洗脑,抛弃联众国,站在了反抗者的行列。正是由于陷入爱情,他才获得了正常人的情感:嫉妒、渴望、悔恨、愤怒。这些情感在他作为联众国的顺民时是没有的,而在陷入I的爱情中时,这些情感才完善了他作为正常人的所有情绪,使得他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正常人。也正是在爱情中,他才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我”而存在,不再是作为群体的“我们”。爱情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排他性,也就是说爱情的空间只容纳得下两个人,爱情的自私表现在它渴望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并且排斥其他人的介入,因此爱情是一种最为私人的关系,也正是在爱情中,D才产生了想拥有一个人的愿望,而这种私人的亲密关系对联众国的统治是致命的。稳定私密的两性关系是极权统治最害怕的,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结成坚固的同盟,获得同伴的支持,产生反抗的团结,从D最后在I的引导下加入革命团体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二)O的反抗
对爱的渴望表现得最为决绝的是0-90。她的反抗并未带半点政治意识。如果不是因为爱上D-503,联众国为她提供的生活就是完美的,她也不会产生丝毫的反抗之心。对O来说,联众国性规定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它对感情的蔑视。O对D的感情表现一直是强烈而直接的,在遭遇情敌时,她立马宣誓主场“他登记在我名下了。”为了表达爱意,她不顾D的反对,偷偷将玲兰花塞在D的被子下;当得知D爱上了别人,她毅然决然结束了他们的性关系,主动退出了D的生活,“现在你知道了,没有你,我再也不会有什么春天了。”“没有你,我无法生活,因为我爱你;我不应该,也再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因为我爱你!”对0来说,性和爱是相辅相成的,性和爱不能对立也不能分离。O的性爱观更接近恩格斯对性爱的理解“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O的反抗,是通过结束无爱的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更能对联众国的性规定产生致命打击。她以自己单纯、专一、质朴的爱向联众国宣战。同时,正是由于对D的爱,想为D生育下一代的愿望使得她与联众国的关系变得紧张对立。与D的两性之爱唤醒了她沉睡的母爱,而O与联众国另一个大的冲突就在于他们对性目的的理解不同。联众国为了极权统治只允许性行为享受快乐,而拒绝家庭、婚姻这样的稳定关系,O则认为性行为的目的不只是快感的享受,更多的是维持感情以及生育下一代。为了保护D的孩子,她站在了反抗者行列,最后通过I的帮助,到达了自由的绿墙之外,彻底脱离了极权国家的统治。正是基于对爱的渴望,以及在母性本能遭受遏制后的反应,使得O成了是《我们》中唯一一位胜利的反抗者,由此可见爱的力量之强大,从而也揭示了联众国对爱的压制的失败。
(三)I的反抗
《我们》中还有I-330的反抗,她的反抗是有组织有计谋的革命。性就是她革命的策略,性在她看来只是达到自由的手段,她的反抗是基于对自由的爱。为了引诱“积分号”的建造者,她对性的拿捏充满狡猾的手段:不是一次性的得手,而是永远的牵肠挂肚。她熟练的掌握了控制一个男人的能力,而性则是其最好的帮手。但是事实是,在与D的周旋中,她同样陷入了爱情,只不过在革命之爱的阴影下,两性之爱太过脆弱和单薄。I对自由的渴求体现在她的每次出场中,她不穿统一制服,穿着古代人的奇装异服;享用酒精(联众国称其为毒药);利用私人关系开假的生病证明。她那让D 感到不安的眉间的“X”,就是源于她对数字化统治的联众国的怀疑和不满。她对未知世界的着迷,对无限世界的肯定,都是未知数“X”的表现。而她的反抗不仅是体现在日常行为中,更体现在她敢于组织革命队伍,通过暴力推翻联众国。
I的反抗是如此彻底而决绝,可以将其与D和O的反抗进行一番对比。D只是出于性欲的引诱而无意被卷入革命之中,O是出于对爱的渴望被动脱离联众国,但I从一开始出场就带有强烈的革命情绪,并且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对自由的渴望。从D到O再到I的革命之路上,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愿望的强度在不断加强,并且更重要的一面是,与男性D相比,女性I和O的革命斗志更为坚定,行动也更为坚决。同时,革命的原因也在不断变化,基于情欲的被动革命,基于爱的主动反抗,基于自由的决不妥协,革命原因逐渐从生物性层次转向精神需求的层次,革命的坚定度也随之上升。但不论革命原因的高低,革命的手段都是性。性作为反抗手段在三位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结语
应该指出扎米亚金的《我们》虽然是源于对苏联极权统治的指涉,但更应该看到,他的意愿并不止于此。作为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家,扎米亚金关注的并不仅仅是苏联当时的政治背景,机器的普及、科技的运用、对理性的过度崇拜都在他的关注之列。人类拥有更多宰制自然的工具,讽刺的是终有一天也会被工具所主宰。而在对反抗途径的思考中,他和他的其他两位同仁赫胥黎、奥威尔一致采用“性”作为手段,这正好印证了福柯的观点,“任何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都不能脱离性态”,统治者需要性作为统治工具,反抗者需要性作为反抗手段,而在《我们》中,性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