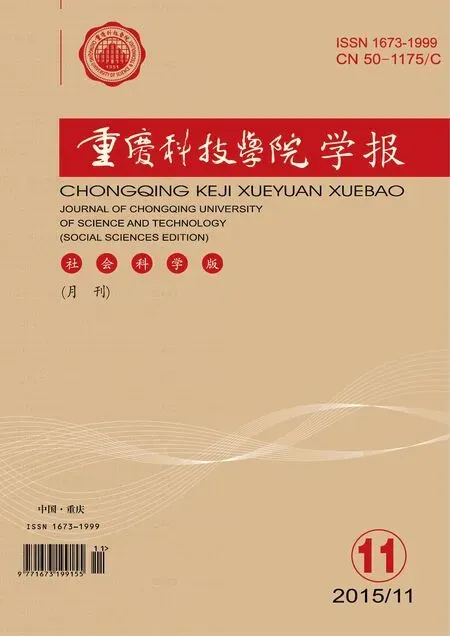口译任务中言外之意的处理策略
2015-08-11孙爱娜冯曼
孙爱娜,冯曼
口译任务中言外之意的处理策略
孙爱娜,冯曼
摘要:语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都能引发言外之意。在口译任务中,言外之意给译员带来了听解和口译策略选择上的困难。从符号学、语用学以及信息传播学的视角分析言外之意的发生机制和生产手段,论述动态语境建构与言外之意听解之间的关系,探讨口译过程中译员应如何准确地辨识和听解言外之意,旨在提出对言外之意进行口译时需关注的要素以及可选择的处理策略。
关键词:口译;言外之意;听解;策略
言与意之谜,自古为学者哲人所执着求解,然而至今其解答仍是扑朔迷离。言外之意是口译任务中常见的处理难点之一。当语言的形与义产生偏离,即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意向意义)不对等时,译员不仅会遇到听解障碍,而且用译语再次传递话语意义时也面临多重选择——到底是译出字面意义还是译出言外之意,抑或两者兼顾?言外之意产生的主要途径有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通过语言手段(如副语言、修辞、语用策略、特定上下文设置等)产生的言外之意通常被看作狭义的言外之意。由非语言手段(如身势体语和语境要素选择)和语言手段所产生的言外之意,则被视为广义的言外之意。广义的言外之意涉及语言交际活动的各个因素,即语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如沟通语境、参与者、渠道、噪音、信息编码解码系统、听者反馈等,都能引发言外之意。
口译既是一个 “解码→换码→编码的思维转移过程”[1]18,也是一个动态的语言交际过程,它不仅涉及语言信息,也涉及副语言和非语言信息,因此口译任务中所处理的言外之意属于广义的言外之意。口译是一个双向的动态交际过程,成功的交际离不开译员对说话人意图的正确识别、领会和传递:译员一方面要准确地听解发言人的话语字面意义和其真正的交际意图,另一方面要采用最恰当、最自然的译语语言形式向听话人传递对等的语效和言外之意。因此,探讨言外之意的发生机制以及言外之意与动态语境建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译员思考如何准确的听解言外之意,关注影响言外之意口译决策的要素,进而在口译时采取恰当的处理策略,成功、有效地传递讲话人的言外之意和交际意图。
一、言外之意的发生机制
无论是从符号学、语用学,还是信息传播的视角,言外之意的发生机制均来源于交际者的主观因素以及与言语活动相关的客观因素。符号学侧重符号意义的产生以及符号规约意义的条件;语用学指明了动态语言使用中的语用规则和语言信息推理模式,揭示了解码的实质是即时的非实证性推理;信息传播理论则从整体上分析了交际中各种交际要素对语言信息的影响。
(一)符号学视角下的言外之意发生机制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是意义的载体,符号所携带的意义具有模糊性和多元性。根据莫里斯的观点,符号的意义存在于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以及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之中。因此,符号的规约意义常常体现为对某一类使用者而言固定在一定语境中的意义。在现实交际中,语言符号自身的局限性经常导致“言”与“意”不对应。一旦符号的常规搭配发生改变,接收符号的参与者、现实语境以及听话人所做的语境假设将会与符号规约意义所指向的这一系列条件发生冲突或偏离,这可能造成听话人不采用符号的规约意义(即一定的文化缺省意义),而激活了与符号规约意义相连接的隐含意义,使其成为该交际中的突显意义(话语意义)。正是讲话人的“主观有意”,造成了突显意义和缺省意义之间的不对等,导致“意”在“言”外,产生了言外之意。熟悉语言符号的规约意义条件,敏感感知现实交际中对这些意义的背离以及符号所连接的可能的隐含意义,是感知并解析言外之意的关键。
(二)语用学视角下的言外之意发生机制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就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者奥斯丁将人的言语行为分成三种不同的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其中:言内行为即以言指事,传递的是字面意义;言外行为即以言行事,传递的是言外之意(话语意义);而言后行为旨在以言成事,强调的是语效[2]94-108。在言语行为的理论基础上,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于1975年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概念,他将言语行为区分为直接言语行为(direct speech acts)——通过话语直接表达话语意图和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通过话语间接表达话语意图[3]34。因此言外之意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产物。
塞尔间接言语行为进一步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l)和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两类。其中,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习惯用法,由于该言语行为的字面意义与话语意义之间联系较为固定,受众可以从字面意义推断出其言外之意。例如,“我可不是吃素的。”此话最开始可能是某个人的创造性表达,但现在已经普遍用于暗示 “某人不好惹”。“你吃饭了没?”一句意不在询问吃饭与否的事实,而是人们的习惯性招呼用语。再如,“Would you mind…?”在英语文化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疑问句,而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礼貌用语。“How do you do?”原先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手工作坊者之间见面的常用寒暄语,现已渐渐发展成社会大众的通用问候语。在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中,仅仅通过字面意义和规约,人们很难判断说话人的言外之意,必须借助语境进行推断。由于讲话人所采用的不是间接言语行为的习惯表达,说话人的话语意图与话语字面意义的联系并不固定,因此其真正的话语意义更依赖于语境。这就要求译员在口译过程中既要关注静态的语言语境、文化语境,还要关注动态的交际语境[4]184。在口译过程中,只有结合具体的语境去分析讲话人的言外之意,才能准确地捕捉和听解其真实的交际意图。
(三)信息传播视角下的言外之意发生机制
目前国内对言外之意产生机制的研究多采用的是语用学视角,事实上言外之意的产生涉及诸多因素,语言信息传播活动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能对其发挥作用,其中香农-韦弗的通讯传播模式图[5]2便很好的阐释了这一点。

图1 香农-韦弗的通讯传播模式
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语言沟通情境下,说话人(信源)根据话语意图选择话语形式(编码),并通过一定的信息传播渠道将信息传递给听话人 (信宿),然后听话人根据自己的预设和参与交际意图,按照一定的语言规则(包括语用规则)来接收、解码信息(译码)并做出反馈。在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源”与“信宿”,即“说话人”与“听话人”,是沟通的参与者;“通道”,指的是沟通的渠道;“干扰”,指的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会有噪音干扰信息传播;“反馈”,则指的是“听话人”对“说话人”传递的讯息所做出的反应。在语言信息传播过程中,以上各个因素都能引发言外之意。
二、言外之意的辨识与听解
由于话语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不对等,语境与言外之意的联系不固定,许多因素都能引发言外之意,这给沟通者带来了一定的交际困难。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来看,要么“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要么“言者有心,听者无意”。对于言外之意的解析,斯帕伯和威尔逊在格莱斯的意图推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6]140。该理论认为,说话人的明示话语行为包含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说话人向听话人发出一定的话语刺激,显明了某种信息,即信息意图;显明这种信息的用意是为了明示或暗含一定的交际目的,即交际意图。无论传递的是明示的还是暗含的交际意图,说话人都需要选择某些语言形式和交际要素来建构特定的语境,从而使得听话人能够产生一定的语境假设。听话人不一定对说话人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理解,但他会将获得的语码与自己的语境假设关联起来,去辨识和理解讲话人的交际意图。因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有助于译员准确地辨识和听解言外之意。
(一)充分了解口译任务的各个沟通要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译员不仅应做好专业词汇和专业知识的准备,还应该多方位收集口译任务所涉及的各沟通要素信息,例如沟通参与者(包含各参与者的角色、地位、相互关系、认知水平等)、沟通语境信息(包括时间、地点、目的、条件、涉及文化背景等)、沟通渠道、及沟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噪音等。译员是沟通的桥梁和媒介,然而相对于沟通的直接参与者而言,译者在共有信息的持有上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译员需要主动了解口译任务涉及的各个沟通要素信息,尽力克服在场和不在场的各种不利因素,充分调动认知资源进行有效关联,预测话语双方的交际意图。
(二)利用口译现场的优势
美国传播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曾提出,“情感表达=7%的言语+38%的声音+55%的肢体语言”。非语言沟通手段虽然常常相伴并辅助语言沟通,但它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却远远大于语言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与笔译相比,口译面临即时性和缺乏文本信息对照的挑战,因此译员在执行口译任务时,不应当只是埋头记笔记,还要关注发言人的体态语、说话人细微的副语言信息变化、及听众的反馈等,充分利用现场的优势去捕捉、推断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例如,在笔者承担的一次商务口译任务中,厂方对自身产品的质量大做文章,然而外商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yeah,yeah,I have heard things about the quality of your products.”。不言而喻,外商不耐烦的语气和模糊的措辞说明他们可能听到了一些有关厂方产品质量的不利传闻。因受托于厂方,笔者认为有必要提请厂方注意,因此将外商的回答译为“是的,是的,我倒是听说了有关贵方产品质量的另一些传闻”。此处的“另一些”传递了外商的言外之意:“我们对你方所述的产品质量信息不认同”。此时厂方意识到有必要澄清对其不利的传闻,接下来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消除了外商的误会。
(三)顺应动态语境
口译时语言交流处于互动、活跃状态,语言理解的环境更具有动态性、变化性[7]160。通过译前准备,译员对双方交际的意图、目标有了初步的认定,但是双方的宏观交际意图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子意图。交际者会根据交际进程和现行语境,不断调整自身的交际子意图,适应或打破现行语境的束缚,创造有利于自己的动态语境[8]74。维索尔伦认为,语境是在听说者之间的动态交际过程中被创造的,并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变化,而话语意义也是在交际双方的不断互动中得以建构。因此,语境的动态性以及话语意义的动态性的确给言外之意的听解带来了困难,译员需要通过把握语境的整体性和显映性来推断交际双方的言外之意。基于语境的动态性、可建构性、整体性以及显映性,译员应该将获得的语言信息、语境信息[6]、交际对象等进行多维度假设匹配,通过不同角度的检验,如上下文语境、交际语境、文化语境等,敏感地发现违背符号规约意义条件的语境假设。
此外,说话人根据交际意图选择语言形式时都会遵循一定的语用原则,即语言使用者为达到一定交际目的而普遍采用的一些语言原则,如由格赖斯提出的“合作原则”[9]26、利奇等人提出的“礼貌原则”[10]119,以及冲突语语用原则、规避语语用原则、最佳关联推理原则等。掌握一定的语用原则,捕捉影响语言意义的语境假设,并通过逻辑推理将语境假设与话语意义进行最佳关联,那么言外之意的听解便可水到渠成。
总之,对于言外之意的听解,译员首先需要娴熟地掌握工作语言、熟悉工作语言符号的规约意义条件,同时还应积极了解口译任务中的各个沟通要素,并充分利用现场优势、构建对交际现实的语境假设,进而敏感地发现与符号规约意义条件相背离的各种因素(如参与者、译者语境假设,非常规符号搭配等),最后根据这种背离将语境假设与交际意图进行最佳关联,找出与符号意义相连接的隐含意义、准确判定讲话人的言外之意。
三、言外之意的口译策略
在准确的听解交际双方的言外之意后,译员接下来的任务是采取恰当的口译策略,使言外之意在译语中得以顺利再现。然而以下因素往往会影响口译策略的选择:言外之意的可译性,言外之意的语效,言外之意的表现手段在目的语中的对应,译者身份与言外之意的解析授权。
在口译任务中,因受时间和工作模式的制约,言外之意可能遭遇不可译的尴尬局面。特别是在同传模式下,译员很难收集到基于语篇的言外之意的完整信息。传统笔译中遇到的不可译问题,如由双关语、幽默产生的言外之意等,在口译环境下显得更加棘手。其次,语言形式与话语意义的匹配程度不同,听众的理解效果也可能不同。对言外之意的处理,很关键的一点是考量承载了言外之意的语言形式所产生的语效,即为什么要制造言外之意:是为了引起注意?为了间接委婉表达?为了加强语言审美?还是为了凸显身份?这要求译员在推理交际双方的言外之意时不仅要考察言外之意的内容,还要考察其使用目的和意图达到的语效,以便在译语再现时具有可供参考的标准。再者,产生言外之意的手段众多且复杂,在原语中能产生言外之意的语言手段或形式即使在目标语体系中可以找到对等的字面翻译,却不一定能够表达同样的言外之意,或未必能产生相同的语效,此时译员需要灵活变通地处理:假设原语语言形式 S1能产生S2的言外之意并带来S3的言后之果,那么在口译时如果对S1进行直译后所得到的字面意义无法带来S2≈T2和S3≈T3的效果,那么译员就应当借助非语言和语言手段,使得译语T1能带来S2≈T2和S3≈T3(S2+S3≈T2+T3)。此外,在一场口译任务中,译员可能同时扮演多种角色,比如沟通协调员、社区工作人员、行政助理、谈判助理和文化协调员等。由于不同的角色指向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角色期待,译员对言外之意便拥有不同程度的解析权。该权利不仅来自委托人的授权,也来自顺利完成工作任务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规约授权。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译员在处理言外之意时,通常面临四种选择。
(一)略译或不译
在具体的工作情境下,尤其是经委托人充分授权,译员在一定程度上能掌控话语交际内容时,可以选择对交际双方的言外之意进行略译或不译。比如说,译者同时充当谈判助理的角色,当己方说话人传递出来的言外之意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产生阻碍时,译者可以选择省略不译。
(二)译出部分或全部字面意义
针对规约性言语行为所产生的言外之意,译员可采用直译的方法,全部译出其字面意义,便能在目的语中表达相同的言外之意和语效。例如,“Would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可以被直译为 “你不介意我在这抽支烟吧?”又如,“Everyman is the architect of his own fortune.”可以被直译为“每个人都是自身命运的建筑师”。
当非规约性语言行为的言外之意能够在特定语境下被目的语听众所识别,且目的语中有对应或类似的表达能帮助听众理解言外之意时,译员可以只译出其字面意义,当中的言外之意则由听众直接推断。例如,“Is it your signature?”译员可直译出其字面意义“这是你的签名吧?”,至于言外之意“当初你已经同意此事”,可以留给听众自己推断。此外,因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而未能在短时间内充分理解讲话人言外之意的时候,译员可以仅译出话语的字面意义,而将推理的工作留给具有背景知识和信息的听众。如果说话人违反了量的准则,重复提供了相同的信息或添加了非重要信息,此时译员不妨只译出重要信息、省略次要信息。
(三)直接译出言外之意
规约性言语行为的言外之意很难在目的语文化中产生同等的规约效果,因此当目的语形式所对应的字面意义不能直接传递源语的言外之意时,译员可以直接译出话语中的言外之意。例如,“Pull yourself up by your own boot strap.”一句可译作“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境遇”。再如,“饭菜不好,请多包涵!”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礼貌待客用语,如果对其字面意义进行直译,很可能造成误解,此时不防直接译出主人话语中的言外之意:“I hope you enjoyed the dinner”。
有时非规约性语言行为的言外之意并不能被听众识别,译员如果只译出其字面意思则容易造成交际目的受阻。例如,谈判中的一方说“我们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了,你也不看看距离”,这说明讲话人已经明显不耐烦了。此时译员应直接点明说话人的言外之意:”We have nothing to discuss.Your offer is too far away from our expectation”。
(四)兼顾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
一些语义范围较广的表达能够将言外之意和字面意义都涵括进来,并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例如,某与会者抱怨“今天天气沉闷,我算是呆够了!”此时译员可以将其译为 “I have already had more than enough of this heavy atmosphere”,用“atmosphere”一词替代原文中的“天气”,便不难起到一语双关的效果。当原语的表达生动并能产生一定的语效,但是目的语听众对该表达并不熟悉时,译员可以选择在译出字面意思的同时显化言外之意。例如,“我说啊,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面对英文受众,译员可将其译为:“I’ll say,you drop a stone only to your own feet,you will suffer from what you have done.”这样一来,说话人的言外之意便得以顺利传递。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译文若缺失了言外之意,其信息会显得不够完整,此时译员也需要在译出字面意义的同时显化言外之意。例如,警察问嫌疑人“Did you buy the car and the motorbike?”嫌疑人回答:“Yes,I bought the car.That’s correct.”显而易见,嫌疑人的回答违反了量的原则,他仅对问题做了部分回答 “I bought the car”,言外之意是 “我没买摩托车”,因此译员可将其译为“我买了汽车,但没有买摩托车”[11]。
四、结语
言外之意是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语言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各个要素都能引发言外之意。当译员了解了言外之意的发生机制,对产生言外之意的手段以及影响我们理解和传递言外之意的因素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之后,口译任务中言外之意的处理就不再是重重迷雾了。在口译任务中,“语言的感知、辨识、语言、语义、语篇、文体、修辞、文化、社会心理分析、意义判断和综合等均在瞬间发生着变化”[12]55,译员须结合语境假设,判断说话人的话语意图,并在字里行间中体会字面意义产生的言外之意。在口译过程中,面对言外之意,译员应根据说话人的意图,结合口译任务本身的目的以及听众的认知语境来确定所译内容的倾向性是偏重语言形式还是其深层意义,抑或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体,从而恰当、准确、充分地听解和传递交际双方的言外之意和预期语效,
促使交际目标的达成。
参考文献:
[1]仲伟合.口译教学刍议[J].中国翻译,1998(5).
[2]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Searle J R.Indirect Speech Act.In Cole,P.&Morgan,J. (eds.)Syntax and Semantics,Vol.3:Speech Act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
[4]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5]Claude E Shannon,Warren Weaver.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M].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49.
[6]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7]刘宓庆.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8]Verschueren Jef.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9]Grice Paul.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10]Leech GN.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London:Longman,1983.
[11]Jacobsen B.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nd Court Interpreting [M].In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eds.)Textologie und Translation.Tubingen:Gunter Narr Verlag,2003.
[12]刘和平.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编辑:张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5)11-0104-04
作者简介:孙爱娜(1980-),女,硕士,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970)南方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冯曼(1975-),女,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跨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26
基金项目:2013年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课题“翻译学研究方法体系建构”(粤财教【2013】412号文)阶段性成果之一;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11BYY01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