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梦
2015-07-24马永波
马永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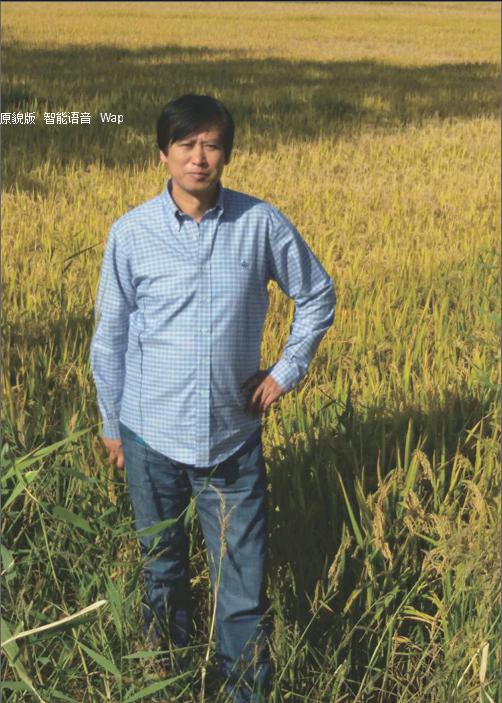
深夜不眠的母亲缠着线团
房间里很快就堆满了棉线
各种颜色,像蓬松的长条爆米花
好像我出生时房间里就堆满了东西
隔着这些柔软的墙壁,母亲
听着她的小宝贝是否在睡觉觉
而我像一根线轴一动不动
闭上眼,听着母亲是否还在那里
担心着困倦的她会拿起那把生锈的剪子
线越收越紧了,房间里越来越冷
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母亲
只有一根缩小的骨头,缠着一道血痕
亲人
半透明的黑暗中,姐姐站在地上
离我睡着的热土炕不远
她一直在包饭团,小心地
把白菜叶的老筋剔掉
土豆泥散发着贫穷的热气
她把白白的土豆泥包好
却不给我吃,我想哭
又怎么也哭不出声
北方冬天的平房,屋里很冷
一个角落里传来熟悉的咳嗽声
原来二哥也在,还有姐姐的女儿薇薇
年纪似乎只比我小了一点
她不停地说, “你们不和我玩
我就找小道士跳舞去。”
于是我们出去,我在一边
他们三个在另一边
踢一只已经旧得很软的篮球
这时大哥也来了,他终于
把球踢到了水洼里
房子之间的空地大得像广场
满是水洼。没有爸爸妈妈
那些老房子和老胡同早已不在了
只有土豆泥喷香的热气
还在晕黄的白炽灯下缭绕
母亲
是一个中午,同样也是秋天
邻居家种的豆角结满了我家平房的窗户
我们用玻璃丝袋子把豆角摘干净
剩下的藤蔓和牵牛花混在一起
在窗上形成绿荫。我就要上班了
还是在工厂,工厂在西边的山上
我请大哥与我同去,说他可以在田野里
采东西玩,他不去,他坐在小凳上
面前摆着录音机放青岛音乐,看小说
我从后门出去,看见街道退远了
原来的人行道改成了后园子
土质低劣,煤渣很多
母亲正蹲在那里仔细地种小白菜
我踩着垄沟来到路上,去上班
醒来,好半天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外面正是初秋,已过了种植的季节
双亲
和什么人一顿乱打之后
绕很远的路回家
没有院子的平房
钥匙在门上插着
房子里灯光明亮
是冬天,母亲起身招呼我
我问,怎么钥匙插在门上
答,是父亲开门时弄弯了
父亲在房子更里面
似乎在准备过年
他没有说什么
他们似乎过得很好
圣诞节梦见父亲
高大的父亲,正与朋友在一起
脸上有泥,我心疼地跑过去
用白色线手套为他擦拭
一边骄傲地说,我爸是英雄
战斗英雄,然后欢快地跑开
叫着,游泳去喽
正是冬天,满地冰雪
人们在诅咒着什么,半天不动
我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那家
叫齐傲志的泳馆
两个同乡让我坐拖拉机去
我根本就不会游泳
父亲的马棚
我在父亲的马棚里到处撒尿
屋地是斜坡,只有未成年的黑暗晃动
许多亲戚,说脏话的两个表妹用唾沫润湿钉子
模仿木匠,磨坊的风车挂在墙上静止成扇子
父亲裹严大被,混在人群中离开自己的马棚
我表姐那么大的未婚妻穿着宽松的马裤,装瘸
我偷窥她下坡的运动员的宽后背
在黑暗的墙上摩擦肋骨
然后在梦中仔细地辨认自己
父亲
大雨后和父亲走在湖边
一尺深的泥泞
我们把青草踩倒,才能继续走下去
很多亲人在村里等我们一起过节
黑色的泥里混合着稻黄色的牛粪
泥泞的声音一路陪伴我们
我们不说话,胶皮靴子发出牛的吼叫
那些泥土的房屋更矮了
门窗像拉开一半的抽屉
我和父亲像父亲和儿子那样沉默着
我们身后,那些青草又慢慢立起来
滴着黑色的泥
巨轮回转的春天
我蹲在路边,把旧式提包里的东西翻出来
半瓶可乐,几个空啤酒瓶
压到下面的书,总是能翻出些重新变得有趣的段落
我就蹲在那里看
我想重新开始生活
父亲帮我把那些瓶子扔掉
我们说,买点草莓和牛奶吧
安静的牛奶,草莓的刺儿在生气
有教师模样的人走过来
好奇地问我笔记上的公式
那是抄的卷子,还没有做完
他说,做吧,别人都在做
这是春天,周围没有人,我还蹲在路边
你的声音
冬天薄暮,集体宿舍改造成的住宅走廊里
更加暗淡了,邻居们回家的声音
炉子相继点燃的噼啪声,红红的炉火
一层层腐烂的白菜和土豆生芽的气味
呢子大衣上粘着的雪花和你头发上的雪花
你们说着工厂里的事情,说着便宜货
幼儿园和孩子,你的声音
还是现在的样子,不年轻,也不年老
你不变的声音,带来了北方的冬天
带来了十二月党人的风雪和远方
带来了我们早已不复存在的生活
你的声音,在狭窄漆黑的走廊里响着
一直响着,温暖而明朗
仿佛除了这个普通的薄暮
世界上不存在饥饿,劳烦和分离
屋子里只有一张大床
靠着窗户的暖气片,一个孩子睡在那里
枕着我的黑色皮夹克
等我把它从他头下轻轻抽出
发现他陌生的脸微微转过去,他是谁的孩子
他不属于我们。凌乱的屋子等待着你的手
而你的声音,还在走廊里响着
模糊而明朗,像炉火摇曳着
保证着这午后的睡眠终会醒来
保证着我们贫穷而踏实的生活
像你的声音不会改变
